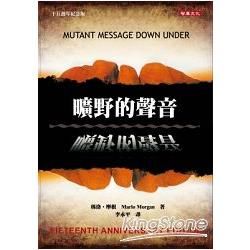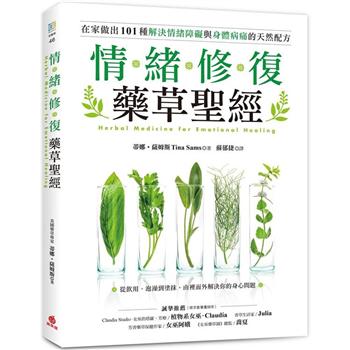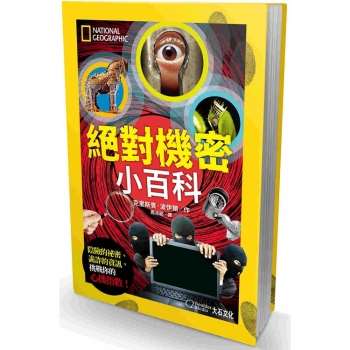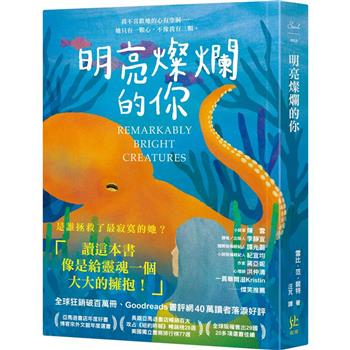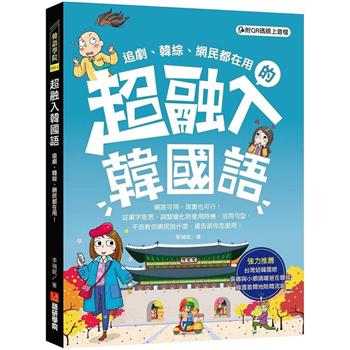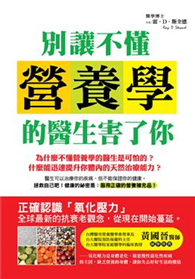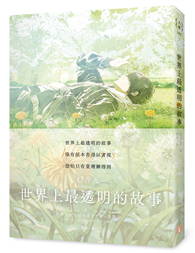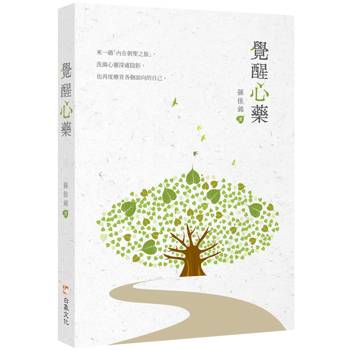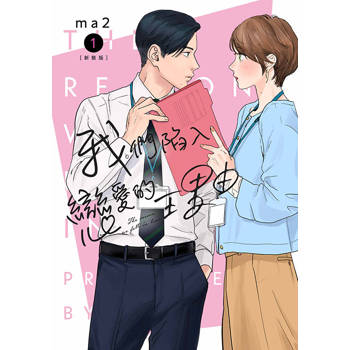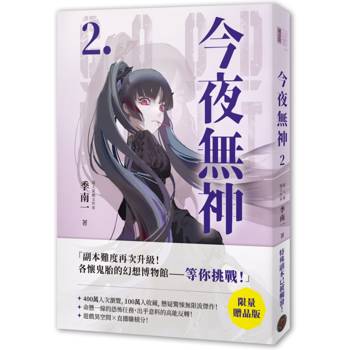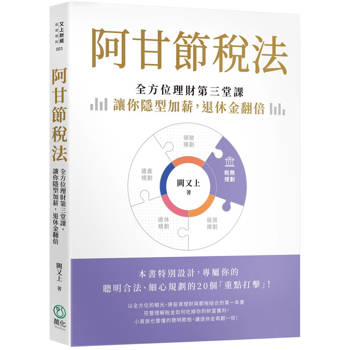十五週年紀念版
新版增加約70頁
新版作者自序
問世後這些年,這本書已經流傳到世界各地,被譯成二十多種語言。在這段期間,身為作者,我也四處旅行。伴隨我巡迴歐美,和我ㄧ起舉行演講會和簽名會的是我的老友,澳洲烏倫傑瑞(Wurundjeri)部落長老布爾南姆.布爾南姆(Burnum.Burnum)。
公元二○○一年,由於這本書,我回到了澳洲。這次召喚我回去的是澳洲大陸最權勢的原住民婦女領袖,愛麗絲.凱利(Alice Kelly),新南威爾斯省東南部穆奚.穆奚族(Mutthi Mutthi)長老、部落法律與知識的守護者、韋蘭特拉湖泊文化遺產(Willandra Lakes Heritage)的看管人。她讚賞我的作品,帶我去探訪她出生的那棵誕生樹,要求我協助,幫她向一間博物館索回古代一位原住民公主──被稱為蒙哥湖夫人(Lake Mungo Lady)──的遺骸。她邀我到家中一坐,與我分享澳洲原住民婦女的智慧。她把我當成值得信賴的聖道守護者,讓我倍感榮幸。
我永遠記得愛麗絲那雙幽黑、銳利、一瞬不瞬凝視著我的眼睛。那時我正準備回答她提出的一個問題:「這本書在讀者的生活中,究竟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呢?一群居住在沙漠,只會講自己的語言,一輩子從未離開家園的人,他們對人生的看法,真的能打動外人的心靈嗎?」
我告訴她加拿大一對夫妻的故事。兩口子都坐輪椅。他們讀了這本書,被書中提到的非競爭性遊戲──沒有輸家的遊戲,人人皆大歡喜──深深感動。於是夫婦倆開始設計、製造些玩具大受歡迎,使這對夫妻能夠自食其力,同時也讓數以千計的孩子,有機會學習和體認「雙贏」經驗的價值。
因為這本書,我也結識了萊爾。那時我受邀前往美國一間聯邦監獄參加一場結業典禮,擔任主講人。儀式的舉行是為了慶祝受刑人心靈復健計畫圓滿成功。這項計畫引用了《曠野的聲音》傳達的訊息。萊爾以一人之力,幫助過數以百計被我們的社會放棄的人。萊爾的作者,讓我再一次見證我書前那首詩所呈現的人生境界:「來時兩手空空,去時兩手空空。我目睹生命的璀璨,兩手空空。」
在一場簽名會上,一位單親爸爸告訴我,他和兩個女兒中的一個關係曾經十分疏遠。這家人曾尋求心理諮商,但親子關係依然保持冷漠。後來,兩個女孩讀到了這本書,就跑去告訴父親說,書中提到一項挺有意思的習俗:每個小孩出生時都會得到一個名字,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身心的發展,孩提時代的名字會不敷使用,這時,他就必須為自己另選一個比較適當的名字,以反映當下他的真正自我。儘管對這位陽剛氣十足的父親來書,這個外國風俗未免有點傻氣,但他還是答應一試;由於他的身分是那保安官,他就給自己取名為「快槍手」。跟爸爸比較親的那個女兒,常陪伴他到射擊場練習打靶,便乾脆把自己的名子改成「正中目標」。跟爸爸比較疏遠、在爸爸心目中行為放縱的那個女兒,則管自己叫「陽光夢客」。這位父親告訴我,為自己取個新名字,就如同獲得一把即時的、無價的鑰匙,從而打開了橫亙在親子之間的那道門鎖。他把他那個疏遠的女兒,終能解開心結,重歸和好,一旦他明瞭了她從不曾大聲說出來的心中想法。
還有一位女性讀者告訴我,她母親彌留時,母女兩個緊緊相擁,一起聆聽(第三度)錄音帶播放的《曠野的聲音》。他特地向我道謝,因為生平第一次,她母親找到了內心的寧靜。她引述書中的一句畫作為臨終遺言:「永恆是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是永恆。」
我向愛麗絲講述一連串的小故事。乍聽雖然瑣細,可意義卻非常重大。我告訴她我曾收到小學生寄來的一個個小包裹,裡頭裝著信函和圖畫,描述這些孩子對一個異國文化的感覺和想法;我還收到從一間殘障學校寄來的一本集子,透過它,一群小孩跟我分享他們自己的內心旅程。讀者中,有些人改變了職業,因為在《曠野的聲音》感召下,他們不願再將時間浪費在他們已經厭倦的工作上;他們尋找另一種貢獻社會的方式,從事一項既能微升、又可以享受工作樂趣的行業。這些讀者告訴我,這種轉變就如同刮掉那塗抹在生命外層的糖衣,找到他們真正在乎、真正需要的東西。
一九九四年到二○○四,十年之間我們的世界發生了很多事情。我摯愛的三個人相繼離開了我們,進入「夢境」,回歸「永恆」:布爾南姆.布爾南姆、愛麗絲.凱利、我的兒子史提夫。但在一九九六年,從「夢境」送來了一件禮物──我的孫女卡爾麗誕生了。
十年間,我們──身為個體以及作者一個社會──繼續接受挑戰,迎來各種機會,藉以學習、充實我們的精神生活。我不敢說,十年之後的人類變得更加愛好和平、更有責任心,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人們在環境保護、了解另類文化和避免戰爭上,顯得更加積極了。許許多多居住在西方社會的人,正學習著將一個古老民族的精神理想,融入他們的生活。而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我懇摯期望你會閱讀這則故事──不管是第一次還是重讀──汲取從澳洲原住民「真人部落」傳來的訊息和新的啟示。
推薦序
洪蘭教授 中央大學認識與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我一直以為,「寧靜致遠」是修身養性、品格方面的形容詞,從來沒有想到它有生活上的真實性。在我看到《曠野的聲音》一書後,才發現「寧靜」的確可以穿透時空的阻隔,達到前所未有的境地。當你把所有人為的東西(珠寶、首飾、衣服、鞋子)通通都拋下,以你最初來到人間的本色去體驗大自然時,你就會聽到風要告訴你的話、看到雲要傳給你的訊息、聞到遠處水的氣息,你就能赤手空拳地在沙漠中生活了。
《曠野的聲音》是一本令人震撼的書,最主要是因為作者瑪洛是跟你、我一樣在大都市──所謂「文明社會」中長大的人。她能跟著澳洲土著一起在滾燙的沙漠中行走、沒有任何文明的配備而活了下來,表示你、我也有這種可能性,這是我們從來不敢相信的。我們從來沒有想到當拋離一切文明,沒有太陽眼鏡、沒有防曬油、沒有Nike鞋,赤著腳在沙漠中遊蕩時,你身體裡祖先傳給你的本性會再度躍出,讓你用幾百萬年前祖先生活的方式,在這地球上生存下去。這是為什麼本書的英文名字叫”Mutant Message Down Under”,我們以為已經沒有了的本能,在層層文明外衣之下,仍然存在;當然,這本書名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原住民給瑪洛取的名字是”Mutant”。澳洲在南半球,從北半球人的觀點來看,澳洲是”Down Under”──這個書名有很多層意義,很有趣。
當瑪洛赤著腳在滿是荊棘的地上走,芒剌扎進她的腳,使她無法行走時,原住民跟她說:「現在你只有忍耐,忘掉腳上的疼痛吧。學會忍耐,把注意力轉到別的地方。」「忍耐」、「把注意力轉到別的地方去」,這是多麼好的處世之道──人是動物,受到大自然的規範,在大自然中哪有處處順利的事?動物出來覓食,找得到食物是福氣,找不到是本份。我們看到大自然中所有的動物都很有耐性,獅子在潛行追蹤獵物時、貓守在老鼠洞口等待時,牠們都知道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有忍耐力的一方,只有人類沒有耐性。人類稍不如意便怨天尤人,以致於憂鬱症越來越多,自殺變成人類死亡的十大原因之一。過去心理動力學派治療憂鬱症病人,是要他們把憤怒發洩出來;後來發現,越發洩越糟糕,本來是小怒,大吼大叫發洩完後,生理反應使小怒升級為大怒,對身心更不利。「忍耐」、「把注意力轉移到正向的事情上」,原是現代治療憂鬱症的方法,想不到竟然從澳洲土著嘴裡說了出來──我們才發現,它原來就是我們祖先能夠生存下來、把基因傳因傳到我們身上的不二法則。現在想一想有多少事,如果當事人忍一忍,風波就能過去,世界會少了多少戰爭、人間會少死多少人命。
瑪洛發現,每天黃昏紮營時是部落人最快樂的時光,他們講故事、唱歌、跳舞、玩遊戲、談心,他們互相搓揉肩膀、背部。靈長類學家發現,猿類黃昏時的「梳理」(Glooming)也是他們最快樂、最寧靜的時光,只可惜現代人每天無事忙,全台灣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家庭可以全家坐下來一起共進晚餐。人際互動、肢體接觸,本是動物情緒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文明的社會為了追求物質的享受、犧性了心靈的需求,憂鬱症變成了現代瘟疫。然而,在一無所有的原住民身上,他們保有人類最初始的快樂──互信、互動、互助。瑪洛提到部落人沒有醫療設備,但他們的壽命卻很長──心靈的平靜與滿足,應該是他們長壽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個原因,應該是「飲食簡單純樸」。瑪洛說,原住民的大餐是用樹枝到樹叢中去挑、去掏,然後用一片樹葉托著美食,再用一片樹葉蓋著、放進火裡去烤。她好奇打開樹葉一瞧,美食原來是一條條的蛆,她從此學會不再說:「永不(Never)。」
很早以前,南中國海有次船難,有十七個人飄流到澳洲北部達爾文港附近,登陸後,因不知身在何處,便往內陸走,結果大多數人飢渴而死,最後被救的是一個中國人。他說,他去腐木中找蛆吃,白人看了嚇壞了、寧死不肯吃。他記得,小時候聽過大人說晉朝的石崇宴客,有一道美味的菜是別的有錢人怎麼也燒不出來的,有一個客人好奇,偷潛入廚房去看用的是什麼肉這麼香滑可口,只見石崇的大師傅拿個盤子到廁所去,用力拍打掛在廁所的一塊腐肉落下許多蛆──原來這個人間美味是「蛆」。他想起了這個故事,知道蛆是可以吃的(是蛋白質),於是他就硬著頭皮吃了,結果就活下來了。
其實,一切都在我們一念之間:「覺得是蟲,就噁心不敢吃;覺得是大自然賜的蛋白質,就可以安心地吃。」所以瑪洛說,他們每天出發行走前,必先禱告,感謝上天將要賜給他們的食物,他們也絕不多取──既然是上天的恩賜,有吃就好,怎可多要?瑪洛這一路上,吃過甲蟲、螞蟻、白蟻、青蛙、蛇、食蟻獸……任何他們遇見的動物。有時,早上或中午都找不到東西吃,她就把路上的風景當成嚮宴,在石頭上、在天空中都看到隱藏的圖畫,用這個方法來忘記飢餓。
原住民沒有時鐘、手錶,山中固然無歲月,但他們有他們計時的方式。他們以唱歌的方式來測量距離和時間,一百句歌詞的、五十句歌詞的,就像中國古代的銅壺滴漏或民間所說的一盞茶功夫、一柱香的時間,一樣可以達到計時的目的。瑪洛說,澳洲原住民排斥書寫的語言,因為他們認為那等於丟棄記憶的能力;我很驚訝地發現,二千年前蘇格拉底也是如此說:「字母的發明,使學習者的心智產生遺忘,因為他們已經不再需要用到記憶了,他們交給外在的書寫文字而不再用記憶來記。」不同的時空、不同的民族,竟然講出一樣的話,它使我有「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那種時空交錯的感覺。
跟原住民在一起生活久了以後,瑪洛開始懂得珍惜、凡事不再視為理所當然,幾口清水可以紓解乾渴、任何食物都有滋味。她這一生,無時無刻不在煩惱著如何保有工作、如何討好老闆、如何投資發財、如何儲存退休老本,在澳洲的沙漠中這一切都不存在了。部落民族唯一的保障,是日出日落、永無休止的大自然循環。而這個最沒有安全保障的民族,卻是最沒有罹患胃潰瘍、高血壓、循環系統毛病的民族。它就是三千年前《左傳》〈顏斶說齊王〉中的「歸真返璞、終身不辱」同樣意思。只要是真理,古今中外不論民族、文化,看到的都是一樣。
這本書給我最大的震撼,是「人竟然可以這樣一無所有地活,而且得的這麼滿足」。人只要不去計較雞毛蒜皮的小事,心一放開,「美」就進來。瑪洛本來最討厭蛇,但在沙漠中看到一窩蛇,有兩百條之多,都有姆指粗,鑽來扭去:如果是過去,她一定驚恐大叫噁心而逃,但現在的她感恩,因為這些蛇的存在是提供旅人的食物、保持自然界的平衡,而任何食物中所含的水份,都是極其珍貴的。他們晚上躺在沙漠中睡覺、圍成雛菊形狀、腳趾相接在圓圈中心,這樣能使有限的獸皮發揮出最大的保暖效果。在星空下,她感受到這些純潔天真充滿愛心人身上所發出來的氣息;他們的「無」,使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碰觸全人類的意識、不需語言而能相互溝通,他們無所求、故無所不在。
我們渴望這樣的社會,一個互信互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在經過這麼多年選舉的暴力語言後,對於這種心靈的平靜特別嚮往。「寧靜致遠」不再是一句話,它是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行動力。這本書在物慾橫流的現在社會像一股清流,讓我們眼睛一亮、心胸自然變大。人是百代的過客,應求此生的目的與意義,就像達文西說的:「充實的一天帶來好眠,充實的一生帶來安息。」但願每一個人都能體會到瑪洛所送出的訊息,不忮不求、充實地過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