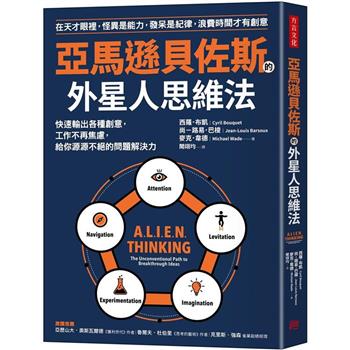遞進民主
中國社會的政治轉型契機──
西方民主與中共體制以外的第三條路
一個大膽、充滿想像力,但也可能非常實際的政治理想
中國的民主化,無疑是所有華人、全亞洲,乃至於全世界關注的焦點。面對未來包括全球化在內的種種嚴峻考驗,中國得透過民主化才能有所因應嗎?未能及時轉型又會有何後果?以及最重要的,中國需要的是哪一種民主,才能在這全世界幅員最廣、人口最多的國家,順利推動幾千年來未曾成功過的民主機制,而又不爆發流血革命、動盪衝突?作者主張在西方民主與中共現有體制之外,必須另闢「第三條路」,也就是所謂的「遞進民主」──一個可以幫助中國從專制過渡到民主,既能避免社會轉型對中國社會造成震盪,又能最終實現自由、民主與共和的理想制度。憑藉對於現代中國政治的嫻熟以及社會結構變化的長期觀察,作者大膽預測中國未來朝向民主化發展乃勢之所趨,並藉由此書勾勒出他心目中更適合中國的全新政治藍圖,以及解決兩岸衝突的有效規劃。
作者簡介
王力雄
一九五三年生,籍貫山東,漢族。他曾以「保密」為名,出版了震驚海內外的長篇政治寓言小說《黃禍》,引起全球媒體的追蹤報導。該書曾入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亞洲週刊》),至今仍在港臺以及海外暢銷,大量盜版更流傳於中國大陸。這位曾被國際媒體譽為「中國最敢言的作家」的其他著作還包括:《天葬:西藏的命運》(「漢人所寫關於西藏的著作中最客觀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書」)、《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作者自認本書分量超過《黃禍》、《天葬》二書的加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