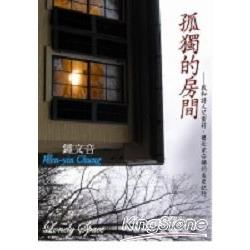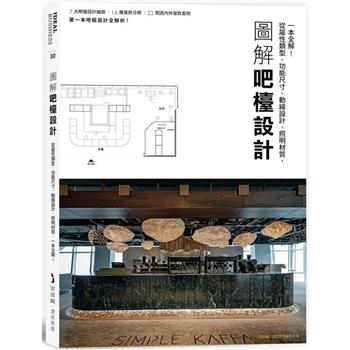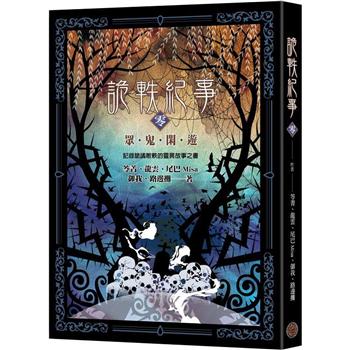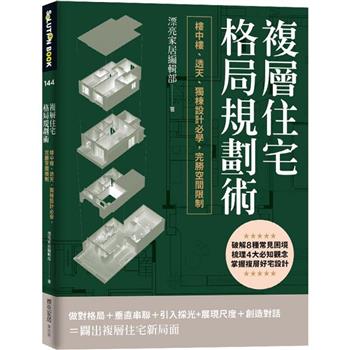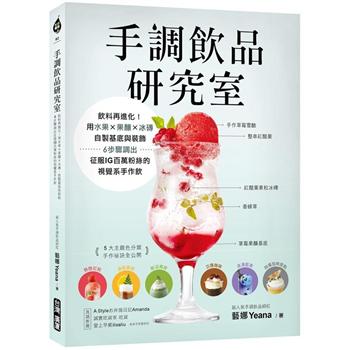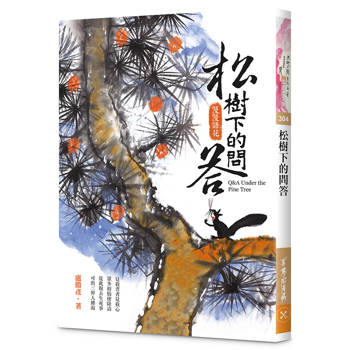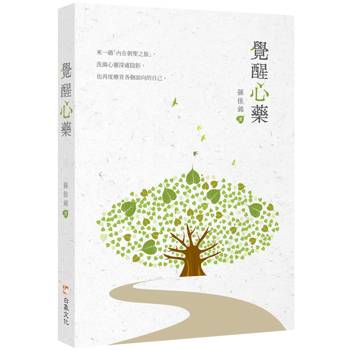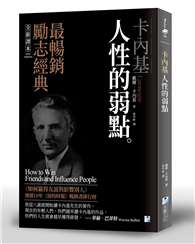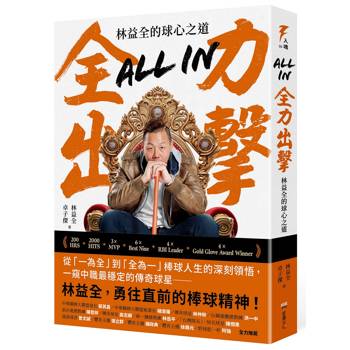我的紐約青春饗宴
人為什麼要去想念一個遙遠的地方呢?
或者該說根本不是想念,是忘不了,是被寄生在體內了。
紐約自一九九五年開始就寄生在我的體內,今年恰恰十年。有時我懷疑我想念紐約根本是為了想念那個一九九五年份的經典情人,紐約是我生命的經典地標,也是我愛情的地標。
在此方的台北想念他方的紐約根本就是自討苦吃,聞不到吃不到摸不到,只有記憶的相思擾人清眠。但說不想卻老想它,可見紐約於我的魅力。
或許在台北常活得太沒有層次了,蒼白且時而單調的日子不免就會把神智牽引到紐約。若是生活在紐約,那麼天氣好的晨光,從西城七十幾街穿越百老匯大道到中央公園散步、靜坐,這樣就足以安我昨夜擾亂的魂魄。
然後向路邊的摩洛哥小販買個五十分錢的夾奶油起司貝果,和五十分錢的小杯美式咖啡,如此拎著早餐走進五十七街的學生藝術聯盟畫室,看著紐約同學都已各自在畫布就定位,模特兒也來了,褪下衣裳任班長調整姿勢,我的目光焚燒著眼前的人體模特兒,她的形體在我的手中變形,我畫她的靈魂。
上午,在台北遙想紐約早餐,最懷念剛出爐的貝果的便宜與可口,我幾乎是百吃不厭,日日換一種口味,從原味吃到什錦,簡直是普羅女郎的廉價天堂。
傍晚時光,通常離開畫室後去逛街,或逛書店畫廊美術館。紐約櫥窗是一則則時尚故事,給我免費的美的課程。紐約上城與下城承載兩個迥異的人種,從富豪的奢靡到第三世界的貧窮移民者,皆是我注目的對象。紐約藏污納垢,龍蛇混雜,卻是我喜歡的層次。在台北的此方,大量中產階級蒼白的西裝與保守的價值觀常讓我無法呼吸,於是我就會禁不住地懷念起紐約街頭多層次的隨性與邂逅。
我喜愛蘇活區倉庫改建的工廠,現在我更喜歡翠貝卡區。在台北的擁擠空間,誰會不眷戀紐約那擁有高聳天花板的畫室。做為藝術家當然要活在紐約寬廣的天空才覺得過癮自在,慾望也才有開花結果的可能。然而或許你會問,既然這樣,那我為何不在紐約繼續生活?
「若是擺開謀生因素的話,我想最主要的是,我是受母土召喚的寫作者,假設我不是作家,不是一個用中文的寫作者,不是一個對故土念茲在茲的寫作者的話,那麼或許我會考慮留在他鄉吧。」我常這麼回答。
在台北開車或搭捷運,卻想著紐約地鐵,七號車充滿東方的移民臉孔,被紐約客稱為「東方快車」。紐約捷運,大熔爐的小縮影,班尼頓服飾廣告般的聯合國臉孔隨著高速列車滑過滑過,閱讀臉譜成了我每天的功課,就像念咒語一般地發生在我的心裡。
然而在台北搭捷運要是一直盯著人看可能遭白眼一頓,台北車廂臉孔幾乎都在和睡神打交道,疲倦的臉孔,寫滿一座城市的勞累與傷痕。台北容易讓人失去熱情,因為傷痕暗藏在心,不像紐約客可隨時宣洩,他們的宣洩可不是大幹一頓,而是以藝術以美食以時尚來作為一種熱情的出口,人人都可以展現自己慾望的城市,於是傷痕也就有了彌合的縫隙,即使不久又會被新的事物撕開舊痕,但就生活在紐約的人而言,那不成問題,因為傷痕本是體驗生活的附屬品,他們深切知道要探慾望的底層就會被荊棘刮傷,生活的實相是一頂戴著荊棘的桂冠。而台北的生活實相是荊棘處處,但終點不一定有一頂桂冠讓你戴。
我懷念紐約,雖然我也常咒罵它。它是一座離開時會特別想念的城市,也許因為它有招人魂魄的魅力。
我花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和紐約建立起有如「小王子」和玫瑰花的馴養關係。紐約曾讓我流淚,而小王子說,當一個人要被馴養時,他就要接受流淚的可能。馴養的過程,充滿各式各樣的情緒,生活在紐約,這城市讓你深度地和慾望交融,也深度地讓你照見自己的無能與寂寞,紐約讓你高潮,也讓你低潮。它情緒不穩,它有時急躁如十秒的廣告片不斷劃過你的眼睛,或者它高速碾過你的身體你的感情,直到你成了碎片。
但奇異的是在這樣的血肉模糊裡,卻有一種不曾有過的歡愉與哀愁快感。
我不喜歡在台北走路,躲閃摩托車之外,路邊也無太多奇特的景觀或美麗櫥窗可供我一路把賞。我在紐約卻最喜歡徒步,除了享受他人目光的禮讚外,也很享受紐約的各種節奏,快快快,慢慢慢,你可以做你自己,紐約這座表面像是洪水猛獸的城市,到了夜裡卻如紅磨坊的豔麗女郎,想要派對那可參加不完,想要看戲看電影聽音樂,節目單是長長一串,然而想要孤獨,這城市也可以回饋你絕對的冷漠。
啊,紐約,善變的情人,你的形影已離我遠去,你的哀歡卻和我在台北同步呼吸,你太複雜了,你不像托斯卡尼或是普羅旺斯可以讓人高枕無憂,你無法讓我隨當地人做一個放逐天涯的閒逸旅人,因為在你的懷裡必須和你通體交融才能和你哀歡與共。在紐約百態,看見更多慾望的自己。
紐約,你像是總不卸妝的情人,戴著各種面具來到我台北的枕畔,我常常認不出你,你的面目變化多端。但不變的是你的慾望,重重的慾望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每一個來到你面前的人。
我曾經在你面前無所遁形,年輕時又常情不自禁。
然而若是年華老去才去紐約,那肯定要大大失望。漸漸地,我心也老了,於是我退逐到我的台北,我在我的故里遙想你。紐約,一九九五年份的舊情人,一再和我藕斷絲連且舊情復燃的老情人。
即使我後來屢屢生活在更遠更遠的他方,我都無法遺忘你。
治不好的眠眩感
紐約常讓我發高燒,一種城市病,永遠有治不好的眠眩感。
許是它高樓切下的陰影過於幽黯,許是它慾望生出的縐褶過於繁複,許是一個人走在此地容易失去座標而任身漂流以致於眠眩不已……。
常常,再回紐約,我就又老了。這城市一直是屬於新一代的,一直是屬於各國子民所共同認養的。
很多年前初抵紐約,遊走時代廣場,某男衝著我喊「西貢小姐!」當時聽了在心頭笑著。頓時感到紐約很像自己,身分不明,撲朔迷離。「非典型」的我就像你所不知道的紐約,紐約看似暴露,其實紐約更多是隱藏。隱藏在這顆「大蘋果」核心下的蟲蠅斑斑。蟲蠅以慾望為名,專門啃噬肉身的神經。我對紐約為何叫做大蘋果從無興趣知悉,但我對於躲藏在果肉核心的蟲卻一再剝見,長時間浪蕩紐約,久了自己也成了那條看不見的蟲。
就像非典型紐約絕對比典型紐約更值得流連,然而非典型也很容易久了成典型,蘇活區是一例。就像邊緣的外外百老匯有朝一日也會成為熱門的百老匯,在艾斯特劇場演了數年的「藍人」也是一例。時代廣場亦然,曾經毒梟妓女躲藏的暗巷深處、馬丁.史柯西斯電影裡的晦暗與慾望幢幢的時代廣場,於今已經被整肅成巨大無聊的觀光商業城。就像蘇活區的古根漢美術館兩年前竟改成了普拉達的服飾旗艦店,商業進駐讓各種隱藏的生活角落的趣味不斷消失。
我所流連的聖馬可廣場及東村和沿哈得遜河一帶則還有浪遊的樂趣,隱藏暗巷的小店與各種人樣都還堪玩味。興起的雀兒喜,原是荒涼倉庫工廠,川久保玲進駐,畫廊進駐,又成了典型的商業區,觀之可惜。
是啊,嬉皮大了也會變雅痞,波西米亞老了也會變布爾喬亞。城市提供人們一種生活的變化,與一種對身分攀爬的慾望。
也許只有唐人街數百年來一直處於不變,角落還是角落,暗巷還是暗巷,潮濕還是潮濕。
對我而言,紐約的好玩在於暗巷有更暗的暗巷,黑夜有更深的黑夜,角落有更曲折的角落,邊緣有更邊緣的邊緣……。
遊走城市各個角落,需索一種看不見卻又明目張膽的姿態。
在紐約沒有姿態,就沒有感官。
紐約,入夜,宛如是下了後台的豔舞女郎,個體常常又快樂又惆悵。在角落裡的營生感是紐約最真實的部分,因為人人都是異鄉人,眾多幽微的角落是最好的隱藏與療傷處。
看不見的紐約,比看得見的紐約更叫我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