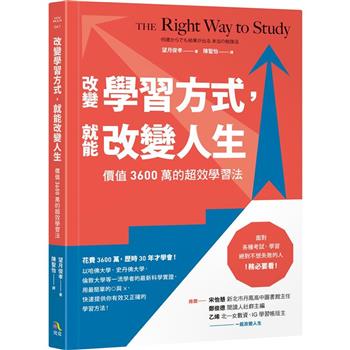譯序
寫實主義過時了嗎?
西方寫實主義小說在經過十九世紀整整一百年的發展之後,到了二十世紀初葉在表面上似乎已瀕臨強弩之末,它首先即面臨現代主義藝術創作觀念的挑戰,在世紀交接之際,整個西方世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劇烈社會變動,人的意識形態跟著產生急遽變化,藝術創作上不管是思想內涵或是表現形式自然而然也跟著發生重大的變革,其中在小說創作方面,最大的變化就是現代主義觀念的萌生和發展,從一八八○年代到一九二○年代左右,傳統外在形式的真實描寫至此必須轉入人物內在世界的細膩描寫,這時候,寫實主義的信念──服膺「現實原則」──面臨苛刻的挑戰而不得不重新加以檢驗,然而,從二十世紀初至今一百年來,我們忍不住要問,寫實主義過時了嗎?寫實主義小說完全式微了嗎?
英國小說家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 1867-1933)於一九○六年開始至一九二八年之間,出版他那著名六大冊的《福賽特家族記事》(The Forsyte Chronicles),在當時號稱是英國寫實主義小說繼狄更斯之後的偉大巔峰傑作,高爾斯華綏的文學聲望至此也幾乎達於巔峰,他更於一九三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當時英國文壇上對這部作品抱持不以為然態度的人還是大有人在,其中特別以吳爾芙女士和D.H.勞倫斯兩人所發表的反對意見最為有名,吳爾芙女士認為這部小說大而無當,根本就不忍卒讀,D.H.勞倫斯則說:「故事很薄弱,人物缺乏骨肉,情感很虛假,一種偉大的虛假。」我們從今天眼光看,光從這套作品出版於一九○六年的第一部《有產者》(The Man of Property)來衡量,這的確是一本平庸不過的寫實主義小說,不但敘述筆調軟弱無力,整體表現風格更是散漫無章,相對於湯瑪斯.曼出版於一九○一年的《布頓柏魯克世家》(編註:又譯《勃登布魯克家族》)一書,同樣是描寫一個商業中產階級家族的衰落故事,比較之下,恐怕就顯得遜色許多,簡直沒辦法放在同一水平去加以比較評論,唯一可以相提並論的一點是,這兩本作品都是奠立在傳統寫實主義手法上面去反映一個時代中商業世界的變遷故事,都是帶有史詩格調寫法的企圖,但問題是,同樣的題材背景,同樣的寫實主義風格,為什麼湯瑪斯.曼會比高爾斯華綏超越許多呢?他所憑藉的優勢是什麼?比較他的一些寫實主義前輩大師,比如狄更斯和福樓拜,他的真正成就又如何呢?這正是問題所在。有兩個問題,首先,十九世紀的偉大寫實主義小說家如何運作他們的寫實主義?亦即如何依循「現實原則」去重現現實的問題。其二,早在高爾斯華綏於一九○六年出版《有產者》之時,吳爾芙女士等一些前衛作家即已宣告寫實主義的死亡,然而,從一百年後的今天眼光去看,寫實主義是否真的過時了嗎?
美國著名歷史學者彼得.蓋伊(Peter Gay)教授於二○○二年出版的新著《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Savage Reprisals),專門談論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小說的創作方法,他特別從歷史學家的眼光去探索寫實主義小說的寫作風格,依創作年代順序,他列舉了三本著名作品:狄更斯的《荒涼屋》(Bleak House)、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以及湯瑪斯.曼的《布頓柏魯克世家》(Buddenbrooks)。這三本長篇小說剛好各自代表了寫實主義鼎盛時期,英國、法國及德國三個地區的偉大代表性作品,這三本小說雖然都是寫實主義的產品,都服膺「現實原則」的創作方式,但其寫作風格,甚至所專注的主題,卻未必都是相同。譬如,狄更斯的作品會比較偏向於對社會體制的批判,然後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彰顯人性的光明面。福樓拜除了對中產階級世界特別痛恨之外,他的寫實主義方法主要表現在用字遣詞的細膩風格上面,在這方面他甚至公認是現代主義的前輩導師,有人還捧他為「新小說」的第一位大家。至於湯瑪斯.曼,他所生長的年代,從十九世紀末期跨入二十世紀直到一九五○年代,以他的第一本長篇鉅著《布頓柏魯克世家》而論,他算得上是寫實主義的集其大成者。除了服膺「現實原則」之外,他更進一步探索哲學性的人生真理:人生到底是什麼?要是容我用偏私的口吻下評判的話,我要說寫實主義到了湯瑪斯.曼手裡,在美學視野上已然到了登峰造極地步,他不僅是小說藝術大師,同時更是冷靜尖銳的人生觀察家。
《荒涼屋》出版於一八五三年,狄更斯那年四十一歲,正是他創作力最旺盛且人情世故臻於成熟的年紀,在這之前他才剛出版極成功的《塊肉餘生錄》,他可以說正是處在充滿相當自信的狀態之下,寫作這本在許多後人眼中是「偉大傑作」的長篇鉅著,有人認為這是狄更斯最好最成熟的一部作品,甚至也有人認為,這是英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一本文學傑作,事實上,這也是狄更斯自認僅次於《塊肉餘生錄》最鍾愛的自家作品。當然,這本小說也是狄更斯所有作品中,格局最龐大、故事最複雜、人物最獨特的一本小說,還有,在敘述策略運用上,也是狄更斯勇於創新的大膽嘗試之作──不同敘述觀點的交叉運用以及不同動詞時態的變換使用。
姑且不談文體和風格問題,就寫實主義這一環而言,狄更斯向來即以擅於批判社會著稱,他的寫實主義就是批判的寫實主義,但他絕不是社會改革家,他沒有這個能耐,也沒有這個本領,他只是個社會現象的見證者,他服膺「現實原則」,貼切寫出他眼中所看到的真實面。《荒涼屋》正是一本典型狄更斯的社會批判小說,但其涵蓋面無疑更為寬廣,它首先箭頭直指龐大顢頇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司法體制,小說藉由一樁纏訟多年的遺產繼承官司拉開序幕,然後側寫與這場官司所有相關人物,當然除了主要角色之外,還包括許多靠法律訴訟吃飯的眾多次要角色,比如法官、律師、抄寫員、訟棍等等。狄更斯年輕時曾在報館幹過實習記者,專跑法院新聞,他對這個圈子自然很熟悉,也樂於尋找機會發揮所長,《荒涼屋》提供給他大肆發揮抨擊英國司法體制的機會。
我們很難想像,在國勢極為鼎盛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為什麼社會仍會是一團齷齪混亂?滿街窮人和乞丐,資本家漫無節制不斷在壓搾勞工,難道國家的財富和繁榮果真建立在剝削窮人這層事實上面嗎?《荒涼屋》一開始的描寫,瀰漫不散的濃霧,髒亂不堪的泰晤士河畔,所呈現的正是一幅帶有象徵意義的荒涼破敗景象。狄更斯筆下的描寫並無誇大不實之處,別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正是在此同一時期,以英國為基地發出他們馬克思主義的怒吼,他們蒐集數據和事實,以資證明這樣的社會非加以顛覆不可。狄更斯不是革命家,也不是理論家或行動家,他只寫小說,偶爾參與小型改革行動而已,他把他所生存的社會加以小說藝術化了,但他從未悖離他眼睛所看到的事實,以至於後來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要回頭研究十九世紀英國社會的歷史,狄更斯是必不可忽略的一環。
然而,問題是,寫實主義小說家闡述現實世界可以走多遠?小說畢竟不是社會檔案,即使狄更斯的小說在當時曾經聳動了視聽,也推動了一些或大或小的社會改革,但他絕不是報導文學作家,他還有許多其他屬於藝術的迷人層面,他經常在小說中流露的幽默筆調證明他是個風趣的性情中人,他創造過許多性格鮮明的迷人角色,以及小說敘述技巧不斷翻新的展現,還有他那充滿音樂性的獨樹一幟的英文文體,據說他成名以後即不斷以職業性姿態當眾朗讀自己的小說作品,風靡了成千上萬的聽眾,這倒是世界文學史上極少有的現象:狄更斯的小說不但要用眼睛看,而且要用耳朵聽。我們今天讀狄更斯,絕不是為了探究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事實,而是為了享受文學的樂趣,狄更斯可以源源不絕提供這些,他是永遠的大師,誰說寫實主義過時了呢?寫實主義小說也許已經式微,但從未過時。
福樓拜的寫實主義風格和狄更斯很不相同,他的魅力在別的方面。我們稱福樓拜為「患有恐懼症的解剖師」,最能說明福樓拜是個什麼樣的作家,以及《包法利夫人》是一本什麼樣的小說。福樓拜一輩子在研究「愚蠢」的道理,事實上,《包法利夫人》一書的主題除了貪婪和庸俗之外,主要還是在研究愚蠢,色情和愛情都只是粗淺的表面。這本小說於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五七年在雜誌上連載時,還曾因為色情問題被告到法庭而聲名大噪,後來福樓拜贏了官司,但他很失望,因為控告的主題不對。這本小說的故事並不吸引人,也缺乏說服力:一個愛幻想的少女嫁了一個平庸無趣的丈夫,後來連番紅杏出牆失敗而陷入債務煩惱之後服毒自殺。現代主義和前衛小說早已不再注意故事內容,他們要的是風格和用字遣詞的功夫,但這套功夫早在一百五十年前,福樓拜早就完成得差不多了,後來的人只是努力再加以發揚光大而已。
法國文學史上有名的圖畫之一是,福樓拜在斗室中坐困愁城,努力尋找適當的字眼去描繪愛瑪和情人第一次幽會回來之後的心情反應:天啊,我在戀愛了!圖畫之二是,福樓拜一手拿著解剖刀和愛瑪血淋淋的心臟,另一手拿著顯微鏡。他因為過分講究文字風格,一段文字可以慢慢推敲,耗上兩個禮拜以上,一本《包法利夫人》可以寫上五年,而他自己還會宣稱,這本小說並沒有表現出什麼。當然,《包法利夫人》肯定是他的嘔心瀝血之作,他會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Madame Bovary C'est moi!)這無非說明了,他在解剖愛瑪的同時,也解剖了自己,我們在審視愛瑪那「愚蠢」的愛情履歷之際,別忘了那背後都是福樓拜的滴滴血淚。
以「現實原則」的標準去看,福樓拜並未像狄更斯那樣廣泛去觸碰社會的真實面,他的寫實主義不在「現實的重現」,反而是個人的「現實的重造」,他以精確的手法重新塑造了「福樓拜式的現實世界」,他藉此創造了一種別具一格的小說藝術方法,因而他的文學經得起一讀再讀,即使他那麼輕忽故事內容的吸引力,但《包法利夫人》的世界永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永遠不會過時。
湯瑪斯.曼在寫作《布頓柏魯克世家》之時,寫實主義其實已經在巴爾扎克、狄更斯、福樓拜、莫泊桑和托爾斯泰等人的手上完成得差不多了,他有再超前一些嗎?曼並未真正超前,他完全服膺「現實原則」,他描寫中產階級世界,他從自己的家族記憶中去塑造人物和發展故事,他並不批判,他只有反省,並臣服於人生命運的法則:衰落和死亡。這種叔本華式的有關意志的悲觀哲學論調,曼在這本小說中運用得多麼有力,多麼有說服力,而這本小說的迷人魅力主要竟然還是源自於此,而且,曼的寫實主義比他的前輩大師稍稍更為超越的地方,恰恰也就是在這個環節上面,他用小說詮釋叔本華和尼采的哲學,還有華格納的歌劇,同時並追溯到歌德的源頭,因此,與其說《布頓柏魯克世家》是一本小說,倒不如說像是貼近歌德未曾寫出的有關生命悲劇的史詩,曼在向歌德致敬。
《布頓柏魯克世家》主要描寫十九世紀德國北部地區一個商業家族歷經四代,由興盛走向衰亡的故事,多少影射曼自己家族的事蹟。這個家族的衰落,除了命定的宿命因素之外,另一不可忽略的要素就是「藝術氣質的入侵」。曼這本小說比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發表,在出版年代上足足早了五年,這兩本書,一本是小說,另一本是社會學論文,在基本論調上有其驚人共同之處:近代資本主義的萌發離不開嚴格自制和重金主義的新教倫理,而這些特點和缺乏自律的散漫藝術氣質是格格不入的。布頓柏魯克家族傳到第三代時在主角湯瑪斯的主掌之下,仍能勉強維持不墜的格局,但已經疲態畢露,他的弟弟竟日在外流連歌榭,不但一事無成,還不斷敗壞家聲,等傳到第四代時,湯瑪斯的兒子迷上音樂,對商務興味索然,這個商業家族至此就注定非衰亡不可了。其實,曼在小說中要批判反省的,不是中產階級,也不是藝術,而是生活,人的盲目生活意志造成了人生的悲劇,但是曼的筆調所要宣告的,人生如果不是悲劇,還會是什麼呢?我們仔細讀到書中主角湯瑪斯在四十歲英年早逝之前的一些篇幅的描寫,看到曼筆下的這個人物是如何的對生活感到厭倦,如何排斥庸碌乏味的商場應對,以及如何汲汲營營想要脫身當下窘境卻不可得,幾乎是近代小說難得一見的精采手筆,曼寫活了他眼中的人生真諦,而這才真正是他小說所要著重的「現實原則」,也是曼這本小說最迷人的地方。
湯瑪斯.曼出版這本小說時才二十五歲,而且書一出版就極暢銷,成為德國文學史上最暢銷也是最長銷的一本小說,時至今日,不管小說藝術有所謂怎樣的進化,曼的這本作品從未過時,即使我們說寫實主義的小說風格早已式微,但其所呈現的真理,卻永遠真實不變,怎麼會過時呢?而且我還要大膽強調,《布頓柏魯克世家》會是一本永遠教人百讀不厭的偉大經典作品,和狄更斯及福樓拜鼎足而立,是永不過時的偉大寫實主義代表傑作。
最後要特別一提的是,研究文學的人向來較少從史學的角度去看小說作品,如今蓋伊教授這本書以歷史學家的眼光去看寫實主義的小說,無疑為我們打開了另一層嶄新的讀小說的視野,我們可藉此以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小說中的「事實」。這本書在翻譯期間曾得助於逢甲大學外文系主任王安琪教授的熱心指正,她是我的同事,也是狄更斯迷,我如今把這本書譯贈給她。
二○○四年九月識 於逢甲大學外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