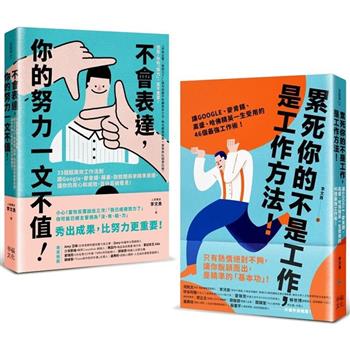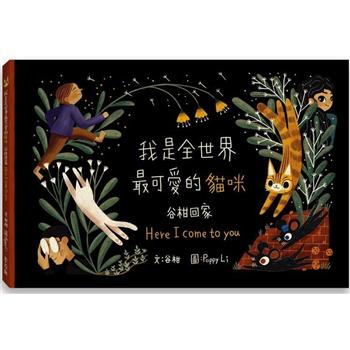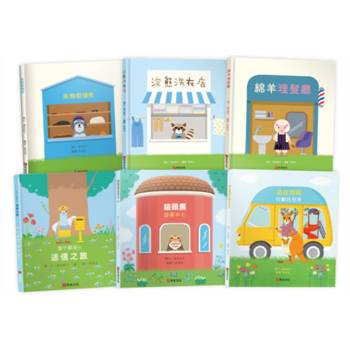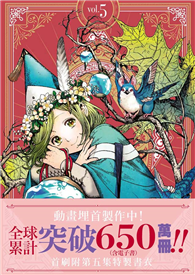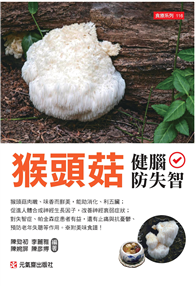什麼也沒做,什麼也沒說,你,真的確定自己,是個好人嗎?
惡人的劣言壞行固然可憎,好人視若無睹的緘默更可怕。世上許多不幸,源自沒有說出口的事。我們雖然自認只是不贊一辭的旁觀者,卻在不知不覺中,成了沉默的共犯……
當我們眼見真理卻不發一語,就是我們開始死去的時候。
人們常會拒絕承認明擺在眼前的事實,在無心或有意中,成了沉默的串謀者,「國王的新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否認諸如亂倫、酗酒、貪污、大屠殺等社會或歷史真相,卻不是童話故事。在家庭、組織、社會,甚至整個國家中,充斥著沒穿衣的國王,還有,基於恐懼、痛苦、羞恥,或難為情等種種複雜情緒,不敢(或不願)聲張的沉默民眾。
沉默的串謀存在於社會各階層,從家庭到公司,從私人情感到政治策略。它是一種集體行為,需要訊息的傳遞者及接受者共同對訊息諱莫如深。令人不安的真相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大家心知肚明,但卻不可談論、不宜議論也不可觸及,就像屋中的大象,明明巨大無可否認,眾人卻小心迴避,心照不宣的佯裝沒看見。
對於人們在面對日常生活或政治社會上「公開的秘密」時,所抱持沉默和否認的社會模式,作者帶來新穎獨特的見解。本書來回穿梭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從日常生活到大規模的歷史事件,並從新聞事件、戲劇、小說、童話,以及電影援引例證,旨在幫助我們了解「沉默串謀」背後的演變過程,以及為何我們會坐視所有人其實都知道的真相,試圖一起對現實視若無睹。作者告訴我們,像這樣的串謀是如何發展、開啟社會壓力,導致人們即使事實明擺眼前卻依然拒絕承認。他也揭示,每個串謀者的否認是如何與其他人形成共存式的惡性循環,以致如癌細胞蔓延;當有更多人共謀,特別是當涉及重要的權力差異,沉默通常更加凝重。
沉默不僅是恐懼的產物,也是恐懼的一大來源。要克服恐懼,我們往往需要攤開那些一開始造成恐懼的不可談論的事情。沉默拖得越久,就越需要「以沉默掩飾沉默」。我們越集體否認大象,牠們越盤據在我們心頭。要打破這種暗中作祟的否認循環,有賴於公開討論「不能被討論」這種現象本身。本書提出了第一個有助於推動此種討論的系統化嘗試。
作者簡介:
伊唯塔.傑魯巴維(Eviatar Zerubavel)
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著有:《七日週期》(The Seven-Day Circle: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Week)、《完美界線》(The Fine Line: Making Distinctions in Everyday Life),以及《時間地圖》(Time Map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ocial Shape of the Past)。
章節試閱
第一篇:
壓抑彷彿是……
一道強制沉默的命令……
彷彿是一種告白,表示對此沒什麼好說、沒什麼好看,也沒什麼好知道的。
──傅柯《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注意力規範」的存在,意味著人們對於何者應予以忽略,抱有一定程度的共識。然而,這樣的共識不見得總是存在。舉例來說,一般的傳統觀念中,習慣將藝術從視覺、聽覺環境分割開來,對此,藝術家試圖提出挑戰,像是竇加(Edgar Degas)的《女人與菊花》(A Woman with Chrysanthemums)、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的《今夜我們即興演出》(Tonight We Improvise)1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紅黃藍的菱形構成》(Diamond Painting in Red, Yellow, and Blue),以及凱吉(John Cage)的《四分三十三秒》(4’33”),莫不是出於強烈自覺意識,對傳統注意力約束所進行的大膽攻擊2。而對於族裔應否列為大學入學許可評鑑要素的爭議,基本上則是一場涉及「關聯性」的論爭。情侶之間針對另一半是否管得著自己過去性經驗而引發的激烈爭執3
,同樣提醒著我們:雖然有時候沉默是符合眾人期待的,但其他時候是否恰當,則很難說。
到目前為止,我們探討了引發沉默串謀的規範壓力,然而,迫使我們漠視某些事情的社會壓力,只有一部分是來自於規範。人們注意及談論的範圍,是由社會規範及政治限制共同所界定的;我們所看、所聽、所談論的內容,同時受到規範壓力與政治壓力的影響。唯有深入研究引發沉默串謀的政治環境,我們才能理解在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中,為什麼是國王(而不是,好比說,他的某個隨從)沒穿衣服,才能如此戲劇性地捕捉所謂「屋裡的大象」的精髓。
注意力與權力
我們的第一步,就是研究在注意力與言論的社會結構中,「權力」扮演了何種角色。畢竟,社會關係通常涉及權力糾葛,而沉默與否認,則往往是權力分配不均的產物4。我們掌握哪些消息,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擁有多少權力。舉例而言,「機密」(遑論「最高機密」)與「非機密」資訊的取得管道,有其規章限制,視人們的安全等級而定;消息靈通的程度,往往也與權力地位的高低互相呼應。
權力也使人有能力掌控傳遞給他們的訊息多寡。假如一個人是透過非正式的管道取得資訊,而擁有這項資訊可能會帶來麻煩,那麼,這個人日後就可能會佯裝自己不知情,藉此逃避責任。畢竟,比起「知情不報」,「完全不知情」的風險,是要低得多了。
因此,那些居高位的人,對於那些自己實際上心知肚明的非法行動,也許會保持「徹底且全然的不知情」(正式的說法,是「脫鉤」),以免受到牽連。或許,約翰.米契爾(John Mitchell)確實不曾向尼克森提及任何與水門案相關的事件,好讓尼克森保持「無菌般不知情」,因而免於法律上的麻煩5。
然而,權力也使人必須承擔更廣的注意視野,例如在科層組織中,社會位階愈高,所必須注意的層面也愈廣6。因此,一個旅長的考量,應該比他麾下的營長更全面,而營長的視野,又應該比連長更宏觀。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只有極少數資深的FBI官員,才有能力把該局鳳凰城與明尼阿波里斯分部,在九一一世貿中心與五角大廈攻擊前提供的資訊「串聯起來」。
不用說,連長之所以從戰術而非策略角度看待軍事狀況,是基於規範上的角色期望所致,而非個人缺乏好奇心使然。我們平常也不會將校長與一般教職員對於校務的認識與關心程度不同,歸因於個人的好奇程度不同。
權力不僅賦予人們更廣的注意範圍,更重要的是,它也賦予人們控制他人注意範圍的能力。舉例來說,透過擬定必讀書單,老師決定了學生認為何者值得研讀;當律師試圖插入反對意見來吸引法庭注意時,法官有權決定接受或駁回其抗議。權力,也與言論範圍的「控制」有關。畢竟,通常是由上司指示部屬「別提那件事」7。
舉例來說,當小布希要求當時的俄羅斯總統普丁加入伊拉克戰爭時,正是基於掌握言論範圍主導權的微妙政治角力,激得普丁說出,美國長期盟友沙烏地阿拉伯與巴基斯坦,在助長全球伊斯蘭恐怖主義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8。要控制他人的注意力與言論範圍,最常見的方法,就是控制「議題」(agenda)。從決定哪些議題該列入(其實同時也暗示了何者不該列入)討論範圍,進而正式定義「檯面上」
媒體的宰制
當然,國家領袖之所以能「抓住」全國注意力,靠的是大眾媒體攫取注意力的力量(而且靠著廣播或電視,甚至能讓全國民眾在同一時間注意同一件事情)10。事實上,媒體決定了哪些事情會出現在我們的共同雷達螢幕上;雖然他們並非總能成功指揮我們想些什麼,卻「極其成功地支配我們想到什麼」11。此外,藉由決定哪些議題或事件登上報紙頭條、成為廣播及電視新聞的焦點報導,他們顯然也決定了社會大眾對新聞重要性的感受12。
媒體光靠「不報導」,也幫忙阻擋了各種議題進入我們的意識。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所有電視、廣播、報紙皆受政府管控的極權社會,就連多元化的政治體系,亦是如此。舉例來說,對於它們所認定在選舉中無足輕重的「弱勢」選人,美國媒體幾乎不約而同地拒絕報導13,很明顯的,這麼做也限制了這類「沒有被報導」的新聞的重要性。
大眾注意力的延續時間長短,其實也受到媒體的宰制。從我們經常接連數週追蹤某則新聞,卻在媒體停止報導後立即忘得一乾二淨,即可見一斑。特定議題或事件,會成為大眾關注焦點,然後停留一陣子,接著逐漸淡去,形成了一種由媒體主導的輿論注意力週期。從這角度來看,也許「犯罪潮」(crime wave)所反映的,是大眾對犯罪活動的關注隨媒體報導而產生的特定變化,而不是犯罪率真的有所升降14。畢竟,即便是非常重大的新聞事件,也往往在風頭過後,退到公共雷達螢幕上較不顯眼的位置,最後完全銷聲匿跡。最好的例子,就是《紐約時報》在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於頭版底發表的聲明:「最近幾週占據獨立版面的伊拉克戰爭及其後續效應的報導,今日起,回到正常新聞版面,起自第十版。」
第二篇
世上許多不幸,源自……沒有說出口的事。
──引自杜斯妥也夫斯基
讓我們來談談──沉默的串謀為個人與社會製造的嚴重。
要計算我們選擇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緘默以對的最後得失,大抵是在權衡短期與長期的影響。這類串謀提供的許多便利之處,不過是為長期問題埋下了短期的種子。《沉默之後》的作者南茜.瑞恩,如此回憶她被強暴之後的幾年:「我持續的沉默,無異是以療癒偽裝的傷害。」1的確,許多似乎在短期間對我們有利的事,日子久了,往往回過頭來纏擾我們。
變形的現實感
否認以其虛妄的本質,必然會扭曲人們的現實感。倘若其他人以沉默串通一氣,問題將更形惡化。畢竟,當其他人似乎一概不承認大象的存在時,你的信念也很難不動搖,懷疑自己是否真的看見了屋裡的大象,或者一切只是出於自己的想像。
因此,在《罪之吻》中,哈里遜跟父親之間從未談起他對她幹的那些好事,而這只會讓她益發懷疑一切是否屬實:「我經常想起他的吻,可是每當我想對父親問起,卻始終開不了口,」一部分是因為,「有時我會懷疑是否根本沒發生什麼事。我問自己,整件事莫非是我自己憑空捏造的?」2其男友的反應,更加深了她的否認:「『我錯了,』我對男友這麼說,『我誇大其辭,話說得偏了。事情完全不是那樣。他也許只是不小心吻了我。』……我男友被我的話嚇到了,一邊聆聽,一邊跟我串通一氣。我們合力遺忘……父親對我做的事。」3
對於還需要靠他人幫忙理解其自身經驗的孩子而言,未經證實的個人經歷,尤其讓人感到困惑,例如,母親才剛帶著自己的五歲孩子,跟祕密情人共度了數小時,之後卻否認祕密情人的存在4
;又例如,當周遭的人從不談論父親顯而易見的酗酒問題時,孩子不由得「懷疑其他人是否真的看見了大象,或者只是她自己的幻覺」,而「既然不能對其他人問起大象的事,她只好一直把問題擱在心上」5。以下這首童謠,似乎抓住了這種未經證實的經驗往往會激起的奇怪感受:
昨天我見到階梯上
有一個不在那裡的男人
今天他又不在那裡
噢,真希望他走開。6
當一個人欠缺堅定基礎,來證實自己的認知經驗時,可能就會開始對自己的感受失去信心,並且如電影《煤氣燈下》(Gaslight)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節那樣,漸漸失去對現實的掌握。
身邊沒有人承認「大象」存在的事實,也容易使得大象似乎越變越可怕。的確,沉默不僅是恐懼的產物,也是恐懼的一大來源(這也說明了它為什麼阻礙了精神受創者的復原)7。要克服恐懼,我們往往需要攤開那些一開始造成恐懼的不可談論的事情8。
犬儒心態
如同<國王的新衣>中一針見血的描述,沉默的串謀,往往涉及某種程度的心口不一,「『這是怎麼回事?』國王自忖,『我什麼也沒看見哪!』然而他大聲讚歎,『真美啊。』……每一位參贊、大臣和要人……一看再看,與國王所見殊無二致,然而他們異口同聲附和國王說,『真華麗!真美啊!太了不起了!』他們齊聲附和,可是誰都沒看見任何東西。」9從這些尖銳的諷刺情節可以看出,這種口是心非的表裡不一,和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兩面思考」相互呼應:「他的腦子不知不覺陷入兩面思考的迷宮世界,知與不知,明白真相卻說著精心編織的謊言,同時抱持兩種看法……明知它們相互牴觸。」10
這樣的口是心非,必然出於某種程度的犬儒心態。一名前納粹醫生,如此說明兩面思考固有的邪惡邏輯:「我不能要求克萊﹝醫生﹞『別把這人送進毒氣室』,因為我壓根不知道他進了毒氣室。你瞧,那是個祕密。這個祕密人盡皆知,可它還是個祕密。」不過,口是心非也需要某種程度的自我否認。雖然那些納粹醫生必定知道猶太人「並非被遷往他處定居,而是被屠殺了,而且『最終解決方案』意味著殺光所有猶太人」,他們得以利用這類具有麻痺本質的委婉修辭,﹁殺人……而不必感受殺人的經驗﹂。而愈常使用這類語言,他們就愈容易「無動於衷」,最後乃至麻木不仁11。
不用說,否認個人感受是非常耗損精神的。「別去想它,」每當哈里遜試著忽略與父親的亂倫關係帶給她的感受時,便會對自己這麼說。然而她逐漸了悟,否認那些情緒,「似乎得使上好大的勁兒。」
導致孤獨的,是沉默
沉默的串謀還會引發孤寂感。一個人確實注意到的事情,跟周遭人士願意承認注意到的事情之間如果出現落差,會傷害群體生活的核心本質,也就是彼此之間互為主體的共識情感(intersubjectivity)13,因而導致深沉的孤獨感。開放性的溝通可以拉近距離,而沉默則使人們彼此疏離。「話語,縱然是最矛盾的話,」湯瑪斯.曼(Thomas Mann)說過,「可以維持聯繫──導致孤獨的,是沉默。」誠如哀傷的詩人絕望地懇求:
噢,求你,念出她的名字。
噢,求你,再說一聲「芭芭拉」。
噢,求你,讓我們談談屋裡的大象。
……
當我對你說起「芭芭拉」,能不能別轉過頭去?
因為你若如此,就是留我一人
獨自……
在屋裡……
與大象共處。15
同樣的,儘管「有那麼多神職人員是同性戀」,一名身為同志的前神學院學生回憶:「這件事從未被公開討論或承認……所以我覺得自己是異類,活在自己的地獄中。」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貝蒂.傅瑞丹《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書中所提到的、那些未得到滿足的家庭主婦身上;她們「羞於承認自己的不滿足,從不知道有多少女人面對同樣狀況」16。
亂倫與強暴受害者之所以經常感受強烈孤獨,沉默的串謀得負起最大責任17。在《潮浪王子》中,湯姆、他的母親,以及妹妹莎瓦娜強迫自己三緘其口,因而導致深沉的孤獨感,更加深被強暴的創傷:「我認為強暴對我的影響,比不上嚴守母親規定的隱瞞和保密所造成的傷害……我們甚至不對彼此談起。那是一個愚蠢至極的鄉下家庭立下的祕密誓約,一個帶來災難的否認協議。我們在沉默中信守個人的恥辱,讓它變成不可觸及的禁忌。只有莎瓦娜打破了協定……三天後,她第一次割腕自殺。」18這無疑凸顯了團體環境的療癒效果,藉由鼓勵受創的倖存者跟其他人交換痛苦經驗,可以消除他們的孤獨感19。
曲折的社會迷宮
然而,沉默的串謀所製造的,不僅是個人問題。許多問題無疑屬於社會層面。要對「大象」視若無睹,得靠眾人通力合作。畢竟,公開的祕密「根本不是祕密,社會大眾得費好大力氣去避免注意或談到它們……當家裡有這樣一個祕密,不啻在客廳中央擺了個十噸重的巨石,還不准任何人提到它。你總得繞道而行,椅子的位置也得調整;你也許可以往它的方向瞥一眼,但不能直視它;一連串話題越來越觸碰不得」20。人們如履薄冰,這樣的屋子就像地雷區,我們得戰戰兢兢繞著每個話題的邊緣打轉,「明白自己隨時可能踏上地雷。」21當然,人們基本上可以無所不談,就是不能觸及大象:
我們談論天氣。
我們談論工作。
我們談論所有一切事情──
只除了屋裡的大象。22
我們於是落得談論「無關緊要卻可談論」的話題,說著雞毛蒜皮的瑣事,只為了掩飾沒說出口的話。為了確保我們不會觸碰禁忌,不小心承認了大象的存在,我們還得跟它保持安全距離,只談論「安全無虞」的話題,避免自己不慎誤闖不可談論的禁地。可想而知,我們能觸碰的話題範圍因而越來越小,逐漸生活在由緊閉的門扉和越來越窄的通道組成的社會迷宮中23。不消說,共同忽略屋裡的大象,需要眾人付出努力共同合作,因此是非常消耗社會力量的。難怪它也會導致強烈的緊張關係。的確,沉默越深重,蓄積在它周圍的張力就越發強大。
眾人一致忽略大象的努力,最後可能會滲透串謀者彼此關係的每一個層面。他們的關係確實可能「因﹝大象﹞而大幅度扭曲,﹝因為﹞他們無法承認或影射大象的存在」。正如一位亂倫受害者對其家庭生活的描述:「祕密在我們之間滋生,玷汙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24 說來諷刺,沉默串謀的存在,部分是出於維護團結之故,然而由於它阻礙了誠實、互信的關係所不可或缺的開放性溝通,反倒傷害了群體的團結25。為了「保護」群體,沉默的串謀往往反倒讓群體機能出現障礙。黑暗中,殘酷和墮落在滋長沉默也會導致道德淪喪,因為它打開了傷害的大門。這就難怪沉默連同祕密,會成為違法犯紀者的一大武器。畢竟,殘酷和墮落都「在黑暗中滋長,要驅除它們,你必須投以最明亮的光芒」26。
俗話說,沉默就是同意。若對不當的行為保持沉默,我們無疑幫助它們正當化,隱約鼓勵了潛在犯行者將之視為確實可行,因而使罪行沒有終止的一天。佯裝沒注意到丈夫侵犯女兒的女人,透過默許而助長了丈夫的罪愆27;年輕老師旁觀資深同事忽略教授與學生之間的不當關係,因而在潛移默化中學會原宥這類罪過,一如年輕士兵旁觀長官公開違反軍紀,卻無人置喙,也有相同的影響。
這說明了為什麼在一則反強暴的廣告中,會使用傳統上象徵「否認文化」的三尊智猴像來譴責沉默,並搭配如下說明文字:「提到強暴,務必壓低音量,否則別人可能會受到冒犯……
或覺得尷尬……或甚至為此下獄。但是,該是人們大聲說出強暴被害者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的時候了。假如你也這麼想,請把訊息傳遞出去,例如那些你投以選票的人。」28這首一九六○年代的東德嘲諷詩作,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時代充耳不聞,
對當前事件視若無睹,
對自己所知者三緘其口的人,
將獨活下來,倖存到老,
然而非得保留一個條件不可:
要如此獨活,
必得有一副鐵石心腸。29
誠然,在許多人眼中,打破沉默是一種「出類拔萃的道德行為」。馬丁.路德.金恩曾經說過:「我們眼見真理卻不發一語的那天,就是我們開始死去的時候。」事實上,也許將來有一天,我們會記得納粹大屠殺,不是由於被害人數之多,而是因為人們對於這起事件竟如此沉默……
第一篇:壓抑彷彿是……一道強制沉默的命令……彷彿是一種告白,表示對此沒什麼好說、沒什麼好看,也沒什麼好知道的。──傅柯《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注意力規範」的存在,意味著人們對於何者應予以忽略,抱有一定程度的共識。然而,這樣的共識不見得總是存在。舉例來說,一般的傳統觀念中,習慣將藝術從視覺、聽覺環境分割開來,對此,藝術家試圖提出挑戰,像是竇加(Edgar Degas)的《女人與菊花》(A Woman with Chrysanthemums)、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的《今夜我們即興演出》(Tonight We Improvise)1、蒙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