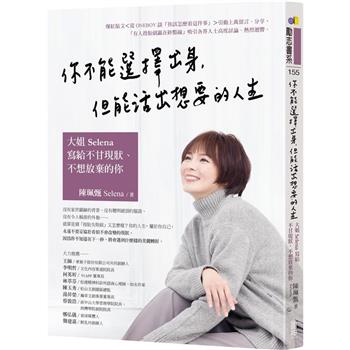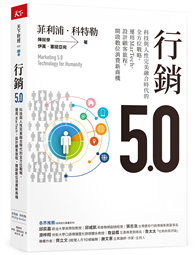性、謊言與政治正確木馬總編輯汪若蘭
在美國戰後幾位重要的作家逐漸退隱,創作量減少之際,曾以冷嘲熱諷描寫猶太人身分認同問題的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仍不斷推出驚世駭俗或帶有強烈社會批判色彩的重量級作品,而且是美國少數把所有重要文學獎,包括福克納文學獎、國家書卷獎、普立茲文學獎通通囊括的小說家。這位歷年來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作家,作品經常在寫實主義中混合著奇思怪想,在政治性的諷刺中參雜著粗俗的鬧劇成份。由於寫作風格與敘述故事的功力搭配平衡,菲利普‧羅斯雖已年過七十,新作《反美陰謀》(The Plot Against America)依然立刻躍登美國各大暢銷書排行榜與年度選書書單之中。
為表彰羅斯在文學上的成就,美國藝術人文學院在2001年頒給他最高的金牌榮譽,這是美國當代任何其他小說家所望塵莫及的。同年,時代週刊「美國之最」的評選中,也將羅斯列為美國當今最佳的小說家。時代週刊認為,羅斯獨領文壇風騷四十餘年,作品都維持一定的水準,在這場創作的馬拉松競賽中,羅斯交出20多本的小說,本本都別具企圖心,都出自一個懷有強烈自我要求的成熟作家之手。
雙重的面貌
菲利普‧羅斯1933年生於美國紐澤西州的紐渥克(Newark),是移民自歐洲的猶太人第二代。羅斯自十餘歲起便離鄉背井家到外地唸書,畢業於芝加哥大學英文研究所,曾任教於賓州與普林斯頓等大學。羅斯一生似乎總是呈現著雙重的面貌,他自己就曾寫道,「極端嚴肅的態度」與「喜歡開玩笑」是他的兩個摯友。羅斯常扮演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角色,一方面是來自東岸的鄉紳,是嚴肅的現代文學代言人,另一方面又以喜劇演員的姿態,孜孜不倦寫下美國最滑稽諷刺的小說。
羅斯這種雙重的面貌也反映在他的小說呈現方式。1959年他以處女作《再見,哥倫布》(Goodbye, Columbus)榮獲美國書卷獎之後,正當各界期待他再度寫出如第一本得獎小說的清新之作時,他卻努力想擴展寫作範疇,自我突破。結果1969年他推出的《波諾的怨言》(Portnoy’s Complaint)敘述一個男子藉由自慰尋求罪惡感與不安全感的解脫,跌破大家眼鏡,也讓羅斯聲名大噪,名利雙收。1972年他還寫了一個關於性慾的卡夫卡式小說《乳房》(The Breast),描寫一名男子半夜會變成一個巨大乳房的荒唐怪誕故事。由於羅斯書中的措詞直截了當,描寫栩栩如生且充滿活力,因此讀者總是將作者本人與書中的主角聯想在一起,為此困擾的羅斯乾脆在後來的作品中加入一個虛構的人物,內森‧祖克曼(Nathan Zuckerman)來發言,創作了一個祖克曼三部曲(The Ghost Writer, Zuckerman Unbound, The Anatomy Lesson),但同時又在八○年代末期之後的作品中,安排主角名叫菲利普‧羅斯。由於羅斯在這些作品中深入探討了真實與虛構的關係,質疑小說與自傳的分野,還常常惡作劇地引誘讀者掉入這些似是而非的陷阱,被當時的文評家稱為「最大膽的當代美國作家」。
快速成名的羅斯在八○年代曾一度陷入低潮,選擇旅居國外各地創作。不過1995年他出版的《Sabbath’s Theater》,顯然是羅斯創作生涯的轉戾點,因為又回到二十多年前《波諾的怨言》造成轟動的那種描寫性心理與偏執的滑稽悲喜劇形式。接下來他完成了一系列美國九○年代晚期最重要的作品,即作者所稱的代表作「美國三部曲」︰《美國牧歌》(American Pastoral)、《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I Married a Communist)、《人性污點》(The Human Stain),分別涵括了美國二十世紀後期幾個重要的階段,包括尼克森時期、越戰時期,以及克林頓時期,呈現形塑戰後美國文化的社會、政治與心理衝突和分裂。在「美國三部曲」中,羅斯再度啟用了內森‧祖克曼來代言,並在稍後的訪談中,稱祖克曼為自己的另一個自我(alter ego)。
人人皆知
《人性污點》是「美國三部曲」中最後的一部,同時也被公認是三部曲中最複雜的一部。故事背景是1998年柯林頓與呂文斯基的性醜聞爆發,全美籠罩在道德重整的氛圍中,主角是麻州雅典娜學院古典文學系系主任柯爾曼。七十一歲的柯爾曼,曾是雅典娜學院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猶太裔院長,學術生涯順遂,家庭生活美滿,但卻在某次上課時,稱兩位一直缺課的美國黑人為「spook」(原意為幽魂,在美語中又指黑鬼),結果被指為有種族歧視之嫌,柯爾曼被迫提早退休,妻子遭受打擊突然中風過世。隨後柯爾曼認識三十四歲在學院當清潔婦的福妮雅,並進而發生關係,同時柯爾曼與新鄰居祖克曼結為好友。沈浸在野性情慾中的柯爾曼,不久與情人福妮雅雙雙在一場車禍意外中喪生,福妮雅前夫萊斯,一個越南退役老兵,被懷疑是暗中行兇者。
真實與謊言、過去與現在,感知與現實之間存在著清楚的界限嗎?書中第一章章名「人人皆知」便是作者對語言使用的嘲諷。由於柯爾曼與清潔婦私通的事被發現,一封顯然來自學院中敵人的毀謗匿名信如此寫道︰「人人皆知你正在性欲上剝削一個受淩辱、沒文化、比你年紀小一半的女人。」人人皆知,人們自以為知道所有在眼前發生的事,卻一無所知背後屹立不動的祕密。作者便藉祖克曼之口說︰「『人人皆知』是陳詞濫調的援引……我們所知道的是,若以非陳詞濫調的方式加以表達,人人都一無所知。你什麼都不可能知道。……我們所不知的一切令人驚訝。而更令人驚訝的是自以為知的一切。」
人生的謊言與真實
《人性污點》一開場這個「人人皆知」的諷喻,正是這本小說獨特之處的基石。因被指控為種族主義而不得不黯然離開學院的柯爾曼,其實本身是膚色極淺的黑人。羅斯在此創造了一個一心想要脫離黑人社群,苦苦追求生存上獨立自由而假冒猶太人的人物。柯爾曼二十歲時便看到這個可以矇混為猶太人的機會,於是決定離開家鄉,斬斷過去,成為一個全新的人,如同祖克曼所形容的︰「為了變成另一個人……拋棄所有的一切,整個的枝繁葉茂的黑人族群……那麼多的渴望,那麼多的計畫、激情、狡猾和偽裝,統統為了滿足離家出走以及脫胎換骨的饑渴。變成一個新的人。雙重人格。」
為了成為一個「比白人更加白人的白人,」柯爾曼每一天努力扮演自己創造出來的自我。他甚至告訴自己的母親,他將永遠不會再來探望她,因為他將以新的猶太人的身分結婚生子,功成名就,而他的母親也將永遠不會看到他的妻子,和她未來的孫兒。諷刺的是,以猶太人/白人身分從軍的柯爾曼,因為名字聽起來太像黑人,曾在召妓時被攆了出去,後來卻又因為所假冒的白人/猶太人身分,被趕出雅典娜學院。
但是與福妮雅的相遇,卻是在暮年遇到人生重大挫折的柯爾曼,另一個真實人生的開始。這兩個人的社會身分天差地別,一個是「三十四歲強壯、瘦削的勞動婦女,語無倫次的文盲,只有肌肉和骨頭」,一個則是「七十一歲思想深沉的年長公民,學富五車的古典文學研究者,精通兩門古老的語言」;兩個人的身世背景也迥異不同,一個是自願跌入社會底層,面對真實自己生活的人,一個則是背負巨大的身分祕密,面對偽造的自己生活的人。可是福妮雅身上獨具的那種野蠻、反社會化的智慧,卻讓柯爾曼過去多年來禁錮著的殘餘獸性釋放出來,他因此決定「是屈服的時候了,是該讓這單純的渴望作為嚮導的時候了。超脫別人的指責、別人的控告、別人的審判。趁沒死之前,學會超脫他們令人發怒、討厭、愚蠢的譴責的許可權,我行我素地生活。」
自小離家出走,選擇過著野蠻粗俗生活的福妮雅認為,性欲,是人與生俱來,不可恥也不需救贖,真正的罪惡並不在於不可違抗的污穢,而是在於對不可違抗的違抗,在於人性對於淨化的追求,當人們開始致力於淨化時,不論是透過政治正確、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宗教狂熱或是保守嚴格的性操守,反而撒下了罪惡種子。相對於祖克曼的感嘆——這性的污染物,救贖性的墮落,使得人類的理想幻滅,永無休止地提醒我們切莫忘記自己是由什麼料做成的。福妮雅則說:「人性污點。我們留下一個污穢,我們留下我們的印記。污染、殘酷、欺淩、謬誤、糞便、精液……和反抗無關。和恩賜或救贖無關。在每個人的身上。存儲於內心。與生俱來。無可描述。污穢先於印記。沒有留下印記之前便已存在。污穢完全是內在的,不需留印記。」
不論是呂文斯基藍色Gap洋裝上的污點,還是有色人種膚色的印記,羅斯在這本充滿隱喻與諷刺的小說中,對於人性的深刻探討,雖有評論者開玩笑說像是哲學論文,但也證明了羅斯已到了福克納所說的,一個每個偉大作家都有的無可比擬的時期,就是速度、力道、才華都到位的時期。當今的美國文學可說是羅斯的時代,一如二○年代的海明威,三○年代的福克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