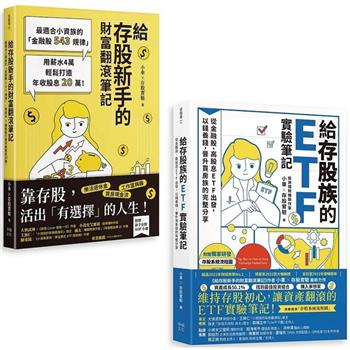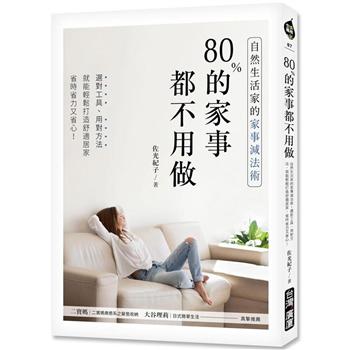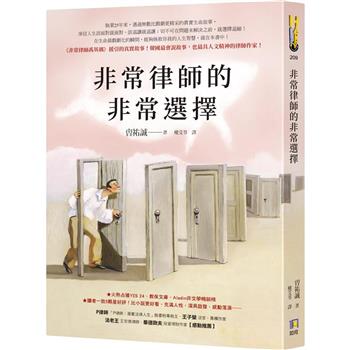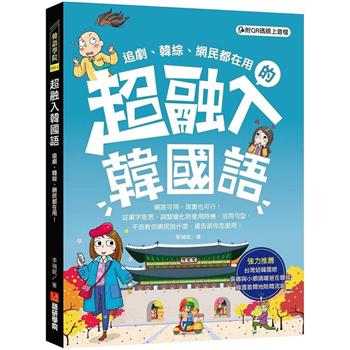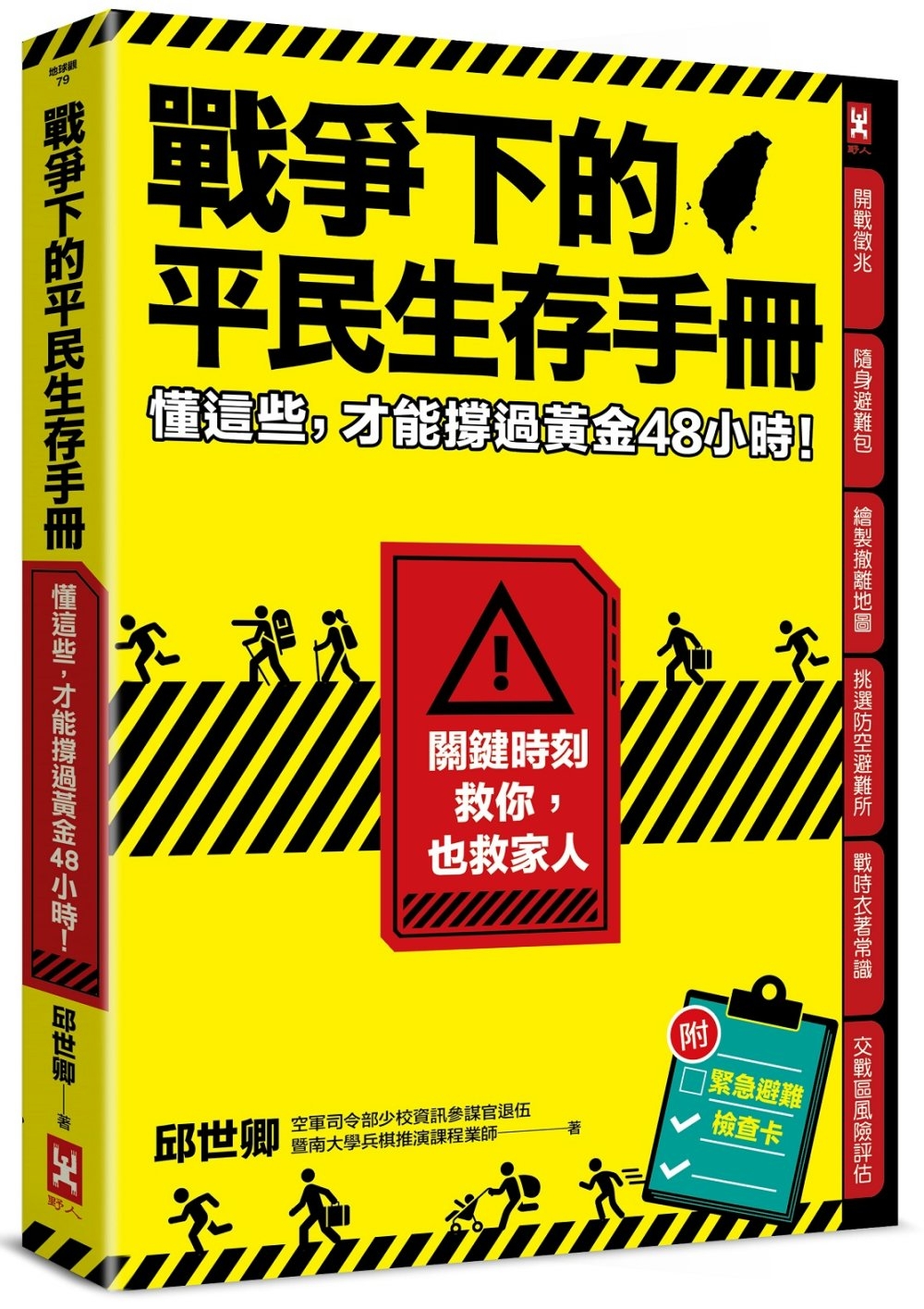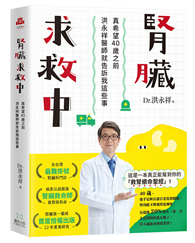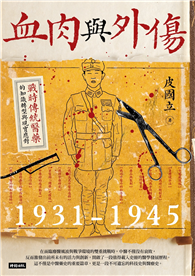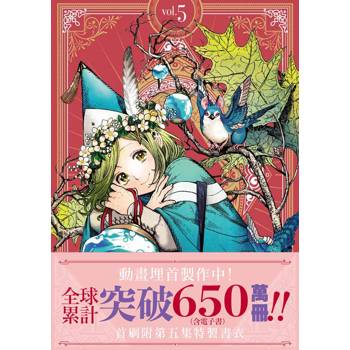強力推薦
本書原由『書林』出版,現在由大地取得授權,重新出版,經典好書不容錯過。
錢鍾書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圍城」,是一部家喻戶曉的現代文學經典,不但奠定了他在文學創作的不朽地位,「圍城」更被譽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最有趣且最用心經營的小說。
「圍城」的含義是:「城內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故事發生在1937年的夏天,方鴻漸到歐洲遊學四年後回到上海,住在已故未婚妻的家中,但因與女博士蘇文紈、大學生唐曉芙發生了情愛糾葛,所以受到丈母娘家人的冷淡。他戀愛失敗後,和原是蘇文紈的追求者趙辛楣成了好朋友,兩人接受內地大學的聘請。一路上歷經艱險,也發生了無數趣事。在學校任教期間,方鴻漸不自覺地捲入校園內個人恩怨的明爭暗鬥中,而與助教孫柔嘉的關係日趨親密更引起其他同事的嫉妒。趙辛楣離校從商之後,方鴻漸更被校方排斥。方鴻漸與孫柔嘉結婚回到上海,但倆人常因瑣事爭吵,終於導致無可避免的分手….
「圍城」吸引人的地方除了通俗的主題之外,講的是一般人最有興趣的婚姻及知識圈內的各種「八卦」,而錢鍾書的機智和諷刺天分,透過文字的表達更是發揮到了極致。小說中的?關語處處皆是,充滿黠慧的語言更是讓人拍案叫絕。
圍在城?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楊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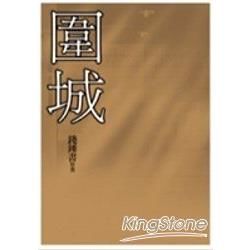
 2021/10/15
2021/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