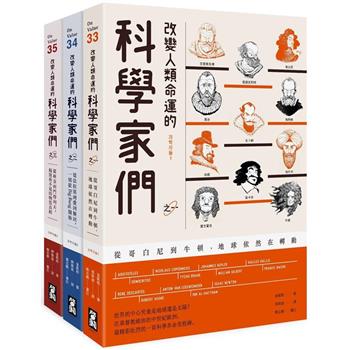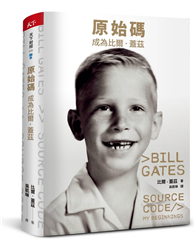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白話賢愚經》序
《賢愚經》、《法句經》、《百喻經》是佛教的根本寶典,而《賢愚經》更是敦煌文化的核心;換言之,《賢愚經》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及影響力,遠在《法句經》與《百喻經》之上。對於敦煌石窟的造像而言,《賢愚經》展現了祂豐富而深遠的寓意及教化之功,這也是《賢愚經》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堅固地位。但自唐宋以後,隨著中國一佛乘思想的成熟與展開,中國佛教思想邁向了抽象的空性哲理,反而讓《賢愚經》這類寓意深遠的故事型經典隱沒不彰,殊甚可惜!
文化的發展,從具相到抽象,從事件到理論,乃是必然的軌跡;但是一經邏輯化、理論化後,其所延伸的意識形態,則是大腦所生文明的另一種罪孽,這是因為人類在積累文明與記憶的過程中,將具相的事件給予邏輯化的過程中,程式的運用,令事件的本身在規格化中被簡化了,而在此簡化的過程中,大腦只選用其所需的題材,因此事件的簡化,使得歷史事件逐漸被窄化而變形,所以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人類逐漸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人性,致使文明與人性脫勾,而不知為何而生、為何而活。佛法傳入中國亦然,逐漸的失去了本意,而產生了純意識的佛教,因此重新發揚《賢愚經》、《法句經》以及《百喻經》的事相法理,使殊勝的佛法回歸到人生中來,乃是當務之急。故而巧遇杜教授這位敦煌學專家,又專擅於《賢愚經》的資料搜集,乃一大幸也!
杜斗城教授是敦煌學的泰斗,對於敦煌學中佔有重要地位的《賢愚經》,自是嫻熟,在百忙的研究生涯中,自工作上的需要激發起興趣,由第一手資料的研究,產生了對法義的研究與探索,因而將敦煌學圖像中有關《賢愚經》的法要匯集成書,親自著寫此書,用舒心懷,甚是可貴!此書不若坊間的教學工具,亦非宗教類弘法工具,而是學者專業研究之餘之紀要,乃實物實證的紀實與心得。由於專家對圖像的研究解讀所產生的心內影像,而將之彙聚成文,乃至積累數十年之功夫而成累案之牘,甚為可貴。近年杜老將簡體版的文稿修改後欲重刊之,適逢兩岸文化交流,空庭書苑有幸蒙杜老慈允,得以獲繁體版的出書機會,殊感榮幸!
排版、出版事小,為了出書的順序以及中印之間往返的中英文版書籍,致使杜老此書一再延宕,實感抱歉。今日終於可以出書,一了心願,倍感欣慰,特此一併記以感恩!
普賢行者 海雲繼夢 合十
前言
《賢愚經》(十三卷)是很特殊的一部佛典,其雖名為“經”,但實際上是一部“佛教故事集”。全書共分十三卷、六十九品(節),也就是說共講了六十九個故事。但實際上,其所包括的故事更多,因為往往一品中又包含了很多小故事。
關於《賢愚經》的來源,現存《大藏經》,題為“元(北)魏涼州沙門慧覺(一說慧覺為曇學之誤)等在高昌郡(今新疆吐魯番)譯”。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九說:有河西(今甘肅河西走廊)沙門曇學“威德等,共有八僧,結志游方,遠尋經典”,到達於闐(今新疆和闐),遇到了那裡五年一次的無遮(人人都可參加辯論的佛教法會)大會。如此盛會,講經論道者,佈施傳法者很多。曇學、威德等八人,隨即根據各人情況,分頭聽講,並學習當地語言,記下了各自聽到的內容。不久,他們便返回高昌,合集各人所記,成為一書。又越流沙,回到涼州(今甘肅武威)。當時河西有一名叫慧朗的高僧,精通佛理,知識淵博,頗受僧界尊敬。他認為曇學等人所記,源在譬喻,兼明善惡,即用譬喻弘揚佛理,勸善戒惡,原想為其命名《譬喻經》,但因此前譯經,也多用“譬喻”之名,遂據其論說善惡之理,取其義而改名為《賢愚經》。
關於《賢愚經》成書的年代,《出三藏記集》說是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唐智昇《開元釋教錄》說是“太武帝太平真君元年”。查其時間,皆為西元445年,但後者所記,可能來源於前者。對此,龍蓮法師和方廣錩博士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他們據《出三藏記集》作者僧佑所記,認為僧佑既在梁天監四年(西元505年)採訪過曾去涼州的沙門弘宗,弘宗時年已84歲,據此推算,弘宗14歲隨師在涼州“躬睹其事”(指集《賢愚經》)時,正當西元435年,即元嘉十二年(北魏太延元年)。由此可知,僧佑所說的“元嘉二十二年”很可能是“元嘉十二年”的訛誤。我贊同這個分析。換句話說,我們認為《賢愚經》成書的最後時間應在西元435年左右,即北涼晚期沮渠牧犍時。元嘉二十二年(西元445年),建立在河西的佛教之國——北涼,已被北魏消滅,涼州城破,經書焚蕩,僧人東奔西逃,河西被北魏控制。此時,北魏太武帝滅佛之心漸顯,曇學、威德等人,絕不可能在此種情況下自投羅網。至於曾給《賢愚經》提名的“河西宗匠”——慧朗,可能早已不知去向了。所以現在流行各種版本的《大藏經》對《賢愚經》問世的年代應作糾正,改“元魏”為“北涼”。
此外,歷代《大藏經》都說《賢愚經》為曇學等在“高昌郡譯”,可實際上此經並不像流傳到中國的絕大多數佛經那樣,是從梵語或從其他語言翻譯成中文的,而是編譯的。也就是說,是由曇學等人各書自己所記,整理記錄後成集的。
《賢愚經》的內容除了講述各類佛弟子及其信徒的前生故事外,還有不少佛本生故事(佛前生故事)和佛傳故事(從降生到成佛的故事)。如《降六師品》講述了六師外道與佛鬥法,結果六師大敗。此類故事,實際上是《西遊記》中二郎神與孫悟空鬥法的來源;《微妙比丘尼品》描述了一個丈夫被蛇咬死,兒子被狼吃水漂,遭受了無數次災難的婦女形象,這又為魯迅的小說《祥林嫂》所借鑒;《檀膩羈品》的倆婦人爭一小孩,國王讓其各自用力去拉,誰拉走,算誰的,結果真母因不願拉傷小孩而退出爭執,國王從中看出真偽,此又為中國民間流傳的“包龍圖斷案故事”所吸收。
總之,《賢愚經》雖說是一部佛經,如讀起來,妙趣橫生,理明事清,妙不可言。如果要瞭解佛經故事,一本《賢愚經》就知梗概了;如果要瞭解一點古代印度的民間故事、題材和表達方式,一本《賢愚經》也夠了;如果要瞭解一點敦煌等佛教石窟壁畫雕刻的創作來源,一本《賢愚經》也夠了。《賢愚經》不像《百喻經》那樣,一個故事,了了數字。其情節曲折動人,內容雖長,但又能引人入勝,不覺冗繁。
同時,《賢愚經》也不像很多佛經那樣,或是講經論理,或是不厭其煩的說教。其寓佛教“勸善戒惡”的旨意於故事之中,它給讀者的不僅僅是豐富的故事,更重視其中的“賢愚”道理,其可以使人的心靈淨化,修養提高,知識增多。
當然,《賢愚經》同很多佛經一樣,往往有一些迷信的成分摻揉其中,在科學的今天,明眼人一看便知。佛教講究“隨緣而教”,為了弘揚自己的主旨,採取的方法是不同的。為了勸善戒惡,講一點地獄天堂之類又有何呢?所以,為了保持原貌,我們把《賢愚經》全文都翻譯了,換句話說,我們不願意採取那些掐頭去尾的方法,把一件完整的作品弄得殘缺不全,支離破碎。
杜斗城
1993年夏于蘭州大學
後記
眾所周知,把古漢語譯成白話本來就很不容易,把佛經譯成白話就更難了。因為翻譯佛經,除了要具備較深厚的文、史、哲功力之外,還需要相當豐富的佛學方面的知識。但由於我們這些方面的功力均有限,所以錯訛之處是難以避免的。還有,我們翻譯時所依據的本子為《大正藏》本,其本雖有斷句,但誤斷極多,原文本身也有不少錯訛別奪。遇到此種情況,只好瞻前顧後,揣摩原意而“理順”了。但為了使原意不致走樣,我們沒有採用“直譯法”。這樣一來,文句上就顯得生硬曲折了一些。此外,由於《賢愚經》是曇學等八人“各書其聞”而集成的,所以全經文風也頗不一致,甚至同一專用名詞的漢譯法在各卷中也各有不同的情況,所以,我們的譯文也很難保持一致。現在,我們唯一能問心無愧的是:我們是在認真地對待這件事情。所以,還希望廣大讀者不吝指教,以期有機會修訂。
最後,我們還要感謝上海佛教協會秘書長、上海佛學書局經理周家俊居士。周居士敬奉三寶積年,頻交大德,學有根基,熱心於佛法之弘揚,兩年前(1992年5月)就曾令我譯此《賢愚經》,他保證出版,但因我忙於教學和塵世雜煩,一直未能如期完成;雖後完成(1993年夏),但因種種原因,不能在上海出書了。總之,如果沒有他的催促和鼓勵,此事恐怕還要托下去的。
此外,我還要感謝蘭州大學歷史系90級許多同學及我的研究生陳海濤、殷光明、劉慧琴並周絢隆諸君,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這本書也是不會現在就展現在讀者面前的。
以上是我於1994年寫於蘭州大學的一段“《白話賢愚經》後記”,見於1994年8月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話賢愚經》。
此次再版,我還要特別感謝臺灣大華嚴寺導師海雲繼夢大法師。法師現為國際華嚴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多年來奔走於海峽兩岸,以濟世救人為宗旨,弘揚佛教,心得頗多,著作等身。而法師的講學足跡更是遍及世界,其精于華嚴,涉獵各宗,實為當代出家者中少見。我認識海雲大師是在西安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共同的興趣與話題使我們有了許多交往。我曾多次邀請海雲大師給我的研究生們講授佛學,並合作舉辦了三次海峽兩岸的大規模學術考察活動,共同走遍了從敦煌至隴東的隴原大地,取得了許多學術成果。現海雲大師鼓勵我把1994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話賢愚經》在臺灣用繁體字再版並配以原文,以便更多的讀者能夠讀到並瞭解它。雖然我感其只是一個佛經的“普及本”,而並非一項學術研究成果,且為多年前翻譯之作,還存在不少問題,然我還是欣然應允了。在此,致大師以衷心地感謝!同時,希望此繁體版面世後,能夠得到更多讀者朋友的不吝指教。
杜斗城於2012年9月12日記於
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