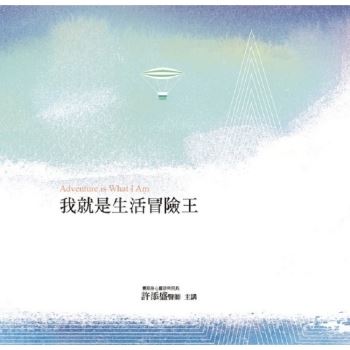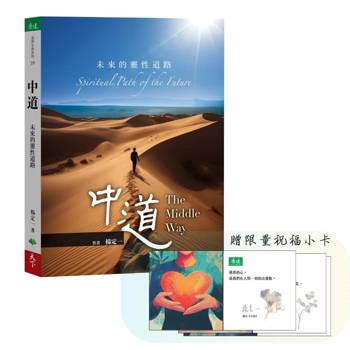我往內旅行,看清楚自己的本質,然後往外探索,和所處的世界連結。
儘管還是處在中年變動裡,但慢慢學會了如何不偏不倚地在自己裡面。
到底,什麼是創意?任教於政大廣告系的陳文玲,一直對這個問題深深著迷。2000年《多桑與紅玫瑰》出版之後,陳文玲38歲,站在中年世界的入口,決定大膽作了一個實驗,朝著跟前半輩子徹底相反的方向走去,四處尋找創造力。
她訪問了很多人(從創意人到美髮師都有);她整理了很多文獻(從佛洛伊德到羅洛梅到內在革命);她邀請一群學者、廣告人、導演、樂手、設計師、出版人和作家來到她的課堂,跟學生們一起激盪碰撞;她飛去紐約參加「夢工作坊」,開始玩夢、玩潛意識、在印地安鼓聲中,以畫筆捕捉夢境的情緒;她也曾到加拿大溫哥華附近小島上的Havan中心,參加Ben & Jock的「自我覺察工作坊」,玩戲劇、作冥想、畫曼陀羅,藉此觸發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夢想和渴望。
陳文玲將這場追尋創造力的實驗比喻成一趟旅行。《越旅行越裡面》是她這六年來的旅程紀事,不只呈現學術的思索,更展現文字和創意之美,充滿了越界的樂趣、誠懇的熱情、創新的深度、勇於挑戰的實驗精神。書中不只呈現國內外許多創意名家的精闢見解,也提出作者自身的質疑和反思;不只針對創意教學提出許多建議,也現身說法示範了各種開發創意的自我訓練途徑;不只呈現創意體驗的光明和美好,更提醒讀者:創作歷程也有緩慢、孤寂、幽暗的一面,只有以熱情和努力突破層層關卡,才可享受甜美的創作成果。書中還收錄了許多手繪曼陀羅及紙牌的彩色圖片,可以激發讀友的創作意願及動力。
經過這趟長達六年的旅程,陳文玲發現,創意的武功秘笈並不在遠方,最大的創意寶庫早就藏在每個人身上,唯有找到自己,通過內心的束縛與障礙,創意和熱情才可能源源湧現,只要勇於傾聽內心的夢想和欲望,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取之不竭的創意之泉。
呂旭亞、吳思華、吳靜吉、孫大偉、徐重仁、張娟芬、詹宏志、鍾蔚文、鍾適芳、鄭以萍、David龔 熱烈推薦
作者簡介
陳文玲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研究員、教育部創造力創意中程計畫〈四季找阿寶〉、〈左邊口袋〉負責人。天秤座,太陽在台北,月亮在花蓮。
她說:「我喜歡教書,在政大廣告系開一些實驗性創意課,例如『夢、陰影與寫作』、『創意體驗與實踐』;我也喜歡旅行,這些年來,越往外走,就越往自己裡面去;途中的光線、溫度、氣味和顏色一點一點流進來,經過時間蒸餾,變成音樂、文字和影像流出去,例如〈這些日子以來〉(點將唱片)、〈當客人離開的時候〉(飛碟唱片)、《多桑與紅玫瑰》(大塊文化)、《越旅行越裡面》和《找阿寶,玩創意》(心靈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