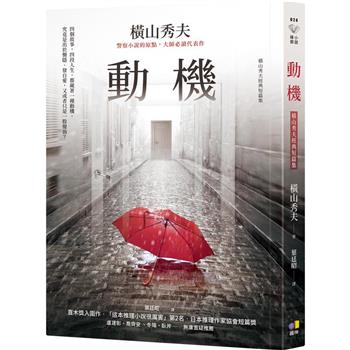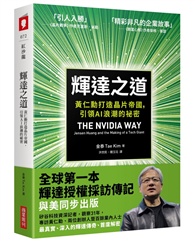圖書名稱:甜與權力
對糖的需求,揭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序幕;
對甜的渴望,勾勒出國際政治的權力網絡──
一粒微小的「糖」,如何串聯起國際貿易體系;
揭露奴役勞工的帝國史;
根本形塑了大眾的消費與飲食習慣?
──飲食人類學之父.西敏司畢生壓卷之作──
「我希望能藉由糖,讓讀者看見更廣闊的世界,解釋其如何長久且持續地改變了人類、社會與物質之間的關係。」──西敏司
曾幾何時,「哪裡有糖,哪裡就有奴隸」,糖甚至是貴族表徵身分、地位的奢侈品,但如今糖卻隨手可得、有些人更食糖過量。而此種「庶民化」轉變,其實是近代世界經濟體系與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
.英國殖民體制如何生產和消費蔗糖,並揭示了何種權力結構?
.英國人對糖的熱愛,是否因此傷害了英國菜,使其成為「黑暗料理之王」?
.糖與現代資本主義的關係為何?
.為何婚宴、特殊節慶上會食用甜食?
.是什麼力量,讓原為奢侈品的糖,成為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人們如何養成固定攝取,且依賴大量甜味的習慣?
.食物是如何體現國家統治者的意願和利益?
.為什麼對糖的需求量會成長得如此劇烈且持續數世紀之久?
.為什麼甜味是人人都渴望的味道?
☆政治經濟學x物質文化研究的不世傑作,首度正式授權繁體中文版
被譽為「飲食人類學之父」、曾獲頒美國人類學協會最高獎項「法蘭茲.鮑亞士獎」(Franz Boas Award)的西敏司,在《甜與權力》中,以自身扎實的田野經驗出發,從糖的角度切入,梳理蔗糖產業如何推動全球經濟體系的發展──一粒微小的糖,背後歷經了土地掠奪、奴隸化生產、加工和全球化商品運銷等過程,更與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結構和運作密切相關。
一杯英式下午茶中的一小匙糖,
是奴役勞工的帝國擴張標誌;
更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推手,
恆久改變了你我所處世界的政經發展。
作為飲食與文化研究的領軍人物,西敏司以突破性的視野,對微小的「糖」進行歷史探索,不僅探討糖的生產與消費間的權力關係;揭示苛使奴隸的殖民侵略史;追溯社會如何賦予糖意義和象徵內涵──從糖的生產者、消費者、生產地區、消費地區到糖本身,無一不全,其兼具開放視野與細膩觀察、既微觀又宏觀地呈現糖的權力演進,實為具里程碑意義的不朽鉅作。
作者簡介
西敏司(Sidney W. Mintz,1922-2015)
美國知名人類學家,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耶魯大學人類學系,獲頒多項人類學教育和研究獎項,被譽為「飲食人類學之父」。其著作包含:《甘蔗地裡的工人》、《飲食人類學:漫話餐桌上的權力和影響力》、《甜與權力》等,其中《甜與權力》更被讚許為「民族誌的政治經濟學」經典。
譯者簡介
李祐寧
畢業於政治大學新聞系,旅居海外,目前從事專職翻譯工作。譯作包含《行為投資金律》、《自私的藝術》、《波克夏大學》、《金融投機史》、《華爾街孤狼巴魯克》、《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跳痛的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