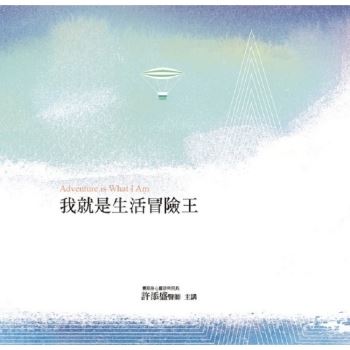自序:母親的兩幅畫像──寫在《媽媽鐘》重排新版之前/保真
那天我去探望爸爸,如往常一樣,講了沒兩句話,爸爸的話又是驢頭不對馬嘴了。我打斷爸爸的話,說:「爸爸,你又開始胡言亂語了。」平常如果爸爸精神好,這時會和我辯上幾句,可是今天精神有點萎靡,聽了我的話一愣,轉頭閉眼不語。我喊了幾聲「爸爸」都沒回應。突然,我靈光一閃,大聲說:「爸爸,你記不記得民國三十六年在南京,你給媽媽畫了一幅像,還記得嗎?」爸爸緊閉雙眼,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我本來是蹲著的,站起來說:「爸爸,我去拿畫像,別睡著囉!」
我興沖沖跑出去,爸爸的一位病友在外面曬太陽,向我打招呼:「怎麼?要回去啦?」我沒有心情和他寒喧,邊搖手邊跑向汽車,開門拿出那兩幅新裝框的畫像。回去路上碰見護士小姐,她盯著我手中的畫框說:
「好漂亮!是誰呀?」
「我媽媽年輕的時候,漂亮吧?」
我把兩幅畫拿到爸爸坐著的輪椅面前,輕輕搖動他乾癟瘦削的身軀,一邊呼喚爸爸爸爸……好不容易他張開了眼睛,不耐煩地問:「什麼?」
「爸爸你看,這幅畫是不是你畫的?」
爸爸的眼睛終於與畫像對焦,他凝神端視。這是一幅鉛筆素描的半身人像,畫紙已經泛黃泛黑,破了一小塊。翠華堂的老闆細心修補,加了一紙白框托襯,外圍是黑色木框。「三十六年於南京」,算算已經將近六十年了。畫中的媽媽還是美少女,剛結婚,一頭濃密長髮飄散在兩肩,臉上是甜美露齒的笑容。
「爸爸,這幅畫裡的人是誰?」
「媽媽!」
我好高興,為爸爸拍拍手。這回爸爸沒有跟著一起拍手,反而從輪椅上伸過手來拿畫框。我扳著他僵硬卻有力的手掌,費了一番力氣才把畫框放在他不聽使喚的雙手中。爸爸握著畫框,開始雙手輕輕搖晃。
我接著從他手裡勉強拿下畫框,再把另一個同樣尺寸的畫框放進他手中,請爸爸再看這一幅畫像。也是媽媽畫像,但是畫中人物是一位少婦的臉孔了,側臉微笑,嘴唇閉住了。同樣是鉛筆素描,沒有前一張那麼細膩,但是媽媽的神韻全在畫像上。泛黃泛黑的畫紙上署名日期是民國五十一年,也有四十五年歷史了。那是爸媽來台灣之後,剛上初中的大哥為媽媽畫的半身人像。大哥小時候逞強,爸爸十八歲時在北京畫了一張埃及豔后水彩畫像,大哥硬要在十八歲時也畫一張;爸爸在南京給媽媽畫了一幅像,大哥也在台南為媽媽畫像。
「爸爸,認得這張畫嗎?大哥畫的。」
爸爸眼神有點困惑,盯著畫像半餉,搖搖頭。我接著問這張畫像不像媽媽?回答是「不像」。我再把民國三十六年的媽媽畫像拿過來,問爸爸可記得自己怎麼稱呼媽媽?爸爸皺眉思索,我提示:「二──」,爸爸很快回答:「二妹」。太好了,標準答案,拍拍手。接著再問媽媽的名字呢,提示後也答對了!「好能幹!」走過旁邊的護士小姐也說。其他病友也微笑看著我們父子。
「爸爸,現在你還能畫畫嗎?」
「能!怎麼不能?」
「真的?你不是吹牛呀?」
「這點……事……還要吹……吹……」
爸爸口吃了,很吃力地想講出下面的話。我替他接上話:「吹牛,你是不是在吹牛?」爸爸也高興了,點著頭一口氣流利地說:「這點事還需要吹牛呀?」講得好流暢。那一刻,我看見爸爸的臉上雖然滿是皺紋和老人斑,眉宇間卻浮現了往昔一般驕傲自得的神情。我的爸爸回來了。既然精神好,多做幾題問答題練習記憶吧!
「爸爸,你想媽媽嗎?想二妹嗎?」
「想!」回答堅定有力,還配合著點頭動作。
爸爸想念的是哪一個媽媽呢?民國三十六年南京的新娘?民國五十一年南台灣鳳凰樹下育有兩子的少婦?還是此刻與自己同樣垂垂老病纏身的媽媽?
幾年前,我的母親告訴我一段故事,我幾乎總是在通識課堂上轉述給學生聽。那時媽媽的身體還好,可以自己搭公車,有一天她一個人在公車上起身要下車,車輛晃動,她怕摔倒,握著欄杆移動的步伐慢了點,大概擋住後面同樣要下車的乘客。一位穿著制服背著書包的女學生不耐煩地說:「快點啦!老太婆,這麼慢!」
媽媽轉身微笑對她說:「有一天,你的母親會老,你自己也會老」。
我的母親講出何等富有哲理的話呀!北歐神話裡有一個其貌不揚彎腰駝背的老太婆緩步走上摔角擂台,挑戰已經百戰百勝的大力士。全場一片哄笑嘲罵聲中,大力士硬是使出吃奶的力氣也無法撼動枯瘦的老婦。最後,筋疲力竭認輸的大力士伏地求問老婦姓名。
「時間。」老婦人簡短回答。
這世界原來沒有不老仙丹,更沒有萬壽無疆,沒有一個人可能扭轉時間。「世間何物催人老,半是雞聲半馬蹄」,其實雞聲與馬蹄何嘗催人老去,只是我們的青春我們的容顏,在勞苦愁煩中不知不覺地衰退消逝,留下的只有驚懼懊悔與萬千感慨,青春露也不能抗拒歲月的無情鑿痕。那天一位朋友執著要來探視我的母親,我陪她來到家裡,門開處她看見母親迎接的身形,不禁脫口而出:「小民阿姨,你好瘦呀!」是的,我也擁抱過母親,她的身軀好小好瘦好輕,抱在懷裡感受的是瘦弱身軀止不住的顫抖。民國三十六年南京的母親、民國五十一年台南的母親,還有那位曾經在我高中時期搖我起床讀書的慈母,最後是眼前的母親,竟然是同一個人呀。聖經說『聖靈用說不出的歎息為你們祈禱』,如今我也學會了祈禱,因為此情此景也只有一聲無奈的嘆息呀。宇宙的天籟是否也只是上主的一聲嘆息呢?
我從台中回到台北家裡,弟弟還在上班未歸,媽媽已經累了要睡了,我獨自在客廳看電視。聽見臥房傳來腳步聲,剛上床的母親下床上廁所,走到客廳來說她要吃安眠藥。吃過藥後我扶她回到床上、抴好被子。媽媽叫我看床邊小櫃上的一張紙,原來是我去年某次出國前傳真給她的飛機航班行程表。媽媽說;「你出國的時候,我躺在床上拿著這張紙流淚,一邊哭一邊喊你的名字。」母親是怕自己萬一發生事故,我在國外趕不回來見她最後一面呀。逆旅中的雞聲馬蹄,原來不只催老了旅人,還有那在家中病榻上日夜惦念遊子的母親。
親愛的讀者:我的父親喜樂先生與母親小民女士都老了、病了。他們的生命宛如風中殘燭,子女能做的只是雙手呵護那將殘的火燄,不被肆虐的狂風撲滅。即使如此,蠟液也已橫流,所剩無多。我的淚水也曾宛如眼前的殘燭,止不住它的點點滴落。啊!我的上主!生命是什麼?人生是什麼?
自序:不停擺的「媽媽鐘」/小民
清明已過,四月的冷雨仍不停的落著。寶島臺灣已是暮春時節,氣候仍然溼冷如冬。
早晨起床,忍不住掛電話到臺中,叮嚀保真別忘了穿件夾克。這麼大的兒子,已經結婚成家了,還勞駕老媽瞎操心嗎?說的也是,我幹嘛不自求安寧,人家做媽的不都在兒女長大了,放下重擔,任他們兒孫自有兒孫福去。我幹嘛還在為孩子愁風愁雨,怕他著涼感冒生病哪?
唉!不是我有福不會享,而是昨天媳婦在電話中向我訴苦。說的就是已經為人師表的兒子,從不懂看天氣添加衣服。不懂又不肯聽太太勸,感冒咳嗽了,害她跟著煩惱!
這種情形,我能不管嗎?其他如孩子熬夜,仗著年輕不知道保養身體,不注重飲食衛生,不會培養人際關係、為前途努力等等,做媽媽的哪一樣不關心掛念呢?所以「母親」的工作永不退休,「母親」的行業永不淘汰,「母親」的角色也永遠不落伍。而且,每位有榮幸做「母親」的女人,自然會變成多功能的「媽媽鐘」。
《媽媽鐘》是我一本散文集書名,已經出版近二十年了,仍然有許多讀者朋友提到這本書。是因為每個孩子,或孩子的母親,無不領會「媽媽鐘」三個字的涵意。記得這本小書初問世,曾經為道聲出版社爭來讚嘆歡喜,造成新書未上市,即被搶購一空的奇蹟。我想起,封面印著紫羅蘭小花兒的新書,陳列在道聲門市部櫥窗,那種滿足與欣喜,只能衷心感謝上帝了!
《媽媽鐘》出版近二十年期間,曾三次更換封面,印行達十萬冊。而當初為鼓勵面臨大學聯考壓力、焦灼不安的那個孩子寫的《媽媽鐘》,這本小書已陪著我三個孩子,度過成長及一道道升學考試難關而長大成人。《媽媽鐘》文中的那個孩子,且已學成回國,到母校任教了!做為一個平凡的母親,我覺得已竭盡所能,不負生命主的交託,做了一個盡職的「媽媽鐘」!
如今因道聲出版社自主持者──散文作家殷穎牧師退休,業務方向改變,去年已將《媽媽鐘》版權交還作者。承蒙文甫兄不棄,重新排印此書;感謝年輕的朋友素芳費心,為此書調整內容去蕪存菁,補進同一時代較整齊的作品,並改頭換面以全新姿態呈獻給讀者面前。此時,我特別懷念為曾此書寫序的趙滋蕃兄,及為原書名題字的張大千老伯──他倆雖已離開世間,但我的感念是永不止息的!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媽媽鐘(新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58 |
文學 |
$ 176 |
中文書 |
$ 176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媽媽鐘(新版)
【本書特點】
★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增訂改版,是母親節最窩心的禮物書。
【推薦得獎】
★2007-04-03 華文獎項 >> 好書大家讀 >> 2006年「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
★2006-09-11 華文獎項 >> 好書大家讀 >> 《媽媽鐘》入選第50梯次「非故事文學組-散文創作」
《媽媽鐘》書寫對兒女家人的親情,分三大輯,31篇散文。文字流暢,深情感人。
小民寫《媽媽鐘》有真誠有期盼,覺得無論世事如何艱難,母親永遠在孩子的身邊。自稱只會寫真實的事情,小民與她的散文,構築了一整個世界的晴空朗照,以一個母親的無私和基督徒的純潔,溫暖著每一個富於感知的不同時代讀者的心靈。
書後附有逢甲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瑞芬評小民散文一文及小民寫作年表。
作者簡介:
小民
1929年~2007年01月20日/ 台灣
小民,本名劉長民,北平市人,家庭主婦。作品溫和親切,著有散文集《媽媽鐘》、《紫色的書簡》、《全家福》等十餘種。並帶動全家寫文章,出版合集《紫色的家》等書。並主編以愛為主題的六書,深獲各方好評。
章節試閱
自序:母親的兩幅畫像──寫在《媽媽鐘》重排新版之前/保真
那天我去探望爸爸,如往常一樣,講了沒兩句話,爸爸的話又是驢頭不對馬嘴了。我打斷爸爸的話,說:「爸爸,你又開始胡言亂語了。」平常如果爸爸精神好,這時會和我辯上幾句,可是今天精神有點萎靡,聽了我的話一愣,轉頭閉眼不語。我喊了幾聲「爸爸」都沒回應。突然,我靈光一閃,大聲說:「爸爸,你記不記得民國三十六年在南京,你給媽媽畫了一幅像,還記得嗎?」爸爸緊閉雙眼,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我本來是蹲著的,站起來說:「爸爸,我去拿畫像,別睡著囉!」
我興沖沖跑...
那天我去探望爸爸,如往常一樣,講了沒兩句話,爸爸的話又是驢頭不對馬嘴了。我打斷爸爸的話,說:「爸爸,你又開始胡言亂語了。」平常如果爸爸精神好,這時會和我辯上幾句,可是今天精神有點萎靡,聽了我的話一愣,轉頭閉眼不語。我喊了幾聲「爸爸」都沒回應。突然,我靈光一閃,大聲說:「爸爸,你記不記得民國三十六年在南京,你給媽媽畫了一幅像,還記得嗎?」爸爸緊閉雙眼,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我本來是蹲著的,站起來說:「爸爸,我去拿畫像,別睡著囉!」
我興沖沖跑...
»看全部
目錄
母親的兩幅畫像/保真 003
不停擺的「媽媽鐘」(自序) 008
卷一 親情記真
孩子的世界 015
無心佳兒 018
媽媽鐘 022
母親的聖經 028
學做好母親 031
真兒心語 034
把孩子當朋友 038
太太鐘 042
念大姊 047
母親多喜悅 053
風箱樂隊 055
一隻紅襪子 064
卷二 閒情記趣
茶情 073
紫丁香 076
糖三角 078
一箱清涼 081
明鏡 084
醫牙記趣 089
迷你書架 098
卷三 至情記感
面對苦難的笑臉 105
麻醉醫師 111
我的朋友白彼德 120
快樂的音符 128
紫色的夢 132
芳鄰難忘 139
母親的繡花鞋 150
愛的祝福 155
...
不停擺的「媽媽鐘」(自序) 008
卷一 親情記真
孩子的世界 015
無心佳兒 018
媽媽鐘 022
母親的聖經 028
學做好母親 031
真兒心語 034
把孩子當朋友 038
太太鐘 042
念大姊 047
母親多喜悅 053
風箱樂隊 055
一隻紅襪子 064
卷二 閒情記趣
茶情 073
紫丁香 076
糖三角 078
一箱清涼 081
明鏡 084
醫牙記趣 089
迷你書架 098
卷三 至情記感
面對苦難的笑臉 105
麻醉醫師 111
我的朋友白彼德 120
快樂的音符 128
紫色的夢 132
芳鄰難忘 139
母親的繡花鞋 150
愛的祝福 155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小民
- 出版社: 健行 出版日期:2006-05-10 ISBN/ISSN:9867753836
- 頁數:20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