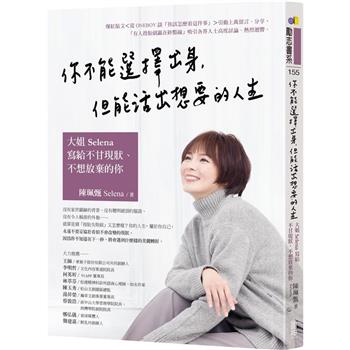第一章 英雄之死
來參加「蹦蹦」葬禮的有一千多人,其中很多是郊區和黃金海岸來的小球迷;還有幾位來自破敗的芝加哥南區——蹦蹦當年就是在這裡學會滑冰和打架的。他是黑鷹曲棍球隊的邊鋒,三年前玩滑翔翼不慎摔碎左腳踝,才被迫退休。葛瑞茨基入隊之前,蹦蹦是隊上自赫爾以來最了不起的英雄。
蹦蹦不相信自己不能再滑冰了,他左腳踝動了三次刀,第三次醫生都不想幫他,但蹦蹦還是堅持,直到第四次所有醫生都拒絕,他才放棄。離開球隊之後,他換了不少工作,雖然很多人都願意花錢僱用他吸引顧客,招徠生意。但蹦蹦這個人就是這樣,認真得很,做什麼都全力以赴,不願意拿錢不做事。
他最後一份工作是在尤多拉穀物公司,他父親也在這家公司待過,在一九三○、四○年代擔任碼頭工人。發現蹦蹦屍體的,就是尤多拉芝加哥分公司的副總裁菲利普,他上週二發現蹦蹦浮在碼頭邊。菲利普立刻打電話給我,因為蹦蹦在員工資料親屬欄上填了我的名字。然而,當時我不在城裡,到佩歐里亞辦案待了三個星期,等警方聯絡到我,蹦蹦那一大群姑姑裡早就有人認完屍,開始安排盛大的波蘭傳統葬禮了。
蹦蹦是我叔叔的兒子,和我一起在南芝加哥長大。那時我們年紀都小,感情比其他兄弟姊妹還親。嬸嬸瑪麗是善良的羅馬天主教徒,印象中她不停生孩子,結果在第十二胎的時候難產過世了。蹦蹦是她第四胎,也是唯一活過三天的孩子。
蹦蹦從小就玩曲棍球,我不曉得他是怎麼迷上這項運動,又從哪學會那些技巧的。瑪麗嬸嬸覺得曲棍球很危險,反對得很激烈,因此,蹦蹦小時候成天都在想辦法騙過他媽出去玩球。通常他都拿我當藉口——因為我家離他家只有六條街遠,而到堂姊家玩這個理由,往往能換來幾小時珍貴的玩球時間。那時候只要是迷曲棍球的小孩子,都很崇拜「蹦蹦」喬飛龍。我這堂弟更是照樣模仿喬飛龍的強攻猛打。於是,其他小孩開始叫他「蹦蹦」,這個綽號從此便一直跟著他。事實上,芝加哥警方打電話到佩歐里亞的旅館給我,問我是不是柏納德•華沙斯基的堂姊,我還愣了幾秒鐘才知道他們說的是誰。
這會兒,我坐在聖溫瑟萊斯教堂的前排長椅上,跟蹦蹦那些淚眼汪汪、長得都一個樣的姑姨表親戚坐在一塊兒。他們全都穿得一身黑,我的深藍色羊毛套裝顯然把他們惹毛了,有幾個還特地在演奏聖樂序曲的時候,湊近我的耳邊大聲告訴我。
我望著教堂裡仿玻璃藝術家提凡尼風格的窗戶,窗上用俗艷的顏色,描繪聖溫瑟萊斯的生平事跡、耶穌釘十字架和迦拿的婚禮。我想,設計師肯定是中國透視法和擬立體主義大師:罐裡的水從人頭上冒出來,十字架後面長出長長的手臂,感覺很恐怖。確定哪隻手是哪個人的,搞清楚誰在做什麼,讓我在葬禮上根本忙不過來,感覺應該(我希望啦)非常虔誠才對。
我父母親都不是虔誠的教徒。我媽是義大利人,有一半猶太血統;我爸是波蘭人,家族裡出了一堆懷疑主義者。雖然每年普珥節我媽都會烤義大利麵給我,但他們決定不要強加任何信仰在我身上。因此,我小時候發現蹦蹦他媽的宗教狂熱,和他家的廉價塑膠聖像,都覺得很恐怖。
要是由我選擇葬禮形式,我會希望在多教派教堂裡辦,安靜一點,最好讓蹦蹦的前隊友上台簡單講幾句話——他們確實提過,但卻被蹦蹦的姑姨們回絕了。我絕對不會選在老家的破教堂舉行葬禮,整座教堂只有一位修士,從來沒見過蹦蹦,現在卻在台上說一堆虛情假意、讓人作嘔的蠢話。
然而,我終究沒有插手葬禮的事,讓那些姑姨們全權處理。堂弟指名我做他的遺囑執行人,肯定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我知道,他對自己怎麼下葬一點興趣也沒有。不過,婚喪喜慶卻是姑姨們生活中僅有的小小娛樂。她們硬是要大夥兒花上幾小時參加完整的死者彌撒,之後還得拖著冗長的隊伍,一路送葬到很遠的南邊。
葬禮過後,一身制服盛裝的副警長巴比•馬羅瑞擠過人群,走到我面前。這時,我正想去找蹦蹦的阿姨海倫(還是莎拉?),度過一個俄羅斯小菜(piroshkis)和肉丸子吃不完的下午。巴比過來找我,我很高興:他是父親在芝加哥警局的老朋友,也是過去街坊鄰居裡頭我唯一想見的人。
「維維,蹦蹦發生不幸,我真的很難過,我知道你們倆有多親。」
所有人裡頭,我只准巴比叫我維維。「謝了,巴比,真的很不好受,很高興你來了。」
四月的寒風吹亂了我的頭髮,雖然穿著羊毛套裝,我還是忍不住打了個冷顫。早知道就穿外套來。巴比陪我走到豪華禮車旁邊,車裡坐了蹦蹦家五十三個親戚。這場葬禮辦下來可能花掉快五十萬,但我懶得去想。
「你會去參加晚宴嗎?我可以搭你的便車嗎?這麼多人,我不在他們也不會發現。」
巴比好心地答應了,帶我到他調來的警車,讓我坐在後座,同時跟我介紹駕駛:「維維,這位是庫斯柏警官,他也是蹦蹦的球迷。」
「小姐,沒錯,我真的很難過,蹦蹦……抱歉,您堂弟不能打球,真是可惜。我敢說,他要打破葛瑞茨基的紀錄,是輕而易舉。」
「叫他蹦蹦沒關係,」我說:「他喜歡這個綽號,而且大家都這麼叫他……巴比,我打電話給穀物公司的人,卻得不到什麼消息,蹦蹦是怎麼死的?」
巴比神情嚴肅地看著我,說:「維維,妳真的想知道嗎?我知道妳覺得自己夠堅強,但我覺得,妳還是記得蹦蹦在曲棍球場上的樣子就好。」
我抿著嘴,我不想在蹦蹦葬禮上發脾氣。「巴比,我沒有嗜血癖,我只是想知道我堂弟出了什麼事。他是運動員,我實在很難想像他會滑倒摔進水裡。」
巴比表情和緩下來,說:「妳不相信他是自己溺死的,對吧?」
我猶豫不決地搓著手,說:「他在我的答錄機裡留了個緊急留言——但是我出城去了,我不曉得他是不是有什麼要緊事。」
巴比搖搖頭,說:「妳堂弟不是會把自己搞到死在船底下的人,妳知道,我知道。」 這會兒我可不想聽人說教,講什麼自殺是懦弱的行為之類的道理。「所以,事情就是這樣嗎?」
「穀物公司沒跟妳說,自然有他們的考量。但妳沒辦法接受,對吧?」他說完嘆口氣:
「要是我不告訴妳,妳可能會把頭伸到船底下自己去看。出事的時候,有艘船停在碼頭邊,蹦蹦掉下去,卡在螺旋槳裡,船一開,蹦蹦就被絞爛了。」
「原來如此。」說完,我轉頭望著艾森豪高速公路,和路兩旁沒有上漆的房子。
「維維,那天很潮溼,碼頭又老舊又是木頭做的,一下雨就非常滑。法醫的驗屍報告是我親自讀的,我想他是滑倒摔下去,應該不是自己跳下去的。」
我頷首,同時拍拍他的頭。蹦蹦視曲棍球如命,被迫退休讓他很難接受。巴比說得對,我堂弟不會臨陣脫逃,但過去這一年他確實像是行屍走肉。問題是,他真的那麼難過,難過到摔進螺旋槳底下?
車子開到莊園裡整齊的磚房前面,我試著把這個想法拋開。海倫阿姨就住在這裡,當年她跟著一群南芝加哥的波蘭佬到艾默伍公園定居。我想她有丈夫,應該是鋼鐵工人吧,但就像瓦齊克家族裡的其他男人一樣,丈夫有名無實。
庫斯柏警官讓我們在大門下車,再把車開去停。那裡已經停了一長排豪華的凱迪拉克。巴比陪我走到門口,但他一下就消失在人群裡,看不見了。
接下來兩小時,對我搖搖欲墜的神經簡直是場可怕的夢魘。不斷有親戚說,可憐的瑪麗這麼討厭曲棍球,柏納德還是照打不誤,真是可惜。還有人說,我不應該和狄克離婚,沒有家人可讓我忙——你瞧雪柔、瑪莎和貝蒂家的寶寶。房子裡到處都是小孩——瓦齊克家族個個都是驚人地會生。
蹦蹦的婚姻只維持了三週,的確可惜——然而,這麼說起來,他連曲棍球都不應該打。重點是,他為什麼要到尤多拉穀物公司上班?蹦蹦的父親吸穀渣吸了一輩子,他就是這樣死的。不過,話說回來,華沙斯基家的人本來就沒什麼活力。
小房子裡煙味瀰漫,還有濃濃的波蘭菜味,和小孩的尖叫聲。我從某位阿姨身邊擠過,她要我去廚房幫忙洗碗,因為我沒有做菜。來之前,我就跟自己說,晚飯除了「是」、「不是」和「不知道」,絕對不說第二句話,但現在看來是越來越難了。
這時,高齡八十二、臃腫、穿得一身亮黑的瓦齊克外婆突然像警察一樣,一把攫住我的手臂,一隻生了翳的藍眼瞅著我,滿嘴洋蔥味地對我說:「那些女孩都在談柏納德。」
不用說,「女孩」就是那群阿姨。
「她們說他在升降機那裡惹了麻煩,說他自己跳進船底下,免得被逮捕。」 「是誰告訴您的?」我追問。
「海倫哪,還有莎拉。雪柔說彼得說柏納德趁沒人注意,自己跳下去的,瓦齊克家的人絕對不會自殺,但華沙斯基家的人嘛……那些猶太人喔,我早就警告瑪麗很多次了。」
我扳開蹦蹦外婆的手指,煙味、噪音和酸包心菜的味道脹得我腦袋發疼,我低頭看著外婆的雙眼,開始說些魯莽的話,但很快就心軟了。於是,我奮力穿越重重煙霧,每走幾步就踢到小寶寶,而男人們這會兒正圍著一張桌子大吃大喝,桌角擺滿了香腸和德國酸菜。這些男人要是腦袋裡的東西和肚子裡一樣多,美國早就得救了。
「是你說蹦蹦自己跳到碼頭下的?你都跟誰說了?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雪柔的先生彼得用一雙愚蠢的藍眼望著我,說:「嘿,維兒,別激動,這話是我從碼頭那兒聽來的。」
他把啤酒杯換到另一隻手,又說:「不過就是聊聊嘛,維兒。蹦蹦和老闆處不好,有人說他偷了文件。可是我不相信。蹦蹦哪需要偷東西啊?!」
我眼前一陣模糊,感覺頭很暈:「該死的你,那根本是胡說八道!蹦蹦這輩子從來不做齷齪事,就算沒錢也一樣。」
旁邊的人不安地看著我。其中一位說:「放輕鬆點,維兒,我們都很喜歡蹦蹦。彼得也說了,他不相信傳言。所以,別抓狂。」
他說得沒錯。我現在是幹嘛,在喪禮上鬧事?於是,我像剛上岸的落水狗甩甩頭,重新擠過人群回到客廳,打開掛著聖母瑪利亞血心徽章的雅致前門,走進沁人的四月天。
我拉開外套,讓涼風吹透我全身,滌清我的思緒。我很想回家,但車留在芝加哥北區的公寓,於是我環顧街道,果然如我所料,巴比和庫斯柏早就不見蹤影了。正當我猶豫地四下張望,心想該叫計程車,還是踩著高跟鞋走路到火車站的時候,身邊突然出現一個年輕女人。個子很小,看起來乾乾淨淨,暗色的頭髮和耳根齊平,一雙蜜棕色的眼睛。她穿著淺灰色的山東綢套裝上衣、長裙和大珠母鈕釦短外套,看起來優雅、完美,而且有點眼熟。
「無論蹦蹦這會兒人在哪兒,我敢打賭都比那裡好。」她邊說邊朝海倫家撇撇頭,同時嘲諷地微微一笑。 「沒錯。」 「妳是他堂姊,對吧?!我是佩姬•卡林頓。」 「我就覺得妳眼熟。我看過妳幾次,不過都是在舞台上。」卡林頓小姐是舞蹈家,曾經跟風城芭蕾舞團合作,編了一齣單人喜劇表演。
她露出觀眾最愛的招牌微笑,說:「這幾個月,我和妳堂弟經常碰面,但都沒有聲張,因為我們倆不想讓賀古斯和葛蕾塔在八卦專欄大作文章——妳堂弟雖然不打球了,還是經常上報。」
的確,我老是在報上讀到堂弟的名字。有個跟你很親的名人,其實滿好玩的。你會經常聽到他的消息,但你聽到、讀到的永遠跟你認識的那個人不一樣。
「我想,蹦蹦最喜歡的人就是妳了。」說著,她皺皺眉頭,思考自己所說的話。她連皺眉都很完美,感覺就是一副專注沉思的模樣。說完,她微笑,彷彿有什麼心事。「我想我們應該是相愛的吧,但我不確定。現在再也沒有機會確定了。」
我咕噥了幾句安慰人的話。
「我很想見妳,蹦蹦老是談到妳。他真的很愛妳。可惜他一直沒有介紹我們認識。」 「是啊,我已經好幾個月沒見到他了……妳要開車回市區嗎?我可以搭便車嗎?我跟著
一群人過來這裡,把車留在北區了。」
她撩起外套的白色絲織袖口,看了看錶,說:「我得在一小時內趕去排練,讓妳在市區下車可以嗎?」
「太好了!我覺得自己好像荒郊野外走失的兔子,想回到荊棘窩去。」 她聽得笑了。「我懂,我懂。我是在布拉夫湖區長大的,但是現在每次回去,都覺得快窒息了。」
我回頭看看房子,心裡想是不是應該回去跟他們道別。有禮貌的話就該這麼做,但我可不想浪費十五分鐘聽人說教,告訴我應該好好清理碗盤和我的人生。於是,我聳聳肩膀,跟著佩姬•卡林頓沿著街走。
她開的是銀色的奧迪五千。要嘛風城芭蕾舞團付的酬勞比其他搖搖欲墜的劇團好,要嘛就是她在布拉夫湖區的家人供給她錢,讓她買得起山東綢套裝和進口跑車。
佩姬開起車來就跟跳舞一樣,帶著迅速、精確的優雅。我們對這一帶都不熟,而且四周房子看起來都一模一樣,因此她轉錯幾次彎之後,才找到往艾森豪高速公路的交流道。
回城的路上,她話不多,我也很沉默,想念堂弟,心裡很沮喪——而且很歉疚。這時我總算明白,剛才為什麼會對那群臃腫愚蠢的表親大發雷霆。我沒有照顧好蹦蹦。我明明知道他心情低落,卻沒跟他保持聯絡。早知道應該在答錄機裡留下佩歐里亞旅館的電話才對。是因為厭倦絕望了嗎?說不定他覺得愛情能夠救他,結果卻沒有辦法?還是就像碼頭邊的傳言,他真的偷了文件——他覺得我能幫得上忙,就像過去成千上萬次一樣,然而,我卻不在。
蹦蹦一死,我就再也沒有家人了。沒錯,我母親那邊是還有一位阿姨住在梅洛斯公園,但是我根本不算見過她,她和她自以為是的胖兒子對我來說,根本不算親戚。蹦蹦和我一起玩耍、幹架、保護對方。雖然這十年來我們聚少離多,但有困難的時候總是互相幫忙。然而,這回我卻沒有幫到他。
車開到九十號和九十四號州際公路交叉口,雨點開始落在擋風玻璃上,打進我徒勞的思緒裡。我發現佩姬意味深長地瞥了我一眼,便轉頭揚眉看著她。
「妳負責執行蹦蹦的遺囑,對吧?」
我點頭,她手指在方向盤上打拍子,說:「蹦蹦和我——一直都沒有互換鑰匙,」說完,難為情地對我微微一笑:「我想到他那裡,把我的東西拿回來。」
「沒問題,我打算明天下午到他家,簡單地看看相關文件。兩點在他家碰面,可以嗎?」 「謝謝,妳人真好……我可以叫妳維兒嗎?蹦蹦老提到妳,我都覺得認識妳了。」
車開到郵局底下,地下六線道,她心滿意足地點點頭,說:「還有,請叫我佩姬就好。」說著她變換車道,繞過垃圾車,在瓦巴西街左轉。她讓我在我辦公室下車——華貝許街和門羅街交叉口的普特尼大樓。
這時,電車從我們頭上呼嘯而過,我試著壓過噪音朝她喊道:「bye bye,明天兩點見。」
第二章 愛的徒勞
黑鷹隊花了一大筆錢找蹦蹦打球,其中不少被他拿來買下切斯納街北邊湖岸路閃亮玻璃大樓的公寓套房。他是五年前買的,因此我去過幾回,通常都會遇到一群醉醺醺但很友善的曲棍球員。
蹦蹦的律師西蒙斯給我公寓的鑰匙,還有我堂弟Jaguar跑車的鑰匙。我和他花了一個早上討論蹦蹦的遺囑。他那群姑姨知道之後,可能會更火冒三丈——堂弟把為數可觀的遺產全都捐給慈善機構和曲棍球員遺孀基金會,裡面沒提到半個姑姨。他留了一筆錢給我,但要求不能全都花在黑標威士忌上。我忍不住笑了出來,西蒙斯律師很不以為然地皺了皺眉頭,跟我說他一直阻止他的客戶加入這條但書,但華沙斯基先生非常堅持。
我們討論完,已經接近中午了。我在金融區,可以順道幫一位客戶辦點事,但我現在不想工作,手邊也沒有好玩的案子——只有幾張傳票要發。有個傢伙跟人合夥,卻捲走半數資產(包括一艘十二公尺長的私人遊艇)不見蹤影,我得把他找出來。不過,這些事都不急。於是,我把車(綠色的水星山貓)從迪爾朋堡信託大樓停車場開出來,朝黃金海岸的方向開。
蹦蹦住的大樓跟其他高級住宅一樣,有門房守著——一個矮矮胖胖的中年白人。我到的時候,他正扶一位老太太走出她的凱迪拉克轎車,沒怎麼理我,讓我一個人在那裡笨拙地試著找出開門的鑰匙。
這時,大廳裡一名女士牽著迷你獅子狗從電梯走出來,狗一身蓬蓬的白毛用藍絲帶紮得整整齊齊。女士推開大門,我往大廳裡走,同時用同情的目光瞧了獅子狗一眼。狗拴著鑲水晶的皮帶,在我身邊繞來繞去,聞我的腿。「菲菲,過來!」女士說著,把狗拉回她身邊。有錢人家的狗是不應該到處亂聞,或做出任何讓主人想到牠們是畜牲的事的。
大廳不大,只有幾棵盆栽樹、一張大窗簾和兩張米白沙發可以讓住戶坐著聊天。大樓裡同樣的窗簾到處都是:針織窗簾,通常綴滿大羊毛結,中間再加幾條長穗帶,是這類高級住宅的標準配備。我邊等電梯,邊漫不經心地研究西邊牆上這張顏色黃黃綠綠的窗簾。我暗自慶幸,自己住在破舊的三人套房,沒有像菲菲主人這樣的鄰居,決定該掛什麼窗簾。
電梯的門在我身後靜靜打開,一名和我年歲相當的女士穿著慢跑裝走了出來,後面跟著兩位要到賽克斯購物的女士,正在爭論要不要順道去沃特塔酒店吃中飯。我看了看錶:十二點四十五分。今天是星期二,她們為什麼不用工作?說不定她們跟我一樣,是私家偵探,趁著辦案空檔處理親戚的財產。我按了二十二樓,電梯迅速安靜地載我往上。
大樓有三十層,每層有四間公寓,蹦蹦花了二十五萬美元買下東北角的套房,面積只有一百四十平方公尺,三間臥室、三間浴室,主臥室旁的浴室還有一座大浴缸。公寓東邊和北邊俯瞰整片湖區,景色美極了。
我打開二十二樓之三的房門,穿過門廊走進客廳,整間客廳鋪著厚地毯,走在上面沒有半點聲音。面東的藍色印花窗簾收攏在窗邊,盡收眼底的景致(湖天連成一顆灰綠色的大球)攫住了我。我沉浸在碩大是美的感覺裡,直到心中一片祥和。我在窗前佇立良久,突然惱怒地察覺公寓裡還有別人。我不曉得自己是怎麼發現的,全神貫注幾分鐘之後,我聽見窸窣聲響,有人在翻動紙張。
我退回門廊,左右兩條走道,右邊是三間臥房和主浴室,左邊走道比較小,通往餐廳和廚房。窸窣聲是從右邊臥室那兒傳來的。
早上跟西蒙斯見面,所以我穿著套裝和高跟鞋,完全不適合應付闖空門的傢伙。於是我悄悄打開大門,預留退路,脫掉高跟鞋,將手提包放在門廊的雜誌架旁邊。
接著,我又回到客廳,拉長耳朵,同時尋找防身的武器。壁爐上有個青銅獎盃,是球隊贏得史坦利盃那年,頒給蹦蹦作為最有價值球員的。我靜靜拿起獎盃,小心翼翼地沿著走道往臥房去。
三間臥房的門都開著,我踮腳走到最近的房間,就是蹦蹦的書房,整個人貼著牆,右手攫著沉重的獎盃,頭慢慢朝門後探。
佩姬•卡林頓背對我,坐在蹦蹦桌前翻閱文件。我覺得被人耍了,心裡非常不悅,便退回門廊,把獎盃放在雜誌桌上,穿上高跟鞋,走進書房。
「妳還真早,妳是怎麼進來的?」
佩姬從椅子上彈起來,丟下手上的文件,滿臉通紅,連胸前襯衫開口的地方和髮梢下的脖子都紅通通的。「我以為妳兩點才會到。」
「維兒,別這麼氣嘛!我兩點臨時有個排演,可是我很想把信拿回來,就說服辛克利,就是門房,上來幫我開門。」那一刻,我似乎看到她蜜棕色的雙眼泛著淚光,但她很快就用手背揩去淚水,同時露出認錯的微笑。「我本來想可以在妳到之前離開。我的信非常非常私人,實在不想讓任何人看到,連妳也不例外。」說完,她哀求地伸出右手。
我瞇眼瞪了她,說:「有找到嗎?」
她聳聳肩,說:「他可能已經把信丟了吧。」說著,彎身去撿我剛剛進來時她弄得一地的文件。我跪下來幫她撿,看起來都是商務信件,裡面有幾封署名費克利。費克利是蹦蹦的經紀人。
「我只找了兩個抽屜,還有六個裡頭有文件。我猜,蹦蹦什麼東西都留——有個抽屜裡塞滿了球迷的信。」
我不以為然地審視書房,八個抽屜,裡頭全都是文件!每次做性向測驗,我的分類整理技巧永遠是最低分。
我坐在桌上,拍拍佩姬的肩膀,說:「我說啊,把文件全部翻過,實在是無聊透了。妳雖然看了一些,但我還是得重看一遍,因為我必須確定,那些文件和蹦蹦的財產有沒有關係。所以,妳何不把這份工作留給我呢?我向妳保證,寫給蹦蹦的私人信件,我一封也不會讀,我會用信封裝好交給妳。」
她對我微笑,卻不是很放心。「我可能只是白忙一場。不過,如果他連不曾謀面的球迷的信都收著,我想他應該也留著我的信。」說完,她又轉過頭去。
我抓著她的肩頭一會兒,說:「佩姬,別擔心,我相信會找到的。」
她吸了吸鼻子,動作很輕、很優雅。「我覺得我會這麼在意,是因為那些信讓我沒辦法對自己說:『對啊,他真的……走了!』」
「沒錯,所以我才會罵他是個該死的收破爛的。更慘的是,我還沒辦法找他當我的遺囑執行人,當作報復。」
佩姬聽了淺淺一笑,說:「我帶了一個手提箱來,因為我想可能要把我留在這裡的衣服和化妝品打包帶走,生活才能繼續向前看。」
說完,她便走到主臥室去收拾東西,留我一個人在書房漫無目的地東翻西摸,希望有點斬獲。佩姬說得沒錯,蹦蹦什麼東西都留著。牆上貼滿了曲棍球的相片,從他小二參加少年曲棍球隊開始,到他效力黑鷹隊的相片,球隊贏得史坦利盃,更衣室裡香檳四溢的相片,到他打出高難度球的相片,還有球星艾斯波西多、豪伊和赫爾的簽名照,連正牌「蹦蹦」喬飛龍的簽名照都有,上頭還寫著「給小巨砲」。
這一大堆相片裡,有一張特別突兀,就是我拿到芝加哥大學法律學位當天,穿著紅褐色學士袍的相片。我對著鏡頭露齒微笑,背後的陽光耀眼燦爛。堂弟他沒念過大學,對我念到大學畢業,覺得非常驕傲。我對著相片裡年輕的維艾•華沙斯基皺了皺眉,就轉身往主臥室走,看佩姬需不需要幫忙。
手提箱擺在床上,裡頭的衣服摺得整整齊齊。我走進主臥室,佩姬正在翻櫃子的抽屜,從裡頭拉出一件亮紅色的套頭衫。
「妳真的會看過他所有衣服,還有其他東西嗎?我東西都拿了,但要是妳發現什麼,請跟我說一聲。六號尺寸應該是我的,不是他的。」說完,她走進浴室,接著便聽見她打開置物櫃的聲音。
臥室很男性化,也很舒服,有家的感覺。正中間是一張特大號的單人床,上面覆著黑色和白色的羽毛被單。布料厚實的米白色落地窗簾收攏在窗邊,看得到外面的湖景。蹦蹦的曲棍球桿高掛在樸素的橡木櫃上頭,紫紅相間的畫作,像在牆上灑滿了顏色,而兩張地毯也是同樣的紅色。蹦蹦跟其他單身漢一樣,臥室裡盡量不放鏡子,以為這樣就能讓別人相信,這裡不是他一個人住。
床邊小桌上有幾本雜誌,我坐在床上,想知道堂弟睡前都看些什麼——《運動畫刊》、《曲棍世界》,還有一份印色很深的報紙,叫《穀物報》。我很好奇,想知道裡頭都是些什麼內容。它是堪薩斯市發行的,全都是有關穀物的消息和資訊——各種穀物的大小、不同的組合交換價格、鐵路和航運費率,還有各家物流公司的合約。要是穀物對你很重要,讀這份報紙絕對很有趣。
「那裡頭有什麼特別的嗎?」
我讀報讀得太專心了,絲毫沒有發現到佩姬已經走出浴室,準備結束打包了。我遲疑了一下,說:「我懷疑蹦蹦絞在螺旋槳底下,是被人害的。這個東西,」我對著她揚揚手中的報紙:「所有跟穀物和運送穀物有關的資訊,全在裡頭了。平常應該是雙週刊,收成時改成週刊,要是蹦蹦到尤多拉工作,竟然開始讀這類東西,我對自己的判斷就有點把握了。」
佩姬盯著我,拿起《穀物報》翻閱一下,邊看邊對我說:「我知道,不能打球讓他很焦慮,就像我不能跳舞一樣,我可以體會那種感覺。更何況我這個芭蕾舞者還沒有他打球那麼出色。但我覺得他和我在一起——應該有讓他好過一點。我這麼說,希望妳別介意。」 「怎麼會呢?那樣的話,我反而很高興呢。」
佩姬用眉筆畫過的細眉揚了起來,說:「那樣的話?妳可以解釋一下嗎?」
「其實沒有什麼好解釋的,佩姬。一月之後我就沒見過蹦蹦了,他那時還在對抗憂鬱,要是妳真的幫他走出來,我當然高興。葬禮上我聽說他在公司惹上麻煩,我猜應該有人在傳,說他偷了公司的文件。他有跟妳提過這方面的事嗎?」
佩姬睜大蜜棕色的雙眼,說:「沒有,完全沒有。就算有,他也應該覺得無所謂才對,否則不會隻字不提。他死前一天,我們還共進晚餐。而且,我不相信他會做這種事。」
「妳知道他想找我說什麼事嗎?」 她聽了一臉驚詫地說:「他有試著跟妳聯絡嗎?」 「他在我答錄機裡留了緊急留言,卻沒有說是什麼事。我猜,他可能在碼頭發現了什麼,需要我的專業協助。」
佩姬搖搖頭,手指玩弄著皮包的拉鍊,說:「我不知道。星期一晚上他看起來不錯。呃,我得走了,抱歉先前嚇到妳,不過我真的得走了。」
我跟著她走到門口,把門關上——我之前回去穿鞋的時候,忘了關門——順道連橫閂鎖也鎖上。我可不想讓門房再放其他人進來,完全不跟我說一聲,起碼我在公寓裡的時候不行。
在令人沮喪的文件整理工作開始之前,我匆匆巡視了堂弟的房子。他跟我不一樣,把家理得整整齊齊,讓人嘆為觀止。換成我死了一個星期,別人進我屋子,可能會發現水槽令人意想不到的噁心,到處都積了厚厚一層灰,更別說臥室裡那堆衣服和文件了。
蹦蹦的廚房根本就是整潔無瑕,冰箱裡裡外外都很乾淨。我打開冰箱檢查,把裡面壞掉的蔬菜清掉,將近八公升的牛奶倒進水槽——我猜他雖然不打球了,但還是保持喝牛奶的習慣。整齊,真是太整齊了。我常這麼跟蹦蹦說,取笑他。想起這些,讓我腹中一陣翻攪,彷彿肚子裡的空氣瞬間抽空了一樣。心愛的人死了,就是這種感覺。爸媽過世的時候,我就經歷過了。總是會有瑣事讓你想到他們不在了,而身體的痛苦得要好一陣子才會消失,不再隨著回憶出現。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奪命碼頭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英美文學 |
$ 25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奪命碼頭
第一章 英雄之死 來參加「蹦蹦」葬禮的有一千多人,其中很多是郊區和黃金海岸來的小球迷;還有幾位來自破敗的芝加哥南區——蹦蹦當年就是在這裡學會滑冰和打架的。他是黑鷹曲棍球隊的邊鋒,三年前玩滑翔翼不慎摔碎左腳踝,才被迫退休。葛瑞茨基入隊之前,蹦蹦是隊上自赫爾以來最了不起的英雄。 蹦蹦不相信自己不能再滑冰了,他左腳踝動了三次刀,第三次醫生都不想幫他,但蹦蹦還是堅持,直到第四次所有醫生都拒絕,他才放棄。離開球隊之後,他換了不少工作,雖然很多人都願意花錢僱用他吸引顧客,招徠生意。但蹦蹦這個人就是這樣,認真得...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莎拉‧派瑞斯基 譯者: 穆卓芸
- 出版社: 天培 出版日期:2006-02-10 ISBN/ISSN:9867759370
- 頁數:368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