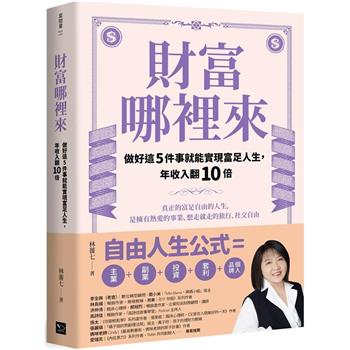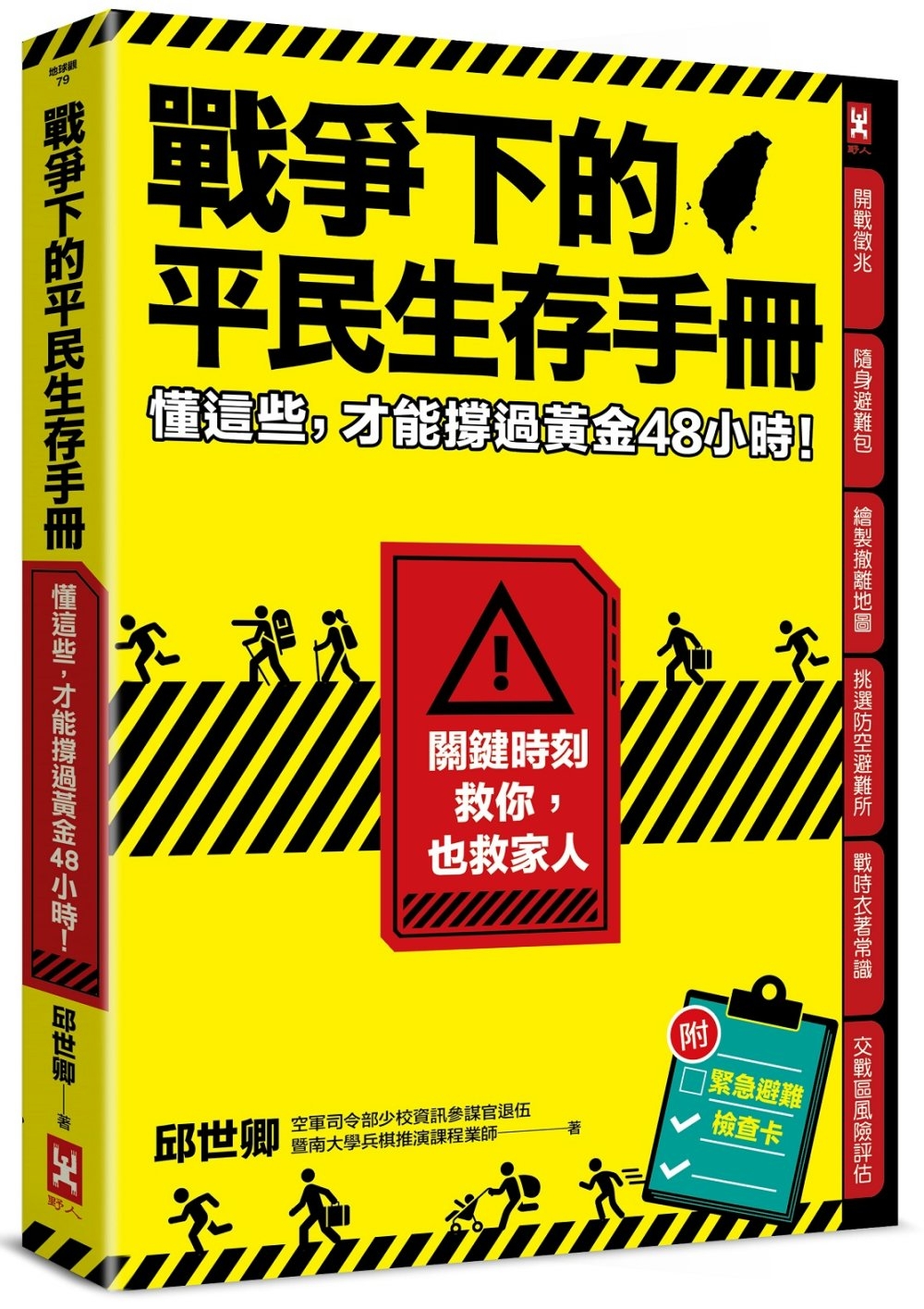第一章 比歐海爾更遠之處
酷熱與一成不變的俗麗風景如同藥物一般,讓大夥兒都陷入了沉默。七月驕陽在沿路商店閃爍,映過了麥當勞、影帶大王、電腦天地、艾比速食、漢堡王、肯德基上校、一個汽車經銷公司,接著又是一家麥當勞。車潮、熱氣和一成不變的景色讓我頭痛,天曉得絲蘿是不是更難受。我們離開診所時,她興奮得不能自已,哇啦哇啦談論著法諾的工作、金錢,以及寶寶的衣物用品。
「這下媽會讓我搬去跟你住了。」她一面歡呼,一面喜孜孜地挽住法諾的手臂。
我從後照鏡看了看,法諾的臉上沒有半點同樣歡喜的跡象,反而鬱鬱不樂。「痞子!」阿爾瓦拉多太太這麼批評他。絲蘿是他們家族裡的寶貝,居然會愛上這麼一個人,為他懷孕,而且還不肯放棄小孩,這把阿爾瓦拉多太太氣壞了。一直以來,絲蘿無論去哪裡,家人都亦步亦趨地保護著(問題是放學時,誰也不能直接把她從學校抓回家),現在等於是遭到軟禁了。
絲蘿一宣布不拿掉小孩,阿爾瓦拉多太太就堅持非辦婚禮不可,而且是要穿白紗禮服、在聖墓教堂舉行的正式婚禮。但體體面面辦完喜事後,她仍把女兒留在家裡,法諾則住在他母親家。這等於是為絲蘿悲慘的命運,又添了樁荒唐可笑的事。而且為了不讓絲蘿受委屈,阿爾瓦拉多太太處心積慮不讓絲蘿的人生陷入不幸。她不要絲蘿變成奴隸,被小寶寶以及一個根本不願意找工作的男人奴役。
絲蘿剛剛念完高中,因為成績優異,提前一年畢業,但她毫無謀生技能。阿爾瓦拉多太太堅持絲蘿無論如何都要念大學。她有潛力成為畢業生致詞代表、校園皇后、領取各種獎學金,絕不能犧牲這些大好前景,一輩子去做些勞筋動骨的卑賤工作。阿爾瓦拉多太太很清楚一輩子做牛做馬是什麼滋味,她這輩子在市中心一家大銀行的自助餐廳當服務生,靠著這份收入拉拔六個孩子。她打定主意要把這個女兒培養成醫生、律師或企業主管,為阿爾瓦拉多家族掙財爭光。那個痞子,那個沒出息的東西,不能毀掉她的大好前程。
這些事情我聽過不只一次了。絲蘿的姊姊凱洛•阿爾瓦拉多是羅緹•赫爾蕭診所裡的護士。凱洛苦苦哀求妹妹把小孩拿掉。絲蘿的健康狀況不好,十四歲就開刀切除過囊腫,又患有糖尿病。凱洛和羅緹都苦口婆心地向絲蘿解釋,以她的健康狀況,懷孕的過程會非常艱辛,但絲蘿是吃了秤鉈鐵了心,非要這孩子不可。當個身懷六甲的十六歲糖尿病女孩不是件輕鬆的事,在沒有冷氣的八月溽暑,恐怕會痛苦難當,但纖瘦病弱的絲蘿卻歡天喜地。打從她呱呱墜地,整個家族就把榮耀與壓力加諸她的身上,現在她找到了一個再好不過的出口,可以逃開這些壓力。
大家都知道,法諾之所以持續找工作,純粹是因為害怕絲蘿的幾個哥哥。法諾的母親似乎毫不介意養他一輩子,而他也相信,只要繼續這樣吊兒郎當下去,時間夠久,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擺脫絲蘿。但是保羅、賀曼和迪亞哥整個夏天都緊迫盯人,凱洛說他們有天還狠狠揍了他一頓。凱洛有點憂心,因為法諾和某個幫派似乎有往來,但那一頓拳腳逼得法諾持續有一搭沒一搭地找著工作。
現在法諾的工作有眉目了。雙伯格附近有間工廠要聘用工人,不需要專業技能。凱洛有個男性朋友的叔叔是那間工廠的經理,他勉為其難地答應,只要法諾來面試,他就給他機會。
凱洛一早八點打電話把我吵醒。她極不願意麻煩我,但法諾非去面試不可,偏偏他的車壞了—「那個混蛋!他八成是不想去,自己弄壞的!」—羅緹在忙,媽不會開車,迪亞哥、保羅和賀曼都在上班。「維艾,我知道這樣真是很對不起你,可是絲蘿的事最好不要讓陌生人介入,而你就像我們的家人。」
我咬了咬牙。從前當公設辯護律師時,我成天面對那種脾氣暴躁又自以為是的小混混,八年前改行當私家偵探後,我就恨不得徹底擺脫這種人,偏偏現在又碰上法諾。但阿爾瓦拉多一家人總是樂於助人,一年前的耶誕節,我在密西根湖意外泡了場澡,凱洛犧牲耶誕假期來照顧我。還有一次,吉兒•塞爾命在旦夕,保羅•阿爾瓦拉多費心看護她。他們幫過我各種大大小小的忙,數都數不清,我不能忘恩負義,於是答應中午到羅緹的診所去接他們。
診所離湖不遠,一陣微風吹來了可怕的夏日酷熱。車子駛上高速公路,往北方的郊區行去時,滯重的空氣迎面撲打在我們身上。我的小車沒有冷氣,熱風從敞開的窗戶灌進來,就連絲蘿的熱情也給熱風吹熄了。
我從鏡裡看見她臉色蒼白憔悴,法諾惱怒地聲稱靠得太近實在太熱,移到了座位的另一側。我們來到五十八號公路的交叉口。
「差不多該轉彎了吧。」我轉過頭喊:「該走哪邊才對?」
「左邊。」法諾咕噥。
「不對。」絲蘿說:「右邊。凱洛說是公路的北側。」
「我看你去跟經理談好了。」法諾用西班牙文忿忿地說:「面試也是你安排的,路你也認得,你放心讓我一個人去面試嗎?乾脆你幫我去面試好了!」
「對不起,法諾,是我不好,我太擔心寶寶了。我知道你沒問題的。」她伸出手懇求原諒,他一把推開。
我們來到奧沙吉路,向北轉了彎,沿街駛了一、兩里。絲蘿說得沒錯,康畢油漆工廠就座落在離公路有段距離的一座現代化工業園區裡,是棟低矮的白色建築,旁邊有座人工湖,湖裡有鴨子。
絲蘿看到這景象,恢復了活力:「好美,你工作的地方外面會有美麗的鴨子和樹,好棒!」
「的確很棒。」法諾酸溜溜地附和:「我在熱死人的天氣裡開了五十公里的路以後,一定會被鴨子迷死。」
我把車停在訪客停車區,然後對他說:「你去面試吧,我們會在湖畔等你,順便欣賞風景。祝你好運!」我盡可能真誠地祝福他。如果他沒能在寶寶出生前找到工作,也許絲蘿會漸漸忘了他,會訴請離婚或撤銷婚姻。阿爾瓦拉多太太雖然古板,但一定會願意照顧外孫。或許小孩的誕生可以讓絲蘿不再恐懼,會願意重拾她的生活。
絲蘿怯怯地向法諾道別,她想吻他,但法諾態度冷淡,她縮了回來,默默跟著我走上通往湖邊的小徑,挺著七個月大的肚子,動作遲緩笨拙。我們在幾棵小樹細窄的樹蔭裡坐下,靜靜注視鴨子。鴨子習慣了人們餵食,滿懷希望地呱呱叫著,朝我們泅來。
「維艾,如果小孩是女生,你和羅緹一定要當她的教母。」
「你要叫她羅緹•維多利亞?這對小孩是多沉重的負擔啊!你應該問你媽媽的,絲蘿,這樣會有助於緩和她的態度。」
「緩和她的態度?她覺得我壞到骨子裡了,又壞又不惜福,凱洛也是這樣想,只有保羅比較同情我……你也這樣覺得嗎,維艾?你也覺得我很壞嗎?」
「不,小乖乖,我覺得你是害怕。他們希望你單槍匹馬去美國人的世界闖蕩,幫他們贏獎品回來。這個工作一個人做太辛苦了。」
她像個小女孩似地抓住我的手:「那你願意當寶寶的教母囉?」
她的臉色讓我有點不安,太白了,臉頰上有紅暈。「我不是基督徒,你的牧師對這點可能會有意見……這樣吧,你在這裡休息一下,我去那邊的速食店買點冷飲來。」
「我……不要走,維艾,我感覺怪怪的,我的腿好像很重……我覺得我好像快生了。」
「不可能,你才七個月而已!」我摸了摸她的腹部,不太確定應該要注意什麼跡象,但她的裙子溼了,我摸她的時候,感覺到一陣抽搐。
我焦急地四處張望,附近連個鬼也沒有。當然啦,在比歐海爾還遠的地方,當然什麼也沒有,沒有街道、沒有街頭生活、沒有人,只有綿延數里的購物中心和速食連鎖店。
我極力壓抑驚慌,冷靜地說:「絲蘿,我要離開幾分鐘,到工廠裡去問問看最近的醫院在哪裡,然後我馬上就會回來……你盡量深呼吸,深深地吸氣,憋住,數到六,然後吐氣。」我緊緊握著她的手,陪她練習了幾次。她慘白的臉上,眼睛又大又恐懼,但她顫抖著對我笑了笑。
我走進廠房,楞楞地站了一會兒。空氣裡瀰漫著一種微弱的酸性氣味,還有噪音嗡嗡作響,但沒有大廳,沒有櫃台人員,地獄的入口大約就該是這模樣。我沿著一條短短的走廊,往噪音的方向走,右側有間巨大無比的房間,裡面滿滿是人,還有大桶子和濃濃的煙霧。左側則有個柵欄鐵門,上面標示著「接待處」。柵欄的後面坐著一個中年婦人,頭髮花白,並不胖,卻有著那種飲食不當外加缺乏運動導致的雙下巴。她正在處理好幾疊的文件,看起來是項艱巨的工程。
我喊她,她猛然抬起頭來,態度煩躁,於是我盡力解釋了情況。
「我必須打電話到芝加哥,通知她的醫生,問問看我要把她送到哪裡。」
婦人的眼鏡閃著光,我看不見她的眼睛。「懷孕的女孩?在湖邊?你搞錯了吧?」她操著芝加哥南區那種帶有鼻音的腔調,應該是從瑪奎公園區搬到郊區的人。
我深吸了一口氣,重新解釋一遍:「我開車載她先生來跟海克•穆諾先生談工作的事,那女孩跟著一起來。她十六歲,有孕在身,而且開始陣痛了。我必須打電話給她的醫生,找家醫院送她過去。」
雙下巴扭動了一下身子:「我不太理解你在說什麼,不過你要用電話,那就進來吧。」
她撳了撳桌旁的一個鈕,鐵門開了,她指指電話,然後又回頭去處理堆積如山的文件。
有些人面對危機時反而出奇冷靜。凱洛•阿爾瓦拉多就是這樣。羅緹正在貝斯•以色列醫院開刀,凱洛說她會打電話去那邊的婦產科,詢問羅緹我該把她妹妹送到哪裡去。凱洛知道我在哪裡,她到這兒找過海克好幾次。她要我先不要掛斷。
我站著等,話筒被我握得潮潤,我的腋下溼淋淋,雙腿顫抖,心裡不耐煩得恨不得尖叫,卻不能不賣力忍住這個衝動。旁邊那個雙下巴一面翻著她的文件,一面偷偷瞅我。我做了幾下腹式呼吸來穩定情緒,集中精神在心裡默唱一遍《蝴蝶夫人》裡的「美好的一日」。凱洛回到線上時,我的呼吸已經大致恢復正常,也能專心聽她說什麼了。
「你那附近有家醫院叫『友誼五號』,貝斯•以色列醫院的海徹醫師說,他們有個頂級的新生兒照護中心,所以你送她去那裡,我們會派麥坎•崔格過去幫忙。我會想辦法聯絡上媽,我盡快休診,然後火速趕過去。」
麥坎•崔格是羅緹•赫爾蕭的同事。羅緹的名氣是在貝斯•以色列醫院打響的,去年她勉為其難答應重回老東家,兼職擔任產婦在產前五個月到產後一個月的產科醫生。但一旦決定當產科醫生,即使只是兼職,也需要有人支援。從開業以來,羅緹第一次聘請了其他醫生。麥坎•崔格是領有專業執照的產科醫生,正在進行周產學研究,就快要結束了。他的醫療理念和羅緹不謀而合,對人也有和她同樣敏銳的直覺。
掛上電話,我稍稍鬆了口氣,轉頭看雙下巴,她正興奮地注視著我。是的,她知道友誼醫院在哪裡,他們工廠發生意外時,都是把傷患送到那裡去。沿著公路開三公里,轉幾個彎,一定找得到。
「你能不能先打個電話通知他們?告訴他們病患是個年輕女孩,有糖尿病,要生產。」
這下她理解事態嚴重了,迫不及待想幫上忙,很樂意打電話。
我衝回絲蘿身邊,她躺在一棵小樹下的草地上,呼吸很淺。我跪在她身邊,摸摸她的臉,她的皮膚上汗珠點點,冰冷潮溼,雙眼緊閉,用西班牙文喃喃說著話,我聽不見她說什麼,只知道她以為身旁的人是她媽媽。
「乖寶貝,我在這裡,你別怕,我們一起來,加油,我的心肝,加油,撐著點,撐著點!」
我覺得我快窒息了,胸脯彷彿凹陷,壓著我的心臟。「撐著點,絲蘿,不要這樣死掉!」
我好不容易扶她站起來,半牽半抱地踉踉蹌蹌扶著她走了九十公尺左右的路,走到車子旁。我很怕她半路會暈過去,幸而並沒有,但一進到車裡,她似乎就真的陷入昏迷了。我用盡力氣全神貫注依照那個收發員匆忙間指示的路線開車,回到我們來時的路上,第二個岔路左轉,下一個岔路右轉。醫院就在我前方,低矮的建築匍匐在地面,像隻海星。我把車撞上急診室門口的路緣。雙下巴很盡責,我一打開車門,就有熟練的工作人員俐落地把絲蘿從車裡抬到一張推床上。
「她有糖尿病。」我告訴急診人員:「懷孕才剛滿二十八週。我只知道這些了。她在芝加哥的醫生會派個了解她病況的醫生來。」
鋼製的自動門嘶嘶往兩側開啟,急救人員火速把推床推進去,我緩緩地跟在後頭,看著推床沒入長長的走廊。
我一面朝著絲蘿被推去的方向慢吞吞地拖著腳步,一面不斷告訴自己,只要絲蘿能靠那些管子啦、唧筒之類的裝置撐到麥坎來,那就沒問題了。沿著走廊走了大概一里半左右,來到一個護理站。兩個戴著漿挺白帽的年輕白人女性正壓低了嗓子熱烈交談,從偶爾爆出又刻意壓抑的笑聲聽來,談話的內容應該和病患的診治無關。
「打攪一下,我是維艾•華沙斯基……我幾分鐘前送那個產科的急診病患進來,請問我可以向誰查詢她的狀況呢?」
兩個女人當中的一個說她查查看「一○八號病患」的資料,另一個摸摸她的帽子,確認儀容端莊,於是擺出空洞且充滿優越感的典型醫護人員式笑容。
「我們目前還沒有關於她狀況的資料哦,你是她母親嗎?」
母親?有一剎那我很憤怒,但對這些年輕女孩來說,我看起來恐怕真的老到可以當外婆了。「不是,我是她家人的朋友。她的醫生大概一小時左右以後會到,叫麥坎•崔格醫師,是羅緹•赫爾蕭團隊的醫生,你可以跟急診室的人說一聲嗎?」羅緹的名聲紅遍全球,但不知雙伯格的人有沒有聽過她。
「只要我們一空出人手,我就派個人過去告訴他們。」我的眼前閃現一個牙膏廣告式毫無意義的美齒微笑。「現在您何不到走廊底端的等候室坐一下?我們希望訪客只有在探病時間才到醫療區來。」
我眨巴著眼睛—這和詢問絲蘿的狀況有什麼關係?但我想,戰鬥的力氣還是留待真正有需要的時候再用好了。於是我往回走,找到了等候室。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失踪的病歷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英美文學 |
$ 25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失踪的病歷
第一章 比歐海爾更遠之處酷熱與一成不變的俗麗風景如同藥物一般,讓大夥兒都陷入了沉默。七月驕陽在沿路商店閃爍,映過了麥當勞、影帶大王、電腦天地、艾比速食、漢堡王、肯德基上校、一個汽車經銷公司,接著又是一家麥當勞。車潮、熱氣和一成不變的景色讓我頭痛,天曉得絲蘿是不是更難受。我們離開診所時,她興奮得不能自已,哇啦哇啦談論著法諾的工作、金錢,以及寶寶的衣物用品。 「這下媽會讓我搬去跟你住了。」她一面歡呼,一面喜孜孜地挽住法諾的手臂。 我從後照鏡看了看,法諾的臉上沒有半點同樣歡喜的跡象,反而鬱鬱不樂。「痞子...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莎拉‧派瑞斯基 譯者: 鄭家瑾
- 出版社: 天培 出版日期:2006-07-10 ISBN/ISSN:9867759451
- 頁數:368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