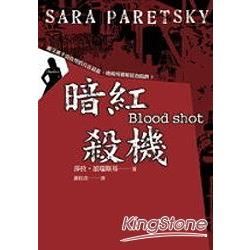第一章 重上四十一號高速公路
我都忘掉那股氣味了呢。即使美國鋼鐵南工廠在罷工,威斯康辛鋼鐵廠拴著掛鎖漸漸荒廢,五味紛陳的強烈化學味仍舊從通風口注入車內。我關掉暖氣,但臭氣(那不能叫空氣)照樣從雪佛蘭車窗的細微裂縫襲來,嗆得我眼鼻都熱辣辣的。
我順著四十一號公路南下。不過就是幾公里之前,我還在湖岸路上行駛,左手邊密西根湖吐著泡泡拍打岩石,右手邊矗立著華樓美廈。到了七十九街,密西根湖驀然失去蹤影。遼闊的美鋼南工廠周邊空地野草蔓生,沿著路面和湖面之間的空地往東迤邐約莫一公里半。遠方電塔、起重機台架、塔台隱隱約約聳立在二月灰濛濛的空氣中。這裡沒有高樓大廈和湖光水色,而是再生地和破敗工廠。
逐漸朽爛的小平房立在街道右側,面對南工廠。有些房舍掉了幾塊牆面,有些羞人答答地露出一條條剝落的油漆,有些門面的水泥台階龜裂歪斜。窗戶倒是通通完好無缺,緊緊關閉,院落裡不見髒汙。或許這裡已經淪為貧苦之地,但我的老鄉親們仍舊挺著傲骨,不放棄尊嚴。
遙想當年,天天都有一萬八千人從這些整潔的小小家園湧入南工廠、威斯康辛鋼鐵廠、福特汽車裝配廠、薛西斯溶劑廠。猶記得當時每隔一個春天,每塊門楣窗框就要重新粉刷,秋天常常見到新的別克或奧斯摩比駛過街道。但那都是上輩子的事了,對我是如此,對南芝加哥也是。
我在八十九街轉向西駛,翻下遮陽板為眼睛擋住西沉的冬陽。左手邊是亂蓬蓬的枯木、生鏽的車輛、頹圮的屋舍,再後面就是卡路梅河。以前我跟玩伴們常常為了表示藐視父母,去那裡游泳;如今想到以前把臉埋進髒水裡面,我不禁反胃。
我們高中在河對岸,幅員遼闊,占地好幾英畝,可是那暗紅的磚房校舍不知怎麼看來好親切,彷彿十九世紀的女子學院。看著陽光從窗戶一瀉而下,年輕人蜂湧進入校舍西首的巨大雙開門,心裡的怪異感更添幾分。我停好車,拿起運動包加入人潮。
當年建造那高聳拱形屋頂的時候,暖氣很便宜,大家也夠重視教育,才會把學校蓋成大教堂的模樣。深邃的走廊是絕佳的回音室,迴蕩著人潮的笑語喧嘩,聲浪從屋頂、牆壁、鐵製置物櫃席捲而來,不曉得學生時代怎麼從來沒注意到這裡的吵嘈。
據說人永遠記得年輕時的事。我上回來這裡是二十年前,可是在體育館門口我想都沒想,便直接左轉,沿著通道走到女子更衣室。卡洛琳.吉亞克等在門口,手上拿著資料夾。
「維兒!我還在想妳不敢來了呢。其他人都到了半個鐘頭,換上舊球衣,起碼那些還塞得進去的人都換好了。妳有帶球衣來吧?《前鋒星報》的瓊安.萊西在這裡,她想訪問妳。畢竟,妳當年可是聯賽的最有價值球員,對嗎?」
卡洛琳仍是老樣子。紅棕辮子剪掉了,變成一蓬捲髮襯著雀斑臉,但這似乎是唯一的變化。她照舊矮人一截,活蹦亂跳,少一個心眼。
我跟她進入更衣室,裡面的喧鬧和外面的走廊不相上下。十個青春少女身上的衣服褪去或多或少,此起彼落嚷著要借指甲銼刀、衛生棉條,或誰偷了我該死的體香劑。穿著內衣褲的她們看來健美而結實,比我們當年強多了。
在更衣室一角幾乎同等喧鬧的一群人,是二十年前跟我一起拿下AA級州冠軍賽的女虎隊成員。昔日的十個隊友來了七個,其中五人穿著黑、金雙色的舊球衣。有些人的T恤緊緊繃著乳房,短褲看來一有大動作就會裂開。
球衣最緊的那個人可能是莉莉.戈林,我們的罰球王,可是瞧那燙髮和雙下巴也說不準。我想艾爾瑪.羅威是那個體積遠遠超過球衣伸展力的黑人,校服夾克顫巍蘶地縮在她肥厚的肩膀上。
我唯一能確認的兩個人是黛安.羅根和南西.克萊宏。黛安勁瘦的雙腿仍然登得上《浮華世界》的封面。她是我們的明星前鋒、副隊長、模範生。卡洛琳告訴過我,現在的黛安事業成功,在市區經營公關公司,專門替黑人企業和個人打造形象。
南西.克萊宏和我大學畢業後就斷了音訊。不過她剛毅的方臉和金色捲髮完全沒變,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能認得出她。就是因為她,我今晚才會來這裡。她在卡洛琳.吉亞克主持的南芝加哥復甦計畫中負責環保部門。當她們倆得知這是女虎隊二十年來首度打進區域冠軍賽,便決定讓舊隊員齊聚一堂,辦一場賽前晚會,既可提振地方名聲,又能替南芝計畫打廣告,同時聲援球隊,人人都有好處。
南西一見到我就笑咪咪:「喂,華沙斯基,手腳快一點,再十分鐘就上場了。」
「嗨,南西。我應該去檢查腦袋,看看怎麼會被妳說服來這裡。難道妳不曉得不能走回頭路嗎?」
我在長椅上找到十公分見方的空間放運動包,迅速褪去衣物,把牛仔褲塞進包包,換上褪色的球衣。我拉好襪子,繫好高筒鞋的鞋帶。
黛安一手摟著我:「不賴嘛,白妞,看來妳在緊要關頭還是跑得動哦。」
我們凝視著鏡子。如今的女虎們有些人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不止,而一七三的我當年已經是隊上第一長人。黛安的爆炸頭大概到我鼻子的高度。我們一白一黑,當年兩人都想打籃球。在那個年代,走廊和更衣室天天都有黑白爭端。我們倆相看兩厭,可是三年級時我們硬是讓其餘隊友放下種族爭端,次年二月就帶領她們打進第一屆全國女子錦標賽。
她笑嘻嘻提起往事:「以前我們爭的那些無聊事根本是雞毛蒜皮嘛,華沙斯基。來見見記者,為這裡的老鄉親講幾句好話。」
《前鋒星報》的瓊安.萊西是本市唯一的女性體育專欄作者。我告訴她我平常就讀她寫的東西,她開心地笑了:「跟我的編輯講一聲吧,最好是寄信過去。好啦,過了這麼多年,重新穿上球衣的感覺如何?」
「像白痴哪。我大學畢業後就沒摸過籃球了。」我是拿體育獎學金念芝加哥大學的。早在美國人知道女生會運動之前,芝大就有這種獎學金。
我們聊了幾分鐘,說起前塵往事,說起逐漸老去的運動員,說起這一帶五成的失業率,說起現在女虎隊的展望。
「我們支持球隊,這個不在話下。」我說:「我很想看她們上場打球。這些人好像很看重訓練,比二十年前的我們認真得多。」
「是啊,他們一直希望女子職籃聯盟東山再起,不然有些中學和大學的頂尖女球員根本沒有出路。」
瓊安收起筆記本,吩咐一個攝影師把我們找到球場上拍照。我們八個回鍋球員魚貫進入球場,卡洛琳繞著大家打轉,像熱情過頭的小獵犬。
黛安抄起一顆球,跨下運球往後傳給我。我反身一投,球打到籃板彈回,我衝上前接住灌籃,老隊友們七手八腳助我一臂之力。
攝影師拍了幾張合照,然後取了黛安跟我在籃下一對一的鏡頭。我們撩起觀眾些許興味,不過大家真正想看的是現在的女虎。當她們穿著熱身運動服進場,觀眾響起如雷歡呼。我們跟著她們稍事暖身,但是一逮到機會便將場地交還給她們。她們才是今晚的主角。
等聖蘇菲亞的客隊穿著紅白運動衫上場,我溜回更衣室,換回便服。卡洛琳找到我的時候,我已經結好領巾。
「維兒!妳要去哪裡?妳答應過比賽完要去看我媽的!」
「我只說我盡量,有空才去。」
「她以為妳會去耶。她連下床都很勉強,狀況很糟。她真的很想見妳。」
透過鏡子,我看得出她的臉頰泛紅,受傷的目光讓藍眼珠更加深遂。她五歲的時候,我不肯讓她跟著我和友伴出去,她也那樣看我。埋藏二十年的怨氣讓我不耐起來。
「妳安排這場笑死人的籃球賽,就是為了布局拐我去見妳媽?還是妳後來才動起那個腦筋的?」
泛紅加深成豬肝色:「妳說笑死人是什麼意思?我只是想為這個地方盡點心力。我不是假惺惺、眼睛長在頭頂上的人,跑到北岸,不管鄉親死活!」
「什麼話嘛!難不成我留在這裡,就能救回威斯康辛鋼鐵廠?還是跟美國鋼鐵廠的豬頭說這一帶還在運作的工廠不多了,叫他們別罷工?」我從長椅上一把抓起水手短外套,氣嘟嘟地將手臂塞進袖子。
「維兒!妳去哪裡?」
「回家啊。我跟人約好吃晚餐,要去梳妝打扮。」
「不行,我需要妳。」她放聲嘶嚎,大眼睛淚汪汪,隨時會厲聲呼叫她媽或者我媽,指控我對她太壞。舊時情景頓時浮現在我腦海,我媽媽嘉百莉兒出來門口說:「維多莉亞,讓她去是會怎樣?帶她去吧。」那意象如此鮮明有力,我只好不甩卡洛琳耳光;她嘴角往兩邊拉得好開,雙脣顫抖。
「妳要我幹嘛?履行一個妳沒問一聲就許下的承諾?」
「我媽活不久了啦。」她嚷著:「難道這不如一個狗屁飯局重要?」
「話是不錯,如果我是要去一個社交場合,我會打電話說抱歉,鄰居的小鬼頭纏上了我,我脫不了身。但我是要跟客戶吃飯,他脾氣很大,不過付錢很準時,我希望讓他高興。」
現在淚水簌簌流過雀斑:「維兒,妳從來就沒有把我當一回事。我們談過妳來一趟對媽媽很重要,那時候我就問妳見面的事,是妳自己忘得一乾二淨。妳還當我是五歲小孩,我說什麼、想什麼都無關緊要。」
我啞口無言。她說得有道理,如果露意莎真的病重,我是應該去看她。
「好啦好啦,我打電話跟客戶取消飯局。下不為例。」
淚花瞬間消失。「謝囉,維兒,我不會忘掉的。我就知道可以仰賴妳。」
「妳是說妳知道怎麼操縱我。」我反駁。
她笑了:「我帶妳去打電話。」
「我還沒老糊塗,自己找得到電話。放心啦,我不會趁妳不注意開溜的。」我瞥見她眉宇間的不安,又補了一句。
她微微一笑:「以上帝為證?」
這是一句陳年誓言了,她母親的酒鬼叔叔史坦總用這句話證明自己神智清醒。
「以上帝為證。」我嚴肅地答應:「希望格雷姆不會一火大就不付他的帳單了。」
我在體育館前門附近找到付費電話,浪費了好幾個銅板才在四十九俱樂部找到達洛.格雷姆。他飆說他已經預訂金絲銀花餐廳的桌位了,可是電話掛掉時我已經化解他的怒氣。我包包掛在肩上,回到體育館。
第二章 拉拔孩子
聖蘇菲亞隊下半場球賽幾乎一路領先,讓女虎們追得辛苦。賽事電光火石,節拍比當年我打籃球時快得多。剩七分鐘時女虎隊兩個先發球員畢業離場,局勢看來不妙。倒數三分鐘時聖蘇菲亞最強的後衛出局。女虎的明星前鋒本來一直被罰坐冷板凳,這時上場一口氣連奪八分,主隊以五十四比五十一獲勝。
我發現自己跟所有人一樣熱烈歡呼,甚至對我的高中球隊興起一絲溫軟的懷舊情緒。這可真意外,母親臥病辭世的事盤踞我青春期的回憶,我都忘了曾經有過快樂時光。
南西.克萊宏先走一步去開會,但黛安.羅根和我跟著其餘老隊友到更衣室向我們的接班人道賀,祝福她們在區域準決賽贏得佳績。我們沒有久留,她們顯然覺得我們老到不可能懂籃球,更別說實際打過球了。
黛安過來道別。「妳讓我重溫青春歲月,這可是千金不換的啊。」她湊過來貼著我的臉頰:「我要搬回黃金海岸,以後就長住那裡了。保重,華沙斯基。」她說著便披著閃亮的銀狐皮草走了,遺下鴉片香水味。
卡洛琳在更衣室心焦地轉來轉去,唯恐我不跟她一道走。瞧她神經緊繃的樣子,我心裡毛毛的,不曉得她葫蘆裡賣什麼藥。有一次就是這樣,她在周末把我從大學拖回家,說是露意莎背痛,需要人手幫忙修理破窗戶,可是到了她家,她卻問我她怎麼會響應聖文西斯勞夫教堂的四旬齋募款,將露意莎的小珍珠耳環捐出去。
「露意莎真的生病了嗎?」我們終於離開更衣室的時候,我質問她。
她目光清明地看著我:「她病得很重,維兒,妳不會樂見她現在的模樣。」
「不然妳還瞞了什麼沒說?」
潮紅湧上她的臉頰:「我不知道妳在瞎說什麼。」
她忿忿地衝出校門,我懶懶地走在後面,恰恰趕上看見她上了一輛破車。那車沒停好,半截車頭凸到街上。我從旁邊晃過去,她搖下車窗,嚷說她在家裡等我,然後輪胎嘶一聲開走了。
我驅車上休士頓街,情緒越來越低迷。上回走這條路是一九七六年,當時我父親過世,我回家處理賣屋事宜,抽空去看露意莎,而十四歲的卡洛琳則絕決地追隨我的腳步,甚至試著打籃球,無奈她身高只有區區一百五,即使精力無窮也進不了一軍。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認識我父母的鄰居。大家真心哀悼我那溫和的好脾氣父親,對當時過世十年的母親則勉強維持敬意。畢竟,同一條街上的女人也跟她一樣積積攢攢,省吃簡用,讓家人溫飽,為家人遮風擋雨。
既然她都死了,鄰居便佯裝不知道母親那些讓他們搖頭的古怪行徑,諸如沒替女兒買一件冬天的夾克,反倒多花十美元帶她聽歌劇;既沒讓女兒受洗,也沒送去跟聖文西斯勞夫教會學校的修女上學;鄰居們實在忍無可忍,有一天找了校長嬌瑟.某某某來我家,結果發生了難以忘懷的爭執。
在他們眼中,她天字第一號大愚行可能是堅持我念大學,而且非芝加哥大學不准念。嘉百莉兒事事追求第一,而我兩歲時她就認定芝大是芝加哥第一名的大學。芝大在她心目中十之八九完全不如比薩大學,一如她在摩根街卡拉巴諾精品店買的名鞋也不如米蘭。但一個人只能量力而為。母親過世兩年後,我領獎學金就讀鄰居口中的共產大學,半懼半喜地去面對那些邪魔歪道,之後就不曾真正回歸故里。
露意莎.吉亞克是這條街上唯一始終力挺母親的人,母親辭世後也照挺不誤。不過話說回來,她欠母親嘉百莉兒人情。也欠我人情啊,一絲苦澀突然掠過心頭,嚇了我一跳,這麼說我仍在氣惱當年的璀燦夏日全在幫露意莎帶小孩,在寶寶的哭嚎聲中寫作業。
嗯,寶寶現在已經長大了,但她仍然在我耳中不知節制地哭嚎。我把車停在她的福特開普利後面,熄火。
她家比我印象中更小,也更髒。露意莎沒硬朗到半年洗一次窗簾,重新上漿,而卡洛琳屬於堅決拒做這種家事的一代。這個我最清楚啦,我也屬於同一個世代。
卡洛琳在門口等我,仍舊焦躁不安。她臉上泛起短暫而僵硬的笑容:「媽真的很高興妳要來,維兒。她憋了整天沒碰咖啡,就是想等妳來一起喝。」
她帶我走過又小又擠的飯廳到廚房,一邊說:「其實她不能再喝咖啡了,可是要她戒太難了,更別說她還要適應生病帶來的一切改變。所以我們折衷,一天一杯。」
她在爐台忙著,耗用太多精力跟咖啡搏鬥,把水和咖啡粉灑得到處都是。不過她倒是屏氣凝神地在托盤上擺好瓷器和餐巾,從窗邊咖啡罐剪下一支天竺葵裝飾托盤,最後放上一小碟加了一片天竺葵葉的冰淇淋。她端起托盤,坐在廚房凳子上的我也起身跟著走。
露意莎的臥室在飯廳右邊。卡洛琳一開門,疾病的氣息便彷彿當面打來,讓我記起母親嘉百莉兒生命最後一年身上那股藥味和肉體朽壞的味道。我右手握拳,讓指甲陷入手心,硬著頭皮踏進房間。
我的第一反應是震驚。我以為自己有心理準備,其實沒有。露意莎倚床而坐,綹綹髮絲下的面容消瘦,灰敗的臉上透著一抹怪異的綠。她穿著陳舊的粉紅羊毛衫,鬆垮垮的衣袖中露出兩隻瘦手。但是當她笑著對我伸出雙臂,我依稀又見到那個腹中懷著卡洛琳的妙齡女郎租下我家隔壁的房子。
「見到妳真好,維多莉亞。我就曉得妳會來,妳這點還真像你媽,連長相也像,即使妳有爸爸的灰眼睛也一樣。」
我跪在床邊擁抱她,衣服下的骨頭感覺好細好脆。
她一個猛咳,整個人都晃動起來:「不好意思,該死的香菸,我抽得太多了,菸齡也太久。這個小女生把菸藏起來,好像抽菸還能把我害得更慘似的。」
卡洛琳咬著嘴脣,移到床邊:「媽,咖啡在這裡,喝吧,也許可以暫時忘掉香菸。」
「是,一天一杯。死醫生,先是給你灌了滿肚子亂七八糟的東西,你都不曉得自己要活還是要死。然後他們把你的腳綁起來,搶走一切讓時間比較好過的東西。女孩,我跟妳說,千萬別落到跟我一樣的下場啊。」
我從卡洛琳手上接過厚實的陶瓷馬克杯,遞給露意莎。她的手微微打顫,讓馬克杯靠著胸口,穩住杯身。我轉身坐到床邊一張直背椅上。
「媽,妳要跟維兒私下聊聊嗎?」
「好啊,當然。女兒,妳忙妳的。我曉得妳有事要做。」
卡洛琳帶上門,我說:「真的很遺憾看到妳病成這樣。」
她比出投擲的手勢:「嗐,管他的。我這麼想都想厭了,我跟那群死醫生也抱怨過很多次了。我想聽聽妳最近怎麼樣。每一次妳辦的案子上報,我都會注意案情發展。要是妳媽還在,一定與有榮焉。」
我大笑:「應該不會吧。她指望我唱歌劇,做一個天價的紅牌律師大概也行。要是她曉得我怎麼過日子,她的反應不用想就知道。」
露意莎一隻枯柴瘦手搭著我的臂膀:「別那樣想,維多莉亞,一分鐘也別那樣想。嘉百莉兒的為人妳清楚,就算只剩下一件襯衫,她也不會捨不得送給乞丐。妳想想當年別人對著我的窗戶扔雞蛋,潑糞水,她是怎麼為我撐腰的。或許她會情願妳日子過得好一點,噯—我對卡洛琳也有一樣的感覺,憑她的頭腦、她的教育、她的一切,大可離開這個鬼地方。可是我真心以她為榮。她做人老實,辦事勤快,堅守信念。妳跟她一樣。老天在上,嘉百莉兒要是能夠看到妳今天的模樣,一定得意極了。」
「呃,當年她生重病,沒有妳我們也捱不過來。」我喃喃說,渾身不自在。
「喂,女孩,別胡說。這是報答她恩情的唯一機會,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教堂那群自以為是的女人在我家前面遊行,嘉百莉兒氣呼呼衝到她們跟前,差點沒把她們趕進卡路梅河裡。」
她沙啞地大笑,笑聲變成猛咳,氣接不上來,臉色略略發紫。她靜躺半晌,急促地喘息。
「大家竟然那麼看不起未婚懷孕的女孩子,很難相信吧?」她終於開口:「現在我們這裡一半的人沒工作,女孩,這才是攸關性命的大事。可是做父母的人哪,女兒未婚懷孕就是世界末日。我是說,連我爸媽也一腳把我踢出家門。」她臉上的肌肉激動地顫抖片刻。「好像千錯萬錯通通都是我的錯。妳媽是唯一護著我的人。就連我爸媽來這裡,決定承認卡洛琳活著,他們也從來沒有真心原諒她來到這個世界,原諒我生下她。」
嘉百莉兒做事向來不遺餘力:我得負責帶小孩,好讓露意莎去薛西斯工廠上夜班。我最討厭帶卡洛琳去拜訪她外公外婆了。他們又兇悍又嚴苛,我不脫掉鞋子就不准踏進屋子。有幾次他們甚至在房子外面給卡洛琳洗過澡,才肯放她進入他們聖潔無瑕的大門。
露意莎的父母年紀不過六十開外。如果嘉百莉兒和湯尼仍在人世,也會是這個歲數。可是因為露意莎有小孩而且自立門戶,我總覺得她是我父母那一輩的人,其實她只大我五、六歲。
「妳幾時停止工作的?」我問。偶爾我良心太過不安,眼前又浮現嘉百莉兒的面孔,便會打電話給露意莎,不過已經有一段時日沒這樣了。南芝加哥向來是我心底的疙瘩,惹得我難受,我不想讓南芝加哥重回我的生命。上回跟露意莎通電話是兩年前,當時她沒提過有病痛。
「噢,我病到不能站,大概—肯定才剛一年多,工廠讓我領健康險的失能給付。只有大概這半年才完全不能走動。」
她掀開被子給我看,那枯柴瘦骨給小鳥用還差不多,皮肉和她的臉色一樣灰敗,足上和腳踝的青黑斑塊是血管不再輸送血液的地方。
「我的腎臟出毛病。該死的玩意兒,不讓我好好尿尿。卡洛琳每個星期帶我去洗腎兩、三次,讓他們把我接到那死機器上面,說什麼幫我排毒。不過,女孩呀,跟妳講句悄悄話,我真希望他們早早讓我安靜地走。」她舉起一隻瘦手:「這話可千萬別告訴卡洛琳。她用盡辦法給我最好的。工廠付錢,所以我不是怕動用到她的積蓄。我不要她以為我不知感恩。」
「我不會的,放心。」我安撫她,輕輕為她蓋被。
她又聊起住在這裡的舊日時光,說往年她的雙腿纖細又緊實,午夜收工後常常去跳舞,去找想娶她的史提夫.費拉羅,還有不想娶她的喬伊.潘考斯基。又說如果一切重來,她不會做任何改變,這樣卡洛琳才會來到她的生命。但她希望卡洛琳能有不同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不要待在南芝加哥,年紀輕輕就操勞成老太婆。
最後我握著她枯瘦的手指,輕輕捏著:「露意莎,我得走了,這裡離我家有三十公里路呢。可是我會再來看妳。」
「嗯,能再見到妳真好,女孩。」她歪著頭,給我一個淘氣的微笑:「我想妳應該沒辦法幫我偷渡一包香菸吧,嗯?」
我大笑:「我打死也不碰那玩意兒,露意莎,妳自己跟卡洛琳商量。」
我為她抖鬆枕頭,打開電視,然後才出去找卡洛琳。露意莎一向不習慣吻別,但她緊緊握著我的手幾秒。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暗紅殺機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4 |
二手中文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英美文學 |
$ 25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暗紅殺機
第一章 重上四十一號高速公路我都忘掉那股氣味了呢。即使美國鋼鐵南工廠在罷工,威斯康辛鋼鐵廠拴著掛鎖漸漸荒廢,五味紛陳的強烈化學味仍舊從通風口注入車內。我關掉暖氣,但臭氣(那不能叫空氣)照樣從雪佛蘭車窗的細微裂縫襲來,嗆得我眼鼻都熱辣辣的。我順著四十一號公路南下。不過就是幾公里之前,我還在湖岸路上行駛,左手邊密西根湖吐著泡泡拍打岩石,右手邊矗立著華樓美廈。到了七十九街,密西根湖驀然失去蹤影。遼闊的美鋼南工廠周邊空地野草蔓生,沿著路面和湖面之間的空地往東迤邐約莫一公里半。遠方電塔、起重機台架、塔台隱...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莎拉‧派瑞斯基 譯者: 謝佳真
- 出版社: 天培 出版日期:2006-10-10 ISBN/ISSN:9867759486
- 頁數:384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