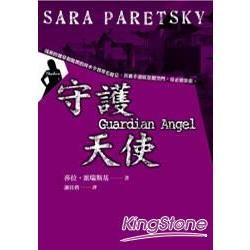第一章 單身女郎的床第
一個個熱吻落在我臉上,將我從沉睡中拉到清醒邊緣。我咕噥著直往被窩裡鑽,想重新回到甜美的夢鄉。但我的伴侶不想休息,鑽進被子裡繼續火辣求愛。
我用枕頭蒙住頭,卻聽到小狗珮皮可憐兮兮地哀叫。我霍然清醒,轉頭瞪她:「現在還沒五點半欸,妳不可能想起床的啦。」
她不甩我,不聽我的話,不管我拚命想將她推下我的胸口。她只睜大了棕色的眼睛痴痴望著我,嘴巴微開,伸出紅潤的舌尖。
我露出慍色,嚇得她來舔我鼻子。我坐起來,將她的頭從眼前推開:「就是妳沒事亂舔亂舔的,才會惹我生氣啊。」
見到我清醒,珮皮可開心了,笨拙地下床走向門口,回頭看我有沒有跟著走,又不耐地嗚嗚催我。我從床邊的衣物堆裡拉出運動衫和短褲,拖著還沒睡醒的腿來到後門,摸弄著打開三道門鎖。珮皮急切地低吠,但她耐心地等待。純種狗果然就是有教養。
我看著她走下三段樓梯。她懷孕了,肚腹兩側隆起,走路速度也變慢。她走到公寓後院門邊平常大小便的地方,拉完後並沒有按照慣例進院子趕走貓咪或其他動物,反倒晃回階梯,站在一樓公寓門口大吠一聲。
好,就讓她和康特拉先生廝混吧。康特拉先生是一樓鄰居,和我合養珮皮。珮皮會懷孕全是他害的。唔,不完全是他害的啦,狗爸爸是隔壁第四間房子的黑色拉不拉多。
珮皮發情的那個禮拜,我離城調查一樁工業陰謀。在出發之前,我跟經營搬家公司的精壯朋友提姆•史崔特講好,每天用短狗鏈牽珮皮出去兩次。我跟康特拉先生說找了朋友幫忙遛狗,他覺得備受冒犯,偏偏他沒難過到無法言語,直說珮皮的教養一級棒,人一叫她就來了,哪裡用得著狗鏈?我算哪根蔥?憑什麼找人遛狗?平常一天二十四小時我就有二十小時不見人影,要不是有他在,珮皮根本沒人照顧,現在我不是又要出城了嗎?顯然再一次證明我冷落珮皮。更何況,我帶回家的那些乳臭未乾的小伙子啊,十個就有九個沒他壯。
我急著出門,沒等他把話說完,以一個七十七歲的人來說,他真的很硬朗,不過還是拜託他聽話,讓別人遛狗。過了十天,我得知提姆第一次上門遛狗的時候,就被康特拉先生趕走。若說會出什麼亂子,用膝蓋想也知道。
當我周末從堪卡基回來,老先生悶悶地來找我:「小可愛,真不曉得怎麼出事的。她一向都很乖,一向都是人一叫她就來,可是那天她卻硬是跑到街上去,嚇得我心臟差點跳出來。我就想,天哪,萬一她被車撞怎麼辦,迷路怎麼辦,被人捉走怎麼辦,妳也曉得報上說過,實驗中心僱人到街上、到人家院子裡抓狗,然後狗就從此消失,也不曉得出什麼事。等我追上她,唔,該怎麼說才能讓妳明白——」
我無情地凶他:「你打算說什麼?你不肯讓她結紮,她發情了你又管不住她。要不是你那麼頑固,就會聽我的話讓提姆遛狗。這麼說吧,我才不要浪費時間找好心人收養該死的狗寶寶。」
我的話惹得他一肚子火,砰一聲摔上門,回他家去了。整個星期六我都在躲他,但我們必須在離城之前和好,總不能由他一個人去顧一窩小狗吧!反正,我年紀已經大到不喜歡嘔氣了。星期天早上我下樓跟他大和解,甚至留到星期一還沒出城工作,以便陪他去動物醫院。
我們就像搞怪青少年的怨偶父母,繃著臉送狗去看醫生。獸醫說黃金獵犬有時一胎能生到十二隻。
「不過既然是第一胎,大概不會生那麼多啦。」他笑呵呵的趕緊補充說明。
看得出來,康特拉先生很開心家裡可能會添十二顆黑、金雙色小毛球。我以將近一百四的時速飆回堪卡基查案,並且盡量拖延回家的日子。
晃眼兩個月過去,我多少接受珮皮懷孕的事實。她似乎打算把康特拉先生家變成產房,我大大鬆一口氣。康特拉先生埋怨珮皮扯爛報紙堆在沙發後面,不過我曉得如果珮皮在我家造窩待產,康特拉先生會哀怨到不行。
即將臨盆的珮皮幾乎天天都待在康特拉先生家裡。昨天康特拉先生的老教會舉辦賭城之夜活動,他幫忙策劃半年了,並不想錯過。雖然他出門去玩,卻打了兩通電話問珮皮生了沒,午夜又撥第三通,確認我有抄下他們活動會場的電話。現在珮皮六點不到就想叫他起床,我不禁幸災樂禍。誰叫他昨天半夜打電話吵我。
六月的陽光燦爛,但大清早的寒意仍然凍得腳丫子失去知覺,感覺不到腳下的陽台。我沒等老先生起床,逕自走回室內。外頭持續傳來珮皮隱約的吠叫聲。我扯下短褲,東倒西歪地鑽回被窩。我赤裸的腿碰到床單上一塊溼溼的地方。是血。那絕不是我的,所以一定是狗的。
我重新套上短褲,打電話給康特拉先生。在他接聽之前,我穿好了長統襪和跑鞋。他的聲音嘶啞到我認不出來。
「你們昨天晚上一定玩得很高興。」我語調愉悅:「不過你最好起床迎接這個大日子——你又要當爺爺了哦。」
「誰啊?」他刺耳地說:「如果妳在拿我開玩笑,應該曉得不能一大清早就吵人——」
「是我啦,我是維艾•華沙斯基,記得嗎?就是你家樓上的鄰居。嗯,你的小狗珮皮在你家門口狂吠十分鐘了,我相信她想進去生小狗。」
「哦,是妳呀,小可愛。狗怎麼了?她在我家後門叫,妳讓她出去多久?她都快生了,不該放她在外面亂叫亂叫的,搞不好會感冒呢。」
我嚥下好幾句調侃:「我剛剛在床上發現一些血跡,她可能快生了。我馬上過去幫忙你準備。」
康特拉先生開始交代一連串繁複的服裝儀容注意事項。他的話沒頭沒腦,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掛斷電話,離開家門。
獸醫曾經耳提面命,千萬不能協助珮皮生產。如果我們在她分娩的時候插手,或是去抓初生的狗寶寶,珮皮可能會焦躁到無法獨力完成分娩。我擔心康特拉先生一興奮就忘掉獸醫的警告。
我到的時候,老先生才剛放狗進屋子,恰好關上門。他從門上玻璃後面沒好氣地瞪我一眼,然後消失無蹤。一分鐘後他才回來,開門塞給我一件舊工作服。
「進來之前先穿上這個。」
我搖搖手拒絕:「這件運動衫已經舊了,我不在乎會沾到什麼。」
「誰管妳的醜衣服會不會怎樣。我在乎的是妳衣服裡面穿了什麼,或者該說妳沒穿什麼。」
我望著他,當場呆住,「什麼嘛,我得穿胸罩才能照顧小狗喔?」
他飽經風霜的臉孔變成暗紅色。光是想到女性內衣就夠讓他害羞了,更別提他還聽到我大聲講出來。
「跟狗沒關係啦。」他慌亂起來:「我在電話上就想講了,但妳掛我電話。我曉得妳在家裡喜歡穿得清涼一點,可是只要妳有穿衣服,我就不會在意,再說妳身上確實通常都有穿衣服。但不是大家都跟我一樣呀,就這樣。」
「你覺得珮皮會介意嗎?」我嗓音飆高:「還會有誰——原來你昨晚從賭窟帶了人回來。喲,你昨天晚上過得真刺激啊,嗯?」通常我不會隨意批評別人的私生活,但老先生這三年來始終在監看我有啥男性訪客,我覺得應該以牙還牙,整他一下。
他更加鬱鬱不樂。「才怪咧,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其實是我的老哥兒們米契•克魯格啦。我們退休之後,他手頭一直很緊,日子不好過。現在他被房東掃地出門,昨天晚上來找我吐苦水。當然啦,就像我跟他講過的,要不是他把房租都拿去喝酒了,也不必為了房租傷腦筋。不過這些都是題外話。重點是他一向不是小器的人,懂吧。」
「我完全了解你的意思。我保證,如果這傢伙被我的風采迷得血脈賁張,我會念及咱們的交情和他的年齡,想法子澆熄他的熱情,絕不打斷他的手。好啦,把你的衣服收走,讓我看看咱們的寧靜女神犬怎麼樣了。」
他不情願地讓我進門。他家的格局和我家一樣,像四個貨車車廂串在一起。從廚房進去就是飯廳,再來是一個小過堂,你可以從那裡進臥室、浴廁和客廳。
米契正在客廳沙發上鼾聲大作,蒜頭鼻,嘴巴微張,一隻手垂下來,指尖碰到地板。毯子沒有完全蓋住他濃密的花白胸毛,露了一點出來。
我努力假裝他不存在,逕自蹲在沙發邊,在襪子臭味中看著窩在沙發後的珮皮。她側臥在一堆報紙中間。她這幾天幾乎都在扯爛報紙,堆在康特拉先生摺成一疊的毯子上面。她見到我,把頭轉開,不過尾巴無力地拍了一下地毯,示意她沒有不高興。
我站起身。「我想她沒問題。我回去煮咖啡,等一下再來。不過別忘了,你千萬不能插手,不可以靠過去摸她哦。」
「用不著妳教我怎麼照顧她。」老先生吼說:「不是只有妳聽到獸醫的指示,我也聽到了。在妳不曉得出城幹啥大事業的時候,我還帶她去檢查過咧。」
我陪笑臉,「好啦,我知道了嘛。我不曉得她對你老朋友的電鋸魔音做何感想,不過換成是我,我會食不下嚥。」
「她又不吃東西。」他回嘴,然後臉色豁然開朗:「喔,我懂妳的意思,好,我會把米契弄進房間,不過在我幫他轉移陣地的時候,我不要妳在旁邊當觀眾。」
我扮個鬼臉:「誰要看哪!」天曉得他那些油膩膩的胸毛下面是啥模樣,如果讓我看到,我恐怕會吐。
回到家裡,我頓時覺得累到沒力氣煮咖啡,更別說去安撫康特拉先生的準爸爸焦慮症。我把染血的床單剝下來,踢掉跑鞋,躺到床上。
再度醒來時已經將近九點。除了啁啾鳥語和待產的珮皮,門外的世界安靜無聲。難得碰上一次市聲俱寂的時刻,就是在這種時刻,一個都市居民心中會湧現祥和的感覺。我盡情享受那片刻時光,直到尖銳的煞車聲和喇叭聲劃破靜謐。外面傳來忿怒的叫罵,看樣子我們拉辛街又有車禍了。
我起床到廚房煮咖啡。五年前我剛搬來的時候,這裡是寧靜的藍領地段,也就是說我還負擔得起。如今這裡興起了老屋重建的狂潮,可愛的店鋪如雨後春筍似地開張,以滿足這些人的高尚品味,結果房價連漲三倍,交通流量變四倍。我只希望剛剛出車禍的是寶馬,而不是我鍾愛的龐蒂克。
我沒如常拉筋,反正今天早上沒空出去慢跑。我很有良心地穿上胸罩才套上毛邊短褲和運動衫,然後重回產房。
康特拉先生應門的速度之快出人意料。他滿臉愁容,我不禁納悶是不是該上樓回家拿車鑰匙和駕照。
「她沒有動靜耶,小可愛。我真的慌了。我打電話去動物醫院,可是今天是禮拜六,醫生十點才上班。他們說情況不緊急,不能給我醫生家裡的電話。要不要換妳來打,看妳能不能逼他們講?」
我暗暗竊笑。不得了啦,老先生竟然覺得我也有比他吃得開的時候。「先讓我看看她吧。」
我們穿過飯廳到小過堂。克魯格的鼾聲從臥房門口傳來。
「你把她弄進房間的過程順利嗎?」喧譁的環境可能會使狗過度焦慮,因而難產。
「妳在暗示什麼?我一向以公主殿下的福祉為優先考量。妳不用批評我,現在批評也沒用。」
我忍著沒吭聲,跟他到客廳。狗躺在原地,姿勢和我上樓時一樣,但我瞥見尾巴周邊有一灘暗紅的血正在擴散,希望這表示分娩有了進展。珮皮看到我盯著她,但完全不理我,只把頭探到身體下面,舐淨自己。
這樣正常嗎?獸醫說不要插手,但萬一我們看不出她出狀況,放任牠難產,那該怎麼辦?
「妳覺得她狀況怎樣?」康特拉先生心焦地問,臉上和我一樣發愁。
「我根本不了解小狗的生產過程。再二十分鐘就十點了,我們不如等醫生上班,我先回家拿車鑰匙,以防萬一。」
正當我們決定幫她在車上弄個應急用的墊子,以防我們得送她去急診,第一隻小狗就出世了,過程真是如絲緞般滑溜順暢。珮皮連忙把寶寶叼到面前清掉胎衣,然後用口鼻和前腳把牠安置在身邊。第二隻小狗到十一點才出現,之後每隔半小時左右出來一隻。我開始想珮皮會不會像獸醫講的,連生十二隻。不過到了三點左右,第八條小生命推擠著找到乳頭,珮皮停止分娩。
我伸個懶腰,到廚房看康特拉先生為她準備一大碗乾狗糧,混入炒蛋和維他命。我跟他說話,但他全神貫注地準備狗糧,既沒回答賭城之夜好不好玩,也沒回答米契•克魯格的事。
我想這會兒我是多餘的第三者。有幾個朋友約我今天去打壘球,到蒙特羅斯港野餐,我跟他們說我盡量看能不能過去。我打開門鎖。
「妳有事啊,小可愛?妳要出去喔?」康特拉先生短暫地停止攪拌的動作。「那妳去吧。放心,我會照顧好公主。嘿,八隻耶。」——他自顧自露出喜色——「怪怪,生了八隻欸,真是厲害。」
我關上他家後門,門後便傳來老先生五音不全的聲音。我爬樓梯回家,走到一半才意識到他是在唱歌。我想歌名是「哦,多麼美麗的早晨。」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守護天使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0 |
二手中文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英美文學 |
$ 27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守護天使
第一章 單身女郎的床第 一個個熱吻落在我臉上,將我從沉睡中拉到清醒邊緣。我咕噥著直往被窩裡鑽,想重新回到甜美的夢鄉。但我的伴侶不想休息,鑽進被子裡繼續火辣求愛。 我用枕頭蒙住頭,卻聽到小狗珮皮可憐兮兮地哀叫。我霍然清醒,轉頭瞪她:「現在還沒五點半欸,妳不可能想起床的啦。」 她不甩我,不聽我的話,不管我拚命想將她推下我的胸口。她只睜大了棕色的眼睛痴痴望著我,嘴巴微開,伸出紅潤的舌尖。 我露出慍色,嚇得她來舔我鼻子。我坐起來,將她的頭從眼前推開:「就是妳沒事亂舔亂舔的,才會惹我生氣啊。」 見到我清醒,珮皮...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莎拉‧派瑞斯基 譯者: 謝佳真
- 出版社: 天培 出版日期:2007-06-10 ISBN/ISSN:9789867759597
- 頁數:384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