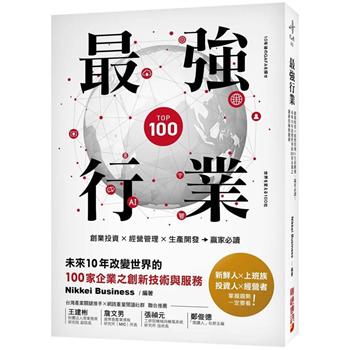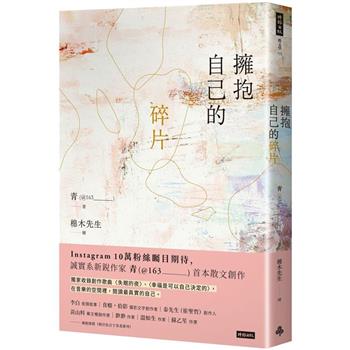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大門口的陌生人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5 |
二手中文書 |
$ 220 |
中國歷史 |
$ 220 |
中國歷史 |
$ 225 |
清史 |
$ 225 |
社會人文 |
$ 23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清代中國的主要「大門」是廣州。「陌生人」(Stranger)的另一中文意思是「外國人」。顧名思義,《大門口的陌生人》是與外國人闖入中國大門的歷史有關的,也是關於鴉片戰爭和外國對中國的侵略的著作。然而這本書的特點在於,它主要不是正面研究鴉片戰爭和英國侵華史,而是以英國侵略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為線索,研究這一歷史時期廣州和廣東省的社會動態,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的各階級、各社會集團如官府、士紳、團練、農民、宗族、秘密社團等對外國的態度、各自的活動、相互間的關係以及這些態度、活動和關係的變化,從而揭示中國近代史開始階段的某些趨勢。這是一種別開生面的研究。這種觀察歷史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對我們很有啟發意義。 在中國近代史領域裏,我們不乏關於帝國主義侵華和關於國內政治鬥爭、革命鬥爭歷史的優秀著作,但它們大抵限於研究侵略和被侵略關係的事實本身、研究這些政治鬥爭、革命鬥爭本身,而較少注意它們所引起的中國社會內部各種成分的動態和變化。這當然不應苛求這些著作,它們本來可能就是以探討這些事實為己任的。問題在於我們的全部歷史研究過分地專注於政治史、政治鬥爭史而忽略了研究社會、研究社會史的意義。關於歷史的內容和研究的物件,事實上有各種不同的理解。我贊成「歷史就是過去的社會」的看法。如果歷史只是過去的政治、對它的研究不擴展及於過去社會的各方面,那麼,對過去的認識肯定至少是不全面的。《大門口的陌生人》的作者以「社會史的觀點研究外交史」,啟發我們認識到歷史研究層面之寬廣;對於中國學者說來,只要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即使是一個似乎已很熟悉的課題,仍然可以發掘出深入的歷史認識而不致有山窮水盡的困惑。 魏斐德教授對太平天國的性質和根源提出問題,層層追蹤,結果變成了「另一種研究,即分析一個新的歷史單位:廣州、廣東、華南」(見本書「導言」)。他提出了「致力於地方史研究」的呼籲。這一見解對發展中國近代史研究也十分有益。中國歷史上各地區的發展狀況,尤其在近代,是很不平衡的;我們需要就社會經濟文化的和自然的、行政的、民族的差別進行地區性的研究,才足以認識過去中國的全體而不致發生偏頗。研究地方史同樣需要有廣闊的歷史視野,才不致將地方史都寫成全國政治史的地方版。《大門口的陌生人》研究廣東。作者在廣東的商館、公行、總督之外,見到了廣大的華南社會,發現了「在官方歷史的表層之下,萌發著民眾的恐懼、希望和運動」。對歷史進行這樣的深入發掘,值得我們認真借鑒。 《大門口的陌生人》全書分四篇。第一篇研究鴉片戰爭期間官府、士紳、團練對英國侵略者的態度和當時中國人的排外情緒,認為三元里抗英事件並非農民的自發行動而是官府倡辦團練和士紳領導的結果。第二篇研究《南京條約》以後廣州城鄉人民長期的反入城鬥爭,包括中、英官府對問題的對策、團練運動的起伏、商人抵制的經濟背景和一八四九年反入城鬥爭勝利的社會政治後果。作者認為城市團練的出現和商人參加反入城鬥爭是英國的經濟蕭條波及廣州的結果;官方利用團練取得反入城鬥爭的勝利,削弱了原有的統治秩序而助長了農村的動亂。第三篇研究一八五○—一八五六年間的「地方主」,即宗族、秘密會社勢力的增長和紅巾軍(天地會)造反以及廣東的形勢同太平天國起義的關係。作者認為,外國入侵促使官府倡辦團練,團練的興起有利於地方士紳力量的擴張,同時又削弱宗族的血緣聯合,增強窮苦農民之間的聯繫。太平天國的進展和天地會起事的失敗,都進一步地發展了地方主義,最終促使清王朝垮臺。作者在第四篇中又強調指出,即使朝廷下令要求採取集體行動以驅趕佔領廣州的外國人,「也不能消釋二十年積累起來的地方主義」。這一篇以「合作主義的政治」為題,探討了廣州被占期間的社會動態,認為這時士紳已把聯軍視為真正的對手,三角洲地區的農民也接受他們作為實際的統治者;並認為當時廣東的現狀,是歐洲帝國主義發展到頂峰時將在全中國發生的情況的縮影。 我們很瞭解廣東。作為中國人與歐洲人交往的地點,它已被人們詳盡地研究過了。它的商館,它的公行,它的總督,在遊記,在官方的檔案及外交史中,都有過記載。但在這些苦心經營的商人及行政機構的周圍,還有著更廣大的南中國社會,在那動亂的年代裏也在醞釀發酵中,文人為中國軍隊的無能而煩躁,地主組織團練,佃戶參加秘密社團,各個家庭為爭奪當地的財富與勢力互相爭鬥。簡而言之,在官方歷史的表層之下,萌發著民眾的恐懼、希望和運動。 當然,並沒有兩個不同的世界。絕不可能在這種地方歷史與民族的或帝國的或世界的歷史之間劃一條簡單明瞭的界限。但難道不正是這一匯合畢竟造成了此時此地的歷史嗎?中國村民向一個英國人投石頭,巴麥尊(PalmersTone)在倫敦白廳發怒,白廳向北京施加壓力,廣東省的一個農民被斬首。地區發生的事情編織進了世界歷史,中國發生了變化。 結果是,研究太平天國的根源,成了另一種研究,即分析一個新的歷史單位:廣州、廣東、華南—它有著自己的一致性。 讓我們致力於地方史的研究吧。
- 作者: 魏斐德
- 出版社: 時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06-01 ISBN/ISSN:986776234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0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