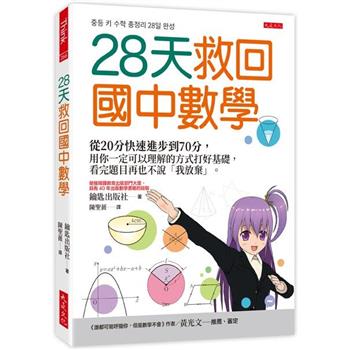作者自序
我是從自己女兒的眼睛去讀這本書的。
接觸兒童文學的人,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吉卜林吧!還記得小時候初接觸到《叢林奇談》時,就為裡頭那個充滿神祕的世界感到新奇有趣,更不用說在孩提時代擔任童子軍的那段時間,對「毛克利」這個名字有多麼熟悉了!
不過,比起《叢林奇談》、《小吉姆的追尋》、《勇敢船長》這些故事,我卻是在長大成人後才接觸《原來如此的故事》這本書的。那實在讓人感到有點難堪,因為當我初次看完這本書後,我發現自己腦袋中想的竟然是:小司圖魚是什麼魚?為什麼我google不到這種魚?為什麼咬小象鼻子的是鱷魚?為什麼是「拜火教徒」?這些安排背後是否有什麼意義?在作者的時代與生活背景裡,這些又各自代表著什麼?那很糟,因為我發現自己似乎對「故事意義」的關注度遠大於「自己對這個故事有什麼感受」。再者,當我試圖去思考自己對故事有什麼「感受」時,我發現我竟說不出自己喜不喜歡這個故事。
我知道它是經典,我明白這本書的背景,我甚至買了三個不同版本的《原來如此的故事》,我知道它充滿著想像力與趣味,我也覺得這些故事「很可愛」、「充滿童趣」,但我卻說不出自己到底喜不喜歡這個故事。
原來,我已經是大人了。
我知道象的鼻子是演化所導致的,我也明白衣索比亞在哪兒,更因為寫另一本小說而閱讀過拜火教的歷史。於是,故事裡那些名詞背後所帶著的神祕感──就如同童年初讀《叢林奇談》時腦中所浮現那個充滿新奇的世界,就這樣隨著時間與一本本的理論書而消逝不見了。那很糟,因為我必須喜歡這些故事,必須喜歡這本書,但「喜歡」是不可能勉強的,也不是靠「理解」而來的。
於是我把小魯版的《原來如此的故事》拿給才上小學的女兒,原本就很愛看書的她很高興地接了過去,然後開始一篇篇故事慢慢地讀下去,不時還發出誇張的笑聲。
「這本書很有趣嗎?」我問,即使我已經知道她會怎麼回答。
「有趣。」她一邊笑一邊回答我。
「那麼,妳喜歡這本書嗎?」
「很喜歡。」
「為什麼呢?」我笑咪咪地問。
「因為這本書很好玩啊!」她仍是一副開心的樣子。
有趣?好玩?嗯,我也這麼覺得,而且要我形容的話,我還會再多加一個「可愛」,不過這些理由對我而言還不太足夠。於是我繼續讀,繼續閉上眼去想像書裡的每個角色、每個畫面,試圖去找出我心中躲起來的那個小孩,要他跳出來好好讀這本書,然後告訴我他如何喜歡這些故事。
但我腦海中浮現出的,卻不是神祕的亞馬遜叢林,也不是所羅門王的花園,而是有張小木床,一旁點了盞溫暖的小燈,還有一位戴著眼鏡、嘴上留著小鬍子的父親,正溫柔地對他心愛的女兒訴說一個個充滿想像與趣味的故事──即使在現實裡,吉卜林是沒辦法真的把這本書讀給他過世的女兒聽。
於是再讀到森林、沙漠與海洋時,這些場景又再披上一層更豐富的色彩,但這些故事的色彩,不是僅僅來自於文字內的豐富想像,而是來自於一個父親所期待的,自己孩子在聽到這些故事之後那充滿期待與喜悅的眼神。
孩提時的我讀不出這種味道,但現在的我卻完全能理解,當一個父親在訴說這個故事時,心裡的感受會是什麼。一本經典,並不只是給某個年紀的人讀,而是當你在不同的時期去讀,都會讀到不同的意義與感觸,那種意義並不是由作者決定的,而是身為讀者的你自己決定的。
於是我終於知道我該怎麼表現這個故事了,那會是一段旅程,一段追尋過去的旅程。於是我選了霏兒,讓她在這個故事裡尋找自己最想念的那個人,正如同吉卜林渴望在故事裡尋找自己女兒的身影那樣。
「把拔,那你喜歡這本書嗎?」後來有一天,我女兒看著我桌上堆著的書問我。
還記得當時的我摸了摸她的頭,微笑地對她說:
「喜歡。」
風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