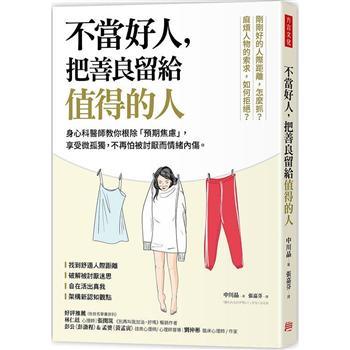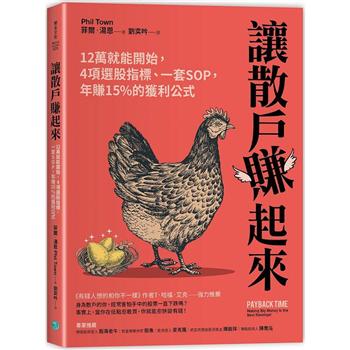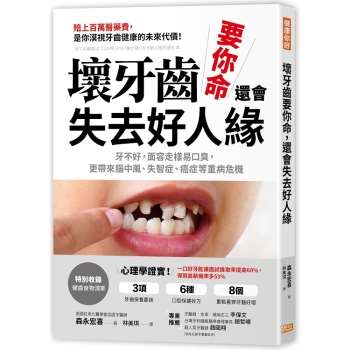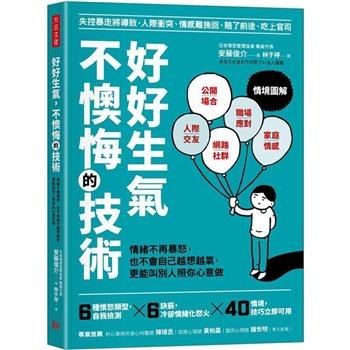施米特《憲法的守護者》導讀
劉 鋒
在近年關於施米特的研究和論爭中,可以發見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對施米特的關注經常來自左派陣營。有一本題為《施米特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的論文集,裡面的所有撰稿人都從左派立場出發探討施米特的思想,尤其著眼於他對自由民主制度的解析和批判。主編穆福(Chantel Mouffe)在前言中說,雖然施米特有不可原宥的道德污點,但是,如果僅僅因為他曾經支持希特勒就將他的著作棄置一旁,我們便失去了許多可資重審和反思自由民主制度的真知灼見。
實際上,即便出於加強自由民主制度的目的,也不能忽視施米特的思想。穆福在同書的一篇論文《施米特和自由民主制度的悖論》中還引述了羅爾斯(John Rawl)的觀點:魏瑪憲政崩潰的部分原因在於,一批德國精英不再相信議會民主制的可行性。這就促使人們認識到,若欲維護正義的、良序的憲政民主,必須對它作出令人信服的充分論證。就施米特而言,羅爾斯的觀點或許在某個限度內是有道理的:魏瑪憲政的實際運行導致了多元主義的分裂局面,從而危及共和國的政治存在。
不過,我們必須看到,施米特在魏瑪共和時期撰寫的大量著作都有維護憲法的明確意圖,力圖將魏瑪憲政從多元主義的分裂局面中解救出來。毋庸置疑,施米特對自由主義作了釜底抽薪的批判,但這種批判卻透露出施米特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深邃洞察,因而從消極的方面構成了反思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契機。
施米特在魏瑪共和時期寫下了《論專政》(1921)、《政治的神學》(1922)、《當今議會制的思想史狀況》(1923)、《羅馬天主教與政治形式》(1923)、《政治的概念》(1927,1932)、《憲法學說》(1928)等膾炙人口的名著,這些論著大都具有思想史的廣闊視野,其中透出的博學、睿智和深度每令研究者驚歎不已。除此而外,還有三種論著被歸入實際政治的範疇:《〈魏瑪憲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民國總統專政權》(1924)、《憲法的守護者》(1931)和《合法性與正當性》(1932)。
本文擬對《憲法的守護者》略作評介,以便為閱讀本書提供一個適當的語境。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本書預設了施米特此前提出的許多重要概念,例如憲法、非常狀態、政治、主權、專政等等。因此,在閱讀本書時,就有必要將它置於施米特思想的整體脈絡中予以定位。在這裡,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在施米特的心目中,究竟何謂憲法。
按照通常的理解,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法,即所謂的“萬法之法”。憲法形成一個根本的、終極的規範系統,一切其他法律都有賴於這一系統,並由此而獲得其效力。這一憲法概念主要偏重於規範層面,基於其上的國家是一個法秩序(Rechtsordnung)。但是,如果拋開規範主義的思路,從政治層面上考慮憲法,就會產生一個完全不同的憲法概念,這正是施米特在《憲法學說》(∼Verfassungslehre&)中所欲達成的一個主要論旨。
施米特著眼于憲政秩序的前憲法要素,即政治要素。並非憲法確立了政治統一體,相反,政治統一體先於憲法而存在:憲法是政治統一體對自身的存在類型和形式作出的根本決斷。施米特在《憲法學說》的開篇刻意區分了兩個概念:憲法(Verfassung)和憲法律(Verfassungsgesetz)。憲法是憑藉制憲權行為產生出來的,“制憲行為本身並不包含任何個別規範,而是通過一次性決斷、針對政治統一體的特殊存在形式規定了它的整體結構。這種行為建構了政治統一體的形式和類型,其中已然預設了政治統一體的存在。” 因此,憲法的實質並不在於其規範性,而在於其政治性,作為一種根本政治決斷,它僅僅涉及政治統一體的存在類型和形式。
另一方面,憲法律則是一批具體的憲法法規,其有效性完全依賴于作為根本政治決斷的憲法:“憲法律必須依賴於憲法才有效力,必須以憲法為其先決條件。一切作為規範性規定而存在的法律,包括憲法律在內,都需要有一個先於它們的政治決斷,這樣才能獲得其最終效力”。 相對於憲法而言,憲法律是派生的、次要的,僅僅具有形式上和技術上的有效性,其正當性根據並不在於自身,而在於作為根本政治決斷的憲法。
憲法與憲法律的區分顯明了施米特的一個重要思想:儘管我們可以將憲法視為“根本法”(lex fundamentalis),但並非寫入憲法文本的全部內容都毫無分別地同樣根本,否則憲法就包含著一個自我推翻、自我否定的因素。例如,如果認為《魏瑪憲法》第一條(德意志為共和政體)與第七十六條(憲法可經國會三分之二的多數予以修改)同樣根本,那就意味著,可以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將德意志民國 由共和政體改為比如說君主政體。在這種情況下,這兩個憲法條款甚至談不上同樣根本了,真正具有根本性的倒是第七十六條了,這樣就會導致與《魏瑪憲法》的本旨完全相悖的荒謬結論。
事實上,如果按照第七十六條的程序來修改第一條,那就不是修改憲法,而是推翻憲法,相當於對政治統一體的存在形式和類型重新作出了政治決斷。因此,憲法修改從定義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其真正含義實際上是指憲法律修改而言,並不涉及根本政治決斷。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施米特為何對廣泛流行的形式主義憲法概念滿腹狐疑,因為這個概念將憲法分解成一系列憲法律,並賦予它們種種外在標記(例如成文憲法、繁難的修改程序等)。在這種相對化的形式主義視野下,憲法完全失去了其作為根本政治決斷的“根本法”性質。
既然憲法的意義不在於其規範性,而在於其政治性,那就首須明瞭,在施米特的心目中究竟何謂政治。這個問題的尖銳性在於,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政治經常已經蕩然無存了。有鑒於此,政治就必須與對政治的否定聯繫起來加以考慮。
施米特在不少著作中論述了現代政治的危機徵象。在出版於1919年的《政治的浪漫派》(Politische Romantik)中,施米特指出,浪漫派將一切都變成了觸發浪漫想像的機緣(occasio),他們缺乏嚴肅的道德意識和責任擔當,回避實實在在的決斷和行動,僅在單純的哲學層面上虛構一個“更高的第三者”,然後通過喋喋不休的話語增生想像性地解決現實的矛盾。
在這裡,關鍵的問題並不在於審美本身,而在於審美的無度擴張。儘管浪漫派通常並不缺乏政治激情、立場和承諾,但他們對自我的崇拜使他們昧于現實政治的實質意義,將審美邏輯伸展到非此即彼的重大決斷領域。《政治的浪漫派》已經隱約透露出施米特對議會民主制的批評,而這一意圖在出版於1923年的《當今議會制的思想史狀況》(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 Lage des heutigen Parlamentarismus)中更為明確地表露出來。
施米特認為,議會民主制根本不是民主制,因為民主制意味著人民的自我統治,即人民與其自身的同一性(Identität mit sich selbst),而議會民主制不過是將民主制與自由主義混合起來,形成一種以自由討論為基礎的體制。在這裡,不難發現議會民主制與政治浪漫派的內在關聯:“在德國人的思想中,按浪漫派的無休止交談(ewiges Gespräch)的概念更易於理解無休止的討論(ewige Diskussion)。”
議會不過是各種特殊的社會和經濟利益的代理機關,其常態運行機制是談判和妥協,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集體決定不是真正民主制下的國民“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而是議會外討價還價的結果。真正的民主制乃基於國民的同質性和同類性之上,而議會民主制則將國民分解成一些特殊的部分,並以議會為中介,調解這些特殊部分之間的衝突和競爭,達成有如“更高的第三者”那樣的妥協。因此,如同政治的浪漫派一樣,議會民主制亦從根本上取消了政治。
通過以上的描述,我們可以約略知道,在施米特的心目中,政治不是什麼。如果說議會民主制從根本上否定了政治,那麼在什麼意義上是如此?換句話說,什麼是政治的本質規定?
出版於1927年的《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就要回答這個問題。施米特在這本書的開篇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國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為先決條件”。這個命題隱含著這樣一層意義:儘管國家與政治密不可分,但兩者卻不是相互等同的,政治是比國家更加基要的概念。
在現代,由於國家與社會的相互滲透,“那些一直屬於國家事務的東西隨之變成社會事務,反之,那些純粹屬於社會事務的東西則變成了國家事務”,在這種情势下,將政治與國家簡單等同起來,就顯得尤其荒謬。
因此,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並不是要界定國家,而是要界定政治,而界定政治的關鍵就是要確立政治的標準。類似的標準可以在人類思想和行動的其他領域中發現,例如,道德領域的標準是善與惡,審美領域的標準是美與醜,經濟領域的標準是利與害。政治領域也有一個屬於自身的標準,一個不依賴於其他領域的獨立標準。
正是在這裡,施米特提出了一個核心思想:政治的標準是劃分敵友。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施米特所說的敵人不是仇敵(inimicus),而是公敵(hostis)。敵人的內涵必須從政治上予以把握:“政治敵人不一定非要在道德方面是邪惡的,或在審美方面是醜陋的;他也不一定非要以經濟競爭者的面目出現,甚至與政治敵人擁有商業往來會更加有利。”
但是,政治敵人之成其為政治敵人,就在於敵人是“自我”得以界定的邊際條件,敵友在生存論上的差異確立了自我的身份認同,或者說,敵人是作為自我的他者而出場的。進而言之,敵友之間永遠處於潛在的衝突中,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存在本身就對其他政治共同體構成威脅,有鑒於此,衝突乃屬於政治的本質規定。這樣,我們便可以看到,每個政治共同體都要通過與之相對峙的其他政治共同體而獲得自我界定,並由此而確立其認同基礎,用邁爾(Heinrich Meier)的話來說,“敵人在我們面前顯得是我們的認同的保證人。當我們找尋自身,他就與我們相遇”。
在極端的情形下,政治共同體的衝突潛勢會轉化為公開衝突甚至戰爭,這種對他性存在的否定有時是無可規避的,因為“只要敵人這個概念仍然有效,戰爭便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敵友區分對其他次級概念造成了一系列邏輯後果,在此僅以施米特對平等的論述為例,即可略見一斑。施米特在《憲法學說》中討論了不同類型的平等,其中流行最廣的就是人人平等的理念。這種平等並不考慮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民族等區分,而是立足於普遍人性的基礎之上。施米特認為,這種普遍的人類平等屬於自由主義的範疇,而與政治無涉,因為它“既不能為一個國家奠定基礎,也不能為一種政體,一種政府形式奠定基礎。”
另一方面,民主制的平等則是一個政治概念,它必然包含著一個相反的關聯概念,即不平等。從政治的視角來看,沒有不平等,就不會有平等,平等是相對於不平等而確立起來的。在這裡,根本不存在人人平等的問題,如果硬要說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平等,那也只能是全體國民的普遍平等。“國民”概念已經隱含著一種區分,與之相反的關聯概念是“非國民”、“外國人”、“外邦人”等,沒有哪個政治統一體會授予非國民以國民的平等政治權利。因此,民主制的平等作為一個政治範疇,乃是指全體國民的平等而言,其指涉範圍僅限於內部,而排除了外部。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平等與不平等、國民與非國民、內部與外部的區分是敵友區分的邏輯後果,突現了政治的衝突潛勢。民主制的平等乃是實質性平等,立足于國族的同質性和同類性之上。離開了這種實質性平等,其他形式的平等,例如法律上的平等、平等的選舉權、平等的投票權、普遍的服役義務、擔任公職的平等機會,就無異於虛幻的空中樓閣。施米特的這番論述進一步昭示出自由主義平等理念的非政治性,因為這一理念恰恰取消了政治。
從政治的觀點出發,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麼施米特說憲法是一個政治統一體對自身的存在類型和形式作出的總體決斷。政治統一體是封閉的,具有所謂的“不可穿透性”( Undurchdringlichkeit)。沒有哪個政治統一體能夠代替另一個政治統一體制定憲法,制憲權主體——不管是君主,還是人民——只能來自政治統一體內部。正因為如此,施米特反復強調各種國際法或國際法協議不能構成實定憲法的內容。
維護憲法,實際上是維護一個政治統一體的存在形式。可以設想,如果一國內部發生了革命,就會對現行憲法構成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就存在著兩種可能性:或者革命被遏制下去,從而維護了既定憲法,或者革命成功,從而用一部新憲法取代了舊憲法。不管屬於哪種情況,政治統一體的存在都是確然無疑的,即便發生了憲法更替,那也僅僅及於政治統一體的存在形式,而不及於政治統一體的存在本身,因為新憲法的設立仍然預設了政治統一體的存在。這一點進一步突現了憲法的政治意義,而非規範意義。
憲法預設了政治統一體的先行存在,體現出政治統一體對其存在類型和形式的自主選擇。不言而喻,政治統一體的當務之急就是維護自身的政治存在,維護一切涉及政治存在的價值和理念,或者用斯賓諾莎的話來說,in suo esse perservare(維護自己的存在)。
然而,在近代市民法治國的體制下,這個問題卻變得越來越模糊。在許多人眼裡,法治國似乎主要以維護個人自由為指歸。施米特在《憲法學說》中討論了近代法治國的兩個法治國要素:分配原則(Verteilungsprinzip)和組織原則(Organisationsprinzip)。
分配原則旨在維護先於國家而存在的一系列自由權利,其根本要義是,個人自由原則上不受限制,相反,國家干預個人自由的權力原則上要受到限制。為了實行此一分配原則,就必須有相應的組織原則,即必須對諸項國家權力進行區分,實行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分立,以便它們能夠相互監督、相互拘束。分配原則和組織原則構成了近代憲法的法治國要素的主要內容,當然也就符合市民階層的自由理念,但是,基本權利乃是個人面對國家時享有的自然權利,既然它先於國家而為個體所自然擁有,它就是一切個體共享的一種普遍權利,而不問個體所屬的民族、國家、宗教、團體為何。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認為國家的存在理由就是保護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通過權力分立的組織手段),那就從根本上誤解了國家的性質。事實上,近代法治國不僅包含法治國要素,而且還包含政治要素,離開了政治要素,法治國就不成其為一個政治統一體了。
在這個脈絡下,施米特論述了兩項政治原則:同一性(Identität)和代表(Repräsentation)。同一性與民主制有著密切的關聯,它意味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治理者與被治理者沒有本質的區分,絕對的同一性就是絕對的民主制。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絕對的同一性只是一種理想,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單憑同一性原則而組織起來。除同一性原則而外,國家還必須實行另外一項原則,即代表原則。
這裡所謂的代表並非私法意義上的代理(Vertretung),其對象是整個政治統一體,而不是政治統一體的任何個別部分或片段。代表具有存在的意涵,它意味著在公共層面上對整個政治統一體的人格體現。絕對的代表制就是絕對的君主制(朕即國家),不過,即便在民主制的條件下,也必然存在著代表因素,同一性和代表是兩項相反相成的原則。如果說君主制是以君主作為政治統一體的代表的話,那麼,民主制就是以每個選民和擁有投票權的公民作為政治統一體的代表。
總而言之,近代法治國憲法必然同時包含兩個要素:法治國要素(分配原則和組織原則)和政治要素(同一性原則和代表原則)。在這個意義上,法治國憲法只能是混合憲法。
如前所述,在民主制的條件下,每個公民理論上都是政治統一體的代表。不過,近代自由主義政制的一個後果就是,公民日益喪失了自己的代表身份,尤其是隨著秘密個別表決程序的引入,公民恰恰在需要針對政治統一體作出重大決斷的關頭變成了私人。如果以為代議制下的議員是政治統一體的代表,那也不過是天真的向壁虛構和一廂情願,因為在近代自由主義政治體制下,議員早已不復為全體人民的代表(Repräsentant)了,而是偶然的私人利益的代理(Vertreter)。
但是,政治統一體必須維護自身的政治存在,在遇到內部騷亂和外部入侵的非常時刻,必須有一個實體能夠代表整個政治統一體作出非此即彼的重大決斷。這樣,就根本不可能回避霍布斯那個咄咄逼人的嚴峻問題:誰來決斷?(Quis judicabit?)
決斷權根本上是一種主權,其性質和內涵可經由神學概念予以把握。在施米特看來,近代國家的一切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的神學概念。這一類比思路固然受施米特本人的天主教背景影響,不過,強調政治與神學的平行性,其旨趣並不在於神學,而在於政治。施米特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信教者,他與天主教會及其神學傳統的關係主要是以政治為中介的。
施米特在《政治的神學》(Politische Theologie)中詳細描述了政治與神學的這種平行或類比關係:全能的上帝變成了全能的立法者,神學中的奇跡變成了法理學中的非常狀態。這種類比為施米特提供了觀察政治的一個視角,突現了政治的一個基要問題:主權。
在近代歐洲,隨著大眾民主政治的興起,主權概念早已被弄得模糊不清了。但是,主權問題並沒有從政治場域中消失,每當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時,這個問題就格外清晰地彰顯出來。如此看來,主權概念必須在非常狀態的視點下予以界定,這就是施米特在《政治的神學》開篇的那個著名論斷的含義:主權就是決定非常狀態。
與施米特同時或稍前的一些法學家刻意淡化、消解或排除主權問題,例如凱爾森等實證主義者將國家視為一個封閉的、客觀的法規系統和秩序,於是,主權作為一種無根據的決斷,就不過是法律之外的政治或心理現實,根本不屬於法學的對象領域。
實際上,如果從國家的常態運行來看,國家的一切活動似乎都可按法律的規範程序予以實施,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回避一個問題:每當出現法律解釋上的疑義、隙縫和爭端時,誰有權作出裁斷。更何況國家一旦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就必須採取一切手段——哪怕是超逾法律常規的手段——來維護自身的存在。如果說主權在常態下通常是隱而不彰的,它在非常情況下就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突出問題。因此,只有以非常情況為參照點,將主權當作一個極限概念(Grenzbegriff)來考慮,才能理解其實質內涵。
鑒於主權是與非常狀態聯繫在一起的,對它的行使就必然超越、甚至打破既定的法律秩序,但看似悖論的是,打破既定法律秩序的目的恰恰是要恢復既定法律秩序。施米特在《論專政》(Die Diktatur)中將古羅馬的專政制度視為模範:每當國家處於危急狀態時,元老院就請求執政官任命一位專政官以採取臨時專政措施,並授予他在專政期間不受限制的權力。這種權力的行使通常有一個固定期限,一旦指定的任務完成,即告終止。施米特將這種旨在恢復既定秩序的專政稱為委託專政(kommissarische Diktatur),不同於旨在確立一個新秩序的主權專政(souveräne Diktatur)。
如同施米特的許多著作一樣,《論專政》看似思想史論著,其實是針對魏瑪共和國的衝突現實有感而發,施米特在撰寫這部著作時念茲在茲的是《魏瑪憲法》第四十八條關於總統專政權的規定。
在魏瑪共和初期,艾伯特總統經常動用這個條款來處置緊急事務(例如平息右翼和共產黨叛亂、解決經濟危機,等等)。按照《魏瑪憲法》第四十一條,總統由全體德國人民直選產生。這意味著,第四十八條的專政權乃由人民授予總統,因而屬於委託專政的範疇。總統在行使此項權力時可以臨時中止涉及基本權利的若干憲法條款,這一行動突現了自由與權威的張力。
一般人僅僅看到《魏瑪憲法》的自由主義外殼,仿佛立憲的根本宗旨就是要保護公民的基本自由不受公權力的侵犯。這一思路顯然承襲了對市民法治國的意義的傳統解釋。但是,施米特強調的是,市民法治國首先是國家,而只要存在國家,就不能回避主權、專政、權威等問題。《魏瑪憲法》作出總統專政權的規定,這一事實本身就使那種僅從自由主義和市民社會的角度解釋憲法的企圖顯得十分可疑。關於總統專政權是不是單純的委託專政,這個問題在研究施米特的學者中間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在此暫不涉及。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施米特是在非常狀態的視點下討論總統專政權的。這意味著,總統專政權與市民社會的自由理念並非勢不兩立,如果國家的存在岌岌可危,個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就不過是空幻的泡沫詞藻。
我們在前面撮要介紹了施米特對政治、憲法、主權、非常狀態、專政、決斷等問題的有關論述,主要是為閱讀《憲法的守護者》提供一個必要的背景;實際上,一旦對施米特的這些思想有了一個基本瞭解,就可以大致推知施米特在《憲法的守護者》中究竟要討論什麼問題,又是如何討論這些問題的。誠然,政治形勢的發展和變化會給施米特的思考注入新的內涵,令其達到新的強度,但施米特的思想有一個前後一貫的脈絡,則是毫無疑義的。
從非常狀態的視點出發解釋總統專政權,這一思路貫穿于魏瑪共和時期施米特的大量論著中,並且隨著共和國危機的加劇而得到不斷強化。《憲法的守護者》(Der Hüter der Verfassung)最早作為單篇論文發表於1929年,隨即經過大規模擴展,以專著的形式出版於1931年。當時正值魏瑪共和國搖搖欲墜的時刻,空前的政局動盪、經濟危機賦予非常狀態的概念以一種迫近的現實感。面對風雨飄搖的局面,施米特提出了一個類似於“誰來決斷”的嚴峻問題:誰來維護憲法?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馬上會浮現出美國最高法院的典範形象,因為美國最高法院行使的司法審查權似乎確立了它作為憲法守護者的地位。施米特指出,這是一種源於對美國最高法院的過度想像而形成的嚴重誤解。其實,美國最高法院只能基於一般規範對特定訴訟案件作出判決,審查法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並且在個案中拒絕法律的適用。在這裡,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是在正常狀態下產生其效力的,一旦遇到非常情況(如南北戰爭中關於奴隸制和通貨膨脹的政治爭議),就連美國最高法院的權威亦相當有限。因此,“法院的作為,不能以經濟繁榮和內政穩定的時期去評價,而必須把危急動盪的時刻也納入考量”。
如同主權一樣,憲法的守護者只能在非常狀態下獲得其真正的意義,而司法機關由於受既定法律規範的拘束,因而根本無力承擔此種職能。就其實質而言,非常狀態涉及到的並非司法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與既定法律規範的強制要求相比,政治統一體的存亡絕續才具有刻不容緩的緊迫性質。如果說主權就是決定非常狀態,那麼,這個危急時刻需要的顯然不是一個通過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處理法律實務的機關,而是一個能夠超越規範而作出即時的最後決斷的實體。在非常狀態的視點下揭示憲法守護者的意義,認為對憲法守護者的籲求乃是政治秩序危機的表徵,這是《憲法的守護者》的一個根本論旨,讀者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