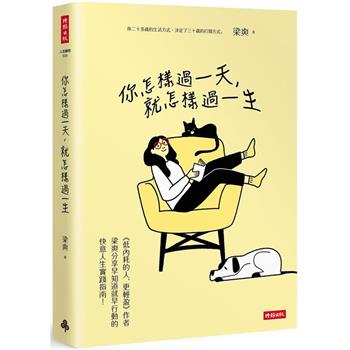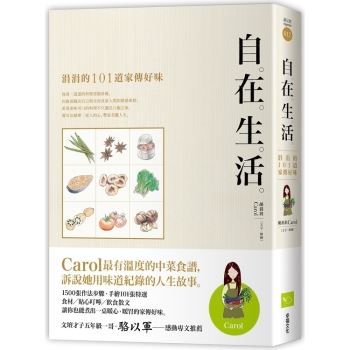五○年代連串的政治災厄,破滅了鄒族人對新時代的理想與美夢。
八八災難的奔騰大水,又傷害刻畫著祖先足跡與記憶的土地。
然而,伐依絲未曾忘記幽默與感謝。
「幸好,樂野部落的土壤,從來不受政治力的影響,不論栽種何種作物,都兀自長得風華茂盛,滋味深遠。當年的農業講習所雖然已渺無蹤影,但土地仍有記憶,本土的、外來的、實驗的、創新的,都在季節的更迭下,融入了我們的生活之中。」
她的書寫,彌補了那個時代部落底層歷史的空白。──監察院副院長 孫大川
我完全能感受她「鄒族女人的心」那樣深沉的痛,模糊了文字默默陪著書中的她心痛落淚。──作家 里慕伊‧阿紀
伐依絲以小女孩童稚之眼,回憶童年與林野坡谷為伍、嘗遍新奇事物的歡快自在,也描繪著族人不理解的政治紛擾,無端將鄒族人捲入太平洋戰爭與白色恐怖,換來無數家庭破碎的時代悲劇。
「國家」何其遙遠,平地都城裡的爭鬥來到阿里山,都成了不明所以的政令與罪行。單純的族人從歡笑、疑惑、恐懼而至噤聲,都是對「國家」與政治的質疑,而緊繃時局下的幽默與笑容,則包含著生命的堅韌與智慧。
時光轉入現代,伐依絲的眼光依舊溫柔。從八八風災至生活瑣事,無處不可見她對土地、萬物、族人、弱勢群體的關懷與愛惜。面對時代與文化的變化更改,伐依絲有孤寂失落,也有坦然釋懷。時代推著鄒族人不得不向前迎接,「但是,流著的鄒的血是一樣的熱,鄒的心也是一樣的堅毅。」她的每一次回望,都是對鄒深切的眷戀與期盼。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火焰中的祖宗容顏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0 |
二手中文書 |
$ 180 |
小說/文學 |
$ 198 |
現代散文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現代散文 |
$ 225 |
現代散文 |
$ 225 |
文學作品 |
$ 225 |
中文現代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火焰中的祖宗容顏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伐依絲‧牟固那那(faisʉ . mʉkʉnana)
鄒族
漢名:武香梅
1942年生於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
曾任幼稚園老師、教會幹事
2000年〈木屐〉獲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佳作
2001年〈親愛的ak’i,請您不要生氣〉獲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
2005年〈火焰中的祖宗容顏〉獲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第三名
2013年〈忘了那一天是中華民國的哪一年〉獲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
著作《親愛的ak’i請您不要生氣》
伐依絲‧牟固那那(faisʉ . mʉkʉnana)
鄒族
漢名:武香梅
1942年生於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
曾任幼稚園老師、教會幹事
2000年〈木屐〉獲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佳作
2001年〈親愛的ak’i,請您不要生氣〉獲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
2005年〈火焰中的祖宗容顏〉獲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第三名
2013年〈忘了那一天是中華民國的哪一年〉獲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
著作《親愛的ak’i請您不要生氣》
目錄
序 荒謬時代的溫柔人性 孫大川
序 伐依絲那顆鄒族女人的心啊 里慕伊‧阿紀
輯一|部落童年
農業講習所
十月十日真高興
我們遠足去
光明乍現
反共大陸的童年
忘了那天是中華民國的哪一年
來拔鬍子哦
我的爸爸是兵隊桑
閹豬婆和接生公
颱風天也可以很豐饒
要記得買尿騷味的魚
輯二|生命之歌
山地文化工作隊
歌來為誰唱
火焰中的祖宗容顏
八八災難(莫拉克颱風)雜憶
災後最美麗的女人
唉啊!meoina呀!
輯三|生活見聞
青鳩聲
笨鳥老三,你要加油!
頂上功夫真好用
二○○七年的聲明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大女人
艾炙
回年輕朋友們的信
輯四|短篇小說
分屍
妳好美哦,親愛的
誓約
序 伐依絲那顆鄒族女人的心啊 里慕伊‧阿紀
輯一|部落童年
農業講習所
十月十日真高興
我們遠足去
光明乍現
反共大陸的童年
忘了那天是中華民國的哪一年
來拔鬍子哦
我的爸爸是兵隊桑
閹豬婆和接生公
颱風天也可以很豐饒
要記得買尿騷味的魚
輯二|生命之歌
山地文化工作隊
歌來為誰唱
火焰中的祖宗容顏
八八災難(莫拉克颱風)雜憶
災後最美麗的女人
唉啊!meoina呀!
輯三|生活見聞
青鳩聲
笨鳥老三,你要加油!
頂上功夫真好用
二○○七年的聲明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大女人
艾炙
回年輕朋友們的信
輯四|短篇小說
分屍
妳好美哦,親愛的
誓約
序
序
荒謬時代的溫柔人性
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每次見到伐依絲,習慣性地問:「最近有在寫作嗎?」她總是一臉歉然,「有啦,只是斷斷續續,家務事瑣碎,老太婆很多事要做啊……。」她是一個低調的人,說話實實在在,依她的個性,她一定誠誠懇懇地找出零碎的時間,一點一滴編織她文學的夢。所以,當我收到她的新作《火焰中的祖宗容顏》時,一點都不驚訝,將近二百六十頁,分四輯共二十八篇,寫作的年代從2000 年到2016 年,幾乎年年都有作品,這就是伐依絲交出來的成績。
或許是年歲的關係,自己對文學的喜好愈來愈清淡,能被感動的事物往往是那些簡單質樸的東西;華麗的詞藻、刻意經營的結構,已經不再能引起自己的共鳴。伐依絲一如往昔,保持平鋪直敘的風格,味淡而永,讀起來就像喝下一杯白開水,沖掉一肚子的油膩。
伐依絲和我二姊同年,三十一年次,她們成長的年代,親身經歷了日本戰敗、國府遷臺、二二八、清鄉、白色恐怖等等錯亂顛倒、光怪陸離的場景。作為樂野部落的鄒族人,由於親族中頗有人涉及敏感案件,因而她兒少時期受到的衝擊比我二姊大,印象也特別深刻。難能可貴的是,伐依絲寫這一段屬於有權力、男性、大人們的歷史事件,一點也不受大歷史敘述的綁架,她很自信地以一個小孩子、女人、平凡族人的視角,輕描淡寫地訴說了部落裡發生的那些事:醬油工廠、駐村參謀軍官、國慶日遊行、反共愛國歌曲、山地文化工作隊……;一個接一個的生活故事,不卑不亢地反映了大時代的變遷與形貌。在伐依絲眼中,真正的主角不是高一生或那些後來被大家追捧的英雄人物,而是部落裡飽受事件影響的平凡的族人,他們怎麼默默忍受、面對這些衝擊,並踏實地盡一切力量保護自己的孩子和家人。這是伐依絲字裡行間最令我動容的一面。有一個晚上伐依絲和堂姊相約去窺探布杜蓋的神祕醬油工廠,堂姊藉自己母親告誡的話說:「眼睛可以看,但是嘴巴絕對不可以隨便說,亂講話可要拿縫衣針線把嘴巴縫起來。」動亂時代部落的小人物,面對日本人、民國人甚至自己人都必須小心翼翼,保護自身的安全;而大人物們在鬥什麼、爭什麼,他們往往是不明所以的局外人,卻又常被牽扯在內,成了驚弓之鳥。
怎麼看待這樣的時代荒謬呢?伐依絲為我們展示了單純的族人和天真的小女孩面對人間世的智慧。他們總是可以在那些肅殺繃緊的氛圍裡找到樂趣,遠足的趣事、到奮起湖迎接蔣總統的心情,乃至山地文化工作隊巡演過程中的種種。小人物看世界自有他們獨特的視角,像是幽暗夜空中的螢火蟲,透顯著人性微弱但又強韌的生命力。在回憶這些青少年時代部落生活的點點滴滴時,伐依絲更讓我驚嘆的是,她並沒有被荒謬的政治黑霧所蒙蔽,她依然可以在周遭的事物和外來者身上,找到善意和人性的溫暖。馬老師和具有旗人身分的魏老師,東北人,不但可以讓部落青年學習比較標準的「國語」,也因為他們通日語又擅長音樂和戲劇,和家長互動良好,樂野部落因而有了不同以往的熱鬧光景。族人雖然都非常討厭那負責監管部落的「兩朵梅花」謝參謀,但是繼任的何參謀顯然對部落有著很深的善意。後來在小堂姊的告白下,伐依絲才知道何參謀其實是為尋訪「心上人」才申調到山上來的。小堂姊父母早逝,被長輩安排婚事前,曾在臺北為人幫傭,在主人家認識了隻身隨部隊來臺的何參謀,並墜入情網。然而深植的原漢情結和身不由己的親族壓力,小堂姊終究沒敢透露這段情緣。亂世中的愛情故事,伐依絲做了這樣的註腳:
「小堂姊已過世多年,我才敢寫這段沒有結局的愛情,箇中的滋味萬千,卻也展現人性不受種族地域限制的真誠與勇氣,讓我反共大陸的灰白童年,有了一個溫柔的尾聲。像樹上朵朵梅花,在冷冽的天氣裡,或在濃濃的大霧中,兀自飄送著淡淡清香。」
伐依絲後來嫁給了漢家郎祖籍四川軍中退伍的劉定剛先生,一輩子相愛相守。定剛先生多才多藝,支持伐依絲的寫作以及其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回歸。伐依絲說小堂姊的故事讓她感慨萬千,因為她最能體會大時代重壓下單純人性所要面對的扭曲與痛苦,而她是幸運的人,既沒有成為荒謬時代的犧牲者,也沒有因怪東怪西遮蔽了她平等看待「別人」的目光,維護了人性的柔軟度。
就是這樣的柔軟度,讓我合卷時腦袋裡不斷地縈繞著三十多年來臺灣族群關係被政治炒作的吶喊聲和怒罵聲。我們何時可以放下宏偉的國族論述,回到平凡的人跟人相互自由對待的關係呢?伐依絲的視角有它永恆的意義。當然,伐依絲整本書還寫了許多家人和部落的事,有不少老太婆的幽默。她的書寫,彌補了那個時代部落底層歷史的空白。她說還有許多故事想寫,我依然充滿期待。
荒謬時代的溫柔人性
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每次見到伐依絲,習慣性地問:「最近有在寫作嗎?」她總是一臉歉然,「有啦,只是斷斷續續,家務事瑣碎,老太婆很多事要做啊……。」她是一個低調的人,說話實實在在,依她的個性,她一定誠誠懇懇地找出零碎的時間,一點一滴編織她文學的夢。所以,當我收到她的新作《火焰中的祖宗容顏》時,一點都不驚訝,將近二百六十頁,分四輯共二十八篇,寫作的年代從2000 年到2016 年,幾乎年年都有作品,這就是伐依絲交出來的成績。
或許是年歲的關係,自己對文學的喜好愈來愈清淡,能被感動的事物往往是那些簡單質樸的東西;華麗的詞藻、刻意經營的結構,已經不再能引起自己的共鳴。伐依絲一如往昔,保持平鋪直敘的風格,味淡而永,讀起來就像喝下一杯白開水,沖掉一肚子的油膩。
伐依絲和我二姊同年,三十一年次,她們成長的年代,親身經歷了日本戰敗、國府遷臺、二二八、清鄉、白色恐怖等等錯亂顛倒、光怪陸離的場景。作為樂野部落的鄒族人,由於親族中頗有人涉及敏感案件,因而她兒少時期受到的衝擊比我二姊大,印象也特別深刻。難能可貴的是,伐依絲寫這一段屬於有權力、男性、大人們的歷史事件,一點也不受大歷史敘述的綁架,她很自信地以一個小孩子、女人、平凡族人的視角,輕描淡寫地訴說了部落裡發生的那些事:醬油工廠、駐村參謀軍官、國慶日遊行、反共愛國歌曲、山地文化工作隊……;一個接一個的生活故事,不卑不亢地反映了大時代的變遷與形貌。在伐依絲眼中,真正的主角不是高一生或那些後來被大家追捧的英雄人物,而是部落裡飽受事件影響的平凡的族人,他們怎麼默默忍受、面對這些衝擊,並踏實地盡一切力量保護自己的孩子和家人。這是伐依絲字裡行間最令我動容的一面。有一個晚上伐依絲和堂姊相約去窺探布杜蓋的神祕醬油工廠,堂姊藉自己母親告誡的話說:「眼睛可以看,但是嘴巴絕對不可以隨便說,亂講話可要拿縫衣針線把嘴巴縫起來。」動亂時代部落的小人物,面對日本人、民國人甚至自己人都必須小心翼翼,保護自身的安全;而大人物們在鬥什麼、爭什麼,他們往往是不明所以的局外人,卻又常被牽扯在內,成了驚弓之鳥。
怎麼看待這樣的時代荒謬呢?伐依絲為我們展示了單純的族人和天真的小女孩面對人間世的智慧。他們總是可以在那些肅殺繃緊的氛圍裡找到樂趣,遠足的趣事、到奮起湖迎接蔣總統的心情,乃至山地文化工作隊巡演過程中的種種。小人物看世界自有他們獨特的視角,像是幽暗夜空中的螢火蟲,透顯著人性微弱但又強韌的生命力。在回憶這些青少年時代部落生活的點點滴滴時,伐依絲更讓我驚嘆的是,她並沒有被荒謬的政治黑霧所蒙蔽,她依然可以在周遭的事物和外來者身上,找到善意和人性的溫暖。馬老師和具有旗人身分的魏老師,東北人,不但可以讓部落青年學習比較標準的「國語」,也因為他們通日語又擅長音樂和戲劇,和家長互動良好,樂野部落因而有了不同以往的熱鬧光景。族人雖然都非常討厭那負責監管部落的「兩朵梅花」謝參謀,但是繼任的何參謀顯然對部落有著很深的善意。後來在小堂姊的告白下,伐依絲才知道何參謀其實是為尋訪「心上人」才申調到山上來的。小堂姊父母早逝,被長輩安排婚事前,曾在臺北為人幫傭,在主人家認識了隻身隨部隊來臺的何參謀,並墜入情網。然而深植的原漢情結和身不由己的親族壓力,小堂姊終究沒敢透露這段情緣。亂世中的愛情故事,伐依絲做了這樣的註腳:
「小堂姊已過世多年,我才敢寫這段沒有結局的愛情,箇中的滋味萬千,卻也展現人性不受種族地域限制的真誠與勇氣,讓我反共大陸的灰白童年,有了一個溫柔的尾聲。像樹上朵朵梅花,在冷冽的天氣裡,或在濃濃的大霧中,兀自飄送著淡淡清香。」
伐依絲後來嫁給了漢家郎祖籍四川軍中退伍的劉定剛先生,一輩子相愛相守。定剛先生多才多藝,支持伐依絲的寫作以及其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回歸。伐依絲說小堂姊的故事讓她感慨萬千,因為她最能體會大時代重壓下單純人性所要面對的扭曲與痛苦,而她是幸運的人,既沒有成為荒謬時代的犧牲者,也沒有因怪東怪西遮蔽了她平等看待「別人」的目光,維護了人性的柔軟度。
就是這樣的柔軟度,讓我合卷時腦袋裡不斷地縈繞著三十多年來臺灣族群關係被政治炒作的吶喊聲和怒罵聲。我們何時可以放下宏偉的國族論述,回到平凡的人跟人相互自由對待的關係呢?伐依絲的視角有它永恆的意義。當然,伐依絲整本書還寫了許多家人和部落的事,有不少老太婆的幽默。她的書寫,彌補了那個時代部落底層歷史的空白。她說還有許多故事想寫,我依然充滿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