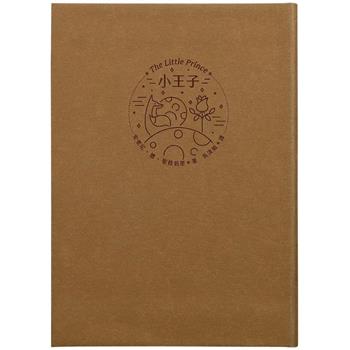人文地理學就是地方的研究。它當然也是許多其他事物,但是在直覺上,它是一門以地方為主要研究對象之一的學科。修習地理學位和課程的學生,往往會對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感興趣。儘管對地方研究有普遍熱忱,但是對「地方」一詞意指為何,卻沒有什麼深思熟慮的理解。無論就理論和哲學而言,或是對修習大學地理課程的新生來說,都是如此。地方是個看似不證自明的字眼。
地方的流行普及是地理學的機會。但這也是個問題,因為當大家談論地方時,沒有人確實明白他們到底在說什麼。地方並不是專門的學術用語,而是我們英語世界中日常使用的字眼。它是個包裹於常識裡的字眼。就某種意義來說,由於地方眾所周知,這使它較易理解。然而,就另一種意義而言,地方做為一本書的主題,這種特性卻使它難以掌握。因為我們已經認為我們知道它的意義是什麼,這使得我們很難超越常識層面,以比較成熟的方式來理解它。於是,地方既簡單(這是地方的部份吸引力)又複雜。仔細審視地方概念,以及它在地理學和日常生活中佔據的中心位置,就是本書的目的。
想想地方在日常言談裡的使用方式。「你想不想順道來我的地方(my place)?」這暗示了所有權,或是一個人和特定區位(location)或建築物的某種關連。這也讓人聯想到隱私和歸屬的觀念。「我的地方」不是「你的地方」—我和你有不同的寓所。「布里斯班(Brisbane)是個好地方」。在這裡,「地方」以一種常識性的方式指涉了一座城市,而它是好地方的事實,則多少是指地方看起來的樣子,以及它有可能成為的模樣。「她使我安於本分」(She put me in my place),比較是指社會階層地位的意義。另一個知名的成語,「萬物之所,各安其位」(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意指在具有社會–地理基礎的世界上,事物有其特殊秩序。地方無所不在。這種特質使得地方有別於地理學中自稱為專門術語的其他詞彙,例如「領域」(territory),或是並未普及於我們日常遭遇中的「地景」(landscape)一詞。那麼,「地方」到底是指什麼?
回想你初次搬進一個特殊空間,有個不錯的例子是大學宿舍房間。你遭逢特殊的樓層空間和某種氛圍。在那個房間裡,或許有些基本家具,例如一張床、書桌、抽屜和櫥櫃。這些家具是所有宿舍房間的共通設備。對你而言,它們並不獨特,除了提供你學生生活的某些必需品外,不具任何意義。但即使是這些最起碼的必需品,也有歷史。仔細審視,或許會顯露前任所有人於無所事事的空堂時刻,在桌上刻寫她的姓名。你注意到地毯上的一處污跡,是某人曾經濺出些許咖啡的地方。牆上有些油漆不見了。或許有人曾經用油灰貼海報。這些就是難以驅除的昔日居住遺跡。這個匿名空間有個歷史—這對其他人意義非凡。現在,你該怎麼做?常見的策略是利用空間來彰顯你的某些特點。增添你的財物、在空間範圍裡重新安排家具、在牆上張貼你自己的海報、特意在桌上擺放一些書。這麼一來,空間就變成了地方。你的地方。
北緯40.46度、西經73.58度,對大多數人而言,沒啥意義。某些擁有扎實地球知識的人,或許可以告訴你這意味了什麼,但是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些只是表明區位(一個毫無意義的位址〔site〕)的數字。這個座標標誌了紐約市的位置—曼哈頓中央公園南方某處。紐約或曼哈頓都是富含意義的地名。我們也許會想到摩天大樓、911事件、購物,或是相關的電影場景。以名稱來取代一連串數字,意味了我們開始接近「地方」。如果我們聽說兩架飛機飛進北緯40.46度、西經73.58度,跟我們得知它們飛進紐約、曼哈頓、雙子星大樓,衝擊程度應該很不一樣。巡弋飛彈是以區位和空間座標來設定程式。如果可以用「地方」及其含蘊的各種理解來替巡弋飛彈設定程式,那它們或許會決定導向沙漠。
靠近曼哈頓南方尖端和市中心東區,是以下東區(Lower East Side)聞名的區域(地方)。這是個以接踵而至的移民群體(愛爾蘭人、猶太人、德國人、義大利人、東歐人、海地人、波多黎各人、中國人)聞名的區域。這個地方位於聲名狼藉的五角區(Five Corners)(電影《紐約黑幫》〔The Gangs of New York, 2002〕的場景)北邊不遠。休斯頓街(Houston Street)以南是廉價出租公寓街區密佈的地方,昔日這些建築物的小房間裡擠滿了大家庭。移民引發的一連串道德恐慌,都集中在這個地方。它也曾是政治暴動和警察鎮暴的地方。這個地方的中央是湯普金斯廣場公園(Tompkins Square Park)—城市裡的一小塊自然地帶,專為大都會生活的嘈雜喧囂提供一處寧靜場所而建。公園建於1830年代,以美國副總統丹尼爾.湯普金斯(Daniel Tompkins)的姓來命名。後來,這個公園除了是兒童遊樂和宣傳戒酒的地方,也成為工會和無政府主義者示威的所在。1960年代以前,這裡是放蕩不羈的反文化者(bohemian counter-cultures)、佔據空屋居住者(squatter)和藝術家主導的下東區中心,到了1980年代,這裡又變得高尚而體面,是新文化菁英品味城市生活的地方。
不消說,房地產價格意味了這些房屋現在不是大多數人買得起的。遊民開始在公園裡睡覺。某些新進的高尚體面居民害怕這種情況,因而支持警察驅逐遊民的行動。
1986年,這座公園再度成為示威和暴動的位址。1960年代以降,居民就忙著在公園周邊空地建造八十四座社區花園。朱利安尼(Giuliani)市長於1997年將花園的職掌從城市公園局轉移到住宅、保存與發展局,目的在出售這些花園以謀求發展。1997年七月,前四座公園連同當地社區中心一起被拍賣掉。1999年五月,貝蒂米勒紐約重建基金(Bette Midlers New York Restoration Fund)和公有土地信託(Trust for Public Land),以合計四百廿萬元的總價,買下遍及紐約各地的114座社區花園,才讓花園免遭發展迫害。然而,私有化政策依舊,花園還是繼續遭到拆除。
如果你造訪現在的下東區,你可以在別出心裁或平凡無奇的餐廳、酒吧和咖啡館用餐,到精品店購物,欣賞赤褐色砂岩建築(brownstone architecture)。你可以信步穿越湯普金斯廣場公園(Tombkins Square Park),參觀殘餘的社區花園。橫越休斯頓街往南走,你可以造訪位於老舊建築物裡的下東區出租公寓博物館(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這些老房屋以前供新移民居住。換言之,你可以看到許多「地方」的表現形式。博物館是個創造不遺忘移民經驗的「記憶之地」的嘗試。花園是移民和其他人為了讓社區享受自然樂趣,努力從曼哈頓的一小塊地開拓出地方的成果。某些社區花園(通常是最早被夷平的花園)是棚屋(Casitas波多黎各社區為了複製類似「家園」的建築物而造的小房子)的所在地。這些社區花園懸掛波多黎各國旗和別處的其他象徵。老人坐在戶外曬太陽、看棒球。社區集會在這些八呎寬十呎長的建築物週邊舉行。如都市史學家海登(Delores Hayden)所述,它們是:
社區組織者的刻意選擇,在破敗的出租公寓區,諸如下哈林區(Lower Harlem)、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以及下東區(Lower East Side)⋯⋯將來自島嶼的鄉村、前工業茅屋(bohio)⋯⋯建構成新穎的社區中心。對於置身阿法貝塔城(Alphabet City)或西班牙哈林區(Spanish Harlem)的移民而言,漆上珊瑚紅、天空藍或淡黃色的住宅,讓人回想起加勒比海的膚色,並喚起對祖國的記憶(Hayden, 1995: 35-6)。
其他不是由波多黎各移民栽種的花園,複製了英國花園的某些理想,較具田園風味。還有其他則是野生自然保護區,保留供當地學校生物與生態課程之用。這一切都是持續不歇且紛雜多樣的地方創造的實例,它們是城市歷史與認同的位址。
回到湯普金斯廣場公園,遊民想要有即使只是最窄小、很不安全的「過夜處所」,某些當地居民則希望保有他們認為迷人且安全的居住和養育子女(不包括遊民在內)的地方,雙方的需求之間仍有緊張關係。地方再次受到塑造、維繫和競逐。紐約與曼哈頓是地方。下東區是地方。出租公寓博物館(Tenement Museum)、社區花園和湯普金斯廣場公園,都是塑造地方豐富織錦的一部份,構築了北緯40.46度、西經73.58度及週邊區域。縱貫全書,我們會經常回到下東區,據以闡述地理學裡使用「地方」的許多面向。
世界各地,人們都投身於建造地方的活動。屋主重新裝潢、擴增建物、修剪草坪。鄰里組織施壓要求居民整理庭院;市政府立法保障新公共建築物表現獨特的地方精神。國族透過郵票、貨幣、國會建築、國家體育場、旅遊指南等,向世界其餘地方表明自身。國族國家內部的受壓迫群體,試圖宣稱他們自己的認同。正如新生爬上床在牆上貼海報,科索沃的穆斯林(Kosovan Muslim)也懸掛新國旗、豎立新紀念碑,並且重繪地圖。塗鴉藝術家在城市牆上,以流暢的書寫體留下他們的名號(tag)。這也是他們的地方。
那麼,是什麼結合了以下這些例子:兒童房、都市花園、市集城鎮(market town)、紐約市、科索沃(Kosovo),以及地球?是什麼使它們成為地方,而不單單是房間、花園、城鎮、世界城市、新興國家和有居民的星球?有個答案是,它們都是人類創造的有意義空間。它們都是人以某種方式而依附其中的空間。這是最直接且常見的地方定義—有意義的區位(a meaningful location)。
政治地理學家阿格紐(John Agnew, 1987)勾勒出地方做為「有意義區位」的三個基本面向。
1. 區位。
2. 場所(locale)。
3. 地方感。
或許最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前述提到的一切地方,都有其位置。它們已將客觀座標固定於地球表面(就地球這個案例而言,是相對於其他星球和太陽的特殊區位)。
紐約在「這裡」,科索沃在「那裡」。如果有適當的比例尺,我們就可以在地圖上找到它們。地方一詞在日常用語中經常用來單純指涉區位。例如,我們把地方當動詞用時(我應該把這個東西放在哪裡?),我們通常是指某種區位觀念—「哪裡」的單純意思。但是,地方不總是固定不變。例如一艘船,或許會成為長途航行者共享的特殊地方類型,即使船的區位不斷改變。阿格紐以「場所」來指社會關係的物質環境—那是真實的地方樣貌,置身其中的人,以個人、男人或女人、白人或黑人、異性戀或同性戀的身分來生活。很明顯的,地方幾乎總是有具體形式。紐約聚集了大樓、道路和公共空間,包括本身就是有形物質的社區花園—由植物與雕像,以及周圍有籬笆環繞的小屋和房舍組成。
兒童房有四面牆、一扇窗、一道門和一個衣櫥。這麼說來,地方是物質性的事物。即使是想像的地方,像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小說裡的霍格華茲學院(Hogwart School),也有使小說得以展開的房間、樓梯和隧道等想像的實體。除了有其定位,並具有物質視覺形式外,地方還必須與人,以及人類製造和消費意義的能力有某些關係。阿格紐所謂的「地方感」,是指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小說與電影(至少那些成功的作品)時常喚起地方感—我們讀者╱觀眾知道「置身那兒」是怎樣的一種感覺。我們經常對我們的住處,或我們小時候住過的地方有種地方感。這就是作家李帕德(Lucy Lippard)所謂的《地域的誘惑》(The Lure of the Local, Lippard, 1997)。隨著全球化勢力侵蝕地方文化,產生均質的全球空間,而哀嘆地方感的喪失,這在二十一世紀西方社會裡是司空見慣的事。我們將在第二章回到「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的議題。
阿格紐的三分式地方定義,確實解釋了大多數地方事例。不過,這也有助於以不同於人文地理學裡其他兩個類似概念(「空間」和「地景」,它們有時候會以「地方」這個詞來替代)的方式來思考地方。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4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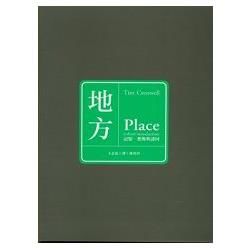 |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 作者:Tim Creswell / 譯者:徐苔玲、王志弘 出版社: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02-2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9 |
二手中文書 |
$ 225 |
中文書 |
$ 225 |
其他財經企管 |
$ 225 |
文化研究 |
$ 225 |
社會人文 |
$ 225 |
其他財經企管 |
$ 238 |
社區再造/都市規劃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
什麼是地方?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基本概念,甚至可以說人文地理學就是地方的研究。但地方同時也是一個包裹於常識裡面的字眼,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兩者的交纏使得這個名詞充滿了魅力。你搬進宿舍裡,貼上海報,在桌上放一些書,等等。然後,這個空間就變成了你的「地方」。北緯40.46度、西經73.58度,對你可能沒什麼意義,但如果我們知道那指的是什麼「地方」,感受可能就大不相同。以「地方」來說,那是:美國911事件,紐約曼哈頓被炸掉的雙子星大樓的所在地。 本書使用新聞、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實例解釋抽象概念,追溯1950年代以來「地方」概念的發展,思考人與地方如何產生情感聯繫,我們如何認同、記憶、想像某個地方,又如何排斥某些元素進入「我們的」地方,並思索「地方特色」是否因為全球化的席捲而消失殆盡。
作者簡介:
TimCresswell 威爾斯大學社會與文化地理學教授,著有《安適其位╱不得其所》(InPlace/OutofPlace,1996)與《美國遊民》(TheTrampinAmerica,2001),並擔任《關注電影》(EngagingFilm,2002)和《啟動地方,定位移動》(MobilizingPlace,PlacingMobility,2003)的共同編者。
譯者簡介:
徐苔玲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譯有《柯斯特對話錄》、《性別、認同與地方》等書,現專事翻譯。王志弘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近期譯有《現代地理思想》、《工作、消費與新貧》、《文化地理學》、《文化理論詞彙》、《第三空間》、《人文地理概論》等書。箸有《流動、空間與社會》、《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等書。
章節試閱
人文地理學就是地方的研究。它當然也是許多其他事物,但是在直覺上,它是一門以地方為主要研究對象之一的學科。修習地理學位和課程的學生,往往會對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感興趣。儘管對地方研究有普遍熱忱,但是對「地方」一詞意指為何,卻沒有什麼深思熟慮的理解。無論就理論和哲學而言,或是對修習大學地理課程的新生來說,都是如此。地方是個看似不證自明的字眼。地方的流行普及是地理學的機會。但這也是個問題,因為當大家談論地方時,沒有人確實明白他們到底在說什麼。地方並不是專門的學術用語,而是我們英語世界中日常使用的字眼。它是...
»看全部
目錄
英文叢書編輯序言謝誌Ch1導論:定義地方Ch2地方的系譜Ch3解讀「全球地方感」Ch4運用地方Ch5地方資源參考書目索引
商品資料
- 作者: Tim Creswell 譯者: 徐苔玲、王志弘
- 出版社: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02-24 ISBN/ISSN:9868107636
- 語言:繁體中文 適讀年齡:15歲以上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文化研究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2019/12/22
2019/12/22 2017/12/27
2017/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