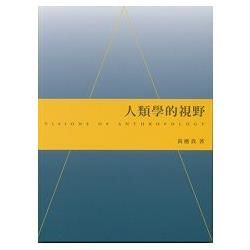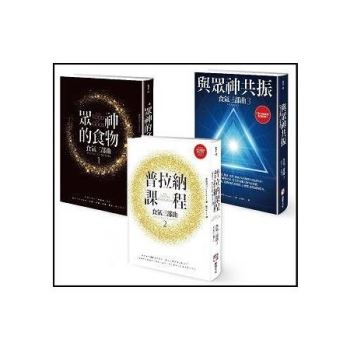第五章 記憶、認同與文化
歷史學家A. Confino在一篇談論集體記憶的回顧性文章之中說:「研究主題的選取,感覺上,大都難免受到時下流行話題左右。而記憶歷史研究主題的界定,若沒有中心或各主題間缺少關連,它就有以某種可預期的方式描述人們如何建構過去的不同主題之組合的風險」(1997: 1387)。換言之,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若不能有獨特的重點以增加對歷史的解釋力,有可能只是成為一種流行而已。筆者並非歷史學者,無法由這領域的研究成果來回答「記憶」做為一研究主題,什麼是獨特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的何在的問題,但可由人類學的相關研究成果,提供一些參考意見。以下,是筆者對人類學中如何討論社會記憶、記憶載體、歷史、認同的一些心得,希望能請教大家。
一、社會記憶與歷史建構
這裡所說的記憶,是指集體或社會記憶,而非指個人的記憶。學界對於社會記憶的討論,大都從涂爾幹的學生M. Halbwachs的研究談起,Halbwachs不僅分辨個人與集體記憶的差別,結合群體與集體記憶的關係,更試圖證明集體記憶為涂爾幹(1992[1950])所說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以其《論集體記憶》(On Collective Memory)一書為例,他提出幾個重要的論點:
1.他試圖以(集體)記憶來連結或超越社會與個人、精神與物質或抽象與具體等的對立。
2.他反對視記憶為一種個人生理或潛意識行為的理論,而強調記憶或回想(recollect)是依觀念架構來重建的有意義的記憶過程,就如同過去的經驗可藉由重建來回想一樣。
3.記憶有許多種(如家族、宗教與階級等),分別有其不同的記憶架構。像家族是排他性的,因此其記憶是限制性的。而宗教的集體記憶是追溯起源之時,或將它與社會生活其他層面分隔等等。他試圖藉此分辨出各種不同的記憶。
4.集體記憶可透過歷史表達認同。進一步而言,相互矛盾的集體記憶的整合正標明更大社會的存在。
5.集體記憶可由制度(如儀式)或物體(如地景)來實踐或運作。
6.社會記憶是一社會事實。
由上,我們可發現之後關於社會或集體記憶研究的基本觀點,大都可見於其理論中。可惜的是,他的研究最初發表時,並未引起學界的注意與迴響而沈寂了許久,一直到1980年代歷史人類學興起,著重於探討文化如何界定歷史的問題,1才被學界重新重視而開始產生作用,因為在Halbwachs的觀點與理論中原就隱含透過集體記憶來建構歷史的面向,因此。例如,F. Zonabend在1984出版的《持久性記憶︰一個法國村落的時間與歷史》(The Enduring Memory: Time and History in a French Village)便是一個例子。
Zonabend在研究法國村落Minot時,發現此地至少存在三種歷史。第一,是由歷史學家記載屬於國家的大歷史,討論的是如1914年或1940年兩次世界大戰等重要的歷史事件。這類大歷史對整個地區的政治、經濟、選舉等活動有影響力,但它基本上是發生在村落外,並依賴同質而持續性的線型時間與文字的記載做為記憶機制。故此,大歷史裡的許多事件,沒有成為當地人的記憶。第二,是地方史或社區史,主要是依靠循環而重複的社區時間,藉由村落內的集體活動(例如,全村性的相互交換、晚間的聚集、葬禮儀式)等實踐過程作為記憶機制,透過所謂持久性記憶(enduring memory)建構與再現的歷史。第三,則是家庭史或個人史,是個個不同的家庭時間或生活與生命的時間,以個人生命週期的關鍵時刻所構成,往往透過出生、結婚、死亡、系譜等為形成所謂「蝟集的記憶」(teeming memory),或個人記憶之機制,建構或再現家屋內的活動。此研究,不僅證明不同的(社會)記憶機制可建構與再現不同的「歷史」,更說明一個群體可能因為存在各種不同的記憶機制,同時擁有幾個不同的歷史,因而凸顯出歷史的多元性。但,也在這個研究中,我們看到不同的社會記憶對於當地的多元歷史的建構,必須與社會的實踐活動,當地人的空間、時間等文化分類概念等相互配合運作,無法單獨產生作用。
這類由社會記憶而探討歷史建構之研究領域,更因P. Connerton在1989年出版的理論著作《社會如何記憶》(How Societies Remember)一書,引起社會人文學者的廣泛注意而產生極大的影響。雖然,這本書最主要的觀點與論點,在上述Halbwachs的著作中都已論及,Connerton只是將前者試圖證明社會記憶為一社會事實的問題轉為「社會記憶如何被傳承與維持(conveyed and sustained)」的問題,並將不同的記憶載體加以精巧化。但這本書背後所隱含的一個論點卻特別吸引人類學家的關注:人類社會除了文字記載外,基於社會文化的不同,可依靠語言的口傳方式、物體(如地景、寶物、紀念碑等)的刻鏤、儀式與日常生活的身體實踐等不同機制,傳承與維持社會記憶。因此,凸顯出西方等主流文明社會把文字記載視為社會記憶唯一或主要載體,是一種文化偏見。這個基本的主要論點不僅符合做為人類學主要研究對象的非西方社會或普羅大眾等的特色,凸顯人類學研究的特長,更可由不同的社會記憶所建構的多元「歷史」挑戰由現代國家所主導的國族史,而彰顯這類研究能為被壓迫者發聲,因而引起人類學界極大的迴響。尤其是該書所強調做為記憶載體的儀式及日常生活中的身體實踐,更在第二節所談的後續研究中發揮作用。
至此,我們可發現社會或集體記憶的提出,不僅涉及其傳承與維持可因文化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機制或載體,也可藉它建構出一個不同於在現代國家機制掌控下而以文字呈現的歷史。這類相對於主流歷史的多元歷史,不僅隱含去除現代國家統治者(包括殖民者)的合法性,具有很強的抵抗性與挑戰性,更因這類歷史建構的過程,往往是透過不同記憶載體的選擇,及以文化分類概念為觀念架構而反映了文化特性。故此,人類學對於集體記憶的研究,最大的影響與成果反而是在對文化特性更深一層的理解上。這可由下一節關於記憶載體與文化特性的討論進一步說明。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人類學的視野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人類/大腦科學 |
$ 270 |
人類 |
$ 270 |
科學‧科普 |
$ 270 |
人類與考古 |
$ 285 |
人類學/民族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人類學的視野
在全球化的情境裡,各種我們習以為常的邊界,可能都在溶解、互滲、交融,隨處都可以聽到看到所謂的「跨界」、「越界」、「離散」、「放逐」等等表態用語。社會學家Z.Bauman甚至形容這個新世界是流動的。一個流動的世界,在後現代主義的解構下,又怎麼能積極而正面地凝視、怎麼觀看、怎麼理解?譬如當人類學原有的分析基本單位都在溶解,人類學怎麼自存?作者透過跨界與歷史學、區域研究等的對話,在本書中呈現他對於人類學前景的思考,人類學需要怎樣的視野?本書另一個沉思的對象是台灣;新世代文化創造力的社會根源,以及台灣史的「圖像」,藉之我們可以為各種分歧並列的文化景象「定位」。這種宏觀的視野及尖銳的提問,毋寧是當下台灣諸多人文社會科學最為迫切需要的一種前瞻性的自省。因為:你看得到,你就有可能做到。
作者簡介:
黃應貴,1947年生。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學士,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所兼任教授。著有《東埔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人類學的評論》、《台東縣史布農族篇》、《布農族》,主編《台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見證與詮釋》、《人觀、意義與社會》、《空間、力與社會》、《時間、歷史與記憶》、《物與物質文化》等書。
章節試閱
第五章 記憶、認同與文化歷史學家A. Confino在一篇談論集體記憶的回顧性文章之中說:「研究主題的選取,感覺上,大都難免受到時下流行話題左右。而記憶歷史研究主題的界定,若沒有中心或各主題間缺少關連,它就有以某種可預期的方式描述人們如何建構過去的不同主題之組合的風險」(1997: 1387)。換言之,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若不能有獨特的重點以增加對歷史的解釋力,有可能只是成為一種流行而已。筆者並非歷史學者,無法由這領域的研究成果來回答「記憶」做為一研究主題,什麼是獨特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目的何在的問題,但可由人類學的相關研...
»看全部
目錄
序言1.社群研究的文化思考2.歷史與文化:對於「歷史人類學」之我見3.再談歷史與文化4.人類學與近代史研究5.記憶、認同與文化6.人類學研究的歷史化7.宗教教義、實踐與文化8.社會過程中的中心化與邊陲化9.進出東台灣:區域研究的省思10.農村社會的崩解?當代台灣農村新發展的啟示11.區域再結構與文化再創造12.想像中的台灣史參考書目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黃應貴
- 出版社: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06-10 ISBN/ISSN:9868107660
- 語言:繁體中文 適讀年齡:15歲以上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7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