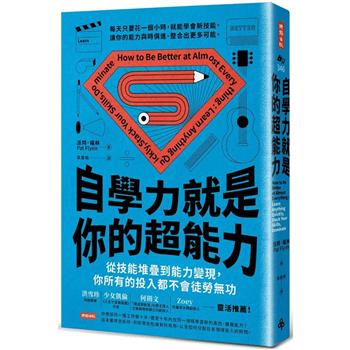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鐵軍的野蠻性史-我們的SM真實故事-WHY?012的圖書 |
 |
鐵軍的野蠻性史-我們的SM真實故事-WHY?012 作者:黃鐵軍 出版社: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7-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鐵軍的野蠻性史-我們的SM真實故事-WHY?012
商品資料
- 作者: 黃鐵軍
- 出版社: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7-01 ISBN/ISSN:986811018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生活風格> 休閒娛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