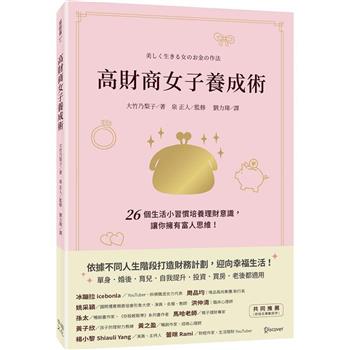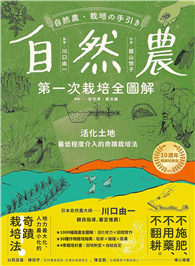推薦序
讓我在失望中仍有希望的科普作家
曾志朗(中央研究院院士)
才健的科普文章,我拜讀很多,主要的著作有《吳健雄傳》和《楊振寧傳》,都非常精彩,絕對是有傳世價值的國寶級大作。他對這兩位在近代物理學做出極大貢獻的科學家,以很真實的社會文化角度,描繪出前者如何以女性的細緻作出貫穿天地的實驗,而後者又如何以大儒的風範去整理出宇稱不守恆的現象,都是劃時代的科學創世之作。他們都來自女性剛解除纏足、男性也才剪掉辮子的封建社會中國,也都在充斥著白人的西方科學世界中,以其蓬勃堅強的科研實力,終爭得一席之地。才健寫他們,心中充滿仰慕之情,也帶有一份民族的驕傲,最重要的是他忠實地歷數他們有時「驚世駭俗」的言行,讀來令人動容。兩本傳記都得到了科學界普遍的肯定。只是才健沒有財運,幾次得獎的那幾屆金鼎獎都只有獎座沒有獎金,可以說老天對他是不太公平的。為什麼?也許是如他所自嘲的,天命難違吧!
至於他的科普專欄作品,我也看了不少,但因為零零散散地這裡讀一篇,那裡又讀一篇,議題都不同,感覺上就不會有很強烈的系統性思維共振。雖然從他傾家蕩產一手獨撐的《知識通訊評論》中所寫的社論,可以感受到他論述科學文明的偏好,但我總以為他還只是一位喜愛科學,卻沒有親身歷練過科學實作的隔岸觀戰者。花了兩個晚上,狠狠地讀完他的《科學夢醒》全書,才真正了解他的科學觀,是一種以數學的純真所演繹出的基本架構,去論述每一項科研發現的本義,他也許讚美,也許批判,但每一句建言都絕非野人獻曝之說,其間的思維轉折,都可看到邏輯論證的周延與完善。這當然和他出身數學的訓練有很深的關聯,而我在閱讀他詮釋的科研事件,就感受到他那種數學為本的科學執著之情!
這些年,才健努力讓最高階的科學知識不中斷地流入台灣,辦了《知識通訊評論》雜誌,沒有政府的支援,也沒有私人企業的長期奧援,在很難有科學廣告資源的台灣社會裡,竟然屹立不搖,即將邁入第一百期的里程碑。我每次收到剛出爐的雜誌,心裡就好高興,它還「活」著,但看完這新的一期之後,就憂心地期待下一期。對才健的熱情、毅力和不「死」心,我心中充滿了崇敬之意。
這本《科學夢醒》書中所敘述的科研故事都很有趣,也都點出了科學多樣多變之背後的社會含義。科學的宗旨說是在提升人類社會的福祉,但科學真的要有目的嗎?為什麼對做不到的事要去規範呢?才健認為不是做不到,是走錯了路!他從人文的思考中,看到了西方科學界的自大,不停地提醒,也不斷地尋找東方的科學觀,以求彌補西方科學走向的不足。
我實在由衷欽佩才健,文筆之外,那不服輸,不放棄的熱情一直感染著我。
其實比之上一個世紀,這個世紀的科研環境有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都深深影響科學家的作法,和自我定位。首先,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已完完全全是個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體系,新的科技當然提升了人類生活的品質,由於交通、醫療、教育、安全都有長足的進步,人類的平均壽命不停挑戰原始生命的極限。但很明顯的,只有有能力掌握知識和資源的社會才會有延年益壽的可能性,所以知識造成的不公不義也還在加速擴大。科學家必須捫心自問,科學的普世價值為何?科學家的自由和責任如何界定?
再來,二十一世紀科學家的科研能力比以往強多了,已經不知不覺地碰觸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以及環境生態的「生」或「死」的問題了!永續的價值觀如何和傳統的演化史觀融合?誰來決定生命是否要有終結之處?「神」嗎?還是超強的科學家們,必須凝聚共識,扮演「超神」的角色,來決定宇宙的「永生」或「自然死亡」呢?還有二十一世紀的網路交通將無遠弗屆,也將使人類無祕密可言。那誰來使雲端上的知識公開透明,而不會烏雲滿布呢?
這些議題會左右科學的運作,對今後社會的影響既深且遠,更需要有好的科普作家來詮釋。相信才健的專欄會漸漸擴及這些議題的領域的。好高興有這麼一位朋友,使我在對台灣媒體科普教育的淡薄無情充滿失望的時刻,還有一線的希望!
科學如何夢醒
江才健
回頭看八年多寫下的這許多專欄,驚覺時間的速逝,也再一次檢視了自己對近代科學的體悟和反省。
這些專欄原本的欄名叫【科學手記】,【科學手記】的開始是好友王志宏的邀約,志宏是一流的攝影和報導文化工作者,他因緣善念而有主持《經典》雜誌的機會,十餘年來辦得有聲有色,八年前他有心使這本雜誌增添一個科學文化的面向,向我邀槁,也使我有機會開始寫下了一百多篇的專欄。
我很願意來寫這樣的一個專欄,源於更早的一個機緣。我自己對近代科學觀察評述,工作了三十多年,起初也是處身在我人文化的主流氛圍之中,對於科學是一種制式的看法,簡單一句話說,就是全面認同科學的所謂「理性、客觀」價值。
但是許多年第一手親歷科學進展的見聞,漸漸使我對科學這個人類近代歷史中的強勢文化,有了全然不同的評價和思維。因此在一九九六年,我在中研院的科學史研討會上,頭一次提出〈科學之後?超越近代科學的再創造〉的論文,那是我公開探討此一問題的起步,我知道自己的看法很大膽,時機也不成熟,當然並沒有企望有熱烈的反應。
兩年後,我將學術體例的論文,改為較通俗的形式,以〈迎接一個後科學時代的宇宙新思維〉為題,在那一年《聯合報》副刊的「五四運動」專輯中刊出。再過兩年的二○○○年五月,我在志宏邀請下,在《經典》雜誌二十二期起,一連四期寫了四篇系列專文,這四篇專文的總題「回顧四百年風光,看科學前景如何」,正反映了我對近代科學的一種評價。
當然,我清楚意識到自己看法的挑戰性,走得也很前衛,我並沒有認定自己的看法一定就對,但是這麼多年的經驗讓我相信,這中間確實有些新意,應該能替我們的文化和人類面對宇宙和生命的態度,帶來一些新的思想啟發。
也因此,兩年後志宏來邀我寫【科學手記】,我很欣然地上路。我知道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需要時間來經營,因此在八年多的專欄中,我用自己在人類科學文化發展許多真實場景裡的體驗,來述說自己如何由我們因沒有發展近代科學,又因輕忽藐視而挫折受辱所承襲的歷史文化包袱中,走出一個對於科學重新定位的醒悟歷程。
在我的這些經驗裡,有許多來自與世界頂尖科學文化締造者的來往對話。由他們言談行止中,我看到科學這個文化創造和思維的孕生歷程,感受到整個過程充滿著的人性特質,我領悟到科學並不是宇宙教本裡寫下的標準答案,不是天籟啟蒙的行當,而是紅塵俗世的摸索。
除了對科學中這些真實人性特質的體認,給我更大衝擊和省悟的,是文化背景對科學創生的影響,也就是說,近代科學如何面對宇宙生命現象,如何構思假想,如何形塑因果,如何建立驗證關係,在根底內裡,無一不受到一個深層文化的影響。這些經驗,都使我身處許多不同的科學場景中,靈光乍現,得如禪宗頓悟般的覺醒。
這些經驗之一,是我四次到過的義大利西西里島高山頂上小鎮艾瑞契,在那個小鎮,有一個由修道院改成的馬猷納科學文化中心。我一直記得二十二年前頭一次到那個山頂小鎮,看到那些因歲月磨得發亮的石板路面,那些四百年未變的石材屋宇,那年八月一天夜幕初垂時刻,我看到一輪黃澄澄的月亮,由小鎮廣場石牆屋瓦背後升起,那種如霎時置身數百年前義大利科學初啟時空的感覺,我頓時覺悟到,那整個科學的宇宙文化思維,與義大利文藝復興以降,基督宗教氛圍、文化背景和歷史時空是如何的息息相關。這就好像在北京才唱出了京劇,在台灣才唱出歌仔戲是一樣的。
另一個場景,是這本《科學夢醒》裡〈異國文化的美感〉一文所述說,我一九九三年在北京的一個經驗。那次與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實驗團隊的北京之行,是在初冬的時刻,當時北京許多住戶還燒煤取暖,空氣中有一種霧般的煙塵和一股淡淡的煤煙味。行程中的一天,當時大陸科委主任(科學部長)宋健請我們在人民大會堂上海廳吃飯,喝了溫熱的上好紹興酒,酒酣耳熱之際,坐在我右手邊一位義大利科學家微醺的向我說,「現在我知道馬可波羅是看到了如何的一個中國。」
在那篇文章中,我曾經寫道,「我了解他的意思,因為那個古老的城宮,煙塵裊裊的氛圍中,是一個謎一樣的古老文明,走過幾千年,依然蒼勁有力,怎麼會不使一個義大利人悠然神往。」
是的,就是二三十多年來我親歷的許多深刻經驗,和許多頂尖科學人物溝通也辯詰的對話,使我由我人文化大氛圍的科學認定中,獨步走出,走向一個全然不同的道路。
近年來,我在許多地方演講,在學校教書,也到包括北京、合肥、上海、武漢、重慶等一些地方做「文化反攻大陸」,都是希望能讓我偶然而得的一種對科學的省悟,能與更多人分享交流。
這些經驗,補足了科學創生中最真實鮮活的面向,使我由過去那些沒有底蘊的科學知識中,看到內裡豐沛的人性因素,使科學由平面的註記,變成立體的鏤刻。我只希望這一篇篇的短文,能如一級一級的階梯,引領我們在自己的傳統裡,找到文化自主根源的創造力,來補足長久以來面對宇宙和生命挑戰,我們一直缺席的自發性文化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