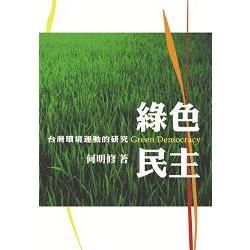序論:台灣環境運動二十歲
1986 年的春天,鹿港小鎮籠罩在一團未知的恐懼之中。在政府的極力爭取下,美國杜邦公司決定在中台灣設置二氧化鈦工廠。對於官員而言,這項投資案一方面可以解決閒置以久的彰濱工業區,另一方面也可以提振自從1984 年勞基法施行以來的低迷景氣。他們有理由相信,鹿港居民也會樂見跨國工業的進駐,以及就業機會與土地價值的提升,就如同二十餘年前,鄰近的彰化市民以舞龍舞獅的方式來迎接台灣化纖公司設廠。樂觀的官員萬萬沒有想到,鹿港居民在新任鎮長的帶領下,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綿密的反對運動,他們要求保存一個自己所熟悉的鹿港—一個香火鼎盛、生意活絡的濱海小鎮,而不是煙囪陰影下的工業城。
在六○年代中期,台化彰化廠正式開工,附近的農民開始發現自己的農田再也長不出結實飽滿的稻穗,因為工廠污水破壞了肥沃的土地。彰化市民失去了新鮮的空氣,長期的廢氣排放,除了引發撲鼻的不適,也導致各種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呼吸道病變。
隔著大肚溪,從台中南下的旅客可以遠眺籠罩在彰化上空的混淆空氣;一進入市區,龐大而醜陋的工廠廠房便是迎接他們的第一個景象。二十年來,彰化居民早就知道在繁榮地方的承諾背後,現代工廠往往隱藏了各種健康、財富的代價。鹿港人見證鄰居二十年來的教訓,他們堅決主張,同樣的故事情節不能再發生於自己的家鄉。為了反對杜邦設廠,他們發動遊行、北上請願、舉行演講、串連其他公害受害地區、組織反公害協會、發行宣傳刊物、動員學童繪製反公害壁報等等。換言之,鹿港居民創造了一個未曾存在過的事物,亦即本土的環境運動。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大衛終於戰勝巨人哥利亞,杜邦公司決定放棄彰濱設廠計劃。這項未意料到的勝利宣告台灣環境運動春天的到來。
從鹿港起義到政黨輪替後的第六年,我們又經歷了整整二十年。在這段期間,環境運動的風潮蔓延到台灣各個角落。無論關於工業污染、焚化爐、道路、水庫、國家公園、行動電話基地台等環境議題,許多社區都經歷了大大小小的集體行動。在要求改善環境的強烈民意下,環保署成立了,公害糾紛調處、環境影響評估、禁用免費塑膠袋、廚餘回收等一系列的制度也開始實施。
二十年前,黨外人士宣稱與鹿港人民站在一起,他們試圖吸納這一股來自草根的反叛勢力;二十年後,他們已經高居國家廟堂,在民進黨執政下,有兩位環保署長更是來自於當初積極鼓吹環境意識的知識份子。事實上,早在台獨運動轉向公投路線之前,二十年前的鹿港反對人士已經在倡導鎮民自決。在接連的環境運動動員下,公投逐漸從政治異端轉變成為一項體制內的民主機制。
環境運動除了帶來結構性的衝擊,也在許多人的生命歷程中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記。二十年前,大學生開始下鄉調查各地蜂起的反公害抗爭,校園的社會參與不再是侷限於七○年代的「農村服務」、「山地服務」,進而轉變成為貨真價實的社會運動。九○年代以降台北街頭的年度反核遊行,也曾經是許多青年的政治啟蒙第一堂課,理想主義的認同也促使其中的一些人選擇了社會運動作為他們的生涯。一位知名的文化評論者第一篇投稿報社的文章就是為了聲援核四公投,另一位反核運動者選擇了在有反核聖地之稱的貢寮拍攝他們的婚紗照。當然也有人因此而付出昂貴的代價,在1991年一○○三貢寮事件之後,林順源已經在花蓮監獄待了十五個年頭,他無法親身體驗後來反核動員的高漲與廢核的頓挫。
在這二十年來,環境運動被觀察者賦與不同的名稱。環境運動是「社會力」,因為它代表了一股獨立於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的反對力量。環境運動是「民間社會」,不滿的人民挑戰了威權控制。環境運動也是「公民社會」,因為它創造了另一種公民之間相互連結的可能性。對於其抨擊者而言,環境運動代表著一股盲目、不理性、不信任專業的「民粹主義」,一位國民黨籍的經濟部長就將環境抗爭比喻為「吸食安非他命」。無論是被推崇或是被指責,被期許或是被畏懼,環境運動無疑的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潮流,深刻地重新形塑了台灣的社會圖像。
該是還給環境運動原本風貌的時候了,這一本書將環境運動視為一種追求環境正義的集體行動。環境運動並不只是美化生活、保護自然,而是要求公平分配資源、承認弱勢群體生活方式、共同參與環境決策,換言之,環境運動終極目標是環境正義的落實。在過去的二十年,這種追求綠色民主的渴望展現出巨大的政治動員能量,也與既有的體制產生激烈的抗衡。環境運動的興起意味著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深層批判,他們強烈地質問,到底新民主政權如何看待環境受害者?對於越來越自我安逸化的民主派人士,環境正義的呼籲不外乎是嗡嗡作響的牛虻,不斷地提醒我們那份未完成的民主化志業。本書追溯環境運動的歷史軌跡,從解嚴前的初步萌芽到政黨輪替之後的轉型。三個主要的質問引導本書的章節寫作:環境運動是起源何種歷史脈絡?在威權到民主的鉅變之中,環境運動扮演了何種的角色?那些道路可以通往環境的民主化?從起源到未來,本書期待能夠紀錄環境運動在台灣的驚異航程,並且透過其故事,理解台灣整體變遷的歷程。
許多熱血青年相信,詮釋歷史遠不如創造歷史重要,但是儘管如此,在若干時候,詮釋歷史的工作也是有其迫切需要的,有待知識界的積極投入。在經歷了解嚴、民主革命、政黨輪替之後,台灣的政治景象產生了劇烈的變動。二十年前,鹿港居民用偷襲的方式,在當時仍叫做介壽路的總統府廣場進行陳情,他們的和平行動沒有進行多久就被軍警勸離;二十年後,在凱達格蘭大道上比較常見的場面是揮舞國旗、高喊打倒台獨的群眾,國民黨中央黨部儼然成為他們的前進指揮所。迅速而根本性的變革迫使我們不得不一直拋棄既有的參考座標,隨時適應新到來的時代。就如同一趟不斷在各個時區轉機的旅程,到最後每一個當地時間都變得那麼不真實,缺乏意義。無論是有意的或無心的,遺忘成為許多人面對過去最好的方式。因此,在這個急劇變遷所塑造的失憶社會中,歷史的詮釋成為不可或缺的集體治療。
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下,知識界也會感染一股參與的熱忱,積極投入創造歷史的活動,這也就使得詮釋的工作被擱置了。扮演社會的良心往往是一種難以抵抗的誘惑;一旦成為了社會導師,即使是再優秀的心智也會喪失了反思能力,無法認清自己所處的現實格局。在時代的集體亢奮下,詮釋歷史成為森林中那一條比較少人走過的路。因此,儘管台灣的社會研究在過去十餘年來有長足的進步,但是至今對於許多重要問題仍缺乏完整的研究結論。就以社會運動為例,台灣有一本八○年代學運史,但是卻沒有關於九○年代的專著。筆者唯一可以找到關於1990 年三月學運的學術期刊論文,是由外國學者所寫的。在勞工運動方面,工運團體所出版的著作比學術界還多。事實上,還有更多的社運故事仍未被紀錄下來。
越是在劇變的年代中,詮釋者越有可能被迫接受「意外」的發展,修正以往的詮釋方式。換言之,不同詮釋方式的鬥爭是研究者所需要獨自面對的事實。這一本書是延續筆者在2000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研究。在取得博士學位的同時,台灣的政權也產生史無前例的和平轉移。在當時,我是以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角度來詮釋1980-1998 年間的環境運動演進。但是面對政黨輪替的變局,我卻發現自己完全無法預測民進黨上台之後的發展,我沒有料想到廢核改革的挫敗、種種反制運動的興起,乃至於民進黨政府的保守化。事實上,我也懷疑有任何人可以預見政黨輪替之後的種種演變。在1999 年,一位反核人士曾告訴我,要終止核四有三種可能,分別是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民進黨取得國會過半,《公投法》立法通過。結果已經有兩個條件實現了,但是核四廠依舊繼續興建。黑格爾說,歷史給人們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無法從歷史學到任何教訓。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句話並不一定是感嘆人類的盲目,而強強調歷史本身的無法預測性。這亦即是說,歷史詮釋者永遠只能依賴後見之明,而且他們隨時要有心理準備,接受後續發展所帶來的挑戰。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0 |
二手中文書 |
$ 324 |
中文書 |
$ 324 |
環工/都更 |
$ 324 |
應用科學 |
$ 324 |
科學‧科普 |
$ 324 |
社會 |
$ 342 |
環境工程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
台灣的環境運動已經20歲了,從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運動以迄晚近的蘇花高爭議。本書完整記錄了保護台灣環境的這段實踐歷史,並剖析政治轉型過程中環境運動所扮演的角色。
環境運動不只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品質,還涉及社會正義此一根本價值:
誰來決定社區的共同願景?
哪些人從開發中獲利?
哪些人需要承擔惡果?
這些問題,環境運動者無從迴避。就此而言,環境運動所追求的其實就是環境的民主化。
本書回顧過去的環境運動路線,包括國會遊說、參選、組黨、公投等,進而揭示未來的「陣地戰」策略,我們可優遊於多元自主的市民社會領域,分別在專業、勞動、消費、投資等議題上推動環境的民主化。
作者簡介:
何明修
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
美國紐約大學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
現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研究領域有社會運動、環境社會學、勞動研究、教育社會學等。
著有:《社會運動概論》(2005,三民)
章節試閱
序論:台灣環境運動二十歲1986 年的春天,鹿港小鎮籠罩在一團未知的恐懼之中。在政府的極力爭取下,美國杜邦公司決定在中台灣設置二氧化鈦工廠。對於官員而言,這項投資案一方面可以解決閒置以久的彰濱工業區,另一方面也可以提振自從1984 年勞基法施行以來的低迷景氣。他們有理由相信,鹿港居民也會樂見跨國工業的進駐,以及就業機會與土地價值的提升,就如同二十餘年前,鄰近的彰化市民以舞龍舞獅的方式來迎接台灣化纖公司設廠。樂觀的官員萬萬沒有想到,鹿港居民在新任鎮長的帶領下,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綿密的反對運動,他們要求保存一個...
»看全部
目錄
代序 書寫台灣環境運動的發展軌跡 蕭新煌
序論 台灣環境運動二十歲
第一章 導論:研究台灣環境運動
第二章 環境運動的起源:專家學者、黨外與草根
第三章 環境運動作為社區復興:重訪後勁反五輕運動
第四章 政治自由化與環境運動的激進化(1987-1992)
第五章 政治民主化與環境運動的制度化(1993-1999)
第六章 政黨輪替與環境運動的轉型(2000-2004)
第七章 環境運動的自主與依賴:比較美濃反水庫與貢寮反核四
第八章 為何民進黨政府的廢核政策失敗第九章環境運動與公投
第十章 結論:環境民主化的未來
附錄 台灣環境抗爭案件...
序論 台灣環境運動二十歲
第一章 導論:研究台灣環境運動
第二章 環境運動的起源:專家學者、黨外與草根
第三章 環境運動作為社區復興:重訪後勁反五輕運動
第四章 政治自由化與環境運動的激進化(1987-1992)
第五章 政治民主化與環境運動的制度化(1993-1999)
第六章 政黨輪替與環境運動的轉型(2000-2004)
第七章 環境運動的自主與依賴:比較美濃反水庫與貢寮反核四
第八章 為何民進黨政府的廢核政策失敗第九章環境運動與公投
第十章 結論:環境民主化的未來
附錄 台灣環境抗爭案件...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何明修
- 出版社: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12-01 ISBN/ISSN:9868298202
- 語言:繁體中文 適讀年齡:15歲以上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48頁
- 類別: 中文書> 科學> 應用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