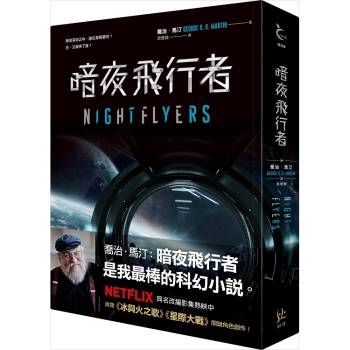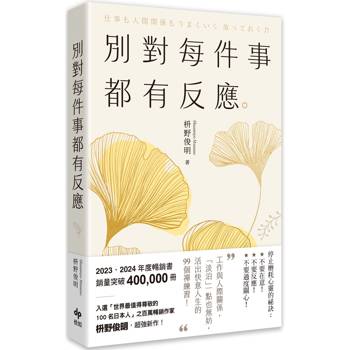異鄉撒網,離岸難回——
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
/莊舒晴
2013 年8月,海巡署將特宏興 368 號漁船自南太平洋戒押回台,當九名印尼漁工下船登上宜蘭蘇澳的土地時,遭遇不測的台籍船員家屬紛紛上前追打,一時全台媒體也不斷放送這起駭人聽聞的印尼漁工殺人事件。
作為移工團體,看到受害者家屬托著遺照哭泣的畫面,我們同樣感到悲傷及不忍,對於生命的驟然消逝,少有人能坦然面對。然而在同一個電視畫面裡,那些低著頭被痛斥和毆打的黝黑身體,也令人不禁擔心起在台灣長期被視為潛在危險份子的移工,是否會因著媒體的發酵,成為人人遷怒責備的對象。
在事件發生後不久,TIWA 主動聯絡律師瞭解相關案情,試圖釐清整起案件的經過。依照我們這些年來處理移工案件的經驗,明白不能僅以「殺人」兩字簡化事件,而後來該案被認定與殺人行為無關的其中三位漁工到 TIWA 的庇護中心安置,更坐實了背後牽連的結構性因素。
受害船長的家屬曾對媒體表示「船東希望方便、降低薪資成本,而以境外聘僱方式進用來歷不明的外籍漁工,而且本國、外籍漁工人數比例懸殊,對遠洋作業的台灣漁民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風險。」可見在憾事發生前「問題」一直存在著,但沒有人敢戳破「境外聘僱」這個制度的黑暗面。即便特宏興案引起全台的關注,大家還是把焦點擺放在印尼人殺台灣人的國族仇恨上,制度也就懸而未決。
自事件發生兩年多以來,TIWA 持續前往看守所與監獄探視六名印尼漁工
,也透過信件往返,逐漸了解他們作為一個個帶有不同生命軸線的人,何以漂洋過海,共同歷經悲劇的剎那。
隔著看守所的鐵欄杆和厚重的玻璃窗,我和 Retno 各自拿起面前的話筒。「那個時候仲介說不用手續費,可以直接去工作,每個月有兩百美金。飛到桃園機場後,馬上有人開車帶我去港口登船,我不知道台灣長什麼樣子,工作六個月也從來沒看過新台幣。」儘管家人們知道他們的兒子是到台灣工作,殊不知境外漁工不被允許在台灣的土地上停留,即便靠岸也只能待在船上,遙望他鄉。
Anto 頂著小平頭大眼睛,「我那個時候已經失去自己、失去理智。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的家人⋯⋯」他像是懺悔一般低頭說出這句話。「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用木棍打人,也會一直罵,有時候打到流血了還一直打⋯⋯我知道自己做了錯的事情,真的很對不起,希望以後來的印尼人不要再發生這種事了⋯⋯」Lufin 的眼底情緒複雜。
數次探視後我們已不再談案情,漁工們對於必須在監牢中漫長服刑也比較平靜面對了。偶爾 TIWA 邀集幾名印尼勞工一同前往,讓大多不諳中文的漁工們至少可以用家鄉話聊聊天,得知一些外界的資訊。
「TIWA 的朋友們,真的很對不起向你們提出請求,不知道是否能請你們幫我查地址和郵遞區號?」Susanto 用工整字體寫來的信件小心地探問,想必他是考慮了許久才鼓起勇氣寫這封信。「我寫了好幾封信回家,但是都沒有收到回信⋯⋯」Yudi 失望地說。
在他鄉服刑,面對獄中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折衝和全控機構的管制,遠方的家人是他們唯一的寄託,然而除了憑藉記憶中模糊的地址和電話,漁工們沒有其他管道和家人聯絡。
TIWA 在因緣際會下認識兩名關注此案的印尼藝術家,他們的團隊憑藉片段的資訊和線索,挨家挨戶地找到漁工的家人,試圖重建漁工與家鄉的聯繫。從不同的位置關注移工議題,我們同樣希望移工權益朝向更好的方向挪移,並拓展和社會對話的空間。於是在他們的邀請下,我們踏上印尼「替代返鄉」的旅程,拜訪六名漁工以及另一移工殺人案 Yanti 的家人。
出了雅加達(Jakarta)後幾乎沒有紅綠燈,原來平坦的水泥公路變得顛簸坑疤,景色從高樓與工廠轉為平房與綠意。
第一站是西爪哇的梳邦(Subang),雖然距離雅加達僅有一百五十公里,但沿途交通雍塞路況多變,還是花了五個小時才抵達。當我們的車子駛進村子裡的小路,兩旁的人家都投以好奇的眼光。同行的印尼朋友說:「這裡不太有人開車,大家都騎摩托車,如果有外人進來,全村的人都會知道。」聽到這句話我們不免擔心,這樣「高調」的到訪是否會給漁工家人帶來困擾?他們的鄰居若知道村裡有人在台灣殺人並坐牢會有什麼反應?他們的小孩會不會在學校被同學排擠,並冠上「殺人犯之子」的標籤?
印尼朋友說「全村的人都知道了。這裡是印尼鄉下,跟大城市不一樣,只要有一點小事一下就會傳開,甚至我今天生了病,隔天可能隔壁村的人也知道了。」不只梳邦村莊的人知道 Susanto 在台灣發生的事,其他五個漁工和 Yanti 的家鄉親友們,也模模糊糊地在鄉里耳語閒談中得知遙遠地方的憾事。
我們到達的是 Susanto 妻子的家,是一間倚著窄徑的白色小平房,路只能勉強讓一台車經過,沒有迴車的空間,我們只好向對面某戶人家借用庭院來停車。對方明白我們是來找 Susanto 家人的外地人,關切及好奇地看著我們,那並非一種猜忌打量的神態,也許心裡對於台灣人的來訪原因也心裡有數,很大方地將庭院借給我們。
家徒四壁,這是進到屋內的第一印象,除了一個櫥櫃和一些生活雜物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多餘的東西。家人們在水泥地板鋪上染著灰的地墊請我們坐,並吩咐小孩去買涼水回來。我們向 Susanto 的丈人、丈母娘、連襟們解釋此行的目的,轉告他們這兩年來 TIWA 探視 Susanto 的狀況,並送上台灣朋友們募集給小孩的一點禮物與給家庭的微薄捐款。家人久未聞 Susanto 的消息,得知他獄中平安,先是鬆了一口氣,但一時也不知道能再追問什麼,再聽到 Susanto 的刑期是二十二年後,本來沈靜的氣氛更是顯得無語。
Susanto 4 歲的小女兒 Nina 拿著台灣來的玩具便開心地玩了起來,13 歲的大女兒 Riri 則坐在角落低頭,克制地流眼淚。
兩個女兒現在都由妻子娘家扶養,Susanto 的妻子則每個月寄小孩的扶養費回來。到此,家人不禁抱怨 Susanto 的妻子把房子和土地都賣了,跑到雅加達打工,甚至準備申請前往台灣工作,為的不是別的,而是再見丈夫一面。
不難理解承擔起照顧工作的親戚們心中難免有些不諒解和怨懟,但孩子呢?Nina 正懵懂,尚未意會到家裡究竟發生什麼事,Riri則是非常清楚這個家的失衡狀態,所以對於大人們所談論的一切聽而不語,那份過於早熟的節制反而令人不忍。臨走前,Riri寫了一封信和兩張紙條,一張是他母親的手機號碼,一張是他自己的號碼,要我們轉交給她的父親。
-
沿著爪哇島的北海岸線行駛,來到Iham在南安由(Indramayu)的家。在台北看守所與Iham 會面時,他說自己因為與妻子離異,找不到生活方向,無所適從,才決定踏上遠洋的船。他始終心繫在故鄉的兒子 Tanto,希望打魚的錢至少可以給兒子比較穩定的未來。
踏入磚砌的屋子裡,我們才發現原來 Iham 的父母也離異了,父親與繼母的家坍塌,所以在 Iham 其中一個舅舅的房子裡與我們見面,兒子 Tanto 跟媽媽一起住,不在屋裡。Iham 的朋友 Toto 得知我們要來,特地也趕來打聽 Iham 的近況。Toto 以前也在台灣的漁船上工作過,他能夠理解那個工作場域的惡劣狀況,所以得知特宏興案時,訝異是有的,卻也不難想像事情何以至此。
Iham 幾乎是與家裡斷了聯繫。從小失學,閱讀和書寫印尼文對他來說十分困難,好不容易寫了信回家,卻遲遲得不到家人的回信。繼母告訴我們,儘管從台灣寄來的信已經付了郵資,但村裡所有的信都被送到村辦公室裡,如果想要拿信,必須付另一筆「取信費」,這是鄉里間不成文的黑色規定。「我們沒有錢,沒辦法拿信。」她如是說。
在我們的要求之下,Iham 的舅舅騎著機車把 Tanto 載來。Tanto 是個非常靜默的孩子,9 歲,頭低低,被大人抓過來又抓過去,眼裡有些倔強和不甘願。他似乎不理解爸爸為何一去不復返,而這些講著異國語言的人又是誰?來日方長,待他成年後,有一天是否會拿著工資去領爸爸寄來的信?
六名漁工要在獄中度過漫長的歲月,與台灣「同學」共處,紛紛試著學習中文,讓日常生活順遂些,只有 Iham 小聲問我們是否能帶印尼文的國小課本回來,他想好好學習自己的母語。也許,他是想有天若能與兒子往來書信,那會是多大的慰藉。
-
前往井里汶(Cirebon)的路上下起大雨,雨水拍打在車窗上,讓原本泥濘的路變得更加難行,沿途經過幾個淹水路段,人們試圖在混亂中涉水而行。水是黃濁,人們一個接一個用腳踩探著下一步,尋找能夠前進的方向。
Lufin 家四周空蕩蕩的,只有滴滴答答的聲音。他的父母外出工作尚未歸來,我們在客廳席地而坐,被刺眼的綠色牆壁包圍著。牆上掛的是 Lufin 姊姊中學時的畢業照片,穿戴學士服笑得靦腆,那份榮耀的神情與斑駁的牆形成對比,也與眼前抱著孩子的婦人不像同一個靈魂。
大雨遮了陽光,即便屋裡開了燈仍舊十分昏暗,傍晚 Lufin 的父母從雨中騎腳踏車歸來,他的父親倚牆沈默不語,母親邊哭邊問為什麼兒子要關那麼久。面對漁工家人直面而來的情緒,該如何回答這個「為什麼」?
「因為你兒子殺了人、殺人就應該付出代價、沒有判死刑已經很幸運了、我們的監獄還要養一個外國的殺人犯⋯⋯」台灣社會裡面最主流的聲調,我們並不打算告訴他母親。一方面不希望「殺人犯」的標籤讓家人懷抱愧疚活著,也把漁工和家人的關係推得更遠;另一方面,台灣關於外籍勞工的制度和結構性壓迫才是釀成悲劇的推手,也是作為移工運動者的我們一直以來在和社會對話的部分。然而,談論後者何其困難,當 Lufin 的母親還沈浸在前者的悲痛中,我們光是承接巨大的情緒都來不及,更是難以向後者的討論挪移。
不久弟弟和妹妹也從雨中走來,姊姊拿了紙筆,趴在地上寫信。
「雨停了再走吧。」Lufin 的媽媽留我們。空氣裡很是沈默,可言說的都說了,只剩面面相覷,相對無言。
這個村子裡的雨,好像從來沒停過。
-
井里汶到勿里碧(Brebes)的距離在地圖上看起來不遠,但印尼的交通並非可預期,尤其沿著爪哇島北部的濱海省道,沒有紅綠燈不代表可以肆無忌憚地加速長驅,得專心提防有摩托車、三輪車和行人橫越公路,甚至在某些路段「祈禱者」就直接站在馬路中央,一邊唸著祈禱詞,一邊拿著像是撈魚用的網子,向行經的車輛揮。有些駕駛會暫緩車速略施小惠,更多的車輛仍是呼嘯而過。祈禱者們在為過路人祈福,網子揮呀揮,但降臨的福份似乎不包含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下的身體。
Retno 的媽媽坐在屋前挑菜,屋頂垂下兩條繩索,綁著一個大布巾,其中一個孫子在裡頭安睡,還有兩個小鬼追來逐去,屋前屋後嬉鬧著。Retno 的妹妹去買涼水回來,這似乎是印尼人家的待客之道,儘管許多人屋裡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就沒其他多餘的東西,但客人來時還是會買來一般時候不會消費的飲料。
妹妹說 Retno 曾打電話回家過,看守所規定只要向獄方提出申請並購買電話卡,一年可以打兩次電話回家。Retno 說了有二十二年的刑期,若在獄中表現良好,刑期一半時能提假釋。但誰說得準呢?沒有人敢對假釋抱有期待。
行前 Retno 特別拜託我們拍他母親的照片,作為獄中的寄託。儘管有少數的機會打電話回家,Retno未曾與最思念的母親通電話,出於羞愧、不孝、屈辱、不堪,他沒有勇氣面對母親,就連聽見母親的聲音都沒有辦法,只能透過兄弟姊妹傳話。「他在船上一直被打,我想進去監獄也許過得比較好吧。」妹妹或許是安慰母親,或許是出於無奈地說到。
我想起去年五月同樣發生在台灣的福賜群號事件,高雄籍遠洋漁船在海上作業期間,兩名印尼漁工一死一失蹤。死亡的漁工生前疑似遭虐待及強迫勞動,在沒有醫療的情況下在汪洋中死去。失蹤的漁工是在工作時失足落海,船長沒有救人,直接將船駛離。「就像一包垃圾被丟下去一樣。」同船的漁工這麼說。福賜群號的漁工跟特宏興 368 號的漁工一樣,都是「境外聘僱」,不適用台灣的法律保障,也不受台灣勞動條件的規範,多少人在船上受到剝削及不合理的對待而束手無策。當他們最絕望的時候,面對的只有白日的烈陽及夜晚無盡漆黑的大海。台灣政府並非不知道境外聘僱所帶來的問題,而是深知於此 ,對雇主來說境外聘僱的成本不到境內聘僱的一半,對政府來說不需要承擔這批勞工的種種「問題」,當事件發生,政府只要雙手一攤說「他們是境外的」,就能規避掉所有責任。今日若非是印尼漁工的屍體被載回港口,或是台籍船員出事,政府根本不打算處理,任其自生自滅,而在這個過程中,滅了的總是最底層的外籍漁工。比起像一包垃圾被丟到海裡去,或許真如 Retno 的妹妹所述,進監獄也許比較好吧。至少回到岸上,還能期待有一天再見。
-
再往東邊行駛三個小時就是直葛(Tegal),Anto 住的村子瀰漫著濃重的魚腥味,路邊人家屋外到處曬鹹魚。
在屋裡等待我們的是 Anto 的妹妹,她的臉和哥哥簡直一個模樣。兩個阿姨聽聞我們來訪,放下挑魚刺的工作來寒暄,她們說「他媽媽有時候會對著枕頭講話,把枕頭當成兒子,講一講又哭。」
「Anto 從小就是個很乖的小孩,每次到港口邊人家都會給他免費的魚,他不會拿回家自己吃,還會分給其他鄰居。」
「他第一次出國賺的錢都匯回給家裡,是個很顧家的孩子。」滔滔不絕地回憶起這個孩子的一點一滴,沒有人知道他日後竟會成為被判刑二十八年的殺人犯。
在判決定讞之時,法院指出:「被告Anto雖為本件殺害OOO最核心之人物,但『特宏興368號』於本件衝突前即已存在海上暴力犯罪之許多因素:我國籍幹部與印尼籍漁工間階級、收入之巨大差異、言語、生活等衝突,海上作業時間長且環境惡劣,案發地點距離我國及任何陸地遙遠等,最終致生此次悲劇。」結構性的壓迫積累,仿若重現三十年前的湯英伸事件。
Anto 的母親結束一天賣魚的工作,見到兒子在信中提及的 TIWA 朋友們,興奮地跟我們說話,她沒想到竟然有人真的從遠方帶來兒子的訊息,彷彿這才放下心來,原來兒子在獄中還平安。
我們問是否有口信要帶回給 Anto,「他女朋友已嫁人,而且有孩子了。這不要告訴他。」她母親說。
「他爸爸最近身體很不好,耳朵一直流血出來,不知道是什麼病。這也不要告訴他,不想讓他擔心。」到此他母親的眼淚潰堤,方才的開朗笑容不復存在,她的哭是哭嚎,手捶著心臟大聲哭出來。
Anto 的妹妹沒說什麼,在媽媽的哭聲中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要我們轉交給哥哥。
是時,Anto 的父親正在海上捕魚。Anto 出國前也在直葛當漁夫,肩負起養家的責任,特宏興案發生後父親又重操舊業,回到漁船逐浪而去。當他在海上,隨著海浪的晃動一上一下,他是否曾想過,他的兒子就是在這麼一片晃蕩汪洋中,受到欺凌、與人爭執、最後鑄下大錯?當他拖著漁網,那些被捕撈的魚群們,有哪隻藏著他兒子捎來的信息?
-
車行至八馬蘭(Pemalang)時,天色已經完全漆黑,我們把車停在大路上,憑藉手機的燈光往村裡住家巷弄走去。
Yudi 和妻子結婚一個半月就出海工作,為了還結婚時跟兄弟借的錢,以為出國一趟就能與新婚妻子安然度過往後的日子。然而事件發生後他的妻子已經很久沒回婆家了,連重要節日都不願意一起過,Yudi 的母親在言語中不免隱含著對媳婦的怨懟。但是何怨何懟?也許彼此心裡也都明白,要求正值青春年華的女子等待不知何時能歸來的丈夫,亦是殘忍的。
Yudi 的母親把他小時候的相片以及從台灣寄來的信攤在地上給我們瀏覽,小時候的他看起來開朗,眼睛像媽媽。牆上掛著仍 Yudi 的結婚照,父親則沈默地坐在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的照片下抽菸。
從蘇哈托(Suharto)政權到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 ,印尼以國家政策強力推動人民出國工作,因為這是最簡便解決國內過剩勞動力的方式,同時能賺取國家外匯,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
遷移需要資本,在印尼最窮的人沒有辦法出國當移工,如果沒有辦法負擔仲介費,生活中也沒有任何管道培養對現代性的想像,光顧吃食溫飽就焦頭爛額了,如何能做出國夢?
我們在印尼期間曾拜訪當地漁工組織,他們協助過多起境外聘僱漁工的重大案件,對於這群不受保障、被各國政府互踢皮球的勞工再熟知也不過。當我們提出是否要以「廢止境外聘僱,落實國對國聘僱」的方向,做為向政府施壓的軸線,印尼的組織者馬上回應:「不可能。」
的確,照台灣目前境內漁工的引進模式,雖然仍存在諸多問題,但受到勞基法的保障,政府也掌握勞雇雙方的資訊,一旦發生問題至少還有處理的基礎,不像無法掌握的境外漁工,「像一包垃圾被丟到海裡」而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但對於輸出國印尼來說,沒有資源進入國對國勞動力協議的人,就是當地最窮苦的人家,而這些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成為境外漁工,不需要手續費,文件辦好即可上船工作。「仲介跟我說一個月可以拿到兩百多美元的薪水。」Retno 曾透過看守所的話筒如此跟我說。
斷了境外聘僱這條路,為的是阻斷剝削,讓政府無法卸責。然而對於底層的人來說,儘管存在被壓迫的風險,仍是一條可能的活路,當無處可走時,至少能把自己的身體交付一紙契約。
結束印尼旅程,第一件事就是寫故事。
拜訪六漁工的家鄉有幾個重要的目的,一是建立起受刑漁工和家裡的聯繫,讓其得以在獄中度過漫長歲月,二是試圖從測繪這六個家庭的樣貌,去叩問他們何以從鄉下地方的小伙子,變成海上喋血的兇手?背後籠罩每個飄洋過海身體的壓迫又是什麼?進而開啟與社會對話的空間。
這並非一個替代返鄉的慈善故事,也並非訴諸悲情與煽情。儘管在漁工家人的眼中,我們難免被視為「好心人」,旅途中的許多時刻也確實令人動容與悲傷,在承接撲面而來各種情緒和狀況的同時,其實很難再進一步與漁工及他們的家人談議題、談結構的壓迫、談這個案件對移工運動的意義,但希望透過紀錄和書寫能激起一些討論。
作為移工運動的組織者,組織的日常中有太多故事,悲傷的、扭曲的、歡樂的、氣憤的,故事隨著每個遷移的身體來去、滾動、發酵,但書寫並非只為了書寫者或被書寫者的利益、抒情、一廂情願。已經有太多「成功的移工故事」為台灣的多元文化塗脂抹粉,故事的背後若非指向結構問題和日常積累的壓迫,那麼就只會是個「漂亮」的故事而已,這趟旅程我們時時警惕自己,避免流於此。
也許我們可以開始思考,當底層的人必須把自己的身體賣給一紙契約、跳進惡水,這意味著什麼?有多少人沒能來得及在最後一批魚獲裡,將自己打撈上岸?
不只是漁船這個空間裡發生的事情,疲累、紛擾、爭鬥、擠壓,整個無形的體制都是壓得人喘不過氣的一部分,最終他們殺了人,但何嘗不是被這個體制殺了?
他們一度離水得活,人人皆曰殺之,最後法官留了一絲生路。但要游回彼岸,還很久,很難。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折翼驛鄉:宏德新村2號的移工的圖書 |
 |
折翼驛鄉:宏德新村2號的移工 作者:移工受刑人探視小組 出版社: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出版日期:2019-11-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二手書 |
$ 195 |
Others |
二手書 |
$ 276 |
Others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社會 |
$ 334 |
Social Sciences |
$ 342 |
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折翼驛鄉:宏德新村2號的移工
第一本紀錄移工受刑人的書籍,試圖理解這些異鄉人的困境。
當他們離開家門時,心中都滿懷想望,但在某個心靈黑暗的時刻,夢想墜入深淵,人折了翼。折翼的人要如何熬過漫長的刑期,才能回到當初離開的家鄉?
2013年,特宏興368號漁船的「海上喋血」案震驚全台。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因為探視涉案的六名印尼漁工,而開始關注外籍漁工的勞動處境,我們試著了解,在他們成為人人喊打的「殺人犯」之前,經歷了什麼樣的事情?作為東南亞移工的身份,在他們身上留下了什麼烙印?而層層堆疊的結構和體制,又如何為這起殺人案件推湧暗潮?
隨著六漁工經歷三審、判刑定讞,進到位於桃園宏德新村2號的台北監獄,我們開始固定每個月到監獄探視。我們也才發現,在監獄裡還有許許多多離鄉背井來到台灣的移工,他們的罪名各不相同,刑期則從兩年到無期徒刑都有。
三年多來,我們持續與這些「罪大惡極」的人互動,漸漸發現他們作為一個異鄉人所面臨的困難;以及他們何以在尋夢的路上,偏離預期的航道,暫停在這陌生驛鄉。
一路上,我們有許多好朋友支持我們持續做探視工作:有開東南亞餐廳的朋友,每個月提供免費的印尼菜讓我們帶到監獄;有擔任空服員的朋友,趁出勤時到東南亞帶移工母國的書籍回來;也有朋友隔一段時間,就餵飽家裡的小豬撲滿給我們作為探視基金……
現在,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書寫,記錄下這些曲折的生命。透過他們的故事,讓我們看見過去被忽視的角落。我們相信,只有更多的看見與理解,才讓一切的改變成為可能。
作者簡介:
移工受刑人探視小組,主要成員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工作人員,以及長期探視移工受刑人的志工夥伴們。
章節試閱
異鄉撒網,離岸難回——
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
/莊舒晴
2013 年8月,海巡署將特宏興 368 號漁船自南太平洋戒押回台,當九名印尼漁工下船登上宜蘭蘇澳的土地時,遭遇不測的台籍船員家屬紛紛上前追打,一時全台媒體也不斷放送這起駭人聽聞的印尼漁工殺人事件。
作為移工團體,看到受害者家屬托著遺照哭泣的畫面,我們同樣感到悲傷及不忍,對於生命的驟然消逝,少有人能坦然面對。然而在同一個電視畫面裡,那些低著頭被痛斥和毆打的黝黑身體,也令人不禁擔心起在台灣長期被視為潛在危險份子的移工,是否會因著媒體的發酵,成為...
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
/莊舒晴
2013 年8月,海巡署將特宏興 368 號漁船自南太平洋戒押回台,當九名印尼漁工下船登上宜蘭蘇澳的土地時,遭遇不測的台籍船員家屬紛紛上前追打,一時全台媒體也不斷放送這起駭人聽聞的印尼漁工殺人事件。
作為移工團體,看到受害者家屬托著遺照哭泣的畫面,我們同樣感到悲傷及不忍,對於生命的驟然消逝,少有人能坦然面對。然而在同一個電視畫面裡,那些低著頭被痛斥和毆打的黝黑身體,也令人不禁擔心起在台灣長期被視為潛在危險份子的移工,是否會因著媒體的發酵,成為...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前言:宏德新村2號
/莊舒晴
2013年的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是我接觸移工受刑人的開端,當時TIWA 的工作人員在新聞上看見被民眾追打的印尼「殺人犯」,主動了解這些飄洋過海的異鄉人究竟經歷了什麼。他們何以狠下毒手將兩名台灣人都丟入汪洋大海,又企圖開船逃逸?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台北看守所,當時判刑尚未定讞, TIWA 和一群印尼移工浩浩蕩蕩搭車過去,兩人兩人一組,進到接見室裡隔著玻璃及鐵窗和六名受刑人說話。Anto、Yudi、Iham、Susanto、Retno、Lufin,他們在監獄裡沒有名字,只有編號;沒有未來,只有對漫長刑期的絕望。我們...
/莊舒晴
2013年的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是我接觸移工受刑人的開端,當時TIWA 的工作人員在新聞上看見被民眾追打的印尼「殺人犯」,主動了解這些飄洋過海的異鄉人究竟經歷了什麼。他們何以狠下毒手將兩名台灣人都丟入汪洋大海,又企圖開船逃逸?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台北看守所,當時判刑尚未定讞, TIWA 和一群印尼移工浩浩蕩蕩搭車過去,兩人兩人一組,進到接見室裡隔著玻璃及鐵窗和六名受刑人說話。Anto、Yudi、Iham、Susanto、Retno、Lufin,他們在監獄裡沒有名字,只有編號;沒有未來,只有對漫長刑期的絕望。我們...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宏德新村2號
台灣的外籍漁工制度:境內聘僱與境外聘僱
第一章
異鄉撒網,離岸難回——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
永劫回歸: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三年之後
在澎湖的異鄉人
在千萬人的城市裡尋找記憶的家——Agus的手繪地圖
海上的人
一個死亡的見證者——記Supriyanto之死
海上喋血大事記
第二章
移工很危險?
異鄉的苦牢——外籍受刑人在監狀況
囹圄城中城
虧欠、感謝、Bima
Yanto家鄉的等待:何時從心靈的黑洞歸來?
十年返鄉路——第一位畢業生,Joe
照片集
寫在後面
移工受刑人探視小組
台灣的外籍漁工制度:境內聘僱與境外聘僱
第一章
異鄉撒網,離岸難回——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
永劫回歸: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三年之後
在澎湖的異鄉人
在千萬人的城市裡尋找記憶的家——Agus的手繪地圖
海上的人
一個死亡的見證者——記Supriyanto之死
海上喋血大事記
第二章
移工很危險?
異鄉的苦牢——外籍受刑人在監狀況
囹圄城中城
虧欠、感謝、Bima
Yanto家鄉的等待:何時從心靈的黑洞歸來?
十年返鄉路——第一位畢業生,Joe
照片集
寫在後面
移工受刑人探視小組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