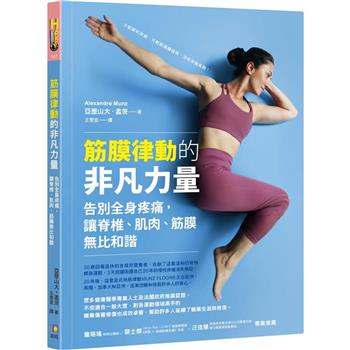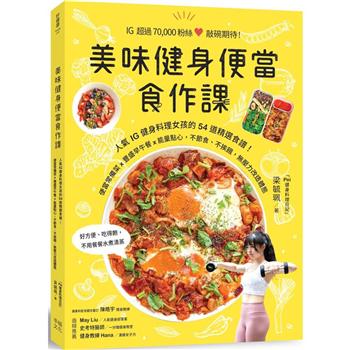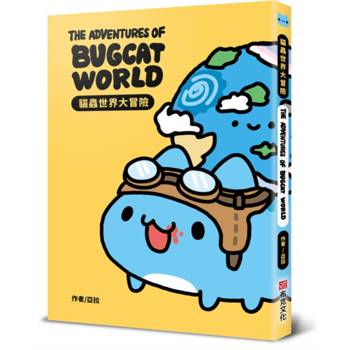《我的回顧與反思》是錢理群在北京大學最後一門課的講稿。在北京大學任教二十多年的錢理群,在2002年退休前夕,決定以自己為研究對象,講述個人生命歷程,同時總結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思想的變遷。 錢理群在1999年被票選為北大最受歡迎的教師,在北大的講課曾經風靡一時,各系甚至各校的學生都會慕名前來。他的學生、現任北大副教授的孔慶東,曾如此描述錢教授的上課情形:「他洶湧的激情,在擠滿了幾百人的大教室裡奔突著,回蕩著。他深刻的見解,時而引起一陣急雨般的掌聲,時而把學生牢牢釘在座位上,全場鴉雀無聲。」 如此影響了一整代北大學子的激情,如今濃縮在這本自我生命與整個歷史交錯的書中。
對他來說,「學術的探討,同時也是生命的掙扎;對研究對象的發現,也是對自我的發現」。換句話說,藉由這本書,我們不但可以瞭解一代學者的生命歷程,更可以理解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問題。 被人稱作「好為人師」的錢理群,更愛與年輕人在一起,即使被嘲笑有「青年崇拜」也不以為意。他自認欠了年輕人的債,認為自己這一代沒能把國家社會搞好,結果讓孩子來承擔,極為不公平。這樣的欠債感、罪惡感,構成了他教學與寫作的驅動力,也讓他決定在北大退休之後,仍要回到當年下鄉的貴州從事中學教職。 錢理群的出身與經歷都可以視為中國的一個縮影:他的父親是對台灣農業貢獻良多的錢天鶴,他的一位哥哥與姊姊則是共產黨員。父親為了救國,加入國民黨;哥哥姐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加入共產黨。這使他對國共兩黨時都帶著很深的感情,無法絕對站在任何一邊。對此,他所能作的,就是寫出歷史的複雜性。
本書以一種「精神自傳」的展現方式,細細回顧數十年來的治學生涯和人生故事,其清醒與深刻的自省鑄練出文字中飽含的情感,是認識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的重要著作。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李家同(前暨南大學校長)、李歐梵(文化評論家)、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文所教授)
老錢是一個北大精神象徵,中國批判知識分子標誌性人物。現在北大第一神話和傳奇,簡直就是北大的聖人。——蕭夏林(文化評論家)
錢理群的思想,通過北大和其他學校的課堂,輻射出去,影響了整個80年代的中國青年界。他的專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魯迅觀,他的周作人觀,他的中國知識分子觀,他的現代文學史觀,早已成為一代學子共同的精神財富。——孔慶東(北大中文系教授)
六十多歲的錢老始終懷抱著一股感情的熱流。書?洋溢的孩童的天真、倔強,匹配了冷靜和義無返顧的決絕,尤為震撼人心。學術不是孩子,但學者應該保持兒童式的懷疑、好奇、赤誠、窮追猛究的激情。向上的天梯孤絕傲立,為什麼還要讀錢理群,已不言而喻。——大眾日報 黃亞明(書評人)
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代知識分子的痛苦和徬徨,他們在逆境中的掙扎與思考。因為他對自己精神世界的袒露,我們也就更能理解魯迅對於他的重要意義。在他那?,「所有的學術討論,對外部世界歷史與現實的追問,都最後歸結為自我內心的逼問,對於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新京報
錢理群堪稱中國現代文化「所化之人」。他全面系統研究了從魯迅、周作人到曹禺,從艾青到穆旦,從五四新文化到左翼文學,到四十年代文學的歷史,他的獨特的研究方式,用他常用的話說是「將自己燒在?面」,「學術的探討,同時也是生命的掙扎;對研究對象的發現,也是對自我的發現」,能使我們經常能從錢理群身上,看到他研究對象的影子。——薛毅(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名人推薦:李家同(前暨南大學校長)、李歐梵(文化評論家)、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文所教授)
老錢是一個北大精神象徵,中國批判知識分子標誌性人物。現在北大第一神話和傳奇,簡直就是北大的聖人。——蕭夏林(文化評論家)
錢理群的思想,通過北大和其他學校的課堂,輻射出去,影響了整個80年代的中國青年界。他的專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魯迅觀,他的周作人觀,他的中國知識分子觀,他的現代文學史觀,早已成為一代學子共同的精神財富。——孔慶東(北大中文系教授)
六十多歲的錢老始終懷抱著一股感情的...
章節試閱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
我的研究工作在學術界從來是有爭議的,或者說是愛憎分明:喜歡就非常喜歡,討厭就非常討厭。我自己很滿意於這樣一個命運。因為一個學者,不能要求大家都說他好,有爭議就說明有特色,有特色就會有問題。這是一個錢幣的兩面。魯迅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文化偏至論》,我就希望自己做一個「偏至的學者」,而不願做一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人人說好的學者。
現在開始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六十多歲講傳記材料似乎有點早,按照中國傳統應該到七十、八十歲。但是我又一想,萬一死掉怎麼辦?所以現在先來講一點,其實這些材料以前都在書裡寫過,今天不過是系統化一點,再補充一些細節。
我曾經說過,我的研究有兩個目的,一個是「還債」,一個是「圓夢」。那麼,我有什麼「債」?簡單說起來,是三筆債:欠家庭的債,欠年輕人的債,欠自己的債。
我的家庭
先談家庭。我出身於世家。外祖父項蘭生,他一生經歷很豐富,從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我昨晚還在看他的年譜,看得津津有味。外祖父出生於1873年,是晚清著名的維新派思想家王韜的學生。他的年譜裡有一段對王韜的回憶很有意思:「韜師住四馬路十路……韜師談論甚豪,論天下 論天下大勢,歷兩時許,滔滔不絕。」第二天他又請外祖父吃飯,「並贈著述十數種,以後往見數次,幾曾嘉許,頗得教益,並嘗通書後,對於八股文不必看的太重,務必多讀史書,認識世界大勢,為立身行己基礎。功名問題,可以堅決放棄。」這裡記述了我外祖受王韜那一代的影響,老師強調的是:八股不要看得太重,要多讀史書,認識世界大勢。這是一個非常開闊的眼光。後來我外祖父成為維新派人士,他最早在杭州辦白話報,開辦安定學堂;然後又擔任浙路公司公務科長。辦學堂,辦報紙,修公路,這都是開時代風氣之先的。以後他做了大清銀行的秘書官,他的日記記載了辛亥革命時大清銀行界對革命的反應,我看了覺得很有史料價值。以後他又創辦浙江興業銀行,擔任董事長,到50歲時就退休了,56歲(1928年)時完全退休。可以看出他是早期維新派人士,而且又較早參與中國銀行界,應該是江浙實業界的一個代表人物。
我的父親天鶴先生是安定學堂第五屆畢業生,外祖父就把長女嫁給自己的得意門生。我的母親從小受西式教育,請英語老師教英文。父親後來大概是1906或1908年去美國留學。他先是考取了清華學堂預科,然後從清華畢業後到美國康乃爾大學學農科。胡適也在那裡學農科,他應該是胡適同學。我曾談過20世紀初有兩次留學高潮:第一次是包括魯迅在內的留日學生,主要學習人文科學,學軍事,學政治;第二次高潮是我父親這一撥留美學生,主要學習自然科學。那時著名自然科學家竺可楨,語言學家趙元任等都是我父親的朋友。他們發起組織自然科學家團體,辦《科學》雜誌,我父親是最早發起人之一。我曾經研究過他們的《科學》雜誌。當時在中國比較早提倡民主科學,一個是《新青年》,另一個就是《科學》雜誌。我們過去對自然科學這一塊不夠重視,其實真要研究五四,自然科學家是不能忽略的。我父親基本主張農業治國,是農業方面的專家。後來「好政府主義」成為這批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強調要改變中國面貌必須進入體制內,這與我們今天某些知識分子的思考非常接近。所以蔣介石1928年統一中國後,國民黨也試圖走專家治國的道路,有一批專家進入國民黨政府機構內,我父親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參加國民黨政府,在抗戰時擔任國民黨政府農業部的常務司長,相當於今天主持業務工作的副部長。我父親主持全國農業有十五年之久,在抗戰時期對大後方農業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我研究了他的農業思想,覺得非常有意思。他提出一個觀點:發展農業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農民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為達到這個目的要綜合發展,強調農業的商品性,發展商品農業,而且從金融,信貸,生產,流通,科技,教育----各個環節發展農業經濟,這些農業經濟思想與今天非常接近。但當時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下不可能實現,實際上沒起多大作用。在我看來這也是個悲劇。總的說來,我父親屬於胡適這個體系。1948年胡適準備組閣,我父親是他組閣名單中的農林部長。我另外一個哥哥,三哥,抗戰時從淪陷區逃到重慶,後來跟穆旦他們一樣作為大學生當美軍翻譯,以後進入外交界,1949年從大陸到臺灣,以後又到美國,作國民黨駐舊金山領事。他和父親都屬於國民黨系統。
我另外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屬於共產黨系統。我們家庭有兩次大分離,一次是抗戰初期,父親隨國民黨遷重慶,就把幾個較大的哥姐留在上海外祖父和舅舅家,我生於重慶,當時哥姐還在上海淪陷區,我們沒見過面。我二姐抗戰時參加共產黨地下工作,從上海參加新四軍,成為一個文工團員。她的丈夫丁毅,就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是一個忠實的老共產黨員。我和二姐解放後才見面。還有一個在淪陷區的哥哥也參加地下黨,成了南京學生運動的一個領導人。在《1948:天地玄黃》有兩個地方提到我的哥哥姐姐,別人不知道,這裡告訴大家一個秘密。裡面有兩章比較特別,別的文學史家不會寫,這與我的家庭遭遇有關。其中一章寫學生運動中的文藝活動,可以說這一章是為我的哥哥寫的。還有一章寫解放區的文工團活動,為的是紀念我姐姐,而且還引用了一段她的文字,是有關知識青年與戰士結合的感受,寫得非常生動。我用這種方式默默紀念我的哥哥姐姐,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大家後來不提這些老共產黨員,我覺得不大公平,所以我盡可能的寫到他們當年的貢獻。
我們家第二次大分離是1949年前後。1948年我父親把我們從南京帶到上海,當時準備從上海逃到廣州,再逃到臺灣去。結果到上海後我母親不肯走,因為他們兄弟姐妹一家人都在上海,我外祖父的好朋友陳叔通和張元濟當時都是進步人士,跟共產黨有聯繫,所以我母親不肯走。於是就讓我父親到臺灣看一看,一看就回不來了。所以這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曾經跟李歐梵先生開玩笑說(我們兩個同年),如果當年到了臺灣,就是跟他在一起了,所以歷史是說不清楚的。這就是我們家第二次分離:我父親去了臺灣,我當外交官的哥哥去了臺灣,後來我大哥去美國留學。我們家後來再也沒團圓過,我曾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家的悲劇:生不團圓,死各一方:我父親葬于臺灣,三哥葬於舊金山,母親葬于南京。
我講這一段歷史有什麼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是研究現代文學,現代思想史,特別是研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的,而我們家庭就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高度縮影,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類型在我們家都有體現。我父親可以看作進入體制內的知識分子,而我留學美國的哥哥則可以看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實我父親也多少帶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色彩,是代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進入體制的類型,我的參加共產黨的哥哥姐姐和姐夫是典型的忠誠的共產黨員,而我們最小的三個則是新中國以後培養出的人才。我們解放後都受到比較完整的教育,我的小哥哥在清華大學學工科,姐姐讀北師大,我是在北大,但我們三個都因為家庭問題發送到邊遠的地方,我姐姐到新疆,哥哥到福建,我到貴州,這都很典型的體現了我們這種家庭出身在解放後的命運。改革開放後我們各自命運又發生巨大變化,變化最大的是我們最小的幾個,我哥哥成了福州大學校長,我姐姐是烏魯木齊市特級教師,我成了北大教授。我們整個家庭就是各類知識分子的濃縮,也就是說我的研究面對的不是與己無關的對象,某種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我的家庭,或者說研究我自己。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我的研究工作在學術界從來是有爭議的,或者說是愛憎分明:喜歡就非常喜歡,討厭就非常討厭。我自己很滿意於這樣一個命運。因為一個學者,不能要求大家都說他好,有爭議就說明有特色,有特色就會有問題。這是一個錢幣的兩面。魯迅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文化偏至論》,我就希望自己做一個「偏至的學者」,而不願做一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人人說好的學者。現在開始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六十多歲講傳記材料似乎有點早,按照中國傳統應該到七十、八十歲。但是我又一想,萬一死掉怎麼辦?所以現在先來講一點,其實...
目錄
引言:“以不切題為宗旨”
第一講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上)
第二講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中)
第三講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下)
第四講 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
第五講 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
第六講 對啟蒙主義的反思
第七講 對理想主義的反思
第八講 思想與行動的關係問題
第九講 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
第十講 最後的話題:關於大學教育和北大傳統
引言:“以不切題為宗旨”
第一講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上)
第二講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中)
第三講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下)
第四講 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
第五講 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
第六講 對啟蒙主義的反思
第七講 對理想主義的反思
第八講 思想與行動的關係問題
第九講 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
第十講 最後的話題:關於大學教育和北大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