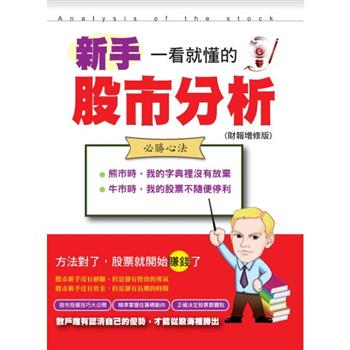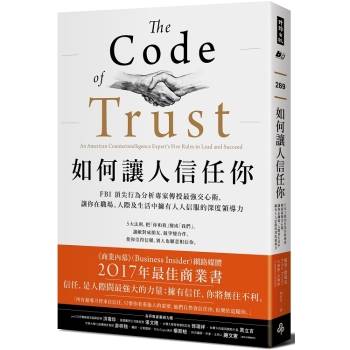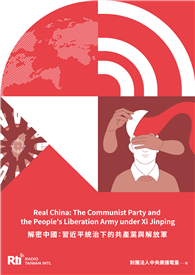英格瑪柏格曼
文|瑪麗特柯斯金納 Maaret Koskinen(斯德哥爾摩大學電影學系教授、瑞典《每日新聞》Dagens Nyheter影評人)
翻譯|郭敏容、塗翔文
前言:一個費里尼,一個安東尼奧尼,一個塔科夫斯基
毫無疑問,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是國際間最著名的瑞典人之一。他不僅是瑞典有史以來最重要的電影人,同時也被公認為世界電影藝術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柏格曼屬於一個相對少數、專屬的電影人集合體──費里尼(Fellini)、安東尼奧尼(Antonioni)、塔科夫斯基(Tarkovsky),這些人的姓幾乎不需要伴隨名,提到他們,只要說姓氏就夠了。「柏格曼」已經是一個概念,它本身就是「品牌」。
單從創作數量來看,柏格曼作為電影藝術家的生涯就已經不同凡響了。從他執導的首部影片《危機》(Crisis,1946)到《芬妮與亞歷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1982),柏格曼總共導演了四十多部電影,其中的一些──如《裸夜》(The Naked Night,1953)、《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1957)、《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1957)、《沉默》(The Silence,1963)和《假面》(Persona,1966)──被認為是電影史上的絕對經典。然而,柏格曼真正獨特、並讓他獲得國際聲譽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能將電影這本質既是工業,也是藝術的大眾傳播媒介,轉為極個人化的表達形式,既用來刻劃存在及心理的困境,在描繪現實世界的衝突上一樣自如。
而與他的電影藝術生涯並行,柏格曼同時也從事劇場創作。他在瑞典及海外導演過不計其數的戲劇作品。事實上,早在年輕的學生時代,柏格曼就開始了他的戲劇導演生涯,幾乎延續到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他最後一齣執導的作品在2002年。他曾經說:「要我離開戲院,得先把我扛出去。」
Ⅰ 電影
生平背景
英格瑪柏格曼在1918年7月14日出生於烏普薩拉(Uppsala),是卡琳安克布魯姆(Karin, née Åkerblom)和艾瑞克柏格曼(Erik Bergman)的孩子。父親艾瑞克是瑞典國教牧師,後擔任國王專屬牧師。柏格曼在大約十歲時擁有了「魔燈」,也就是影片放映機。根據柏格曼的自述,這是一個「會咔嗒作響的鐵盒子,外加一管煙囪、一盞煤油燈以及一條不斷循環的膠卷」,這個「魔術機器」搖曳的光影投射在母親懸掛的床單上,讓他感到奇異的「神秘與刺激」。這台原始的影片放映機,成了柏格曼的創作源泉,這一點在兩方面可清楚的得到印證:一個是《魔術師》(The Magician,1958,另有譯名為The Face)。片中,藉由催眠師兼藝術家沃格勒之手出現;另外則是在半自傳性作品《芬妮和亞歷山大》,出現在少年亞歷山大的臥房。柏格曼以這個童年的玩具為自己的回憶錄定名《魔燈》(Laterna Magica,1987,中文繁體版譯為《柏格曼自傳》),也絕非偶然。
在幼年時,柏格曼也有過一組偶戲團。他自己製作小木偶、畫景、並寫短劇,這個偶劇團經過他少年時代,逐漸擴張。他所添設的燈光、轉台和滑動台「又大又重的塞滿了我的房間,沒有人進的去。」
換句話說,仍在孩提時,柏格曼就已經沉浸於他後來將整個職業生涯都投入其中的兩個領域裡:戲劇和電影。成年之後,他將戲劇稱作他「忠誠的妻子」,而電影則是他「奢侈的情人」。
不過,童年時代對柏格曼後來作品的重要影響,在其他部分也得到了證實。一方面,它在創作過程中是一個無窮盡的靈感源泉。柏格曼曾在《柏格曼自傳》中寫道:「我仍然能夠漫步於我童年的風景中,並再一次體驗到那光線、氣味、人群、房間、瞬間、姿態、語調和物體。」另一方面,就像他後來多次提及的,童年還有一層很重要的特殊意義,尤其當它涉及到柏格曼與他父母間充滿衝突的關係。這一關係以反覆出現的主題和母題,在多部電影中得到了明確的展現。這包括柏格曼在關注藝術家所面臨問題的作品中,「真實/假象」的主題和「羞恥」的母題在其中所佔據的顯著位置。就像一個生活在家規嚴格的家庭中的孩子一樣,藝術家發現自己被放逐到了社會權力等級結構中的最底層。
從其他方面來看,柏格曼的電影作品似乎同樣源自於個人洞察與體驗。一位早期的柏格曼傳記作家瑪麗安霍克(Marianne Höök)就曾寫道:「柏格曼的作品帶有強烈的自傳性,是以第一人稱敘述的戲劇,以眾多聲音道出獨白。」一些研究柏格曼的學者說,他們甚至能在柏格曼影片的拍攝年代列表中,發現某種自傳性的「生命曲線」:早期作品是脆弱的年輕人面對難以理解的成人世界;五○年代前期那些相對成熟的影片表達「對性和婚姻的困惑」;五○年代後期及六○年代大部分影片的共同特點則是「對宗教的掙扎和對藝術的疑問」;而他六○及七○年代心理分析取向的影片,部分以自我分析的方式呈現,在這些影片中,不同的人物似乎成了某一個心靈或敘述者的多個面向。在這個進程中,甚至還能偵查到某種譬喻,用瑞典裔美籍、研究柏格曼的學者碧姬塔斯丁(Birgitta Steene)的話來說,就是從「關於心靈的發展推論到現代人類心靈的發展。」
這些自傳性的聯繫,在某種程度上也由柏格曼本人在《柏格曼論電影》(Bilder,1990)一書中進行了證實。柏格曼在這本關於他影片的回憶錄中自述他要呈現作品的來源──他的五臟六腑,以及那些使其作品成形的體驗和記憶。在九○年代,柏格曼還開始了另一項寫作計劃,試圖為父母和自己的童年時代提供一幅更為細膩的肖像畫。這就是將小說與劇本合而為一的《善意的背叛》(Good Intentions,1991)、以及由他兒子丹尼爾柏格曼(Daniel Bergman)執導的影片《週日生活點滴》(Sunday’s Children,1992)的劇本創作。柏格曼對自身的描述,可用來解釋他影片中寓言式自我心理分析的另一個證據。正如柏格曼在談到《善意的背叛》時所說:「我所創作的是一幅非常奇異的圖畫……它可能是母親,可能是父親,但也可能就是我。」
主題、風格和藝術發展
顯然,對英格瑪柏格曼來說,藝術與生活是一體的。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有理由對僅僅依據「生平事實」來解讀柏格曼作品的方法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這樣做不僅有陷入個人崇拜的危險,更糟糕的是,當這種對創作者(假定)的情感生活的「診斷」不知不覺成為焦點時,柏格曼作品──影片本身──卻反過來要承受被忽視的危險。正如跨芬蘭及瑞典的作家兼文化評論家約恩多納(Jörn Donner)在他關於柏格曼的著作中指出的,論者從柏格曼藝術生涯的初始就對他本人懷有相當強烈的興趣,而這一特點在瑞典作家的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他們在這裡尋找的是……柏格曼的面孔、他的靈魂,但他們卻忘記了尋找柏格曼電影所展示的面孔。」
作為一種「平衡」,值得注意的是,柏格曼在電影生涯早期就表現出的非凡的多樣性。從一部影片到另一部影片,從一個十年到下一個十年,柏格曼電影的主題與風格化元素都歷經了不斷的變化、能量的迸發以及內涵的轉換。實際上,這種現象所達到的程度,已經使人們無法再套用任何一種傳統意義上的發展曲線,來整理柏格曼的作品。取而代之,他的藝術發展模式,像是在循環的位置裡反覆做著相似運動的某種螺旋體;而它每次的運動,又都是在不同的層面上進行的。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瑞典電影(POD)的圖書 |
 |
瑞典電影(POD) 作者:台北電影節統籌部 出版社: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出版日期:2012-07-09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61 |
戲劇 |
$ 269 |
中文書 |
$ 270 |
政府出版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瑞典電影(POD)
瑞典電影(Pod)
/a>
理解人類生存的狀態,原來道道都是難題。然而這些愛與恨,透過銀幕嵌入我們的腦海,每個畫面都是短暫的混亂、萬物常規的裂隙,這些畫面不像特寫一樣讓渡協商,不以目的或意義的頓悟來企求挽救日常生活,而是讓畫面自己說話——每個情境都承載著矛盾的可能。瑞典的電影,也因觸及語言與文字難以形容的祕境,而永難取代。
作者簡介:
台北電影節統籌部
隸屬於台北市文化基金會,1998年創辦至今,所舉辦的影展一直是每年夏天最重要的電影活動之一。每年選映超過160部的國內外影片,以「國際青年導演競賽」、「主題城市」、「台北電影獎」為主要節目單元。
主編 塗翔文
曾任媒體與電影圈多項相關工作,參與電影編劇作品《第四張畫》,著有《電影A咖開麥拉》一書。現任台北電影節策展人。
章節試閱
英格瑪柏格曼
文|瑪麗特柯斯金納 Maaret Koskinen(斯德哥爾摩大學電影學系教授、瑞典《每日新聞》Dagens Nyheter影評人)
翻譯|郭敏容、塗翔文
前言:一個費里尼,一個安東尼奧尼,一個塔科夫斯基
毫無疑問,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是國際間最著名的瑞典人之一。他不僅是瑞典有史以來最重要的電影人,同時也被公認為世界電影藝術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柏格曼屬於一個相對少數、專屬的電影人集合體──費里尼(Fellini)、安東尼奧尼(Antonioni)、塔科夫斯基(Tarkovsky),這些人的姓幾乎不需要伴隨名,提到他們,只要說姓...
文|瑪麗特柯斯金納 Maaret Koskinen(斯德哥爾摩大學電影學系教授、瑞典《每日新聞》Dagens Nyheter影評人)
翻譯|郭敏容、塗翔文
前言:一個費里尼,一個安東尼奧尼,一個塔科夫斯基
毫無疑問,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是國際間最著名的瑞典人之一。他不僅是瑞典有史以來最重要的電影人,同時也被公認為世界電影藝術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柏格曼屬於一個相對少數、專屬的電影人集合體──費里尼(Fellini)、安東尼奧尼(Antonioni)、塔科夫斯基(Tarkovsky),這些人的姓幾乎不需要伴隨名,提到他們,只要說姓...
»看全部
作者序
在電影研究的領域中,「國族電影」(National Cinema)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傳統且過於廣泛的概念,它是以國家或民族劃分,探討不同地區電影的獨特性,並且可從美學、歷史、經濟、文化甚至政策的角度切入,進行研究或解讀。有趣的是,在如今世界電影的發展大勢下,全球化的路線與跨國合作的普遍性,似乎也讓某些人對於這種以「國家」做為電影研究標的之路線,開始產生質疑。
但是,在電影研究與電影論述並非蔚為文化主流的台灣,我們除了對少數地區的電影(如美國、法國)有較為普及或廣泛的論述之外,其實若要尋找對於其他世界各國的中文電影...
但是,在電影研究與電影論述並非蔚為文化主流的台灣,我們除了對少數地區的電影(如美國、法國)有較為普及或廣泛的論述之外,其實若要尋找對於其他世界各國的中文電影...
»看全部
目錄
序
PART 1 軌跡
瑞典電影的早期發展:六○年代之前│塗翔文
從六○年代迄今的瑞典電影│佛瑞卓克沙林
當代瑞典電影│塗翔文
PART 2 對望柏格曼
英格瑪柏格曼│瑪麗特柯斯金納
柏格曼深淵中的迷離光影│黃建業
對照集:那些恨柏格曼以及柏格曼所愛的│聞天祥
我的迷戀與他的迷戀│林書宇
臉之特寫│李時雍
PART 3 焦點導演
洛伊安德森:日常生活的矛盾本質│James Callow
魯本奧斯倫:社會現象實驗室│李達義
瑞典重要導演、演員小傳
柏格曼的其他作品
PART 1 軌跡
瑞典電影的早期發展:六○年代之前│塗翔文
從六○年代迄今的瑞典電影│佛瑞卓克沙林
當代瑞典電影│塗翔文
PART 2 對望柏格曼
英格瑪柏格曼│瑪麗特柯斯金納
柏格曼深淵中的迷離光影│黃建業
對照集:那些恨柏格曼以及柏格曼所愛的│聞天祥
我的迷戀與他的迷戀│林書宇
臉之特寫│李時雍
PART 3 焦點導演
洛伊安德森:日常生活的矛盾本質│James Callow
魯本奧斯倫:社會現象實驗室│李達義
瑞典重要導演、演員小傳
柏格曼的其他作品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台北電影節統籌部
- 出版社: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出版日期:2012-07-09 ISBN/ISSN:978986841465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 類別: 中文書> 政府考用> 政府出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