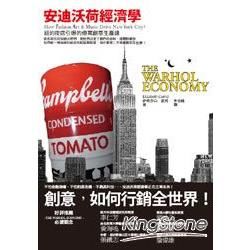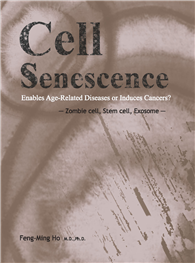看見創意行銷全世界的經濟力!
這些現代的安迪沃荷們,是他們決定了我們的品味、流行與美感。
他們每晚在紐約夜店裡,快速激盪發想創意,結合名人、傳奇與商品,
在天亮後大量生產、再快速推向全世界。
這種經濟躲過金融海嘯、不怕能源危機,不靠高科技
它是在夜店裡打造的億萬創意生產線,它是安迪沃荷經濟學。
這是一本真正扭轉人們看待未來經濟發展新重心的鮮活作品,書的場景發生在紐約;而要探討的是紐約真正贏得全世界優勢的幕後故事──文化、流行與創意產業在這裡是如何紮根與散布到全球市場。
南加大的年輕女教授裘芮在這本書中,提供了許多第一手的報導,訪問了超過百位的紐約時尚界及文化經濟名人與觀察者,包含了名製作人昆西、瓊斯、當紅設計師馬可.傑可柏斯、Zac Posen、Diane von Furstenberg(美國時裝協會主席)、藝術家Ryan McGinness、靠部落格自發片而崛起的「拍手叫好」(Clap Your Hands Say Yeah)樂團,及首倡城市中「創意階級」族群興起的城市學大師理察.佛羅里達等。
而本書也證明了紐約經濟的長期成功,其實不是靠櫛比鱗次的企業總部及快速嗜血的金融市場脈動,而是靠它強大密集的文化、藝術及創意社群條件。這些條件配合著媒體與互動頻繁的「文創產業社交圈」,使得紐約得以享有全球品味的決定權、讓一首歌或一款象徵能以鋪天蓋地的湧向全球市場並攖取利潤。
回顧經濟史,紐約就算在美國經濟最黑暗的時代,它的衰退期也比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要短得多;時至今日,過去推動紐約成長的經濟能力如:貿易港、製造中心,已成為退位的功能(這些優勢別的城市「只要努力都能追得上」);不過,論起讓一個新設計師尋找更多的試身手機會、藝術界的前輩與新秀「偶遇」或然率最高、音樂樂手的初登台可能性最大的地方,仍非紐約莫屬。
這裡是世界文創產業經濟勢力與工作者的天堂,這裡每晚的夜店與舞池就藏著無數個全球流行概念與爆紅商品的開端。這樣的紐約生態推到極致,就猶如主張讓藝術與金錢深刻聯結的安迪沃荷那句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擁有成名15分鐘的機會。」
這種主宰未來,靠城市與創意圈發生、在夜店裡杯觥交錯間蘊釀的「軟經濟」力是怎麼一回事,它是否能搬來台灣的都市中上演,紐約「沃荷經濟學」,紐約的全球品味製造者社群,是門最值得我們讀的競爭趨勢學。
章節試閱
看不見的社交生活產業
社交網絡是人們來紐約搞創意的原因。紐約的藝術與文化很少有什麼事純是因為個人表現好的關係,社交網絡才是最實際的,總歸一句話:一切都要看你認識了誰。
還有,你認識的人認識誰。
4月底一個晴朗的週末下午,淺藍色的天空看不出一絲雲或是夜晚的跡象。我跟最要好的朋友瑪麗莎走在西村的西四街上,想找馬克.傑可伯斯的店。我知道店位在布里克街(Bleecker Street),但西村的街道迂迴曲折,知道這點並不能幫助我們找到目的地。我看看四周,跟一個穿著體面、有點年紀的男人打了照面。
「先生,你不會剛好知道布里克街在哪邊吧?」我問他。
「當然,」他回答。「往那邊走一個路口就是。」
「謝謝,我們在找馬克.傑可伯斯的店,」我解釋說。
「喔,就在那個街角,」他說,「其實我認識馬克。我就住西村,離他很近。」
隨機偶然中的創意經濟與社交
馬克?他直呼他的名字。顯然他們是朋友,或至少認識。馬克.傑可伯斯是時尚界長期以來的寵兒,一頭蓬亂厚重的棕髮,喜歡穿長袖帽T,擅長把1940年代的女教師套裝設計得性感無比。他可說是自拉夫.羅蘭之後最多產、也最受讚譽的美國設計師,在羅蘭與商業妥協之後,他仍維持著威望和自我的品牌。傑可伯斯是現代美國時尚的寫照。我很愛他。
「你認識馬克.傑可伯斯?」
「是啊,我們是朋友。我叫吉爾斯,我做珠寶的。」
機不可失,我立刻開始解釋我的研究計畫,以及我非常想要訪問馬克。
「嗯,馬克應該很適合,而且我想他會有興趣,」吉爾斯回答。「我這禮拜會見到他。妳把連絡方式給我,我拿給他,跟他提一下。我想他會讓妳訪問。」
這幾個月來,我一直設法連絡馬克.傑可伯斯,打電話到他的總辦公室,寄電子郵件給在時尚界工作的朋友,拷問受訪者看能不能弄到連絡方法,統統沒有結果。沒想到就在這裡,一個買鞋子的晴天週末下午,我真的就撞上一個訪問機會。於是,我想把這個故事送給住在紐約、渴望出人頭地、找到成功機會的幾百萬個藝術家、設計師、樂手等創意生產人。
要看出這類互動有多重要並不難。但若要了解這類互動的廣泛影響,尤其是在今天的城市環境裡,我們就得去探索過去三十年來這座城市和經濟經歷過哪些改變。驅動今日經濟發展的那些動力學,讓城市生活的架構以及隨機性的對話和巧遇,變得比以前更重要,也更意義深遠。
人力資本為後工業經濟之母
1970年代時,全美各城市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經濟跌到谷底。十九世紀晚期興起的製造業,原是美國的經濟之本,但很快(幾乎是一夜之間)就成了西方經濟世界裡的昨日黃花。從紐約、匹茲堡到底特律,曾經提供都會中心成千上萬個工作機會和數十億收益的高級製造業,面臨了嚴重危機。日益加速的全球化和科技發展,讓原料得以在世界各地輕鬆運送,也就是說,製造業公司可以直接在發展中國家設廠,利用當地的便宜勞工與源源不斷的資源。全球諸如巴西等國家,都提升了煉鋼技術,讓匹茲堡和克里夫蘭的鋼鐵公司變成花費昂貴的過時品。美國城市的製造業再也沒有競爭力。許多地方很快淪為城市廢墟,深陷在高失業率和財政大出血的痛苦泥沼,廢棄的製造廠和工廠,以及冷清的市中心,變成了犯罪的溫床。
在這同時,奇怪的事情也在進行著。雖然全國的製造業經濟都面臨危機,但有些地方不但躲了過去,甚至還發展得非常非常好。舊金山外圍的矽谷以及整個南加州,商業正在蓬勃發展。該地的經濟雖然與生產有關,但卻是完全不同的產業—主要是高科技產品(南加州的部分則是娛樂相關產業)。在此同時,紐約市雖然也遭逢嚴重的財務危機,但來自其他產業的獲益,減輕了製造業衰退所帶來的效應。就在製造業於紐約崩盤的時刻,其他諸如金融、管理、娛樂及服務等產業,則邁出大步,取代紐約市製造業的地位,到了1980年代中期,城裡的經濟幾乎全面復甦。
這些新產業製造的產品,跟製造業全然不同,彼此之間也沒有相似之處。最明顯的證據便是,雖然美國經濟全面蕭條,但這些產業卻發展得既茁壯又強盛。它們的成功,不是因為產品的不同(不管是電腦、會計試算表或設計師服裝),而是生產方式的不同。
1973年,就在製造業經濟崩盤的前夕,哈佛大學社會學家丹尼.貝爾(Daniel Bell),就全球經濟的轉變寫了一本預言般的著作——《後工業社會的來臨》(The Coming of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當時貝爾在書中提出,經濟基礎將發生徹底改變,將從製造業轉變成資訊、科學及科技,而且將以提供服務為導向。貝爾認為,後工業主義將成為支配一切的架構,社會與經濟將在這樣的結構之下運作。再看一次那些在製造業下滑之際逆勢繁榮的產業—科學、科技、金融、娛樂等等,然後想想,這些產業與過去百年來驅動美國經濟(事實上也是世界經濟)的製造業有多麼不同。
鋼鐵廠和生產線不會自己運作。它們需要工人,也需要一小群懂得在生產科技上創新,或是決定新產品及塑造工作環境的人。但貝爾的後工業經濟,亦即主導矽谷和1980年代中期的紐約市的那種經濟,卻是由能夠持續革新並創造先進的工作新方式的產業所構成。凡是革新方法的集中程度越高,負責革新的人士越多的地方,就越為成功。就是因為這樣,在製造業一片沒落的風潮中,擁有許多工程師、電腦科學家和設計專家(革新背後的高人力資本)的矽谷,不但擁有繁榮的經濟,甚至還顯示出光明無限的前景。紐約市雖然受到工業崩潰的牽連,但正設法以比其他都市更快的腳步踏上復甦之路,因為它已經開始建立以人力資本為導向的產業,包括金融與娛樂業等。換句話說,後工業經濟的存在與否,乃取決於人力資本的有無。
革新者(不論是設計半導體或專輯封面)需要技術才能勝任,而且這些技術多半是經由正式學習得來的,而非邊做邊學。因此,為了分析「人力資本」與都會或地區生產力的關係,經濟學家通常會把當地的「基本教育程度」(大學畢業以上)納入考慮。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葛拉瑟,是一位充滿活力、思緒敏捷的經濟學者,他為測試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做過了無數分析。他發現,1980年與1990年的高人力資本產業,都預言了未來數十年將帶來集中度更高的高技術勞工,以及更好的經濟生產力。
維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公共政策系的教授佛羅里達,則非常中肯地詳述了社交與人力資本在經濟成長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1999年初次遇見他,當時我還在匹茲堡的卡內基美隆大學就讀。當時在該校任教的佛羅里達,已經觀察到一些經濟活躍城市之間的差別,並開始思考其中的原由。在那之前,他曾探討過大量生產的衰退以及高科技工業區在日本與矽谷的興起,並深獲好評,但他有關城市與經濟發展的研究,又把他帶往一個新方向。
在佛羅里達針對「人力資本」進行更細微的觀察之後,他指出,成功的城市都有高集中度的創意人士,他稱之為「創意階級」,這是一個比藝術與文化工作者還要廣泛的分類。但這些創意人士是哪些人呢?這跟他們受多少教育比較無關(雖然這經常被拿來預測某人或某個階級在工作時的創新程度),而和他們用自己的人力資本做些什麼,以及如何運用創意和想法有關。佛羅里達採用職業類別而非教育程度,來測試每個城市的表現。舉例來說,一個藝術家、作家或樂手可能沒有大學文憑,但他們的工作本身需要不斷創新。
超級創新者如比爾.蓋茲(Bill Gates)從大學輟學,但替社會策劃了科技演進。佛羅里達的數據證實了,擁有最多人從事革新職業的城市,經濟成就也最高。佛羅里達的論點,相當能夠解釋貝爾的後工業經濟之運作:人們驅動經濟成長,因為人類的想法與創意是革新的要點,刺激了經濟擴張。擁有最多人參與以想法驅動的產業及職業的地方,經濟生產力就最高。
人際互動和概念分享是發展新經濟的關鍵力量
不過,教人意外的是,這類勞動零件與部門的轉換,卻也促成了處理人員之間的資訊與知識交流。大家開始交談心得,交流筆記,交換工作。當工程師或設計師彼此碰面時,會聊到某台新電腦的設計如何跟內部的硬體配合,或是某種特別布料很適合某設計師的春裝等等。他們可能交換了許多想法,甚至是與當下工作沒直接相關的想法,可能是其他打樣師的名字,或是米蘭時尚工業的狀況。這類知識交流,最後會被轉譯成新的想法和新的產品,改革者把想法帶入新環境,解決長久以來困擾公司的問題,建立增值知識,帶來突破。
當人們跟自己公司以外的人交流,通常會從彼此身上得到靈感,腦力激盪出新的產品,分享新科技的知識。生產新產品所牽涉到的勞力分工,讓人們依賴彼此,進而在這樣的過程中發現,「非物質資本」(nonmaterial capital),也就是人際互動和概念分享,對於公司或產業的生存,和物質資本具有同等重要性。經濟地理學家麥可.史托普(Michael Storper)將這種現象稱為「非交易式的相互依賴」,若想了解為何某個地方的新經濟發展優於其他地方,這點非常重要。
安娜李.薩克瑟尼安(Annalee Saxenian)是政治學者及都市計畫專家,目前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資訊管理學院院長,她探討過矽谷的成功與波士頓「128公路」的明顯失敗。128公路是圍繞波士頓的公路,距市中心大約十英里,把遙遠的郊區與市區隔開,二十世紀中有很長一段時間,這條公路曾經是高科技生產中心。然而到了1990年代,幾乎在一夜之間,矽谷出頭,128公路沒落。原因不只是因為矽谷的生產增加,更是因為它成為半導體及微處理器工業的革新領導者。薩克瑟尼安訪問了許多曾經從事高科技產業的人,從電腦工程師、創業投資人、經理,到那些管理高科技公司貿易協會的人。最後她發現,這兩個高科技生產中心最大的差別在於它們的運作模式。128公路的運作方式跟製造業的組織很像─大型獨立公司,不跟其他公司分享資訊,擔心想法被盜用後產生競爭,導致公司營運下滑。相對的,矽谷卻營造出一種合作互助的環境,許多工作是由去中心化的生產網絡裡的眾多小公司所完成;而這正是皮歐與薩伯的「彈性專業化」的最佳範例。
矽谷的去中心化合作環境,促成了更多革新,並鼓勵公司用不同方法來利用相同的資訊和資源。這種動力學被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稱為「內生成長」,指的是財富、生產及勞力分工都是由同一個地方培養出來,而沒有外在因素投入帶來的成長。機器跟知識不同,機器的生產力會隨時間下降,因為需要維修,無法跟新科技配合,或者無法再製造消費者想要的產品,但知識卻有「報酬遞增」的特性。當公司或個人以新方式來解釋相同的資訊,知識就會持續累積,而且越來越有生產力。知識不會隨時間越來越無用,反之,知識可以有無限(或近乎無限)的應用方式。不過,要把知識或資訊做最佳應用的唯一辦法,就是讓要更多人獲得該項知識。開放、去中心化的知識分享,是矽谷與128公路最重要的不同,也是前者為何能夠不斷革新的原因。
薩克瑟尼安對於矽谷的探討還有一點很有趣,那就是知識交換的「場所」。有的當然是發生在會議室和辦公室,但薩克瑟尼安發現非正式環境有出乎意料的重要性,例如社團、餐廳和酒吧。最主要的地點是當年PC還未普及前的「自組電腦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創始人在布告欄上貼了這樣的廣告:「歡迎志同道合的人參與。交換資訊、想法,協助計畫,都可以。」不到幾個月,這個俱樂部成員便超過五百人。根據薩克瑟尼安的報導,過去數十年間,自組電腦俱樂部裡的成員成立了不下二十間電腦公司,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史提夫.賈伯斯(Steve Jobs)的蘋果電腦,以及比爾.蓋茲的微軟。也許正如薩克瑟尼安所解釋的:「該地區的社交與專業網絡,不只是技術與市場資訊的傳播管道,也是很有效的找工作網絡。」
在矽谷,工作場所之外的非正式合作、資訊和想法,就跟工作時的互動一樣重要。自組電腦俱樂部經常在「綠洲」(Oasis)聚會,這是當地的一間酒吧;Google在矽谷的丹尼餐廳(Denny’s Restaurant,美國最大的二十四小時營業家庭式連鎖餐廳),以十六億五千萬美元買下YouTube。
志同道合又互補的員工聚在一起,讓這種交流以及交流發生的地點充滿意義。如同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黛伯拉.史卓姆斯基(Deborah Strumsky)及其同僚所發現的,「一個都會區研發出專利的能力,跟住在該都會區的發明家數目有密切關係」10。然而真正令人意外的事情(如今已被當成常識),就是矽谷公司對產業文化及組織文化的重視。這兩者的合作,讓許多志同道合的工程師得以分享彼此的許多想法。他們或許分屬不同公司,但都專注在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謂的「限制性生產」:工作不只是為了賺錢,更為了創造理想的電腦。這種動力學運作得很成功,因為它擁有紮實的勞力池、公司和金融機構等正式架構,讓非正式的交流可以順利進行,而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這些人分享著同樣空間。
就如重要經濟學家艾佛列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說的:「從事同樣高技術行業的人們,可以在鄰近的社區活動,實在是一大優勢。行業的祕密再也不是祕密:它就在空氣裡。」
創意是研發、生產和行銷網絡的複雜結合
文化商品(例如時尚、藝術和音樂)的交換,最仰賴社會網絡市場。文化產業及產品都是由品味而非性能所驅使。你購買某設計師的商品,是因為其他人喜歡他,因為他出現在某份時尚先驅雜誌裡,或因為他出現在某些場所,而不是他的毛衣穿起來最暖和。這麼說並不表示技術效能對於人們的選擇一點影響都沒有,只不過那不是最優先考慮的因素。
我們為何選擇身上的衣著,或是聽某種音樂,這跟「品味」以及附加的文化價值有很大關係。雖然這過程看似無常理可循,但其實品味和價值的形成,是有其實際的機制。哈佛大學經濟學者理查.考夫(Richard Caves)在他精闢的著作《文化創意產業:以契約達成藝術與商業的媒合》(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中,探索了創意產業(如藝術、音樂與詩)的特殊經濟特質。考夫認為,創意產品看似單純,但事實上代表了研發、生產和行銷網絡的複雜結合。產業本身就包含革新以及富有意義的新形式,在生產過程中幾乎所有階段都是如此。
考夫主張,創意產業有好幾種特質,首先,創意產業仰賴考夫所稱的「雜七雜八」特質:必須結合各式各樣的人群、團體和產業,合作完成一件商品(試想好萊塢電影工業)。創意產業也仰賴「誰知道」的特質,也就是說,我們很難預料這種商品或產品進入市場後能否成功。而且,創意經濟有種加乘生產的關係:過程中的所有輸入,都必須出現在適當時機才能發揮功用。掌管輸入因素(例如布料、服裝、化妝)和市場的種種關係,仰賴的正是契約,特別是誘因契約和聲譽。
誘因契約是用於獎勵具備附加價值或是能獲得成功的產品。生產者得到的報酬,是根據商品的成果(例如藝術品最後的賣價)。聲譽的運作則有兩種層面,首先,它讓創意工作者推出他們的最佳作品,以獲得或維持他們的聲譽。懶散隨便的作品,毫無疑問會受到惡評的懲罰,將影響到產品在市場上成功的機會。第二,聲譽或可稍微解答神祕的「誰知道」特質。藝術、電影、音樂表演和書籍,除非親身體驗過,否則很難評論,因此藝術家的聲譽往往是影響購買的因素,雖然他們還不知道產品的滿意度(例如馬克.羅斯科的畫,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 的小說,或巴布.狄倫的演唱會)。
卡夫對創意產業的特性描述,跟一個成功經濟體內部的社交網絡、多元公司及勞力池有相當大的關聯。某些創意產業,如好萊塢的電影製作或是唱片製作,是在中間地帶運作,既需要大規模、永久的生產及投資,同時又要順應日新月異的科技、社會議題和潮流。16然而實際上的音樂錄製和歌曲寫作等等(唱片製作的創意部分),大多不需要大型生產設備或營運費用。在此,創意是可更動的,端看企業能否立即從本身的弱連結裡找到技術人士。同時,創意生產者本身也仰賴企業對技術的需求。
你的社交圈決定了你的經濟機會
不過,這一切與大設計師馬克.傑可伯斯有什麼關係呢?文化經濟最重要的特點,也是讓探索文化經濟顯得如此有趣的特點,就在於它雖是人力資本經濟的一環,卻是由品味而非性能所驅動。人們決定合夥做生意,不是因為誰的半導體跑得較快,或是誰的零件獲利較高,而是基於喜愛該產品而決定合夥,這是一種主觀的判斷。由於評估某項產品能否成功的標準如此含糊,甚至根本不知有沒有標準可以評估,因此在決定該雇用誰來做平面設計,或是該把哪一個鞋樣送交生產時,社會動力學便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藝術與文化經濟是在不斷「超社會化」(hypersocialization)的狀態下運作,在這種環境中,弱連結具有非比尋常的重要性。而促成這些抉擇的社會因素,正是創意地理(也就是創意發生的地方)何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換句話說,「地方很重要」,因為社交網絡就是植基在文化生產及消費的特定地點。
以上這些高調的社會與經濟學理論,在在說明了我在紐約市街頭與馬克.傑可伯斯鄰居巧遇的重要性。想了解紐約何以能一直維持創意中心的地位,就得去挖掘紐約市的社會網絡是如何運作,從而給藝術家和設計師帶來經濟優勢。其中,包括精確指出哪些社交動力學的重要性較高,其發生的地點,以及更廣泛而言,文化市場是如何在朝九晚五的傳統公司之外的地方運作。這也是為何週六下午碰見傑可伯斯的鄰居,在經濟學上有其意義。
看不見的社交生活產業社交網絡是人們來紐約搞創意的原因。紐約的藝術與文化很少有什麼事純是因為個人表現好的關係,社交網絡才是最實際的,總歸一句話:一切都要看你認識了誰。還有,你認識的人認識誰。 4月底一個晴朗的週末下午,淺藍色的天空看不出一絲雲或是夜晚的跡象。我跟最要好的朋友瑪麗莎走在西村的西四街上,想找馬克.傑可伯斯的店。我知道店位在布里克街(Bleecker Street),但西村的街道迂迴曲折,知道這點並不能幫助我們找到目的地。我看看四周,跟一個穿著體面、有點年紀的男人打了照面。 「先生,你不會剛好知道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