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折磨自己,創造悲劇,為的就是要成名!
「作家研習營。拋開你的生活,就此消失。將你生命中的一小段時間賭在可以創造一個全新未來的機會上。及時行動,過你夢想中的生活,名額極其有限。有興趣者請來電:1-800-滾你媽的蛋」
《惡搞研習營》包含了二十三個恐怖、好笑,又讓你反胃的故事。說這些故事的人都是應一則「作家研習營」的廣告而來,卻陷入類似「求生」情節的處境中──他們沒有暖氣,沒有電力,沒有食物。這些說故事的人越來越絕望時,他們的故事也越來越極端。然而,他們無情地密謀著,讓自己成為由他們受苦經驗改編而成的實境節目中的主角。這將是你所讀過最令人心裡發毛且暴虐的小說,惟有恰克.帕拉尼克才能寫得出來。
作者簡介
恰克.帕拉尼克 Chuck Palahniuk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生於華盛頓州帕斯科鎮,在巴爾班克鎮上和家人同住的拖車屋裡長大。他的雙親後來分居、離異,經常將他和三名手足送到外公在華盛頓州東部的牧場居住。
帕拉尼克在二十多歲時就讀奧勒岡大學的新聞學院,於一九八六年畢業,三十多歲時開始寫作。他的第一本書《失眠:如果你住在這裡,你就已經到家了》(Insomnia: If You Lived Here, You’d Be Home Already)始終沒有完成,不過有一小部分留存下來,用在《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裡。他的第二本作品是《隱形怪物》(Invisible Monsters),卻被出版社因為內容太過令人不安而退稿,這使得帕拉尼克開始寫他最有名的作品《鬥陣俱樂部》,原因為遭到出版社拒斥而刻意寫出個令人更加不安的故事,沒想到出版社竟然願意出版。《鬥陣俱樂部》精裝本問世後,大獲好評,也得到數個獎項,後來改編成電影搬上大銀幕,於一九九九年由大衛.芬契(David Fincher)執導完成。修訂後的《隱形怪物》和他的第四本書《殘存者》(Survivor)也在那年出版,讓帕拉尼克本人成為受到狂熱崇拜的一代宗師。二○○一年,帕拉尼克終於有了第一本擠上《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的作品,就是長篇小說《窒息》(Choke),從此以後,帕拉尼克的作品一帆風順。這樣的功成名就使他能巡迴多地宣傳他的著作,朗讀他的新書和即將出版的作品。
二○○三年,帕拉尼克為了宣傳《日記》(Diary)巡迴時,在簽名會上朗讀了一篇題名〈腸子〉的短篇小說,內容敘述一場在水底自慰時發生的意外,這個短篇將收錄於他的新書《惡搞研習營》(Haunted)裡。據說到那時候為止,已有四十個人在聽他朗讀時昏倒。《花花公子》雜誌在二○○四年三月號刊登了這篇小說;帕拉尼克提議讓他們同時刊載另一個短篇,但是編輯部門認為那第二篇太過聳動。在二○○四年夏天巡迴宣傳《比小說更離奇的真實故事》(Stranger Than Fiction: True Stories)一書時,他又向觀眾朗讀同一個短篇,使得昏倒的人數增加到五十三人。後來在宣傳《日記》平裝本時,同一篇故事讓昏倒的人數增加到六十人。到了那年秋天,他開始宣傳《惡搞研習營》,繼續朗讀〈腸子〉。二○○四年十月四日在科羅拉多州波爾得市的朗讀會上,帕拉尼克發現,到那天之後,昏倒的人數已經攀升到六十八人。最後一次有人昏倒的情形是在二○○七年五月十八日,發生於加拿大卑詩省維多利亞市,一共有五個人昏倒,其中一名男士是在準備離開現場時昏倒,結果在倒下時頭部撞到了門。帕拉尼克顯然完全不受這些意外事件的影響,也沒有影響到其他書迷來聆聽他朗讀〈腸子〉或其他作品。他朗讀這篇小說的錄音開始在網路上流傳。在《惡搞研習營》一書最新一版後記中,帕拉尼克報導說〈腸子〉已經使七十三人昏倒。
《惡搞研習營》在二○○五年獲得史鐸克小說獎最佳長篇小說獎的提名,同名電影正準備拍攝中。
譯者簡介
景翔
工科畢業,服役後曾從事電腦程式設計工作,後轉入新聞界,退休後延續自民國五十一年開始之翻譯工作,迻譯文類廣泛,而用心與誠懇則始終如一。重要譯作有:非小說《瘋子、教授、大字典》、《雲端的帳棚》、《超級巨星》等;傳記《破水而出》、《我心深處》等;散文《浪吟行》、《梭羅日記》等;暢銷小說《午夜情挑》、《此情綿綿》等;文學獎作品《他們》、《樂觀者的女兒》、《中性》等;電影小說《越戰獵鹿人》、《午夜牛郎》、《再見女郎》、《第三類接觸》等;同志小說《男人的愛人是男人》、《教我如何愛你》、《彩蝶之翼》等;推理小說《布朗神父探案全集》、《骸骨與沉默》、《猶大之窗》等;科幻小說《非人子》、《異形》、《海柏利昂2》等;奇幻小說《最後的精靈》等;成長小說《毛巾頭》等;恐怖小說《惡搞研習營》為首次嘗試此一文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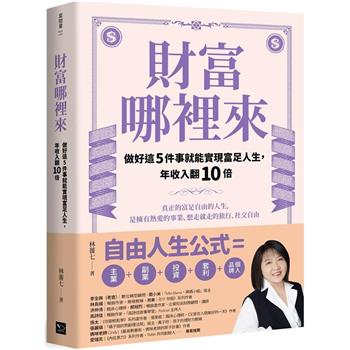









標題:看完《惡搞研習營》才知道這世界變化太快!以前脫了內褲才能看到屁股,現在得掰開屁股才能找到內褲! 當初甄選試讀的時候,小異出版表示看完23則短篇中的〈腸子〉後先行發表五十字以內的心得,那時候發表了兩次,會發表第二次是只因為想起了很早以前網路看到一句話,覺得很能代表〈腸子〉這一篇:「這世界變化太快!以前脫了內褲才能看到屁股,現在得掰開屁股才能找到內褲。」 閱\讀後,不管是《惡搞研習營》還是「餓到研習營」(因為故事的角色每個人都在挨餓),作者在這裡分享了很多乖旦荒謬的精采故事,24則不可思議的內容,尤其是串聯23篇短篇小說的主軸,更是扯濫到了極點,充斥著人性的好奇,以及人心的黑暗面,或許\很黑色幽默,但我實在很難想像這些故事的真實性究竟是如何,因為,這些都可能是已經發生,或是正在發生,甚至是將要發生的事。 書裡一首關於大自然的詩寫道:「有多少天使能在一根針尖上跳舞?」,所以我要問了,又有多少讀者可以看完這本令人不安的故事。 提到讀後心得,寫作研習營主辦者魏提爾先生曾說:「除非你能忽視週遭環境,做你誠諾過要做的事,否則你就會永遠受到這個世界的控制。在這裡阻擾你的正是阻擾你一輩子的那個東西」或許\也是作者恰克‧帕拉尼克的寫作心聲,不妨也可以當作一種意見參考,所以這篇心得,我是窩在棉被裡寫完的。 當然,除了一開始《聖無腸的故事》之外,《大自然的故事》、《否定督察的故事》、《毀謗伯爵的故事》...每個都陰暗詼諧,所以千萬不要以為這是一本整人的小說,雖然裡面有很多被整的橋段!簡單說這是一本極奇噁心但極具教育意涵的小說,只不過,不適合未滿十八歲!孕婦!及患有心臟病的長者! 會說有教育意涵,是因為很多角色的對話都是充滿了值得思考的人生哲學,譬如裡面的一段話:「就算你今天對自己說:『今天,我要用錯的方式去喝咖啡......倒在一只髒靴子裡喝。』就算是這樣也還是對的。因為你決定用靴子來喝咖啡。」因為你不會做錯事,你永遠是對的。就算你說:「我真是白痴,我錯的好厲害......」你還是對的。說你錯這件事就說對了。就算你是個白痴,你也還對的。「不管你的構想有多蠢,你也一定是對的,因為那是你的構想。」感覺是錯的但又是對的,感覺很無厘頭但又句句屬實。 再隨便說書中另一個謬論,在克利夫蘭分屍魔,波士頓絞殺鬼,芝加哥開膛手,土耳其悶棍男,洛杉磯亂刀客......在這一波波連續殺人案起來的時候,當地城市的所有犯罪都降低了,只有很少數受害者,砍了手腳,身首異處,除了這些驚人的犧牲者之外,每個城市都有史上最安全的一段時期。紐奧良利斧連續殺人案發生期間,兇手寫信給當地的報紙《時代小報》。承諾說三月十九日那天晚上,他絕不殺在家能聽到爵士樂的人,那天晚上,紐奧良全城響著音樂聲,沒有一個人遭到殺害。在警方預算有限的城市裡,一個惡名昭彰的連續殺人兇手可是規範一般人行為最有效方法。 最後,這麼扯蛋的小說要我報告讀後心得,那我就跟作者一樣,分享我一個朋友的故事。 不過在說這個故事之前,我得鄭重聲明,這不是我本人,是有關於我朋友真實的一樁很大便的事。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種嗜好,或說是習慣,或說是「上癮」。我不敢說《惡搞研習營》的作者是否有收集荒旦故事的喜好(但因為這本小說的出版,顯然是可以這樣說沒錯),但至少我敢說每個人總有一些小收藏。有名的收藏,可以收個門票開個博物館之類的,不過大多數人一定都是做為純欣賞之用,閒來沒事就看一下把玩一翻,很個人的。就說我吧,我的收藏很普通,就是收集塑膠袋跟紙袋,一方面實用,一方面是袋子越作越精細漂亮,而且不用錢,但是現在,我不是為了炫燿幾百幾千個袋子,而是要說我朋友幾千幾萬個的收藏。 百分之百的人的收藏,都是拿外來的事物來藏,我這位朋友則是收藏自己身上的東西。人的身體有什麼東西多到可以收集,譬如頭髮很多,但是都一樣就沒什麼收藏價值。拜數位相機之賜,我朋友收藏他的照片,看起來是沒什麼了不起,因為光我自己的照片也有數千張,但是關於我自己大便的照片,一張也沒有。這就是我朋友的嗜好,有時候還真想幫他報名「我猜」節目。 幫大便拍照其實也沒什麼不好,就像是每天量血壓一樣,可以給醫生當作參考。譬如從嘴巴吃什麼就會大什麼便一樣,朋友說這是很健康的,鼓勵大家一起跟他這樣做,其實他只是想跟別人交換大便的照片,增加自己的收藏而已。 關於我朋友的大便資料庫,舉凡有各式各樣形式的便,譬如綠色的軟便、混著火龍果種子的黑色點點淺色便、麻辣鍋的褐色條狀便、吃壞肚子的噴射狀稀便、做完x光攝影的白色鋇劑便、胃出血的黏稠狀黑便、腸子出血的血色便、痔瘡破裂後外圍有紅色環狀的咖啡色便......。 關於大便最重要的還有味道,朋友當然很期待將來的數位相機連味道都可以紀錄,不過目前還是採用編寫方式,譬如有著綠色植物的田野蔬菜味、白色火龍果的芳香、豬大腸混著鴨血的憨厚臭味、吃壞肚子消化到一半的惡臭味、做完x光攝影的化學藥劑味、胃出血的濃厚血腥味、腸子出血的輕微血腥味、痔瘡破裂後的淡淡糞便味...我不禁懷疑,他是不是有用手指戳過嚐過。 關於大便照的欣賞重點,就是配角的馬桶。譬如台鐵自強號上的、華航飛機上的、台北各捷運站內的、百貨公司的、電影院裡面的。當然還有旅館的浴缸、晚間戶外的游泳池、醫院病人的便盆、學校的操場、公園的溜滑梯及盪鞦韆、大樓電梯及樓頂層、機車置物廂、飯廳的餐\盤、幹!還有我的馬克杯(罵了髒話對不起)。 關於欣賞大便,還有動態攝影及沖水時的瞬間。這需要搭配功\能高規的單眼相機,以及多次的拍攝經驗才能補抓到完美的剎那,他的人生,除了吃喝就是拉拉拉,為了拉屎,把自己搞的很忙,我只能說他還真是一肚子大便啊! 有了這麼多的收藏,他老兄其實就有想要炫的心態,這也就是我為什麼會知道的原因。所以他花了點時間做了一份近兩百張的Power Point報告,只要點一下開啟檔案,他就可以仔細道來他的收藏。當然,還有他最愛的十「大」排行榜,電腦桌面就是第一名那張。 只是這樣的收藏已經不能滿足我的朋友,所以他製作了「千人錄」,顧名思義,就是一千個人的大便照。要拍一千人的大便照,剛開始很簡單,從好朋友跟同班同學下手總是可以容易成功\的,只可惜一個人的朋友同學總是限度,所以從朋友的朋友,同學的同學溝通,我個人就贊助了十幾張,連我阿公阿嬤都「遼落去了」,差不多到了一半的時候就是極限,而且很耗時,他的堅決態度,證明了他對大便這件事的執著,因為他老兄堅持要自己照,理由很簡單,他只相信自己的專業。 最後逼不得已,他採取各種手段,所以現在,他以妨礙自由及侵犯個人隱私坐牢當中,照片當然也在法院做為呈堂證供。後來因為表現良好,所以在獄中他被容許\可以幫獄友的大便拍照。現在,他的「千人錄」第二本已經快完成了,他說,這兩本將是他最珍貴的收藏。 再次聲明,這不是我本人,所以不要來信向我索取十「大」的照片! 最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他的網站:http://www.stool.ma_tong.com 翻成中文就是:打不溜打不溜打不溜 點大便 點馬桶 點看 如果查無此網址,我想,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我朋友還在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