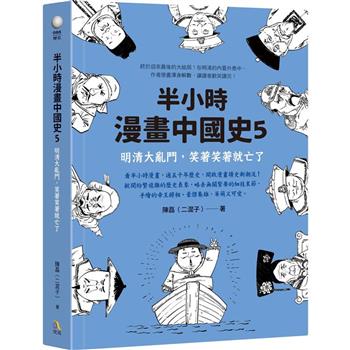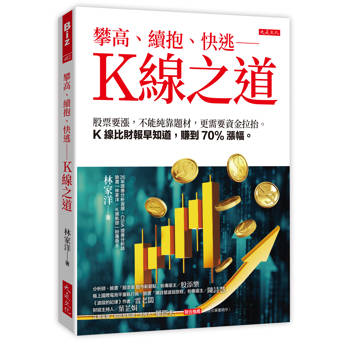有些事,是你至死也不想講,是你巴不得死掉,也不想看的。
我卻親眼目睹了。
故事發生在五○年代,場景設在綠樹成蔭的街區,這裡有修剪整齊的草坪、清澈的溪流與舒適的住家。我們的主人翁是個略微害羞男孩大衛,在他十二歲那年的夏天,遇見了初次讓他感到心動的女孩瑪姬。因父母車禍雙亡,瑪姬與跛足的妹妹蘇珊前來投靠遠親阿姨,住進了錢德勒家,成了大衛的鄰居。想到與瑪姬種種可能的未來,興奮不已的大衛萬萬沒想到,他只來得及參與她如噩夢般的悲劇。
在一條死巷裡,錢德勒家陰暗潮溼的地下室中,瑪姬被綁住手腕,吊在天花板的橫梁上,嘴巴被塞住,眼睛也被蒙上,她深受精神有問題的遠房阿姨蘿絲的蹂躪,蘿絲的瘋狂影響了她的三個兒子,最後更擴及整個鄰區。一群冷漠的孩子,和一個鼓吹惡行的成人,再加上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態,不忍悴睹的可怕罪行,便發生在這看似寧靜的住宅郊區。
透過糾葛其中的大衛的眼睛與耳朵,讀者也參與了蘿絲和兒子們的罪行,它道出我們心底的慾望,渴望窺探恐怖暴行的本能;我們無力轉開眼神,只能成為共犯,直到翻完最後一頁……
作者簡介:
傑克.凱堔 Jack Ketchum 本名為達拉斯.邁爾(Dallas Mayr),曾做過演員、歌手、文學經紀人、木材推銷員,也是位汽水迷;家裡賣花,是戰後嬰兒潮的一員,自認在1956年時,貓王、恐龍和恐怖漫畫救了他。在進入恐怖小說領域之前,凱堔曾寫了一些詩、劇本、兒童故事、短篇小說,也曾在搖滾音樂雜誌及男性雜誌上發表文章。 凱堔的首部長篇小說《淡季》(Off Season,1980年出版),雖引發《村聲週報》(Village Voice)公然撻伐,痛責出版商出版暴力色情小說,卻被許多類型讀者所喜愛,被描述成「終極恐怖小說」,至今仍影響許多文壇新人的寫作風格。《淡季》描寫一群遊客遇到食人族的故事,原先出版的版本曾被出版社刪掉許多辛辣的情節,之後完整版重新推出,讀者紛紛收集,奉為經典。 續篇《後裔》(Offspring,1991年出版)於2009年被搬上大銀幕,在美國的上映時間卻遲遲未定,最後決定直接發行DVD。今年(2009)五月,傑克.凱堔的《鄰家女孩》更在知名八卦網站POPCRUNCH票選中,榮膺史上十大最令人不安小說之首,可見凱堔式的恐怖即使在二十一世紀仍被視為極端的禁忌。 傑克.凱堔的作品一直以來皆為史蒂芬,金所推崇,稱他為恐怖懸疑作家的英雄,類型讀者的標竿。凱堔曾說過,他只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錢賺到夠用就好,他不會為了想多賺幾個鳥錢去寫;寫作對他而言,就像一種更高階的遊戲,而且除了自慰以外,寫作是一人獨享的最大樂趣。 凱堔寫長篇、也寫短篇小說,作品多次獲得史鐸克獎(Bram Stoker Award),如短篇小說:《盒子》(The Box)、《逝去》(Gone);合集《和平國度》(Peaceable Kingdom);長篇小說《打烊時間》(Closing Time)。被改拍成電影的有:《迷失》(The Lost)、《鄰家女孩》(The Girl Next Door)、《紅》(Red)、《後裔》(Offspring)。作者網站:http://www.jackketchum.net/。
譯者簡介:
柯清心
台中人,美國堪薩斯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現任專翻譯。著有童書《小蠟燭找光》;譯有《不怕小孩問》、《8的秘密》等數十部作品。
章節試閱
第二十八章
「我們跟她講突擊的事了。」唐尼說。
「跟誰說?」
「蘿絲,我媽媽,要不還會有誰,笨死了。」
我進門時,唐尼一個人在廚房做花生奶油三明治,我猜那是當天的晚餐。
流理台上有花生奶油、葡萄果醬的油跡和麵包屑。我好玩地數了數抽屜裡的餐具,還是只有五組。
「你們跟她說啦?」
他點點頭,「是吠吠說的。」
唐尼吃了一口三明治,然後坐到客廳桌邊,我在他對面坐下,木桌上有一條以前從沒見過的半吋煙痕。
「天啊,她怎麼說?」
「什麼都沒說。好奇怪哦,好像她本來就知道,你懂吧?」
「本來就知道?知道什麼?」
「知道所有的事啊,好像沒什麼關係,好像她老早就知道我們在幹那件事了,好像每個小孩都會那樣。」
「你是在開玩笑吧。」
「沒有,我發誓。」
「狗屁啦。」
「我告訴你,她只想知道有誰跟我們玩,所以我就告訴她了。」
「你告訴她了?你把我、艾迪、每個人都招出來了嗎?」
「我說過她不在乎了嘛。喂,你別那麼緊張好不好,大衛?她又沒覺得怎樣。」
「黛妮絲呢?你也跟她講黛妮絲了嗎?」
「是啊,全講了。」
「你有說她沒穿衣服嗎?」
我真是不敢相信,我向來以為威利比較笨。我看著唐尼啃三明治,他對我笑了笑,搖搖頭。
「告訴你,安啦。」他說。
「唐尼。」
「真的啦。」
「唐尼。」
「幹嘛,大衛。」
「你瘋了嗎?」
「沒有啊,大衛。」
「你有沒有想過,萬一怎麼樣的話,我會……」
「你不會怎樣啦,拜託別這麼大驚小怪行嗎?拜託,她是我老媽吔,你沒忘記吧?」
「所以我就應該很放心,讓你老媽知道我們把一個裸體的小女生綁到樹上了嗎?」
他嘆口氣,「大衛,我要是早知道你這麼白癡,就不跟你說了。」
「白癡?」
「是啊。」這下換唐尼生氣了,他把最後一口黏糊糊的三明治塞進嘴裡,然後站起來。
「你是豬啊,要不然你以為防空室裡是怎麼回事?現在是怎麼回事?」
我呆呆地看著他,我怎麼會知道防空室裡怎麼回事?誰在乎呀?
接著我懂了。瑪姬在裡面。
「不會吧。」我說。
「就會。」唐尼到冰箱裡拿可樂。
「狗屎。」
他大笑說:「你能不能別再說狗屎?你若不信,自己去瞧瞧,媽的咧,我只是上來吃三明治的。」
我衝下樓,還聽見他在後頭高聲大笑。
外面天色漸黑,因此地下室的燈是亮的,裸露的燈泡懸在階梯下的洗衣機、烘衣機,以及角落抽水機的上方。
威利站在蘿絲後面,防空室的門口。
兩人手裡都拿了手電筒。
蘿絲扭開她的手電筒,像哨站的條子一樣,朝我晃了一下。
「大衛來啦。」她說。
威利瞄我一眼,意思是誰理他呀。
我張開嘴,覺得好乾,我舔舔嘴唇,對蘿絲點點頭,然後從門口望進角落。
一開始我還沒意會過來──大概是因為太突兀,加上是瑪姬,而蘿絲又在那兒的緣故吧。我覺得像在做夢一樣──或像萬聖節玩的某種遊戲,所有人都化了妝,即使知道對方是誰,還是不太認得出來。接著唐尼走下樓,用手拍拍我的肩膀,遞給我一罐可樂。
「懂了吧?」他說,「我就跟你說嘛。」
我真的懂了。
他們把釘子釘進老威利架在天花板上的橫梁裡──兩根間隔三呎的釘子。
他們割了一條兩倍長的曬衣繩,綁住瑪姬的手腕,然後把繩子纏到兩根釘子之間,再把繩子綁到沈重的工作台桌腳。這樣一來,只要解開桌腳上的繩子,繞著釘子調整鬆緊度,再綁好繩子就成了。
瑪姬站在一疊書上──三本厚厚的紅色世界百科全書。
她的嘴被塞住了,眼睛也蒙上了。
瑪姬光著腳,穿著髒兮兮的短褲和短袖上衣,她拉長身子,露出衣褲之間的肚臍。
瑪姬的肚臍是凹進去的。
吠吠在她面前來回走動,拿著手電筒上上下下地照著她的身體。
瑪姬眼罩下的左臉頰上,有一道瘀傷。
蘇珊坐在一箱蔬菜罐頭上看著,頭髮上綁著藍色絲帶做的蝴蝶結。
我看到角落有一堆毛毯和充氣床墊,才知道瑪姬睡在那兒,我不知道這情形有多久了。
「大家都到了。」蘿絲說。
淡琥珀色的昏光自地下室其他地方射進來,但防空室裡則以吠吠的手電筒為主光,隨著他的走動,陰影搖晃不定,更添鬼魅氣氛。高處唯一的鐵窗,似乎也微微來回移動。兩根支撐天花板的四吋見方木柱,以怪異的角度斜過房間。堆在瑪姬床舖對面角落的斧頭、鶴嘴鋤、鐵橇和鏟子,似乎互換位置,忽近忽遠而變幻不定。
摔落的滅火器亦在地上爬行。
其實,佔據整個房間的,是瑪姬的影子──她頭往後仰,雙臂張開,搖來晃去的,簡直就是恐怖漫畫的重現。那是《黑貓》裡的吸血鬼,《知名怪獸》裡的景象,是以宗教審判為背景的廉價恐怖歷史小說的場景。這些我們都有收集。
你不難想像會有火炬、怪異的刑具、隊伍,以及裝滿燒炭的火盆。
我簌簌發顫,不是因為冷,而是因為各種可能。
「突擊的規矩是,她得招供。」吠吠說。
「好吧,招什麼?」蘿絲問。
「招出一切,供出祕密。」
蘿絲點點頭笑道:「聽起來不錯,只是嘴裡塞了東西要怎麼招?」
「媽,她不用立刻招啦,」威利表示,「反正等他們準備好後,妳就知道了。」
「你確定嗎?妳要招了嗎,瑪姬?」蘿絲問。
「妳準備好了嗎?」
「她還沒準備好啦。」吠吠堅持說,但他是多此一舉,因為瑪姬根本沒發出半點聲音。
「那現在怎麼辦?」蘿絲問。
靠在門框上的威利慢慢晃進屋內。
「咱們先抽開一本書。」他說。
威利彎下身,抽掉中間那本書,往後站開。
繩子拉得更緊了。
威利和吠吠雙雙扭開手電筒,蘿絲的還放在一邊沒開。
我看到瑪姬的手腕被緊繃的繩索勒出紅痕,背部微微拱起,短袖襯衫拉高起來。她勉強貼站在剩下的兩本書上,但已經看得出小腿和大腿都拉緊了。她用腳尖站了一會兒,讓自己的手腕稍稍鬆緩,接著身子又軟掉了。
威利關掉手電筒,那樣感覺比較恐怖。
瑪姬只是留在原地輕輕晃著。
「快招,」吠吠說完哈哈大笑,「不,先別招。」他說。
「再抽掉一本書。」唐尼表示。
我瞄著蘇珊,發現她也在盯著。女孩兩手放在大腿的衣服上,表情非常凝重,她目不轉睛地看著瑪姬,但完全看不出心裡在想什麼,或有何感覺。
威利彎腰抽出一本書。
現在瑪姬已經踮起腳了。
但還是沒出聲。
她的腿部肌肉拉得很緊。
「咱們看她能撐多久,」唐尼說,「一會兒之後就會開始痛了。」
「不行,」吠吠說,「那樣還是太便宜她了,咱們抽掉最後一本書,讓她踮著腳尖站。」
「我想先看一陣子,看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一點動靜都沒有,瑪姬似乎決定堅持到最後,而且她非常能忍。
「你難道不想給她一個坦白的機會嗎?難道不是這樣玩的嗎?」蘿絲問。
「不行,」吠吠說,「還太早。唉呀,這樣不成,再抽掉另一本書,威利。」
威利照著做。
接著嘴巴被塞住的瑪姬發出聲音了,但只有一聲,像小小的吐氣聲,好像呼吸突然變得困難起來了。她的上衣拉高到胸部下方,我看到她肋骨上的肚皮起伏不定,她的頭向後仰了一會兒,然後又往前倒。
她開始不穩,搖晃了起來。
瑪姬臉色醬紅,肌肉繃得死緊。
我們默默看著。
她好漂亮啊。
隨著拉力增加,伴隨呼吸發出的聲音也越來越頻繁了。瑪姬忍耐不住,雙腿開始發顫,先是小腿,接著是大腿。
「我們應該把她衣服脫掉。」唐尼說。
這句話懸盪片刻,就像僵在空中、拼命維持平衡的瑪姬一樣。
我突然覺得頭昏起來。
「沒錯。」吠吠說。
瑪姬也聽到了,她憤怒而害怕地搖著頭,拼命在咽喉裡喊著「不、不、不」。
「閉嘴。」威利說。
她開始試著去跳,扯著繩索,想將繩子從釘子上弄鬆,同時扭來扭去。可是這一切只把自己弄得更痛,連手腕都磨破了。
瑪姬似乎不在意,她死也不肯讓人把她的衣服脫掉。
她不斷奮戰。
不要,不要。
威利走過去拿書砸她的頭。
她跌了回去,嚇到傻了。
我看著蘇珊,她的手還是緊扣在大腿上,但指節已經泛白了。她直直看著姊姊,沒看我們,不斷咬著自己的下唇。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我清清喉嚨,勉強擠出聲音。
「嗯,呃……各位……聽我說,我覺得好像不能……」
吠吠立即轉身看我。
「我們是經過許可的!」他尖喊道,「真的!咱們剝掉她的衣服!脫啊!」
我們看著蘿絲。
她站在門口,雙手交疊在腹部上。
一副很嚴厲的樣子,好像在生氣,或正在認真思考。蘿絲將嘴唇抿成一條細細的直線。
眼睛釘在瑪姬身體上。
最後她終於聳聳肩。
「突擊就是這樣玩的,不是嗎?」她說。
防空室比屋子的其他地方涼,甚至比地下室涼,但此時涼意盡去,一股朦朧的滯重感逐漸升起,熱氣冉冉自每個人身上散出,飄在空中,環繞著我們,分隔著我們,卻又將所有人籠罩在一起。你可以從威利緊抓著百科全書,微微傾立的樣子;從吠吠挨上前,以手電筒的光,在瑪姬的臉上、大腿及腹部遊走撫觸的樣子看得出來。我感覺到旁邊唐尼和蘿絲身上散出的熱氣,像某種甜蜜的毒藥般流竄到我身上,那是種心照不宣的默契。
我們就要動手了,我們就要去脫她的衣服了。
蘿絲點燃一根煙,把火柴扔到地上。
「去吧。」她說。
煙氣在斗室中裊繞。
「由誰動手?」吠吠問。
「我來。」唐尼說。
他越過我身邊,吠吠和威利拿著手電筒對準她,我看到唐尼伸手從口袋裡拿出他一向帶在身上的小摺刀,他轉頭看著蘿絲。
「衣服弄破沒關係嗎,媽?」他問。
蘿絲看看他。
「我不用割短褲或其他地方。」他說,「可是……」
唐尼說得沒錯,只有用扯裂或割開的方式,才有可能脫掉她的上衣。
「沒關係,」蘿絲說,「反正我不在乎。」
「咱們看看她是什麼貨色。」威利說。
吠吠哈哈大笑。
唐尼仔細地解開上衣釦子,把衣服從她身上撥開,似乎羞於碰觸她。唐尼滿臉紅霞,手指十分笨拙,他在發抖。
瑪姬開始掙扎,後來又覺得最好不要。
釦子鬆開的襯衫亂七八糟地掛在瑪姬身上,我看到她底下穿了件白色的棉胸罩。不知為什麼我吃了一驚,大概是蘿絲從不戴胸罩,所以我也以為瑪姬不會戴吧。
唐尼握著筆刀伸出手,將左邊袖子往上割至頸線,他得割破縫線,不過他的刀子很利,襯衫掉到瑪姬身後了。
瑪姬開始哭了。
唐尼走到另一邊,以同樣手法割開右邊的袖子,然後嘶地一聲,快速扯裂縫線,再退開來。
「短褲呢。」威利說。
你可以聽見瑪姬輕聲哭泣,並試圖從塞住的嘴中說出「不要,求求你們。」
「別亂踢。」唐尼說。
短褲拉鍊脫開了一半,他把拉鍊鬆開,將褲子從她臀上拉下來,並一邊將她薄薄的白色內褲往上調整好,然後把短褲從她腿上褪下。瑪姬的腿部肌肉抽抽顫顫的。
唐尼再次退開看著瑪姬。
我們都是。
我們曾看過穿這麼少的瑪姬,她有一套兩件式的泳衣,那個年頭大家都有,連小孩也是。我們見過她穿。
但這個不一樣,胸罩和內褲是貼身私物,應該只有其他女生能看。屋子裡的女生只有蘿絲和蘇珊,但蘿絲卻容許這樣的事,鼓勵這樣的事。我實在無法細究。
何況前面還有瑪姬,她就在我們眼前,我所有的思緒和憂慮全被感官的刺激給蒙蔽了。
「妳要招了嗎,瑪姬?」蘿絲柔聲問。瑪姬點頭表示「要」,而且是很急切的「要」。
「不,她才不想招咧,不可能。」他頭頂和前額泛著一層薄汗,威利將汗水拭掉。
此時我們全都在流汗,瑪姬流得最多,她的腋下、肚臍凹和整片腹部都閃著汗珠。
「把剩下的也一起脫了。」威利說,「到時也許再讓她招供。」
吠吠咯咯笑著說:「等她當完歌舞女郎後再說吧。」
唐尼踏向前,把瑪姬的胸罩右邊肩帶割斷,然後是左邊,瑪姬的乳房向上微微一彈,罩杯鬆開了。
唐尼本可從後面解開胸罩的釦子,他卻偏偏繞到前面,把刀片伸入兩個罩杯之間的白色細帶子下,然後開始割鋸。
瑪姬哭出聲了。
哭成那樣一定很痛,因為每次她身體一動,就會被繩子扯住。
刀子很利,但還是花了點時間,接著啪的一聲,胸罩掉下來了,瑪姬的酥胸袒露而出。
她的胸部比身體其他部位更白皙,蒼白完美而豐潤,並隨著她的哭泣而顫動,粉棕色的乳頭十分凸長──對我而言──而且頂端幾乎是平的,像是兩座小小的肉丘。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東西,立即有觸摸的衝動。
我已進到防空室裡了,蘿絲現在變成在我的背後。
我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聲。
唐尼跪到瑪姬前面,手往上伸,乍看之下像是在膜拜。
接著他的手指勾住內褲,將褲子從她臀上緩緩拉到腿上。
接著又是另一項驚奇。
瑪姬的毛髮。
一小撮泛著汗珠,淡金橘色的毛髮。
我看到她大腿上半部的點點雀斑。
看到她兩腿間若隱若現的肉褶子。
我仔細打量她,不知她的酥胸摸起來是何感覺?
她的肉體對我而言是難以想像的,我知道她兩腿之間的毛髮必然很軟,比我的還柔軟,我好想撫觸她啊。她那顫動不已的胴體必然十分溫潤。
她的腹部、大腿、結實雪白的臀部。
慾念在我體內凝聚竄升。
室內瀰漫著性的氛圍。
我感到胯下變硬變重了,我走向前,興奮不已。我走過蘇珊旁,看到目不轉睛的吠吠臉色蒼白,血色盡褪,看到威利的眼睛盯著下邊的那撮毛髮。
瑪姬停止哭泣了。
我回頭望了蘿絲一眼,這時她也走向前,踏進門口了。我看到她的左手撫著自己的右胸,指頭輕輕抓住,然後又鬆開了。
唐尼跪到瑪姬面前抬頭看她。
「招供吧。」他說。
瑪姬的身體開始痙攣。
我可以聞到她的汗香。
她點點頭,她必須點頭。
那是在投降。
「去鬆繩子。」唐尼對威利說。
威利走到桌邊解開繩索,讓瑪姬在水泥地上平站,然後再將繩子綁好。
她的頭向前軟倒。
唐尼站起來抽掉嘴塞,我發現那是蘿絲的黃色方巾。瑪姬張開口,唐尼把之前捲起來塞進去的破布抽出來丟到地上,並把方巾放到他牛仔褲的後袋裡,方巾的一角微微露出,使唐尼看起來像個農夫。
「你能不能……?我的手臂……」她說,「我的肩……好痛。」
「不行,」唐尼說,「就這樣而已,只能鬆開這麼多了。」
「招供吧。」吠吠說。
「告訴我們,妳是怎麼自慰的。」威利說,「妳一定有把手指放進去吧?」
「不。告訴我們梅毒的事。」吠吠大笑說。
「對吔,淋病。」威利咧嘴笑說。
「快哭。」吠吠說。
「我已經哭過了。」瑪姬說,看得出她不那麼痛後,又稍稍恢復之前的頑強了。
吠吠只是聳聳肩,「那就再哭一遍。」
瑪姬沒答腔。
我注意到她的乳頭已經鬆軟下來了,變成平滑絲亮的粉紅色。
天哪!她好美。
瑪姬似乎讀透了我的心意。
「大衛在這裡嗎?」她問。
威利和唐尼看著我,我無法回答。
「在。」威利說。
「大衛……」瑪姬開口了,卻無法把話說完,但她並不需要,因為從她說話的方式,我就懂了。
她不希望我在場。
我知道原因,這令我非常慚愧,就像瑪姬之前也令我羞愧不已一樣。可是我無法離開,因為其他人都在,何況我並不想走。我想看,我需要看。羞恥心遇到了慾望,只能撤守。
「那蘇珊呢?」
「也在。」唐尼說。
「天啊。」
「管他的,」吠吠說,「誰鳥蘇珊啊?妳不是要招供嗎?」
瑪姬用不耐煩且非常成人的語氣說:「招供是很無聊的事,我沒什麼好坦白的。」
我們全都被堵死了。
「我們可以再把妳吊起來。」威利說。
「我知道。」
「我們可以用皮帶抽妳。」吠吠說。
瑪姬搖頭道:「拜託你們,別再來煩我了,讓我一個人。我沒什麼要招的。」
沒人料到會變成這樣。
一時間,大夥只是愣愣站著,等著誰先開口,講點能說服她,讓她按遊戲規則玩「突擊」的話。或強迫她,甚至讓威利再把她吊回去,反正任何能讓突擊繼續進行下去的方法都行。
可是在那片刻裡,氣氛已然丕變,若想恢復過來,勢必得從頭再來一遍。我想大家都知道,危險緊張的刺激感突然不見了,瑪姬一開始說話後,便消失無蹤了。
關鍵就在那兒。
她一開口,便又成為瑪姬,而不再只是某個美麗裸體的受害者了。瑪姬是一個聰明有腦、勇敢直言的人。
把布塞拿掉真是失算。
眾人鬱卒不已,氣惱又挫敗。我們只能杵在那裡。
蘿絲率先打破沈寂。
「我們可以那麼做呀。」她說。
「怎麼做?」威利問。
「照她的話,讓她一個人自己去想想,我覺得那樣也很好。」
我們想了一會兒。
「好吧。」吠吠說,「讓她在黑暗裡,吊在那裡靜一靜。」
我心想,那也是一種重新開始的方式。
威利聳聳肩。
唐尼看著瑪姬,我知道他並不想走,因為他目不轉睛地望著她。
唐尼抬起手,猶豫地慢慢探向瑪姬的胸部。
霎時間,我似乎成為他的一部分,感受到自己的手也伸在那兒,就要摸到她了,我幾乎可以感覺到她溼滑溫熱的皮膚。
「呃,」蘿絲說,「不可以。」
唐尼看著她,停下手,僅差幾吋就摸到瑪姬的酥胸了。
我吸了一口氣。
「不准你碰那女孩。」蘿絲表示,「我不准你們任何人碰她。」
唐尼垂下手。
「像她這樣不乾不淨的女孩,你們的手千萬別沾到她,聽到沒?」蘿絲說。
我們都聽見了。
「是的,媽。」唐尼說。
蘿絲轉身把香煙踩在地上,然後對我們揮手說:「走吧,不過你們最好先把她的嘴塞住。」
我看看唐尼,他看著地上的布塞。
「弄髒了。」他說。
「沒那麼髒。」蘿絲說,「我可不希望她整晚對咱們鬼吼鬼叫,塞回去。」
接著她轉頭對瑪姬說。
「小姐,妳給我好好思考一件事,嗯,事實上有兩件事。第一,吊在那邊的有可能是妳小妹,而不是妳。第二,我知道妳幹過一些壞事,我很想聽妳親口招供,所以這不是小孩子的遊戲。要嘛妳們兩個自己說,要嘛我從別人嘴裡聽到。妳仔細考慮考慮吧。」蘿絲說完轉身離開。
我們聽到她爬上樓梯。
唐尼把瑪姬的嘴塞住。
他本可去摸她,但他沒有。
彷彿蘿絲還在房裡監視著,她的存在遠大於殘留在空中的煙味,即使人不在,卻陰魂不散地纏著她兒子們和我,如果我們敢反駁或違逆她,我們就會永無寧日。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她的許可是何其厲害的手段了。
這是一場專屬於蘿絲的秀。
所謂的「突擊」根本不存在。
瞭解這點後,我覺得豈止只是瑪姬而已,我們大家全都被剝得赤條精光地吊在那兒了。
第二十八章「我們跟她講突擊的事了。」唐尼說。「跟誰說?」「蘿絲,我媽媽,要不還會有誰,笨死了。」我進門時,唐尼一個人在廚房做花生奶油三明治,我猜那是當天的晚餐。流理台上有花生奶油、葡萄果醬的油跡和麵包屑。我好玩地數了數抽屜裡的餐具,還是只有五組。「你們跟她說啦?」他點點頭,「是吠吠說的。」唐尼吃了一口三明治,然後坐到客廳桌邊,我在他對面坐下,木桌上有一條以前從沒見過的半吋煙痕。「天啊,她怎麼說?」「什麼都沒說。好奇怪哦,好像她本來就知道,你懂吧?」「本來就知道?知道什麼?」「知道所有的事啊,好像...


 2017/01/13
2017/01/13 2010/07/06
201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