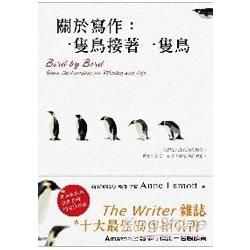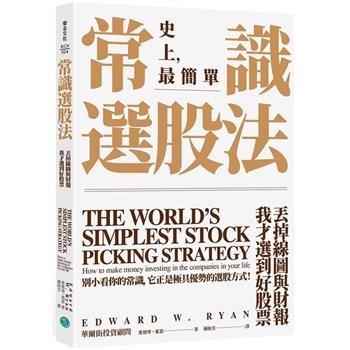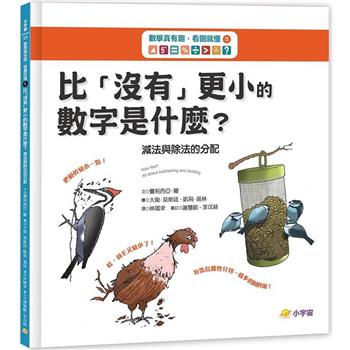三十年前,我的哥哥十歲,第二天得交一篇鳥類報告。雖然他之前有三個月的時間寫這份作業,卻一直沒有進展。當時他坐在餐桌前,周圍散置著作業簿、鉛筆和一本本未打開的鳥類書籍。面對眼前的艱鉅任務,他不知如何著手,簡直快哭出來了。後來身為作家的父親在他身旁坐下,把手放在他肩上說,「一隻鳥接著一隻鳥,夥伴。只要一隻鳥接著一隻鳥,按部就班地寫。」
多年來,安‧拉莫特把這個故事謹記在心,寫作的時候,以及和寫作班的學生上課時,她總把它當成一個鼓勵;並且,轉而贈與我們一份獻禮:一本循序漸進、教導如何寫作和處理過程中各種狀況的指南。
幾乎沒有一本教寫作的書,像這樣令人時而捧腹大笑,時而感動落淚,並且如同小說般,讀畢竟有依依不捨的感覺。安‧拉莫特坦率風趣的文筆,將寫作的各個面向,闡述得一針見血又引人入勝。這大概是本書之所以成為暢銷經典的原因──自1994年出版以來,蟬聯Amazon網路書店分類排行榜第一名長達十四年之久。
作家布洛德瑞克(Jim Broderick)說:「每個熱愛寫作的人,都應該要有像拉莫特這樣的朋友!」她幫助你一路解決寫作的困境,探索寫作的方法,深入閱讀與寫作的喜悅中。
你只要一個字一個字地將你想到的寫下,靈感便會來敲門。你可以將寫作當成例行工作,也可以將它當成一件樂事。你的寫作過程可以像小時候被叫去洗碗般不情不願,也可以像表演日本茶道般細心專注,讓自己完全沈浸其中,同時找到自我。
然後我們也會擁有可以付出的東西,一首能唱出來的歌。
即使沒想過成為作家,也可以為自己而寫。然後我們會發現,寫作最好的回報,就是寫作本身。
那個當下,正是我們的歸屬。
作者簡介:
安‧拉莫特(Anne Lamott)
1954年生於舊金山。自馬里蘭州古徹學院(Goucher College)肄業後,便搬回舊金山灣區從事寫作。1980年,推出第一本小說《大笑》(Hard Laughter),接下來出版的小說包括《蘿西》(Rosie)(1983)、《喬瓊斯》(Joe Jones)(1985),以及《所有新人》(All New People)(1989)。1993年推出根據個人經歷寫成的《幽默與勇氣──一個單親媽媽的育兒日記》(Operating Instructions,中文版由方智出版)。1997年出版另一本小說《變調少女心》(Crooked Little Heart),其他著作包括《人生旅途中的恩賜:對信仰的一些思索》(Traveling Mercies: Some Thoughts on Faith)(1999)、《備份計畫:對信仰的深入思索》(Plan B: Further Thoughts on Faith)(2005)。
身為古根漢學術獎得主的安‧拉莫特曾為《小姐》(Mademoiselle)雜誌的書評專欄作家,也為《加州》雜誌撰寫過美食餐廳評論,並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及全美各地多個寫作研討會教授寫作。
目前和兒子山姆定居加州聖拉斐爾。
章節試閱
第一部 寫作
動筆
我總會在寫作研習坊開課的第一天告訴新生們,照實描述是寫出好作品的要素。我們是一種需要、也想要瞭解自己是誰的生物。羊蝨似乎不像我們一樣擁有如此渴望,所以牠們不寫作。我每年的學生都有一籮筐故事想說出來,於是便興致勃勃、甚至可能滿心歡喜地開始動筆寫作──相信最後人們將會聽到他們的聲音,而他們也打算全心投入這件從小便由衷渴望的工作。但在書桌前坐了幾天後,卻發現要以生動有趣的文字描述事實,竟有如幫貓洗澡般困難又磨人。有些人便喪氣了,自信和對故事的感覺也隨之崩盤。過程大致如下:當他們第一天來研習坊上課,看起來就像滿懷期盼的天真小鴨,打算跟隨我到天涯海角,但到了第二堂課,他們只是木然地看著我,彷彿熱情完全消逝了。
「我甚至連從哪裡著手都不知道。」有人會這樣哀聲抱怨。
我告訴他們,從自己的童年往事著手。一頭跳進你的回憶,沈浸其中,並將所有記得的事盡可能照實寫下。弗蘭納莉•歐康諾(Flannery O’Connor) 曾說,任何有本事撐過童年的人,一輩子都不缺題材可寫。或許你的童年過得悽慘悲苦,但若能照實寫出來,悽慘悲苦也不算太糟糕。不過先別擔心寫得好不好;開始動筆就對了。
現在,你想到的題材可能多到讓腦子當機。在經過多年撰寫美食評論後,我的腦海充塞了太多關於餐廳和各色菜餚的記憶,以至於有人臨時要我推薦,我反而連一家曾親自光顧過的餐廳都想不起來。但若對方能將範圍縮小,比方說印度菜,我可能會想起某次我的約會對象曾在一家富麗堂皇的印度餐館向侍者索取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的作品集錦,接著竟然還開口點韃靼牛肉;而牛在印度人的心目中可是神聖無比的動物。然後,許多跟其他約會對象和印度餐廳有關的記憶便會隨之湧現。
所以,不妨就從回想並寫下你入學最初幾年遇到的每一件事著手。先從幼稚園開始。當你想到那些事,試著記住並寫下來。別擔心寫得不好,因為沒人會讀到。然後回想一年級時,接著再到二年級、三年級。你的老師和同學有哪些人?你穿什麼樣的衣服去上學?你嫉妒過誰?曾珍藏什麼?然後再將範圍擴大些。那幾年間,你曾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去度假嗎?寫下來。是否還記得你總覺得別家人看起來就是比自家人體面得多?是否還記得你拿著汽車內胎當游泳圈到河裡玩水,每當鑽進和鑽出內胎時,大腿總是留下一道道刮痕,只因為家人老是搞丟理應旋緊在內胎充氣孔上的小防護蓋,而別家的人卻從來不會把蓋子搞丟?
如果這個方向沒有用,或者它有成效、但也挖得差不多了,不妨將重點轉到節日和重要聚會,看看它們能否幫你回想起過往生活的點滴。寫下記憶中每年過生日、聖誕節、復活節或任何節日所發生的一切,包括在場的所有親戚。寫下你曾發誓絕不告訴任何人的所有事。你能否想起自己的生日聚會──災難性的插曲、生日到來的前幾天、還有親戚們被蛋糕燭光照亮的臉?仔細回想所有細節:人們吃的食物、放的音樂、彼此的對話、身上的服裝──那些縫滿花瓣裝飾的難看泳帽,男士們醜陋的游泳褲,以及你那位胖姨媽身上緊到恐怕得動用油壓剪才脫得下來的小洋裝。寫下女士們頭上塞豬鬃毛梳成的蓬捲髮、你的父親伯叔們用來固定西裝襪子的襪帶、祖父的帽子樣式,還有表兄弟們身上的童軍服是如何筆挺整潔,而你自己身上的那套卻活像是剛從衣櫃角落挖出來似的。描述風衣、披肩和短外套的樣式,人們穿著和脫下它們後的模樣。試試看能否想起十歲那年聖誕節收到的禮物,還有它帶給你的感受。記下那些成年人多喝幾杯後的言行舉止,尤其是你父親在某年國慶日調了魚庫潘趣酒(Fish House punch),結果所有喝了酒的大人在屋子裡搖搖晃晃地走來走去的景象。
記住,你的經歷是屬於你自己的。如果你的童年稱不上幸福,你很可能從小到大都認為,若把家中發生過的一切照實寫出來,就會有一根瘦長的白色手指從雲端伸出來指著你,以如雷般令人不寒而慄的聲音說道,「我們警告過你不可說。」但那些畢竟都已是陳年舊事了,所以不妨寫下你對父母、兄弟姊妹、親戚和鄰居的所有記憶,我們稍後再來討論毀謗的問題。
「可是,該怎麼做?」我的學生問道。「那你是怎麼做的?」
我告訴他們,坐下來;試著在每天差不多固定的時間坐在書桌前。這是訓練自己的潛意識動起來的方法。於是你每天,比方說,在早上九點或晚上十點坐下來,將紙放進打字機,或啟動電腦、打開檔案,呆呆看著它一小時左右。然後你開始前後搖晃身子,起初只是小幅度的,到後來簡直像個有自閉症的大孩子。你盯著天花板,再望向時鐘,打哈欠,然後又回到紙上。接著,你將手指放在鍵盤上,一個影像開始在腦中成形──某個景致、地點、人物、任何東西──於是你試著靜下心,好讓自己能排除腦子裡的其他聲音,聽見那個景象或人物要說什麼。其他聲音是妖精和搗蛋鬼。它們是焦慮、批評、悲觀、罪惡感,以及嚴重的憂鬱症。此外可能還有一個蠻橫的聲音對你下命令──例如你還有一堆瑣事得立刻處理:必須把食物從冷凍庫拿出來、有約會得取消或改時間、或眉毛該拔了。但你幻想自己正拿著一把槍指著頭,強迫自己待在書桌前。你可能感到頸根疼痛無比,當下懷疑是否得了髓膜炎。接著電話響起,你不快地翻了翻白眼,要求自己認命地接了電話,語氣禮貌但可能帶了點幾乎聽不出來的不耐煩。對方問你是否在忙,你回答沒錯,因為你的確是。
然而在這一切的表面下,你清理出一個角落給寫作的熱望,大刀砍掉其他聲音,開始組織句子。你開始將一個一個字如珠子般串成一段故事。你極度渴望表達、啟發或娛樂,渴望保存美善、歡樂、或超凡的時刻,渴望重現真實或想像的事件。但你不能期待它一蹴可及。這是一件關乎堅持、信念和辛勤耕耘的工作。所以不妨直接動筆。
我希望能擁有什麼速成秘訣,某種我父親臨終前以微弱的聲音傳授給我的秘方,某種讓我坐在桌前就能像導航員般帶領創意航機降落的口訣。但我沒有。據我所知,幾乎我認識的每個人都有非常類似的寫作過程。好消息是,有天你會發現,寫作的過程感覺上就像是跳脫自我設限的框框,好讓任何想要被寫下來的東西,都能透過你訴諸文字。這有點類似要跟某人討論一件難以措辭的事,當你打算付諸行動時,內心不禁希望和祈禱,只要站在對方面前並試著開口,就能說出適當的話。通常,你也的確找到適當的措辭,也「寫」了好一陣子,將許多想法訴諸文字。但壞消息是,若你跟我類似,很可能會把自己寫的東西從頭到尾讀過,然後整天滿腦子只想到它,同時祈禱在能夠全部重寫或刪除之前不會死掉,以免引頸期盼的眾人會看到並發現你的初稿寫得有多爛。
即使滿腦子想著它並沒有害你失眠,痛恨自己也可能會讓你在晚餐前陷入嗜睡症的昏迷狀態。就算你在正常時間入睡,十有八九你還是可能因為夢見自己死了,而在凌晨四點驚醒。結果死掉這件事感覺上遠比你過去想像得還瘋狂。通常你會靠回想前一天寫下的東西來安撫自己──那篇又臭又長的文字。你或許會因為它寫得實在很爛而輾轉反側,覺得這一生毫無意義,也從來沒有人真正愛過你;你可能滿腦子都是波濤洶湧的羞愧感,認為自己的作品沒救了,也明瞭你恐怕得將目前為止寫的所有東西扔掉,再次耙梳回憶並重寫。但你沒辦法這麼做。因為你突然發現自己得了癌症,病入膏肓。
然後奇蹟出現了。太陽依然升起,於是你起床,照慣例一件接一件做著起床後該做的事,最後,九點了,你發現自己回到書桌前,茫然盯著你前一天寫的幾頁文字。第四頁前半是一大段關於各種生活經歷的敘述,當中描寫的氣味、聲音、顏色、甚至一段對話,讓你不由得非常、非常輕柔地對自己說,「嗯。」你再次抬頭望向窗外,但這回,你的指尖輕敲著桌面,也不在乎前三頁了;那些會被扔掉,那些是你需要寫出來、好引出第四頁這一大段其實打從一開始動筆便已存在腦中的文字,只是當時你並不知道,也無從得知,直到你真正寫出來。於是故事開始成形,你也逐漸明瞭自己不是在寫什麼,而這點將幫助你發現自己是在寫什麼。不妨想像一位優秀的畫家正嘗試捕捉腦海中的某個景象。他會從畫布的一角開始,在適當的位置描繪,畫出後卻覺得不夠好,便用白色顏料蓋掉,再試一次。每回他都會發現自己想畫的不是什麼,直到最後終於發現他要畫的是什麼。
當你真正發現自己內心景象的一角是什麼,便等於開始起跑了。而這也的確像跑步;我總會想起《兔子快跑》(Rabbit, Run) 一書的最後幾句話:「他的腳跟先是重重落在人行道上,但一種奇妙的恐慌促使他立刻輕易地集中心神,腳步變得更輕、更快、也更小聲,他跑著。啊:跑吧。跑吧。」
我希望能更常體驗到那種靈光乍現的感覺。我幾乎從來沒有過。我唯一知道的是,若在書桌前坐得夠久,我就會有收穫。
我的學生盯著我一會兒。「我們要如何找經紀人?」
我嘆了口氣。如果你準備就緒,那麼目前有一些列出眾多經紀人的名冊。你可從中挑出幾個人,寫信過去詢問他們是否願意看看你的作品。他們大都不會答應。但如果你真的寫得很好,又很有耐心堅持下去,最後會有人願意讀讀你的作品,並簽下你。我幾乎可以如此保證。但此刻,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寫作這件事,以及如何成為一個更優秀的寫作者。因為成為更優秀的寫作者,將能幫助你成為更好的讀者,而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回報。
但我的學生不相信我。他們想擁有經紀人,想出書。而且,他們想退錢。
他們大都早已寫了一段時間,有些人甚至投入很多年。其中不少人以前常聽到別人稱讚他們文筆不錯,而他們想知道為何當自己坐下來要動筆時,還是會覺得不可思議,為何他們想到好點子並寫出一個句子後,卻驚恐地發現它竟然那麼拙劣。接下來折磨他們的各種精神病主要病徵便如鱒魚跳出水般一下子發作──妄想、猜疑、過度自我膨脹、厭惡自己、注意力無法集中,甚至洗手強迫症、病菌恐懼症。尤其還加上偏執。
我告訴他們,你可以對這些感覺棄械投降,任它們擺佈,或者也可以,比如說,把偏執視為一個好題材。你可以將它當成剛從河裡淘上來的生黏土般隨意捏塑:你筆下的角色之一理所當然是偏執狂,所以透過賦予他這個特質,你可運用並塑造出某種真實、可笑、或恐怖的形象。我曾在某人寄給我的一首菲利普•洛佩特(Phillip Lopate) 的詩中讀到這類描述,內容如下:
身為你最親密友人的我們
認為該是時候告訴你
我們每個星期四都有團體聚會
我們既不如你所願那麼愛你
也不放你走。
因此我們想方設法
讓你身陷無邊無際的
不確定
挫折
不滿
和折磨。
你的心理分析師
還有你的男友
你的前夫
全都知情;
只要你還需要我們
我們就會一心
讓你感到絕望。
當告知你
眾人聯手的那一刻
我們便明瞭
這等於將
對抗不確定
當然還加上我們
的解藥
放入你的手心。
但既然週四之夜
讓我們達成一致目標
重點理所當然幾乎非關它本身
而是你
所以我們認為你很有可能
繼續無理索求關愛
若這不是出於你的毀滅性人格
便是為了大家的利益。
我的學生們活像電影《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裡的角色般瞪著我。幾乎只有三個人覺得這首詩有趣,或甚至是一個把自身的偏執化為精彩和誠懇文字的好例子。少數人好像不太舒服。最想出書的那些人則認為我是個極度憤世嫉俗的人;當中有些人似乎很喪氣,有些人則以明顯的厭惡眼神望著我,彷彿我正赤身裸體的站在螢光燈下。
最後有人舉手。「你是否可以直接將稿子寄給出版社,或者你一定得透過經紀人?」
過了一會兒,我回答,你一定要透過經紀人。
這個疑問之所以反覆出現,是因為這些人太想出書了。他們是想寫作,但內心真正想要的是出書。我告訴他們,這個目標並非一蹴可及。我們都想進入這道大門,而寫作可以幫助你找到並開啟它。寫作能帶給你像生養小孩般的感受,促使你集中注意力,幫助你變得柔和及清醒。但出書不會;你絕無法透過出書得到這些。
我三歲半的兒子山姆(Sam)有一組塑膠玩具手銬和開啟它們的鑰匙。某天早上,他故意將自己鎖在家門外。當時我正坐在沙發上看報,聽見他將玩具鑰匙插進前門鎖孔,試圖開門。接著我聽見他說,「喔,屎(shit)。」我的臉立刻像孟克(Edvard Munch) 畫作〈吶喊〉(Scream)中的那個男人般拉長了。過了一會兒,我起身開門。
「寶貝,」我問,「你剛剛說了什麼?」
「我說,『喔,屎。』」他回答。
「可是寶貝,那是髒話。我們都不該說髒話,好嗎?」
他抬著頭想了想,然後點點頭,並說,「好的,媽。」接著他靠過來,像要透露什麼機密般對我說,「可是我要告訴你我為什麼說『屎』。」我說好。他說,「因為那些他媽的鑰匙!」
假鑰匙並不能幫你打開門。你期待出書為你獲取的一切,幾乎都是假的,都是幻影──就像印在信用卡上的展翅老鷹並不會真的飛上天,只是看起來像是而已。真相是,若你每天堅持不懈地創作自己的音樂,慢慢試著更加努力練習,聆聽傑出音樂家演奏你喜愛的音樂,你也會變得更優秀。有時當你坐在書桌前工作,會感到乏味和提不起勁,而接下來的一整天或許都處於這種狀態,或能夠慢慢擺脫這種狀態;但若以為成功的作家就不會有感到乏味和挫敗的時刻,不會有強烈感覺自己如水黽般神經質和渺小的不安全感,那就錯了。他們的確有。但他們也常在寫作時感受到巨大的驚奇,並明瞭到這正是自己此生唯一想從事的工作。所以,如果你內心最大的渴望之一是寫作,那麼有一些方法能幫助你達成,也有好幾個理由可以說明為何動筆去寫很重要。
再說一次,那些理由是什麼?我的學生問道。
因為對我們當中的某些人來說,書籍幾乎跟世上的一切同等重要。這些小小的、扁平的、堅硬的方形紙製品,竟能在我們眼前展開一個又一個天地,陪伴、撫慰、平靜、激勵我們的心,實在不可思議。書幫助我們瞭解自己是誰和自己的行為反應。它們讓我們看到群體和友誼的意義,以及如何生活和死亡。它們充滿了我們無法從現實生活中獲得的一切──例如美妙、充滿情感的語彙。此外還有長時間的專注:我們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留意到一些令人驚奇的小事物,卻很少停下來仔細觀察。而某位作者竟能寫出使你專心沈浸其中的迷人作品,這是一種偉大的天賦。我對好書的感激是無窮盡的;我對它們懷抱著跟大海等量齊觀的感激。你不也一樣嗎?我問道。
大多數人點點頭。這正是他們在此的原因:他們喜愛閱讀,他們喜愛好作品,他們也想寫出來。但少數幾個學生依然帶著絕望和被背叛的表情望著我,彷彿他們打算上吊。我輕快地告訴他們,想退錢已經太遲了,但我有更好的東西。接下來是我所能傳授的兩個最有用的寫作概念。
短文
第一個有用的概念是撰寫短文。通常當你坐下來準備動筆,你想寫的可能是一部講述童年的自傳體小說,或一齣關於移民經歷的戲劇,或比如說,一段婦女的歷史。但這就像想親自測量冰河;你的雙腳很難站穩,每個指尖凍得發紅龜裂,然後你的各種精神病徵也如行蹤最詭秘的重病親戚般,來書桌前報到。他們拉開椅子,環坐在電腦前,即使他們試著不吵不鬧,但你知道他們就在背後,散發出帶腥味的怪異氣息斜睨著你。
當我面臨這樣的時刻,感到越來越驚慌,聽見腦中的叢林戰鼓響起,知道靈感之井枯竭了,看不見未來,必須趕快找份工作,但我一無所長;此時,我的應對之道是暫停。首先,我試著深呼吸,要不然我不是坐在桌前像隻迷你犬般喘氣,就是會像哮喘病患死前喉頭無意識地發出緩慢的咯咯聲。所以我坐在原處一分鐘,放慢、平緩的呼吸,任思緒漫遊。過了一會兒,我可能發現自己正思考我是否年紀大到不適合做牙齒矯正,而現在是不是打幾個電話找人的好時機。接著我又開始考慮學化妝,說不定這樣就能找到一個狀況不算太差的男朋友,我的生活將會非常美滿,我也會永遠快樂幸福。然後我想到所有早在我坐在桌前準備動筆前就該回電的人,還有我也許至少該跟我的經紀人報到一下,告訴他我剛才想到的好主意,看看他是否也認為如此,以及他是否覺得我該去做牙齒矯正──如果這正是每次我們一起午餐時他真正在想的事。接著我想到某個我實在很討厭的人,或某個讓我抓狂的財務問題,便打定主意一定要在今天開始寫作之前解決。於是我彷彿變成一隻擁有潔牙玩具的狗,先啃它一陣子,再將玩具甩在地上,跟它玩角力,再把它往身後扔,追它,舔它,咬它,再甩到身後。我停下來喘口氣,只差沒有真的汪汪叫。但這整段過程只花了一到兩分鐘,所以我還不算浪費太多時間。不過這讓我喘不過氣來。於是我再次嘗試平緩的深呼吸,最後注意到我放在桌上用來提醒自己撰寫短文的一英吋相片的相框。
它提醒我,我唯一該做的就是寫出一英吋見方的短文。這是目前我應該寫出來的篇幅。當下我想做的是,例如,寫一小段故事背景設定在我家鄉小鎮的敘述,時間是五○年代,當時仍有火車停靠。我將用我的文字處理機透過文字描繪它。或者我想敘述的是主角的首度出場,即她在故事中第一次走出屋門到前廊的情景。我甚至不打算描述當她第一次注意到那隻瞎眼的狗坐在她車子輪後時的表情──我只需要能塞滿一英吋見方框框的文字,一小段描寫這名女子在以我成長的小鎮為背景的故事中首度出現的景象。
道科特諾(E. L. Doctorow) 曾說,「寫小說就像夜間開車。你的視線只達車頭燈照得到的範圍,但你還是能這樣走完整段路。」你無須看見自己將去何方,也不用看見目的地或途經的一切。你只要能看清前方兩、三英尺的範圍即可。這是目前為止我所聽過關於寫作或人生最好的建議。
所以在把世上我最憎恨的人、我最明顯的財務問題、當然還有牙齒矯正全想過一遍,因而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竭之後,我記起那個一英吋照片的相框,並為我要說的故事想出一英吋見方的文字敘述,一小塊畫面,一個回憶,一段對話。我也想起一個故事,我知道自己曾在別的地方講過,但它總能幫助我掌握竅門。三十年前,我的哥哥十歲,第二天得交一篇鳥類報告。雖然他之前有三個月的時間寫這份作業,卻一直沒有進展。當時在我家位於博利納斯的度假小屋,他坐在餐桌前,周圍散置著作業簿、鉛筆和一本本未打開的鳥類書籍。他面對眼前的艱鉅任務,不知如何著手,簡直快哭出來了。後來我父親在他身旁坐下,把手放在他肩上說,「一隻鳥接著一隻鳥,夥伴。只要一隻鳥接著一隻鳥,按部就班地寫。」
我又把這個故事講一遍,因為它通常能在我的學生感到極度頹喪時起點作用。有時,這個故事的確為他們帶來希望,而希望,正如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 所言,是讓我們在遭遇理應感到絕望的狀況,卻還能保持愉快的力量。寫作可能會是一件令人非常喪氣的工作,因為它牽涉到我們內心最深切的需要:需要被看到、被聽到,渴望自己的生命有意義,需要覺醒、成長和有所歸屬。也難怪我們有時會太過認真看待跟自己相關的一切。以下是另一個我常說的故事。
比爾•墨瑞(Bill Murray) 在電影《天高地不厚》(Stripes)中飾演一名剛從軍的新兵。其中一幕是在新兵訓練營的第一夜,墨瑞所屬的那一排在軍營內集合,以彼此認識並和領導他們的中士(由華倫•奧提斯〔Warren Oates〕飾)見面。每個人有一點點時間告訴大家自己是誰、來自何地。最後輪到那個極度緊繃、憤怒的傢伙,法蘭西斯(Francis)。「我名叫法蘭西斯,」他說,「但沒人叫我法蘭西斯──如果這裡有任何人敢叫我法蘭西斯,我會殺死他。還有,我不喜歡別人碰我。如果這裡有任何人敢碰我一下,我會殺死他。」此時,華倫•奧提斯跳出來說,「嘿──放輕鬆點,法蘭西斯。」
把這段台詞貼在你書房的牆上也不壞。
不妨盡可能和善地告訴自己,嘿,親愛的,我們此刻所要做的,就只是寫一段描述河上日出景致、小孩在俱樂部泳池游泳、或一名男子與他未來將結為連理的女子邂逅的文字。我們現在要做的就僅是如此。我們只要「一隻鳥接著一隻鳥」慢慢來,終究會完成這一篇短文。
第一部 寫作動筆我總會在寫作研習坊開課的第一天告訴新生們,照實描述是寫出好作品的要素。我們是一種需要、也想要瞭解自己是誰的生物。羊蝨似乎不像我們一樣擁有如此渴望,所以牠們不寫作。我每年的學生都有一籮筐故事想說出來,於是便興致勃勃、甚至可能滿心歡喜地開始動筆寫作──相信最後人們將會聽到他們的聲音,而他們也打算全心投入這件從小便由衷渴望的工作。但在書桌前坐了幾天後,卻發現要以生動有趣的文字描述事實,竟有如幫貓洗澡般困難又磨人。有些人便喪氣了,自信和對故事的感覺也隨之崩盤。過程大致如下:當他們第一天來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