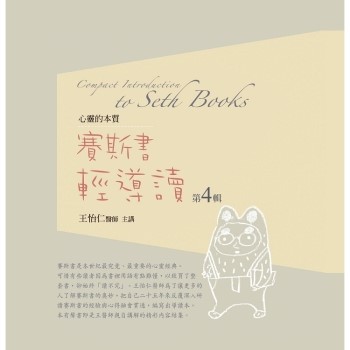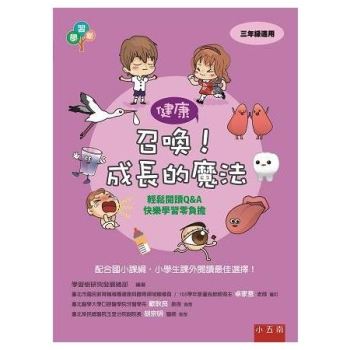名人推薦:
世界已經悄悄不同 248農學市集召集人 楊 儒 門
農民、農業、農村,在台灣,幾乎到了盡頭。一個又一個的法案,對整個農業環境的不友善,不外乎辛苦、勞累、成本大、效益低……但是每日三餐桌上的到底又是什麼,終日努力,最低的要求,不就是三餐的溫飽。沒有農民、農業、農村之後,我們要吃什麼?到底有多少人認真去想過?
隔著海峽,中國大陸的農民問題,似乎又漸漸浮出了檯面,畢竟這關係到超過13億人的生活,不認真去看的話,會是無法解決的問題。樂見春桃與桂棣老師透過「中國農民調查三部曲」的《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與《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兩本新作,提點大家繼續關注、重視。不管是在台灣、中國,或是日本,任何國家,農民、農業、農村仍是穩定社會的力量,當這股力量趨於破碎時,社會的問題就會浮現出來。
拜讀《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過程中,每每回想起過往歲月……呵,心中其實沒有多大的起伏。有人說,過去了就好,有人說,年少輕狂,有人說,是年輕不懂事……大多數的人以為我只關了幾個月,所以公共電視訪問完回去做專題時,直接在口白上,打上「關了一年」。自己看到這一幕的時候,是想笑的,很少人知道,也很少人去關心,其實我關了兩年七個月。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時間,一個人有多少個兩年七個月可以去浪費,去留白。但這卻不是我所關心的事情,當一個人做了選擇,就該承受起所有責任,毋需逃避與否認曾經發生過的任何事情,因為時間是不會重來的,向前走的同時,一切也都交給社會去評斷。
所以當有人覺得我眼熟、似曾相識、忌諱說出我之前所做的事或媒体賦予我的外號 ─「白米炸彈客」時,大家都想太多了。「萬般帶不走,只有業隨身」。對我來說,過去的一切,是我,現在的一切,仍是我,並不會因為時間的改變,而有所不同。生命的腳步,在人生的旅程中,就像在沙灘上赤腳走過的足跡,隨著時間的流逝,海水潮來潮去,終將化為一片平坦,但是我們不能說沒有走過……
因為走過,所以《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裡面描述庭訊的過程,也讓我回想起當時一幕幕情景。在開庭的時候,法官告訴我,他家是種田時,讓我思考許久;聽到法官認定我是自首,一步出法庭門口,法警那振臂高呼,接著踩到我的拖鞋的那一刻,內心則是平靜的,心情上不會比現在坐在電腦前的我有多少起伏。倒是覺得有趣,為什麼別人的心裡,會比我還要開心?雖然出來之後沒有如關心友人的願望走上教途與演講之路,而是選擇直接幫農友劃出另一條產銷道路:投身進農學市集與消費者直接面對面的溝通,努力地與儒欣、建誠、育民和一大群關心的朋友,一同在觀念上的推廣上,劈荊斬棘地開出一條嶄新道路。路途是遙遠的,也是辛苦的,但一路走來,仍相信這是一條對的路。
走別人不走的路,或許不是最辛苦。相較《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裡發起「分田到戶」、歃血為盟的主人翁嚴宏昌,才叫我滿心地佩服。故事的時代背景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當時是改革開放還未起步的時候(一個月後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基本定調)。文化大革命發生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中越戰爭發生在一九七九年,當時竟有人膽敢挑戰共產黨的基礎 ─ 無產階級萬歲,吃大鍋飯的年代裡,那真的是砍頭的事,但卻有人敢於此,這就是中國改革第一村的發起人嚴宏昌先生。
每件事都有一種過程,看了《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發現嚴宏昌正是最好的例子:即便無私地奉獻,即便努力的過程中一直遇到朋友親人的阻擾、政府單位的阻擾,但他還是始終勇往直前,為了「眾人的事」而努力。認同,始終是件不容易的事,當我們向前行時,面臨的不會只是做事而已,還包括做人,而做人,才是另一種困境的開始。
也因此,自己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曾再寫文章,原因是實作之後發現「做比說來的重要」,甚至有一段期間,連溝通都有一點的懶。當好奇者、有心人、朋友等人詢問到市集的組成與發展時,都透露出點點的不耐,覺得問那麼多,多數人都只當成滿足好奇心。而沒有進一步的行動,而覺得很氣餒。為什麼大家只喜歡空口白話,而沒有實際的動能。忽然一時之間,有點氣,有點悶,有點苦,無人可以訴說!這種想法卻違背當初成立市集的宗旨「讓生產者與消費者有面對面溝通的機會」。但平心靜氣後,自省,何必,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不應因為前一個人的因素,而加諸任何不快於下一個人身上,這是不公平的事。一點通,萬點靈,又恢復原本搞笑的個性,沒什麼,這就是人生!
「我們無法改變世界,只有努力的向前走,當年老坐在搖椅上,在田間的小路旁乘涼時,世界已經悄悄地不同了」。
媒體推薦:
南方朔 / 文化評論家、亞洲週刊總主筆
舒詩偉 / 青芽兒主編
吳介民 /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教授
黃孫權 / 破周報總編輯
張鐵志 / 旺報文化版主編、作家
林生祥 / 音樂創作人
吳東傑 / 綠色陣線協會執行長
黃德北 /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
胡忠信 / 政治評論者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編輯推薦:
給台灣讀者的一段話 — 關於《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
《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出版後,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是空前的。我們真的沒有想到,僅僅因為講了真話,將中國農民悲苦無奈的生存狀態和中國農村改革艱難的歷史如實寫出,就引起這樣大的震動。更沒想到的是,書的發行不到兩個月時間,對此書的宣傳就突然被「叫停」,並要求各地的書店將這本書立即「下架」。
真話遭到「封殺」,做假便有了市場,於是我們在書中批評到的一位官員,便以損害了他的名譽權為由,把我們告到了他所在城市的法院。
我們同樣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大陸所有的新聞部門都被告知,不准介入到這場官司中,這就意味著,作為「社會公器」的傳媒,也不能再對這一案件進行正常的輿論監督,所有關心我們的讀者也被剝奪了依法享有的知情權。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大陸所有傳媒的一次集體失語。由此,這個本來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所謂名譽權糾紛案,便迅速演變成了對《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及其作者的政治審判。
《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記錄的正是我們自出版了《中國農民調查》之後五年來的坎坷經歷,以及遭遇到的一場荒唐而又惡劣的官司。
原以為,寫我們自己親歷的這場官司,總會比寫《中國農民調查》容易得多,不曾想,卻寫得一樣的艱苦,一樣的沉重,一樣的歷時三年。當然,寫完了之後,也才發現,只有馬克思的一句話,可以道出當時的輕鬆:「我說出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如果說,《中國農民調查》是在為九億農民講真話,那麼,《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則是在為自己伸張正義。這在有著言論自由,有著新聞出版自由的台灣讀者看來,也許有些不可思議,但我們這五年來的經歷,確實是置身其中的民主與法制狀況的一個樣本。
可以說: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三十年,當今改革的核心問題已不是經濟,而是法治。我們甚至相信:《等待判決》的出版,對推動中國法治的進步是會有意義的。因為故事中的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有著巨大的體制罅隙需要叩問,有著深刻的教訓值得記取。
陳桂棣 春 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