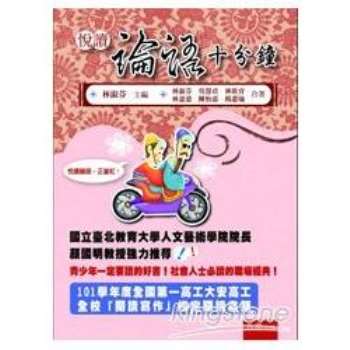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永遠的下一站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10 |
詩 |
電子書 |
$ 210 |
華文現代詩 |
電子書 |
$ 210 |
文學小說 |
$ 267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藝術家盛正德長期致力於畫作及文字,探索人的存在與孤寂。其創作不論詩或畫都充滿影像與故事,串連起來猶如一幕幕寓意深遠的電影。自言要讓「虛幻的時間在指尖流動,喃喃敘說不曾聽聞的故事」。近十年來他化身「沒有行李的旅人,於夜晚的街頭獨行」,以七十餘幅粉彩畫與一百多首詩作,引領讀者進入黑白灰的世界,在光與暗之間遊走,傾聽所有曖昧與神秘的足音。四十多年創作歷程之後,終以最純粹的形式,將光陰一筆一筆譜成絕美篇章,繼而「舉手輕揮,不是呼喚旅人,而是向溜走的時光告別」。
「想像溫柔、想像浪漫
想像一切性、愛或死亡
像街頭二輪電影
光影交錯著荒謬的故事」
「愛情什麼時候熄滅?
在暖風吹過的晚上
希望何時用罄?
在流浪街頭的黃昏」
「然而我知道
人間孤寂的重量是相同的」
作者簡介
盛正德
無從選擇地出生於水瓶座,隨著時間的流逝,瓶內的水逐漸蒸發,敲打出的音階也就不同了。年輕時畫著大幅的油畫,如今畫了好一陣子的油性粉彩,華麗的色彩不見了;畫面常是回首看見燈火闌珊處的景緻。不知幸或不幸每天仍在動筆──畫筆或中性筆──頑固地不用電筆。
除了作畫寫字之外,喜歡看書及電影,近十年畫展少了些,另在社大講藝術電影,希望能聚集更多同好共賞、共談。
生活中大部分時間都是獨處,不,不是獨處,總有狗狗相伴,常和狗狗說些莫名其妙的話,狗兒們歪著頭用充滿疑惑的眼睛看著我,說到後來自己也迷惑地不知所云。
等水瓶乾涸了,語言、文字與畫,也會一起消失。這世界只有遺忘才是常存不變,寫詩與作畫只是讓自個兒的遺忘能稍緩片刻吧。
一九四五年出生,作畫四十餘年未輟。
著作有:《有條河名叫中港溪》文化局出版
《覡者妖言》彩藝得出版
《以畫療傷》心靈工坊出版
《時間的影子》心靈工坊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