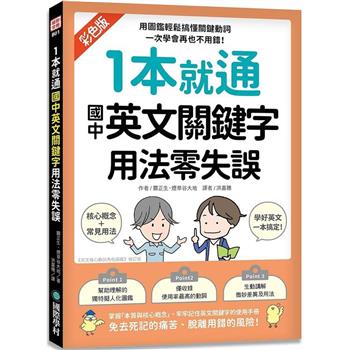序言
十年,一種異類人生、一種社會觀察
李政亮
這是一本用歲月累積寫成的一本書,源自異類的人生軌跡與社會文化觀察。
二○○○年的秋天,踏進北京大學西門那個掛著毛體書寫的「北京大學」牌子的校門,那一瞬間開始,我已然走了一條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詩句中所說的「較少人走的路」,而這條路,確實也如同詩句中所說的,「就是這樣使得一切都不同了」。這十年是台灣與中國社會的一個關鍵時刻:台灣歷經了兩次政黨輪替,大陸政策由敵對走向和解、中國從與國際接軌到北京成功舉辦奧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也有著更大的影響力。而隨著經濟高度發展,除了世界工廠之外,中國也是全球資本賦予厚望的世界市場。
十年來,台灣對中國的認識又是如何?媒體像是一面鏡子,反映出集體的社會心理與想像,在電視螢光幕上,大陸電視劇諸如《康熙王朝》、《大宅門》等曾在台灣引起收視熱潮;現今,大陸劇在台灣不再局限於歷史劇,諸如《醜女無敵》)等描寫現代年輕人生活的時裝劇,雖然未引起熱潮,但也成為眾多大陸劇的選項之一。此外,中國引起轟動的選秀節目運作模式也在台灣開始出現、股市新聞裡大陸股市用語「熊市」與「牛市」也早已被使用、甚至「自我感覺良好」也成為台灣媒體經常出現的語彙……等等。
部分中國元素已然進入台灣的媒體中,然而,「中國」在台灣並非沒有爭議,與中國相關的議題到產品,從統獨爭議、藍綠對抗到部分店家所貼的「拒絕中國黑心貨」的貼紙,便說明了台灣複雜的「中國情結」,這個情結埋在台灣人心靈的最深處,也隨時展現在政治對抗的場域中。
越來越堅信人活在「結構」底下,而結構也制約著人。這十年,我離開台灣來到北京讀書,進而執教。這十年,我歷經人生重要的幾個關口,從學生到老師,從單身、結婚到育有一子,八年的北京生活加上兩年巴黎生活的點綴。生活在一個經濟高度發展、社會變遷劇烈的國度中,任何一個走了「較少人走的路」的社會文化觀察者,都會擁有「就是這樣使得一切都不同了」的興奮感。除此之外,走了「較少人走的路」,也經常意味著要在僵硬的體制中付出代價,特別是在兩岸關係中的身分政治夾縫中掙扎,例如:台灣對大陸學歷的承認問題、台灣人身分能否在大陸(中國)的單位乃至學校任職等。
□ 五年級生的大陸印象
為什麼我走了一條「較少人走的路」?十年之前,我對中國的印象與一般五年級末段生沒有什麼不同:小學時候,相信大陸同胞吃香蕉皮;每年的一月二十三日是「自由日」,我們會在電視上看到谷正綱先生高呼「自由民主萬歲」之類的口號;玩著床頭的電晶體收音機,把頻道調到邊緣地帶,不是聽到台灣向大陸的喊話,就是聽到大陸向台灣發出解放的口號。
國中讀的地理是已然成為歷史的地理,秋海棠葉上的東北仍是九省、某某鐵路與某某鐵路的交會口是一種遙遠陌生的強記,而共產黨則是「一分抗戰、二分應付國民政府、七分壯大自己」藉以奪權。
高中是台灣政治與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挑戰威權的氛圍在島嶼上無處不在,「大陸」對當時的執政者來說是一種尷尬的存在。一九八七年,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與徐璐突破禁忌經由日本赴大陸採訪,同一年,政府開放探親,許多外省人帶著鄉愁踏上昔日生活的土地。
考上大學的那個夏天,在「鐵的紀律,愛的教育」的成功嶺上,看著諷刺大陸官僚政治的電影《假如我是真的》。上了大學之後,兩岸關係成為政治焦點議題之一,當時台灣的政壇流行成立智庫,在一場智庫所舉行的討論中,一位學者力陳政府應開放台灣的夕陽產業到大陸的論調,引起台下如雷的掌聲,這或許是當時台灣對大陸的主流想像。有趣的是,面對中小企業的西進熱潮與想像,當時的李登輝總統提出「南向政策」做為回應。
除此之外,簡體版的左翼書籍開始出現在台大附近的書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西方馬克思主義、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法蘭克福學派等等,都成為時代的關鍵字。
提到九○年代初期的中國意象,不能不提現今仍在部分頻道一再播放的《大陸尋奇》,這個電視節目一如張藝謀的許多電影,透過許多地方軼事向觀眾展示一個鄉土原初的中國,這也是許多五年級末段生的中國印象。
九○年代中期的研究所生活,已有一些老師同學致力兩岸問題的研究。當時的我,只覺得中國是一種遙遠的存在。當時對大陸的認識管道,大概有兩種,一種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問題相關的書系。然而,更鮮活的印象,來自於親身在大陸蹲點的研究所朋友。他們談論中國的方式,現今想來說多少是一種「獵奇式」的觀察。
例如,市場化之後,一切以金錢為上,甚至連公家單位都在經營生意,廣州的飯店知道是台灣客人(男性),早餐便送來十全大補湯之類的見聞。這種獵奇式的想像,也出現在一則網路笑話上,這則笑話列舉了一堆台灣與大陸電影名稱譯法的差異,例如美國電影Top Gun,台灣譯為《捍衛戰士》,大陸譯為《好大的一把槍》(事實上是譯為《壯志凌雲》)。這種笑話的製造,一如冷戰時期美國反諷蘇聯的笑話:有蘇聯民眾罵赫魯雪夫是白痴被捕入獄,其罪名不是毀謗罪,而是洩漏國家機密。
對我來說,大陸一直是個抽象而遙遠的存在,即便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潤八月》成為暢銷書,但我始終覺得那是小說,直到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前夕的飛彈危機。一大早趕到台大上課,課程正是兩岸關係,而授課教授也是日後曾任陸委會主委的陳明通。他告訴大家,根據NHK的報導,美軍已在沖繩島演習。原來已不只是兩岸的劍拔弩張。那一刻,突然想起法國小說家都德的《最後一課》,難道所學的東西就要翻轉了嗎?有點像吳念真說過的比喻,他的長輩認為書不用讀太多,因為□□□□□學沒多久便就變成ㄅㄆㄇㄈ。這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嗎?
□ 進入真實的中國
歷經從小到大被賦予的各種中國意象,真正讓我對中國開始感興趣,進而隻身到北京讀書,是十年之前的一段際遇。二○○○年的總統大選,有機會接觸到中外記者。相較之下,台灣記者所關注的問題不外乎陳水扁、宋楚瑜、連戰之間的權力對抗,外加李登輝與陳水扁之間弔詭的傳承問題。相較之下,外籍記者更側重兩岸問題的報導與分析。其實各黨派並非沒有兩岸政策,但更像是作文比賽。簡單說,是一種沒有認識基礎的兩岸政策,這些陣營的幕僚策士有多少人在中國真正生活過、讀書過?一九九六年飛彈危機的意象突然浮上腦海。
看到中外記者提問上的差異,加上朋友的引薦,我在二○○○年夏天第一次到中國參訪,行程包括北京、上海與南京。在北京大學留學生宿舍勺園,我看到各種膚色的留學生。校園的餐廳裡,所播放的盡數是台灣流行歌曲,任賢齊的歌曲更是從餐廳到計程車四處可聽聞,一位大約五十多歲的計程車司機,以一口濃郁的北京腔外加如同年輕超級粉絲的口吻告訴我:「我喜歡任賢齊!」
在南京,南京大學的校園裡掛著一條紅底白字的橫幅:「為把南京大學辦成世界高水平大學而奮鬥」;在一所職業技術學校中,看到學生們努力地上電腦課程。在上海的書店裡,自由主義譯介的書籍被擺放在明顯的位置,我也注意到一些關於城市文化的書籍開始出現。老實說,這打破我既有的中國印象,例如,中國是一個閉鎖的國家(至少北大看起來不是)、當時台灣人對大陸的普遍印象是落後等等。此外,我在南京的職業學校裡看到另一種向上提升的力量,上海書店裡滿屋的書,從議題到包裝都已然跟研究所時期所看過的大陸書截然不同。
法國精神分析大師拉康曾以古代畫家澤克西斯(Zeuxis)和帕拉西奧斯(Parrhasios)的繪畫比賽為例,說明人們總是相信事物背後藏著些東西。澤克西斯把葡萄畫得如此逼真,引來飛鳥啄食。而帕拉西奧斯的畫蒙著畫布。澤克西斯急於觀看以決勝負,伸手去揭開畫布時,方才發現帕拉西奧斯畫的僅僅是一張畫布。
其實我們一般人大概都跟澤克西斯一樣,有一種想揭開謎底的衝動。也在這樣的情境之下,二○○○年的夏天,我決定捨棄多年的德國夢,轉而到大陸讀書。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較為「真實」的選擇。台灣有許多留學西方的學生,然而,兩岸之間的政治對峙、經濟關係的緊密,卻又說明兩岸關係無法逃避,台灣該如何面對這個「存而不論」的大議題?
這一年,一位在上海經商的台商所寫的《我的上海經驗:從旅遊、投資到定居大陸的戰守策略》、《移民上海:我的台灣經驗遇上海派作風》等書出版之後迅速暢銷,台灣的上海熱達到高潮。
十年前走進北大校園,最顯著的特徵便是英語熱,精確來說,是英語熱的尾巴。北大昔日張貼各式言論的三角地,百家爭鳴的聲音已讓位給各式語言學習班的廣告。三角地已在數年前拆除,當時貼在上頭的廣告訊息中,英語角也佔有一席之地。所謂的「英語角」,是一種自發學習英語的團體組織,通常成員聚在一起時都說英語,藉以提升英語的實戰經驗。有時這樣的團體至少會有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外國人在裡頭。
北大附近的「新東方」,則是另一個英語學習的空間象徵,幾乎中國大陸所有要出國的學生都會到這家補習班上課,「新東方」也像是大陸學生到國外的跳板,就連美國《時代》雜誌某一期的專輯「中國的年輕人」,「新東方」也成了必經的採訪之地。
英語背後所突顯的是,英語成為一種社會流動的工具,也是大陸對美國複雜的情節。一個反諷的笑話是,九○年代美國「誤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北京大學生群情激憤,甚至有發動遊行到美國大使館抗議。有人曾諷刺,這群學生一手高喊抗議,一手拿著託福考試書。
不僅英語、美國夢,美金在大陸也很好用。一般來說,留學生都會在北大附近的小店拿美金換人民幣,這類小店門口總有人把風,而小店內部空間不大,但卻有各種幣種的交換。除此之外,部分大陸朋友也樂於與留學生兌換貨幣,一方面,人民幣不能在大陸境內兌換外幣,另一方面,則是美金是強勢貨幣,存著美金總有好處。
北京大學的校園生活幾乎就是我的全部。經歷過工作的生活,此刻只想待在知識迷宮裡來回穿梭。除了我所屬的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現已為哲學系所合併)之外,中文系、社會系的課堂都有我駐足的痕跡。特別是在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戴錦華教授所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裡,度過了幾年的時光。
當代中國一幕幕的變遷,就像一個個文化研究的議題,這些表象就像一個個的符號,在工作坊中,我們力圖抽絲剝繭地解開現象背後的政治經濟脈絡,從農民工議題、社會身分的形塑問題乃至網路現象等。這些過程或有討論甚或辯論,場景或在討論室、或在許多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路邊攤。很多夜裡,是在惱人艱澀的理論文字,與自己所遭遇的社會現實中交織度過的。
在北大的日子裡,我也穿梭在北京大學的次文化中。在北大棒壘協會,我和大概小我十歲的年輕人相處,猶記當時痞子蔡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正紅,幾乎成為這些年輕人的台灣印象。這些年輕人有人略知中華職棒(幾年後也有人視王建民為偶像,但我不知台灣棒球在奧運與經典賽連敗中國兩場之後,他們對台灣棒球是否還感興趣?)、有人迷戀美國大聯盟、鈴木一郎是最多人的偶像、日本漫畫《H2》甚至年代久遠的《巨人之星》都深受歡迎。
在這些年輕人中,有幾位成為我的哥兒們,他們引領我進入在地生活,我開始透過他們給我的中學語文教科書知道誰是雷鋒﹖什麼是年輕人流行的新現象?京味小說有哪些?棒球隊中始終有日本留學生陸續加入,這條人際網絡也成為我學日語的開始。驚喜的是,其中一位在二○○九年的日本國會大選中代表民主黨出馬,沒有太多政治資源的他,以三十五歲之齡當選。
□ 變動中的北京
十年前的北大西門附近,有幾家酒吧,價格與三里屯或是朝陽公園旁的酒吧相較,可稱是平價酒吧。各色人等穿梭其中,從學生到衣著普通的平民皆有。酒吧外面有幾家羊肉串的攤販,他們來自安徽等地,一如前來北京打工賺錢的小販,工作之外,還得提防城管的取締。在他們眼中,城管簡直就是凶神惡煞。
酒吧與足球經常是連在一起的,每逢足球賽事的轉播,酒吧總是擠滿人。大陸的足球經常是在歎息聲中收場,咒罵聲也不時隨賽事而出現。印象中唯一的例外,是二○○一年中國國足戰勝阿曼提前進入世界盃,這是時隔四十四年之後再次進入世界盃,酒吧裡的人們看著電視螢光幕上「我們晉級世界盃」的字樣,隨著音樂拍手慶祝,也有激動的客人請喝免費啤酒。這一年,世界離中國近在咫尺:除了足球,還有加入WTO、北京申奧成功,媒體普遍將之命名為「中國年」。隔年春節聯歡晚會的相聲小品,更是說了「中國風景獨好」!
然而,幾年之內,中國形象卻不斷在正負之間來回擺蕩。二○○三年SARS期間,因封鎖消息備受國際媒體批評;二○○八年,北京奧運會風光結束,但三鹿奶粉含三聚氫胺成份被揭露,引起即大的恐慌。
與北京大學西門相較,東門顯得較為寂靜。最早的雕刻時光、萬聖書園坐落在胡同裡。「雕刻時光」是一位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台灣學生所開設的咖啡館,經常可見西方留學生或是談論著人文藝術的人們。萬聖書園則是當時北大附近幾家人文取向的書店之一,據說那幾家書店老闆都有意打造出台北誠品的風格。除了咖啡館與書店,當時東門還有家影音光碟店,那裡以藝術電影為主,從侯孝賢、楊德昌、王家衛到大島渚、阿巴斯一應俱全。
我的生活重心幾乎都在北京大學所在的北京西北角。如果要我說當時對北京的總體印象,那大致是施工中的大樓、農民工簡陋的宿舍、日夜不停的施工聲、一三○○cc的紅色夏利計程車、許多以白色噴漆寫上「拆」字的低矮樓房......,北京的一切都在現在進行式的變動中。
一個親身所見的有趣例子是北京電影學院附近的酒吧。當時酒吧是大學附近的次文化空間之一,這些酒吧經常放映電影,北京電影學院附近的黃亭子酒吧便是據點之一。猶記有陣子沒去,隔一段時間再次造訪卻未能尋得,問了書報攤老闆,這位老闆不無幽默地用手指一指說:「就在那兒。」。他所說的「那兒」,早已是黃土一片。可以想見,黃土上面日後大概會成為大樓。
二○○六年在大陸引起轟動的電影《瘋狂的石頭》的劇情相當切合大陸的現實,整個故事從房地產廠商垂涎一家經營不善的國有工廠開始。土地即資本,特別是在北京這樣的大陸都中更是寸土寸金。然而,錢堆起來的大樓卻也嚴酷地考驗著城市中人們的生存能力。
北京的計程車司機就是一個例子。他們曾像是北京的地景一樣,有很多故事與特色。特色之一是他們喜歡和車上乘客無所不聊,然而故事卻有些寂寥。在計畫經濟體制之下,一般人能領多少物資都有規定,有錢也無法買到物資,除非擁有外匯券。外匯券是供外賓購物使用的憑據,可到特定商店消費,不受計畫經濟的約束。計程車司機因有較多機會接觸外賓,也因此有機會與外賓以種種方式交換外匯券。當時,計程車司機不僅收入豐而且社會地位也高,甚至未婚的女性也將計程車司機視為理想的結婚對象。
然而,隨著市場化,外匯券制度取消,外加計程車數量也迅速增加中,計程車司機不再是一個昔日的高檔職業。幾年前搭乘計程車經過一棟新開盤的大樓,計程車司機憤怒地說:「現在房價這麼貴,誰買得起?」記得從那一陣子開始,注意到過去愛跟乘客說話的司機們都逐漸沉默了,有些甚至在照後鏡掛上毛澤東的肖像,對他們來說,毛是社會平等的象徵。計程車司機越來越沉默,不過,他們依舊在城市中生活著。
隨著北京大樓與各項公共建築的興建,大量的民工們成為城市一景,然而,當這些建築萬丈高樓平地起之後,他們的身影也消逝在城市的視線中。
□ 中國ing
北京的發展腳步總是不停歇,北京大學附近的空間就是一個象徵。北京大學西門那些狹小的街道與酒吧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學生宿舍;北大東門的胡同也早已拆除,雕刻時光已經在北京有幾家風格相同的分店、萬聖書園在東門附近另覓地點,除了書店之外,旁邊的咖啡館也成為另一種文人討論議題的公共空間。
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附近的五道口,原本就是留學生的聚集地,百貨商場、咖啡館、酒吧的進駐,使得五道口也成為觀光客前往的北京一景。新東方再也不是四環邊上老舊的建築,而是另遷他處,而建築則是亮麗高聳的典型辦公樓形式。
二○○五年五月,連戰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訪問大陸,國共鬥爭乃至冷戰時期的對峙仿如昨日幻局。一時之間,大陸媒體盡是連戰風采,就連北大附近餐廳的老闆也在忙碌之餘,專心盯著電視機看連戰的演講。
二○○五年秋到二○○七年夏,在巴黎生活。其間也曾短期回北京。彼時的北京,又是另一種風貌,銀行裡大排長龍的人群,只為基金開戶。這時的大陸股市也攀上高峰,股市的漲幅直牽動人心。尾隨資金活絡而來的,是房地產的飆漲以及賣方市場主導的買房熱潮。然而,股市、基金的熱潮很快隨著牛市、熊市的快速翻轉告終,儘管如此,大陸的股市仍被長期看好。資金的熱絡,標示城市人的生活標準又再一次波動,城市人又再一次地問自己:我的生活到底是在哪個級別?物質化的指標成為社會的主流標準,所謂的人文藝術已被排擠到邊緣的位置。
二○○七年的秋天,我站在傳播系講台上,開始我教職生涯的第一堂課。我所面對的學生是媒體口中的「八○後」甚至是「九○後」,在他們身上可以清楚看到時代變化的刻痕。他們成長於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在媒介環境變遷之下,他們在電視節目、流行文學、流行音樂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他們有自己的意見,曾有西方人說,大陸的八○後是generation why。”Why”的背後則是代際文化政治的再現。這些why也讓我嘗試進入不同的研究領域。
二○○八年台灣再次政黨輪替,大陸觀光客來台與兩岸直航改變了既有的兩岸關係模式。兩岸關係從專家學者口中的複雜言說,轉變為一般人日常生活都可感知的現象。總之,面對進行式的中國以及兩岸關係,作為觀察者很難停下腳步歇息,這本書也僅是一個小小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