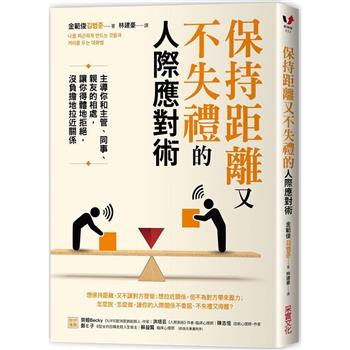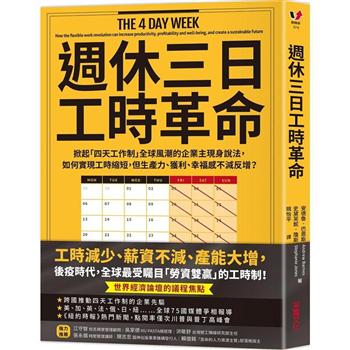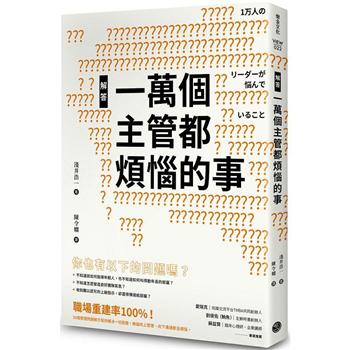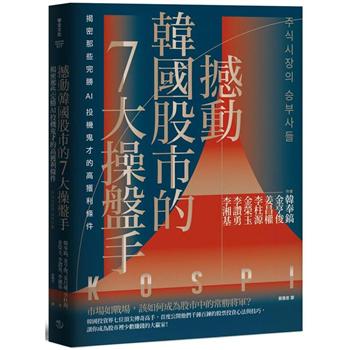『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古典音樂家之一』
葛蘭‧顧爾德(Glenn Gould,1932-1982)
──怪異的天才,隱居、固執、一個慮病的炫技者
一九六四年放棄演奏舞台,顧爾德轉而投身多種媒體:錄音、廣播、電視台和平面媒體。五十歲時,他英年驟逝,震驚了全世界,但他的音樂與遺作持續帶給世界許多啟發。
哲學家暨評論家馬克‧肯威爾把顧爾德視為一位新銳的思想家,顧爾德對音樂的想法影響了自己的一生。有趣的是,這些思想往往自相矛盾、惡作劇的、極盡挑釁之能事。
顧爾德在一九五五年版的《郭德堡變奏曲》專輯錄製過程中先錄了二十一次,最後才決定開頭的詠嘆調如何詮釋,肯威爾依法炮製,為顧爾德的生命提出二十一段詮釋。每一段詮釋都為這位音樂家提出一個不同的觀察向度,以及每一段,肯威爾都細膩地撫觸了顧爾德其精彩一生中所有和諧與不和諧的交錯狀態。
◎本書特色
1.哲學家VS.音樂家,細膩且邏輯的觀察。
顧爾德不只能把鋼琴演奏地很棒或很不同而已。顧爾德是音樂界的哲學家,他的音樂理念統御了整個人生。作者馬克‧肯威爾(Mark Kingwell)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家,他找到一個角度重新刻畫我們習以為常的葛蘭‧顧爾德,他筆下的顧爾德、不管是因著聲音或靜默,都是一位能夠帶領我們認識自己的非凡人物──卓然,更甚以往。
2.探索音樂上的尖銳課題,直搗傳統的哲學領域。
顧爾德的一生,活在音樂之中,也是透過音樂而存在,許多音樂上的艱深課題始終縈繞在顧爾德腦海裡:音樂到底是屬於物質性還是非物質性?我們所聽到的音樂是一串揭露內在結構的序列、還是一道經過協調過後的時刻之流(stream of moments)?在音樂的表象與實相之間是否存在著什麼差異?以及現場演奏是否在倫理上優於唱片專輯,或者反之為真?他甚至提出了一些更尖銳的問題,直搗傳統的哲學領域。
3.顧爾德音樂人生的二十一個主題:天才、演奏、寂靜、意識……
本書不採用慣常的單線直敘法介紹顧爾德,而嘗試以「21」這個別具意義的章節數,展開對顧爾德萬花筒式的觀點,書中透過顧爾德音樂人生中最感興趣、最具爭議、充滿深意的主題:關於天才、時間、孤寂、演奏、寂靜、意識……等許多大哉問的命題,與讀者進行對話。
據說,寫這本書時,作者也曾易稿多達二十一次,每一篇書稿都呈現出一個不同的顧爾德。
作者簡介:
馬克・肯威爾(Mark Kingwell)
哲學家暨評論家馬克‧肯威爾是十五本書的作者,包括暢銷加拿大的《更好的生活》(Better Lining)、《我們想望的世界》(The World We Want)及最新出版的《獵捕與釋放》(Catch and Release)、《具體的幻想》(Concrete Reveries)。
目前肯威爾於多倫多大學哲學系擔任教授,並為《哈潑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的特約編輯,常在《皇后季刊》(Queen’s Quarterly)、《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等媒體發表專文。其中《具體的幻想》(Concrete Reveries)獲二○○八年作家信託(Writers’ Trust)非小說類獎提名。
【曾獲】
一九九六年政論類的史匹茲獎斯皮茨獎(Spitz Prize)
二○○二年國家雜誌獎(National Magazine Award)的論文獎。
譯者簡介:
劉宴伶
台灣大學政治系、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所畢業。興趣寫作、翻譯,曾任雜誌編譯、駐外記者、專欄作家,具筆譯、口譯專業經驗,譯作散見雜誌期刊。關注議題廣泛,時尚、藝術、宗教、人文、歷史等;亦為顧爾德資深樂迷,著有《柏林灰色》、《漢撒橘色》等書,譯作《驚豔顧爾德》。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哲學家的音樂萬花筒
焦元溥
(《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談錄》作者、資深專欄作家資深專欄作家、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候選人)
指揮家、作曲家薩羅年(Esa-Pekka Salonen)當年至義大利進修作曲時,指導老師卡斯提吉歐尼(Niccolò Castiglioni)交給他一首自己的創作,要薩羅年就此曲作分析研究。「那是很複雜的曲子」,薩羅年回憶,「拿來一看實在看不出什麼脈絡。我花了好多好多時間,才從那些錯縱複雜的音型結構中看出一點端倪。」
那一個星期,薩羅年哪也沒去,關在房間對著樂曲來回思索,終於讓他整理出樂曲內在的規律邏輯。隨著花得功夫愈來愈多,他所看出的細節也愈來愈豐富,自信心也愈來愈強。當他把論文寫好並和老師報告時,他確信自己已經完全分析出卡斯提吉歐尼的作曲意圖與寫作手法,作品的大小結構皆被他整理地清楚分明。
「真是非常感謝,你一定花了很多時間,才能整理出這樣詳盡的分析。」帶著微笑,卡斯提吉歐尼看著眼前的芬蘭學生,「但是,身為這首曲子的作者,我必須誠實告訴你──這其實是我亂寫的,樂曲根本沒有任何邏輯脈絡可言。」
不用說,薩羅年當下自然覺得被耍了,而且極其憤怒:「早知如此,那個禮拜我大可以出去遊玩,好好享受義大利的陽光呀!」但轉念一想,他明白這是老師給他的震撼教育:「一、再怎麼沒道理的作品,分析者還是可以自己整理出一套道理;二、無論整理出什麼道理,真相可能永遠和自己的分析相異,甚至相反。別以為自己做了苦工,所得到的就會是正確答案。」
以此來看鋼琴家顧爾德(Glenn Gould),以及關於顧爾德的種種討論與著作,一樣可以成立。
作為一位具有高知名度、高話題性、甚至高爭議性,又留下數量龐大的錄音、演講、文字、影像的藝術家,顧爾德比二十世紀任何一位樂器演奏者都能成為討論焦點。關於他的種種論述,數量既超越他喜愛的鋼琴家李希特(Sviatoslav Richter),也勝過他所討厭的霍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因此,一如卡斯提吉歐尼那首音符堆滿譜面的樂曲,只要有心整理,無論真相為何,關於顧爾德的一切,我們必能提出一套詮釋脈絡來解釋他的思想、行為以及藝術。光是顧爾德的說話,就有論者分析出其「腔調的子音、尤其是t跟d,會發得非常簡短——事實上這種風格乃是源自於顧爾德彈奏中對協和音所採取的清澈而精準的處理手法。」如果顧爾德的語調能和他的音樂彼此聯結,那麼進一步,論者更推導出他「思慮上的雜音可以透過不斷搜尋正確單字或精美複合句而獲得規範,而這其實就是他對音樂、對彈奏的想法。」
這樣的解釋是言之成理,還是自作多情?我們不妨再來看另一個例子。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集《臺北人》是家喻戶曉的經典,也因故事和時代密切連結,再加上頻繁出現的隱射比喻,讓無數讀者學者投身考證。比方說「永遠的尹雪艷」,故事中那死神化身的女主角,是否真有其人?「尹雪艷」之名又從何而來?「玉帶林中掛、金釵雪裡埋」,如果《紅樓夢》中的「薛」寶釵是如「雪」千金,那麼「尹」會不會是「隱」的暗喻,「尹雪艷」就是「隱冷豔」?
在演講裡,白先勇給了讓人錯愕的回答:會想到用「尹」,其實是因為字型美麗,特別是尹字最後一筆獨具性格。
有了作者現身說法,「尹雪艷」命名之謎應該有了解答吧?但「尹」字之發音若不是「隱」,即使字型再美,白先勇是否仍會選擇「尹」呢?即使作者本人未曾如是思考,或主觀上想的是另一回事,誰又知道他潛意識裡不曾如此想過?當卡斯提吉歐尼自以為隨興,在譜紙上亂寫,他又怎能確定,自己的「亂寫」其實不曾暗藏某種連他也無法察覺的內在規律?或許當他「亂寫」十首樂曲,在那些「塗鴉」中就會浮現一致的安排體系——不然,佛洛伊德那部《夢的解析》又如何而來?
這是所有顧爾德論述,其實也是所有討論音樂家、藝術家論述,最令人苦惱,卻也最趣味橫生之處。在音樂範圍中,我們永遠可以相對安全地討論某位音樂家如何詮釋某部作品。甚至,我們也可以整理某位演奏家的詮釋習慣,從相同或相似的處理方式中歸納其音樂觀點。然而一旦我們走出音樂,走出作品,而試圖歸納一位音樂家的完整思考,對其行為提出全面性的合理化解釋,我們就像當年拿到樂曲的薩羅年,可以用盡心血,卻永遠不能保證結論正確,甚至根本不知道結論是否存在。
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哲學家、評論家馬克・肯威爾(Mark Kingwell)寫作《顧爾德:琴鍵上的祕密》時,他絕對意識到自己正像面對樂曲的薩羅年,而這首「樂曲」之錯綜複雜,又超過卡斯提吉歐尼的譜頁何止百倍。真的能夠整理出一個全面的合理化解釋嗎?——或許他曾這樣問自己,甚至——就算真有這樣的解釋,如此解釋出來的顧爾德,還是會是那個讓人迷戀又困惑的顧爾德嗎?
於是,他選擇讓筆尖在段落中遊戲。二十一個篇章所呈現的,是絢爛豐富的萬花筒。他保留邏輯與悖論,可解與不可解。萬花筒每一轉都是顧爾德,而你絕對不會從中只得到「一個」顧爾德。這也正呼應他在序言中對顧爾德的理解:「他一次又一次從不同的領域、不同的重心去探索生命可以到達什麼程度,尋找著那個被遮蔽、難以捕捉、到最後似乎根本不存在的正當。那個被選取的版本,永遠都只是眾多版本當中的一個。」
而在所有文字遊戲與思考辯證之後,我們仍能從肯威爾的文字中感受到,顧爾德的音樂如何感動了他。那是他寫作本書的動力,照射萬花筒的陽光,也是超越一切哲學討論,顧爾德的終極魅力。
顏序
《打破傳統彈奏風格的鋼琴家》
小時候彈巴哈的小品,是因為鋼琴老師指定;高中時期彈巴哈的〈創意曲〉,是為了大學入學術科考試;就讀音樂系時彈巴哈《十二平均律》,是因期末考規定,而且教授說這是「鋼琴曲目的舊約聖經」,非學不可。真正親近巴哈,是在德國留學期間,從管風琴音樂、清唱劇、宗教音樂到布蘭登堡協奏曲...;而愛上《郭德堡變奏曲》,則是回國任教,講授西洋音樂史時。課堂上為了引起學生興趣,除了講解《郭德堡變奏曲》委託人凱瑟林大公(Count Keyserlingk)的失眠故事外,我找了不同版本的唱片,包括李希特(Karl Richter)的大鍵琴版和席夫(András Schiff)、顧爾德(Glenn Gould)的鋼琴版等。授課時間很有限,既要說明巴洛克時期的鍵盤樂器和音樂的演進,又要講解這首名作的變奏曲形式,所以幾乎談不上討論不同演奏者的詮釋問題。但是在準備教學的過程中,我仔細聽了顧爾德的錄音,那種驚艷與感動,可以說是從未有的經驗。
二十世紀約七O年代以前,演奏家著重原音重現的詮釋:作曲家的生活環境社會、時代文藝思潮、作品創作背景、當時的樂器性能、表現法等等。儘管音樂界、觀眾都尊重和容許演奏者有一定的詮釋空間,也就是「再創造」的角色,但是大多數的演奏家在面對大師以及他們的作品樂譜時,都表現的謙卑、低調、謹守分際,樂譜上標示forte (強),他絕不敢彈 piano(弱);速度記號是allegro(快板),他絕不敢彈andante(行板)。絕對音樂應該表現地嚴謹、純粹,演奏家絕不敢使用誇張夢幻的手法。另外,對唱片工業的興起,音樂專業人士雖也肯定唱片的推廣功能,卻更推崇現場音樂會的溫暖人性、臨場感動。因此,在六O、七O年代,不按牌理出牌、過分突顯個人風格、狂言錄音比現場更能展現藝術價值、甚至整個退出演奏舞台的天才鋼琴家顧爾德,被認為是古怪、神經質、荒經怪誕。人們對他的評價可以說是非常的兩極化:他既是音樂家、天才、國寶、名流、偶像,也是怪喀、隱士、丑角、憂鬱症者、人格分裂者...。他在1982年驟逝,享年不過五十,對他的懷念、討論、爭辯、研究卻如雨後春筍,喜愛他音樂的愛樂者,更是遍及世界各地,絲毫沒有因為他的過往而消退。
這幾年我在博士班開設了「音樂理論與實際」(Performance Practice)的課程,與研究生一起探討近年來國際音樂界對「演出實踐」各方面的見解,發現在觀念上已有很大的發展與改變。音樂學者對音樂史的探討、書寫,已經將演奏家的地位大大的提升;對經典名作的「忠於原典演出」的論點,在過去的二十年來如火如荼的展開辯論,認為:文本(樂譜)無法百分百代表原作者的本意,而原作者自己在演出同一作品時,也會因時空背景改變而有差異,因此沒有所謂「真正忠實原典」的詮釋典範;而且,音樂的真正呈現在於人們聽得到的演奏實踐,演奏者可以用他覺得最自然、最好的方式演出,如此才能感動聽眾。被稱為「演奏家時代」的十九世紀,大師級的演奏家之間風格差異極大,這也是當時愛樂者的期待;二十世紀,唱片工業發達以來,雖然演奏技巧更加精進、傑出音樂家輩出,但是演奏風格卻互相學習模仿、差異日漸縮小,令人不無遺憾。在這樣的發展中,顧爾德的堅持與獨特,能獲得廣大愛樂者的青睞,也就不足為奇了!
顧爾德離世以來,已經有為數不少的傳記和相關出版品。馬克・肯威爾(Mark Kingwell)撰寫的這本書,並不是傳統的生平記載,而是更深一層的音樂哲學論述。和顧爾德一樣,肯威爾也是加拿大人,他更是一位博學多聞、深諳音樂藝術的哲學家,本書的二十一章,每章都用一個簡短的名詞當作主題:詠歎調(Aria)、寂靜(Silence)、虛構(Fiction)、記憶(Memory)、存在(Existence)、天才(Genius)、夸德力貝(Quadlibet)......,這些標題看起來就很哲學,的確,內容也很哲學。但是,請讀者不用擔心,作者雖到處引經據典,卻不賣弄學問;而且他的筆觸單純流暢、娓娓道來,沒有看不懂的憂慮。對顧爾德這位走在時代尖端的曠世天才,他不是要繼續歌功頌德,而是要從主人翁一生中的作為、言論、思想、演奏,甚至從他的廣播人角色、加拿大人本色、自相矛盾、反社交態度等等,去探討各種問題,例如音樂藝術的本質、天才的意涵、音樂的存在問題、音樂會的社會角色等等,像彈鋼琴的過程涉及了心智活動:視譜的視覺心智(eye-mind)傳達、奏出聲響的手指心智(finger-mind)輸出,延展到空間與時間的心智表現等。
本書內容有許多精采的討論,作者常常提出一連串的問號,然後一一抽絲剝繭,有如在一片陰沉的黑幕中,曙光般的逐漸明亮起來,問題也迎刃而解。舉第六章「天才」為例,作者提出了「天才」(Genius)與「天賦者」(Talent)的區別和合而為一的概念,然後,他引述了名家如羅威爾(J. R. Lowell)、王爾德(O. Wilde)、愛默生(R. W. Emerson)、米爾(J. S. Mill)、康德(I. Kant)等人的看法,再回到顧爾德是不是天才的問題,真的是精采絕倫。而顧爾德對現代音樂的態度,涉及了「傳統」與「前衛」,「保守」與「進步」的概念與鬥爭:
新的潮流自動常被假定是優於舊的流派......於是布烈茲宣稱「荀伯格已死」的不久後,自己也成為「時代精神(Zeitgeist)的受害者。...在同樣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替代邏輯之下,如今換布烈茲被史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或約翰‧凱吉(John Cage)所取代了。......
肯威爾的論述就是能從顧爾德身上再延展出去,讓讀者享受更多議題的討論和思考。
本書的翻譯委實不易,因為內容涉及很廣,橫跨音樂、美術、文學、歷史、哲學、美學等領域,援引之文獻又遠溯希臘古典、近取現代科技,且各種專門術語隨處登場。而這些,竟然都難不倒譯者劉宴伶,連哲學性的邏輯思辯,他都翻譯的遊刃有餘;除此之外,譯者亦能適時為讀者做一些註解,特別是較罕見的專門術語,多能體貼的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加以解說,增加閱讀的理解與樂趣。其文筆之流暢,毫無譯著中難以避免的牽強拗口,是我多年來閱讀的譯著中,非常少數的優秀譯作,值得一讀再讀。
顏綠芬 2010年3月31日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音樂學博士/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
名人推薦:哲學家的音樂萬花筒
焦元溥
(《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談錄》作者、資深專欄作家資深專欄作家、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候選人)
指揮家、作曲家薩羅年(Esa-Pekka Salonen)當年至義大利進修作曲時,指導老師卡斯提吉歐尼(Niccolò Castiglioni)交給他一首自己的創作,要薩羅年就此曲作分析研究。「那是很複雜的曲子」,薩羅年回憶,「拿來一看實在看不出什麼脈絡。我花了好多好多時間,才從那些錯縱複雜的音型結構中看出一點端倪。」
那一個星期,薩羅年哪也沒去,關在房間對著樂曲來回思...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詠歎調
那聲音:聽起來急驟、精準、自鳴得意,帶點炫耀浮誇。
皺巴巴的旁白裡,充斥了不甚高明的解說企圖,就像個太常講述內容一模一樣的學者,永遠在同一個段落強化同一個重音、插入同一個典故,由於實在講過太多回了,聽起來是這麼地迂腐油亮。那聲音也是戲謔的,帶有娛樂效果、慧黠、迴腸盪氣、兼惡作劇。它深切地投入其中,但並不閃爍其辭或自我耽溺。講述者自問自答,津津有味地咀嚼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一系列的問題當中,還會出現連講述者自己都覺得可怕或嚇人的問題。
他的語句結構俐落,段段精實,令人信服之餘,也帶有建築氣質。這是葛蘭‧顧爾德話語中的音樂性,這個來自半世紀前加拿大文化菁英的腔調,如今卻幾乎可以從全加拿大人口中聽到;這種音調混合了刻意平抑但又相當響亮的音位,它已經變成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加拿大外交部、加拿大學術界人士的招牌腔調。這種腔調的子音、尤其是t跟d,
頁二
會發得非常簡短—事實上這種風格乃是源自於顧爾德彈奏中對協和音所採取的清澈而精準的處理手法1。顧爾德措辭中挾帶為數龐大的罕見單字:隨興所至、圍繞同一主題、並常常擺在從屬子句裡頭,這些單字有些太過音樂專業,有些太過矯揉造作。一系列如繞口令般的單字大多為一個半音節的詞彙。
對葛蘭‧顧爾德而言,話語的結構跟思考的結構是互為從屬的,思慮上的雜音可以透過不斷搜尋正確單字或精美複合句而獲得規範。這套信念放諸顧爾德冗長、無限蔓延的文章寫作中,也是適用的。最重要的是,這其實就是他對音樂、對彈奏的想法。不但如此,葛蘭‧顧爾德會去整理出音樂當中的結構、去找出一首曲子的基架,反映到他的詮釋裡頭,有時候會被貶抑成「散漫」,因為對傳統的學院標準而言,這種作法太不尊重曲式了。其實不然,這種作法充其量是「新穎」,而不是「散漫」—或許就一首曲子的多數觀點而言,聽起來可能是散漫,但其實它的內涵一點也不散漫。就像他談話中的音樂性、他談話的格式、內容,沒有一樣是散漫的。
「機遇的」(aleatoric)這個字意指受到即興或偶然所影響的音樂主題。該詞源於拉丁字的alea,意思是骰子,骰子當然就是一個讓機率隨機出現的小方塊。「機遇」一語在一九五0年代被引入音樂理論中,指涉一系列如法國作曲家皮耶‧布烈茲(Pierre Boulez)、德國作曲家史托克豪森(Pierre Boulez)等人的音樂,
頁三
不過它其實可以擴充泛指一些更早之前、樂曲結構更龐大、但當中帶有隨機元素的音樂。以記憶力和技巧面著稱於世的葛蘭‧顧爾德,一般通常不太把他跟即興音樂或那些前衛作曲大師聯想在一起;但要理解他的音樂、也就是他的思想,卻不得不把線索導入機遇音樂。因為顧爾德不僅是在演奏音樂罷了,他根本就是以即興的理念在彈奏。他要把一首早被寫定完成的曲子,演奏成讓聽眾聽起來感覺像是他當場即席譜寫出來的一樣。
要達到這樣的效果,需要對自我以及他所能支配的小世界施展異常精湛的控制和自律。
「對我來說,面對現場觀眾是一個浩大的負荷。」在一九六八年發行的一張唱片當中,顧爾德這麼對訪談者說道。這段特別強調的語句,道出顧爾德在稍早四年之前決定退出演奏舞台背後的真正理由。
首先,我厭憎現場演奏的「一次性」、那種「沒有第二次」可來的處境。老實說我都還記得起來,在很多場的北美巡迴演奏當中,我有許多次的演出都是不太理想、甚至是非常混亂的;或許是我還練習地不夠,或因為我會錯覺我是在跟自己的唱片版本互相較勁、如果當時那首曲的唱片已經問世的話
頁四
—重點是通常我都覺得唱片版已經存在了!—然後如果我這麼認為,那麼連我事前要去練習這首曲子時都會糟透了,事實上是這樣子。而如果一場演奏是那種情況,我就會超想停演的—講到這裡,我相信精神科醫師大概又有好些長篇大論可以借題發揮了,『第二錄!』但一個演奏人在沒有傳出醜聞或招致惡劣樂評等風險的情況下是沒有理由可以辭演的,所以我也從沒正式宣告過。不過我一直很想這麼做2。
這時唱片裡的訪談者慫恿道:「有何不可?當然現今的演奏圈文化是沒有聽說過這樣的案例,但一位藝術家本來就有權力去決定這樣的事情。」顧爾德笑了一笑。兩人都有默契,對當年退出舞台的事件並不是很介意。他的回答也很妙:「要是真那麼做,我看光是議題效應就跟回到舞台沒什麼兩樣了。」下一個問題。
一九八二年,葛蘭‧顧爾德死的那一年,我十九歲,當時我從來沒親眼見過他或聽過他的任何一張專輯—關於從沒聽過他專輯這一點,完全不是因為我在那個年紀聽的多半都是衝擊合唱團(The Clash)和艾維斯‧卡斯提洛(Elvis Costello),而不是巴哈或貝多芬。跟大多數人一樣,我只從他的演奏專輯和他發表過的文章聽說過他—如果「聽說過」這個字眼是合適的說法的話。但自從顧爾德死後,音樂界、或說體驗著音樂的這世界,
頁五
卻見證了許多重大的改變。其中一個最大的改變就是聽取音樂變得很容易,這也帶來相關的後續效應,包括世界各地的音樂製作也變得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這兩項重大改變都是顧爾德會樂於迎接的:前者應允了顧爾德長久以來一直主張「錄製的音樂比現場演奏是更細緻、卓越」的觀點,後者則成功推翻音樂的「進步史觀」,也就是依特定的風格或曲風去認定音樂史上的種種流派和樂期是有先後繼承關係的。當前這個世界—我們或可稱之為「後歷史(post-historical)的音樂世界」—是當初顧爾德所預見並鼓吹的。然而值此同時,顧爾德卻也常常自稱是藝術界的清教徒,並不時哀悼音樂界的重商沈淪。走筆至此,類似這樣的悖論,只是他種種矛盾、激昂、如萬花筒般的敏銳頭腦的開端而已。
音樂家。藝術家。天才。怪喀。國寶。名流。藥罐子。憂鬱症患者。隱士。偶像。清教徒。北方人。丑角。葛蘭‧顧爾德的一生,是一個反覆被傳頌、版本很多種的故事,也是一段精彩絕倫的故事。在每一個版本中,故事都不免帶有「這是一個你一定要知道的人」、一些傳奇噱訛的色彩、和傳統人物傳記的敘述。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裡由不必再重複做這些事。人物傳記中的虛構性,恰恰就是顧爾德喜歡玩弄的一點小危險。因為除了玩弄鍵盤之外,
頁六
他也喜歡在一些原本應該很正經八百的文章中,假扮成不同人稱、自問自答,或以一些很富於幻想的筆名雅號來杜撰一些虛擬的評論,甚至會在錄音間裡、在廣播節目中、在電視上穿起道具戲服、裝腔作勢地扮成特定角色、瞎鬧一番。當年他決定退出演奏舞台,搞得自己聲名狼籍—但這一步,卻是他視為錄製更好的音樂、散播真正好的詮釋的一大步,而不是死守著一小套曲目,在演奏會中反覆彈奏—當然這一步也從此將他帶出公眾場合之外,自此為他蒙上一層謎樣般的神秘色彩。在那之後,他除了透過音樂專輯和著作出版品之外,就不再讓自己現身了。
所以呢,少了一個葛蘭‧顧爾德,大眾媒體就開始製造一個具有多重面貌的顧爾德幽靈,用以繼承這個話題,但這些報導全都是片面而且誇大不實的。在這股熱潮背後,除卻龐大的商業利益不談,它還衍生出其他的藝文效應,包括在不同的文化場景中,顧爾德依然是個威力十足的人物。例如在顧爾德之後,每一輩的演奏者都必須面臨他在演奏上所樹立的超高標竿。每一世代的聽眾,也都必須去妥協於他說「錄音優於演奏」的音樂觀點。他停止演出的那一段時期,媒體領域的學說正由麥克魯漢的言論所引導,相關論戰從此如火如荼展開。這個情況或許曾讓後來的評論家和樂迷們一度覺得誤信了顧爾德、甚至對顧爾德產生荒謬的期待,但就算如此,那也都是因為,他、是、顧、爾、德—一個超前時代的人,一個已經為我們完成艱困的拓荒思想及先鋒洞見的人。
頁七
事實上,要為這些繁殖不停、增生不已的傳說軼聞和矛盾說法敲定一個最終的真確版本,似乎是不可能的—不同時期的顧爾德、各種形象的顧爾德,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也因此,任何想要將這些多元面貌的顧爾德提煉成一個形象統合的個體,這樣的企圖往往在一開始就注定是錯謬的,茲舉一例,就像某個作者所寫道的,「一個人的一生,可以被濃縮成幾百頁的文字—就像自家釀造的果汁醋被裝在瓶子裡一樣。」3
然而,若真要理解顧爾德這個人的話,我們要考量的恐怕並非只是這些常見的貶抑之聲,而是有其他更多足以使無數的傳記版本都相形失效的思考點。顧爾德的一生,既活在音樂之中,也是透過音樂而存在,這顯示這一個完整的個體,他並不只是一個經由外界報導而被型塑出來的人物;他也是一個從內在世界所伸展出來的角色。外界所賦予的描繪,只是為某人的一生做出一種合理的敘述,甚或只是一種順理成章的解釋。我意思是說,在最能有效代表顧爾德的那個形象中,反而似乎是含藏著「獨立個體」這樣的概念,唯有這個概念能去解說他那晦不透光的天賦,以及種種顯露在外的詭異氣質不過是這份天賦的外在表徵而已。人們持續不放棄地想要描述顧爾德,我們也看到種種說詞版本依舊競相推出。
越是艱深難懂的事情,它反而越是尋常易解的,幻象就是那個由內到外的延展:首先是那個讓我們得以將種種知覺意識灌注到單一個體的這個虛擬角色,隨後是針對這個個體存有以及相續性格的種種投射。
頁八
在這兩種虛構之下,生命被詮釋為線性的,因為生命被假定成應該如此這般地活著,這兩種虛構相互依存並彼此強化。不過這也意味著,它們是同時存滅的。所有自內而外的那份虛構,如果經驗了任何動搖,這些動搖也將悉數傳遞給那個由外向內的投射。所有被規範成線性敘事的顧爾德,都是失真、失去線索的顧爾德。
葛蘭‧顧爾德對於這些幻象的操弄是非常清楚的,他一邊在音樂中找尋前進線,卻也一邊在生命中顛覆發展線。事實上,我們或許可以將他在音樂上的追尋,視為他自覺生命缺乏發展線的結果,某種對於生命的偶然與意外所抱持的一份悲劇感的覺照。從顧爾德表述的、和在媒體上所呈現的種種觀點看來,似乎是指向這樣的複合哲學,雖然他不曾在任何地方明確表達過這樣的立場—說不定這又是出自於他的精明直覺,知道說把自己過得高潮迭起絕對要比去說去講更有效力、更惹人注目,也有趣多了。
因此,在顧爾德發表過的各式著作中有一個不斷出現的主題(所謂著作,就是他那摻雜直覺和紊亂理論的混合物),亦即,所有主張音樂進步史觀的敘事文獻、一如生命中的線性發展—都是不可信的、甚至是詭詐的。舉例來說,在他早期的專業生涯中一度被認為,他相信一個新傳統(neo-traditional)的觀點放到一個最現代的時機是恰當合宜的,當然每次他這麼被媒體界定時,他又是顯得百般無奈、一副被曲解的樣子。後來,他逐漸對音樂界盛行的所謂流派、運動的界定說法都感到不信賴,都持懷疑態度。
頁九
一開始他將這些論述都當作一時輿論、炒炒新聞罷了,後來,更糟,他把這類文獻視為音樂史這個大磨坊所掉出來的碎屑而已。值此同時,在顧爾德音樂哲學中的統一思想—也是此處我存心看待他作為一個音樂哲學家的核心思想—音樂中唯一一個最重要的面向,是建築,或說是音樂線:亦即一首作品的全觀架構,它是體現在演奏行為的美感中。它非關調式、非關音質、不是音色或音調。這就是為什麼在他的演奏中,發音和斷句會這麼重要—「就像X光照出骨架一樣,」他說;這也是為什麼所有巴哈曲目中所蘊藏的結構彈性和詮釋自由會這麼吸引他、以及他彈起來會如此動人。雖然他本身拒絕「巴哈專家」這樣的標籤,但他演奏巴哈和其他賦格及對位法名家的作品其頻率還是遠高於其他他所錄過的共三十幾位作曲家的作品。
對音樂線的熱愛,也是導致他在彈完都鐸時期大師威廉‧拜爾德(William Byrd)的作品時說道,這帶給他「極大的喜悅」,以及起碼在三次不同的錄音場合時他說道,他「最心愛的作曲家」是奧蘭多‧吉本斯(Orlando Gibbons)—「絕對是我最認同的作曲家,一位已經進入某種我不打算解釋的神秘精神地帶的作曲家。」一九七0年他在接受美國《高傳真》(High Fidelity)雜誌專訪時,顧爾德被要求列出「荒島必聽碟」,他的第一個選擇就是戴勒夥伴聲樂團(Deller Consort)的吉本斯聖歌與讚美詩專輯,
頁十
「因為打從我十幾歲開始,這個音樂(尤其是戴勒夥伴聲樂團的這張專輯,大概有將近十五年的時間以來)就非常非常地感動我,比任何我所能想到的聲音經驗都更加深刻。事實上,這也是我所有的音樂收藏中,唯一一張真的被我聽壞掉三張的作品。」4
拜爾德在鍵盤樂器方面是個多產的作曲家,吉本斯則不是,而顧爾德也只錄了一張專輯來收錄他們的作品—其實還蠻可惜的,因為跟他所有最好的專輯比較起來,這張的水準在智性方面、在情感方面,都有動人且均質的表現。說真的,吉本斯和拜爾德這兩位作曲家,在他那些演奏兼解說的表演場合,搞不好三兩下就可以一言帶過,比起他對莫札特和貝多芬這兩位他宣稱不太喜歡的作曲家身上所耗費的言論,可以說是不足一提,連他在講巴哈的對位法奇才也都是洋洋灑灑、長篇大論的。但吉本斯和拜爾德—「這兩位北方大師」(他這麼稱呼他們;以顧爾德對北方氣候、北方凜冽孤寂的熱愛來看,這麼尊稱要算是極大的讚譽)—展現的是作曲中的純粹性,在典雅的曲式中可見到一個近乎完美的數學結構,儘管這種曲式也預示了隨後在音樂取向上的重大轉變。如同顧爾德所形容的,「從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現代世界的前情,那是一個跟後文藝復興時期迥然不同的風尚與典範。」5
頁十一
顧爾德在拜爾德的《薩靈格圓舞曲》(Sellinger’s Round)中,緊緊尾隨一個較為鬆散而零星出現的降B大調音符—這個作法在都鐸時期的音樂裡是前所未見的,象徵一個新的精神,他認為,這預示了之後現代發展的來臨。他並且主張這兩位都鐸時期的作曲家「是共享了同一種風格,但分屬於不同的氣質」,他覺得吉本斯代表像馬勒(Gustav Mahler)那種的哀婉柔美,而拜爾德則屬於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的茂盛繁榮。兩者並陳所共同體現的,是音樂線之美,就是這個東西讓顧爾德愛上音樂,也是這份摯愛讓顧爾德變成一位音樂家。作為世紀末作曲家的拜爾德和吉本斯,他們倆也佔據了一個時代轉折的時刻—這種時機是顧爾德非常喜歡的,就如同他也很享受自己身處二十世紀末的處境。在他們那個年代,「一種以音調為主的和弦概念正在發展當中,不出幾年,絕大多數的樂曲都會採納這種作法。」如今我們視為理所當然「什麼音調配什麼和弦」這樣的一般通則,是當時這兩位屬於小眾的天才作曲家所預見的。那麼,顧爾德在他自己世紀交替的時刻所預見的,隨後、或者很快地我們是不是也將視為理所當然?在這本書當中,這個問題我將努力去找出答案。
然而,我們所探討的這個問題並不那麼單純,我們得小心處理才行。音樂史和音樂這兩者都是典型的我們稱之為「經驗型構成物」,一種需先被體驗、被經歷,然後才能被組合出來的結構。它們是根據因果時序而被訴說或傳頌的暫時性經驗。可是,不管這些說辭或定義多麼實用、乃至到了必須的地步,這些敘述都是虛幻的。這些敘述的形成基礎,是建立在實際時間的跳躍性選擇上,
頁十二
也就是在真確的浩瀚時間序列裡,這些時刻根本是不可能連續、不可企及的,是以這些敘述都是論者硬強加上去的6。同理,傳記也是一個虛幻的後設文本。這就是為什麼我決定以一連串跟認知、意識、時間、寂靜有關的組合命題來敘說顧爾德故事的原因,一種非故事體裁的故事,從各種角度去看待這些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切片。
法藍可‧吉哈德(François Girard)發表於一九九三年的短片《葛蘭‧顧爾德的三十二個短篇》(Thirty Two Short Films About Glenn Gould)便從許多角度揭示了這位鋼琴家。為什麼是三十二呢?熟悉他專輯的顧爾德迷們馬上知道答案。巴哈的《郭德堡變奏曲》相傳是為德勒斯登的凱薩林伯爵(Count Von Keyserlingk)所作,伯爵有失眠的苦惱,巴哈寫好的作品交由伯爵的宮廷大鍵琴師約翰‧戈禮伯‧郭德堡(Johann Gottlieb Goldberg)演奏,以此作為伯爵的失眠治療,該首變奏曲以一段三十二鍵的詠歎調開啟,往後是一系列在調性上、節奏上與這個主題有關的三十段變奏。至於詠歎調本身,很有可能是巴哈為妻子所作,日期上標著一七二五年,《郭德堡變奏曲》7的尾聲,也重新回到這個詠歎調主題。這首曲不僅在寫曲方面被鄭重公認是主題與變奏的絕佳範例,在彈奏上也始終被歸為鍵盤樂器中最「窮兇惡極」的高難度曲目之一。
詠歎調主題被中間的三十段變奏演繹成各種風貌,從幽微輕柔的顫音到精心策劃的數學解構,通通安排在居間的九首卡農中。
頁十三
這三十二個基礎低音以漸進方式開展出輕柔的詠歎調,並不是女高音唱的那種悽愴旋律,這使得它成為一首出色的胡吉洛(ruggiero),胡吉洛有點接近巴哈也常寫的夏康舞曲(chaconne)或帕薩卡里亞(passacaglia),只是在樂曲進展中是採取不規律的轉位(inversion)—如同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所註解的,「這使得透過明暗對比法(chiaroscuro)來呈現帕薩卡里亞變得可行。」所以開頭的詠歎調、加上曲終的主題重複,中間再放入三十段變奏,就構成了擁有三十二樂段的《郭德堡變奏曲》:即「主題—變奏—主題」的樣式。顧爾德自己寫到,「這是史上最精湛的基礎低音傑作。」8(《葛蘭‧顧爾德的三十二個短篇》片中,三十二個短篇雖然沒有全然模仿《郭德堡變奏曲》的樂曲結構;但以傳記片而言,該片的段落處理依然不失為一個出色的安排。)
眾所皆知的,顧爾德前後錄過兩次《郭德堡變奏曲》。第一次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十號到十六號之間,在哥倫比亞唱片公司位於紐約三十街的錄音室;專輯甫發行便立刻獲得全世界的喝采,奠定他本來就在快速躍升中的演奏地位。第二次是一九八一年四月到五月間,剛好就在原來錄音室因毀損而被輿論嚴厲抨擊的時候,也恰好是他滿五十歲生日的前一年、也就是他過世的前一年。這兩個版本都被多番地比較過。或許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來說明兩者之間的差異,那就是一九五五年的版本是出自一個年輕人之手,而一九八一年的版本則是來自於一位成熟的音樂家。第一張版本是傲慢的、幾乎是乳臭未乾,以令人讚嘆的高速飆過,挾以讓人不寒而慄的堅實技巧,整體的調性雖然優異輝煌,但聽起來總覺得少了一點感染力。第二個版本,之所以會被錄製,
頁十四
是因為顧爾德宣稱他要重新找尋這首曲的音樂線,所以第二張的速度放慢了、情感溫暖了、甚至帶有點輓歌意味;在呈現自由速度(rubato)和表現鋼琴的聲勢幅度時,基礎低音的出現也更為明淨清晰。而演奏者的招牌「哼唱」在這裡也變成一種鋼琴擊鍵的和聲對位旋律,而且他這個哼唱不是普通的大聲,是清楚到連劣質的播放設備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達到人琴合一的演奏境界。
回想起來,也許透過這首音樂,我們會很想去了解一些事情也說不定。每一個人比較喜歡哪個版本,這是品味問題,或者個性、年齡因素。有時候是隨著一天當中的不同時刻,我們也可能喜歡聽不同的版本。
一九五五年這一次的早期錄音經驗中,顧爾德可以說是卯足全勁到達掙扎的地步—不是技巧面的問題,而是奮力要找出那個符合他對整首曲子其音樂邏輯的最適版本,往後這也是他在錄音時常常會進入的苛求狀態。紐約那批哥倫比亞唱片公司錄音室的錄音師們—後來偶爾會對媒體爆料一些關於這位加拿大年輕鋼琴家的種種怪異行徑,例如他演奏前按例要把雙手浸到熱水裡的「浸泡儀式」、他那罕見的駝背姿勢、他對北極牌(Polar)礦泉水的偏執癖好、只吃竹芋餅乾裹腹等等,當然這些都是誇大其辭—當時他們都立刻對他的完美主義感到印象深刻,但也深感挫折。顧爾德在錄音室裡的這份頑固倔強,日後會成為他一生的標誌形象,某種意義上也帶來毀滅的影響。
頁十五
至於那些怪異行徑呢,當然是立刻成為公關部門所選取的八卦飼料: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哥倫比亞唱片公司便狡獪地發佈新聞稿,摘要這位年輕明星的「種種儀式、小怪癖、討人喜歡的小動作」,還包括裝著不同藥錠的藥罐子、二十分鐘的熱水浸泡等等。以及被形容成「最讓人感到『郭德堡』(鄉巴佬)的」,是那張帶有四支可調整椅腳的折疊式琴椅:「一直到正式開錄前,錄音室裡的這批懷疑論者(譯按:即錄音師們)以為這是所有怪異舉徑的最高級。萬萬沒想到,他們看見葛蘭在進入變奏曲中他那頗為精湛的交叉彈奏段落,竟然順勢調整了其中一隻太高的椅腳。」9
在顧爾德為這張唱片所寫的封套解說裡(這是他最早的重要著作),他提出以下非凡而真摯的見解:
透過技術面的檢視,我們已經觀察到,這首曲開頭的詠歎調跟它往後的變奏段其實是很不相容的,關鍵的低音線以其完美的輪廓加上和弦的佈局,開拓出驚人的進展,並遏止傳統上的帕薩卡里亞走上一個厚重漸增的方向。以及透過分析,我們也已經觀察到,詠歎調的主題內容宣示了一個分設且獨立的規範,這使得每一段變奏的設計與安排都是獨斷獨行的,因為這層緣故,導致後續的變奏樂段沒有一個是運用雷同的原則下去譜作的,也不會看到那種高原堆砌的景象,
頁十六
這跟貝多芬或布拉姆斯等人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寫出來的變奏曲很容易產生像建築叢聚般的一致性和厚重感。然而,我們不需要透過分析就能感受到的是,這首曲子存在一種我們稱之為「自我意識」的核心調和元素。因此,我們被迫修訂我們看待變奏曲的標準,因為原來的標準並不是設計用來權衡音樂與形上學的結合—亦即技巧性昇華(technical transcendence)這樣的領域。10
往後的生命裡,顧爾德會繼續產出一系列相關的個人宣言和「詩篇般」的摘要。其實,「宣言」在他最喜歡的寫作型態中佔有一個超然的地位,就像小說家艾福林‧沃(Evelyn Waugh)在《插上更多的國旗》(Put Out More Flags)一書中所描寫的小說角色一樣,小說家寫道,「永遠偏好使用宣言文體。念中學時他寫過一篇;上大學後他寫了一打,二十幾歲晚期他和他的朋友哈特(Hat)及梅爾派(Malpractice)甚至用宣言來撰寫一個派對的邀請函。最後,這甚至成為他迴避共產主義的諸多原因之一,因為《共黨宣言》是唯一一次非他所為、由別人所撰寫的宣言。」顧爾德始終未脫一種年輕人特有的志氣,尤其是在智性方面,他從不吝於闡述他個人的理念,作為一種導正世界的方法。上述這段摘錄—雖然,一如往常地,他的文章真的很難讓人讀懂—但從中,我們還是可以讀到作為一位音樂家、特別是作為一位巴哈的詮釋者,顧爾德所抱持的特出見解。
頁十七
在建築叢聚般的分析式熱情與含蓄獨到的非分析式知覺之間,隱藏著他身為一位演奏家與藝術家的秘密。
這一段足以繞樑三日的郭德堡詠歎調,雖不是全首作品中最高難度的段落,但事實證明這一段的確是不好搞。在棘手的交叉彈奏與轉調段落,顧爾德雖已展現出大師級的詮釋,但錄製當時顧爾德還是躊躇再三、裹足不前。他和他的錄音師們這一段錄了二十次,還是覺得都沒辦法用。在第二十一錄的時候,顧爾德終於滿意了。「這是一個問題,」顧爾德後來說道,「要不要使用前面的二十次錄音,來清除我對它在詮釋上的過剩情緒,但沒有比這更困難的了。」11當你播放這張CD時,你所聽到的詠歎調就是那一個最精髓的顧爾德:技巧面的品質保證、預示著燦爛的炫技即將到來、傳達一個如科學般的精準詮釋。雖然專輯一開始出現的就是它,而我們也只聽得到最後所收錄進來的這一個唯一版本,但事實上這首音樂的這一段是存在有二十一種不同的描寫方式。這一個版本是最終被選定的版本、被正式定案的故事。沒有那另外的二十套版本,就沒有這一個最後的定案。那麼另外的那些詮釋,它們是如何存在、以及存在於何處呢?
當時,重要的並不是那三十二段變奏,而是那二十一次錄音:同樣的譜、不同的解讀、為了尋找出一個可被接受的版本,一個將要被錄製並發行的版本。
頁十八
有一些傳記作者試圖想要從顧爾德的音樂中去解釋他個人的詭異性,或反之想從顧爾德的詭異性去解讀他的音樂。然而不管結論是什麼,他們都服膺了一個傳記的標準推定,那就是他們必須為主人翁找出一個單一統合的人格形象,必須為主人翁的生平找出一條單一的敘事路徑。可是生命,如同顧爾德所深知的,並非尾隨著這樣的線性發展,而且就連他這樣一個深入研究作曲中的音樂線問題的人,他尚且反對音樂裡的進步史觀、反對帶有牽強意味及妥協意味的敘事作法。
在思考顧爾德的生命與藝術時,我是嚴正地看待他的反對立場。在他的生命中,不該有單一統合的主題、也沒有統一的決定性調式。他的音樂見解御駕出他那樣的人生,但在他的音樂見解中本來就存在許多互為矛盾、彼此對立、淘氣和蓄意挑釁的觀點。在塑造一個哲學角度的傳記文本時,我早已決意拋棄標準的敘事形式,而採納一個如萬花筒般的概念結構。我的每一個摘片,就是顧爾德的另一個版本,永遠是片段、永遠是不完整的。一次又一次的播放過程中,永遠都有一點不一樣,永遠都在摸索一個切題性與深度理解,顧爾德在這裡被當成有點像是有機哲學唱片的主旋律。12
頁十九
第二章
寂靜
音樂自寂靜中揚起,也在寂靜中沈沒。寂靜被鉤織在音樂中,在兩個音符的空隙裡,沒有這一剎那的間隙,音符無從存在。音樂在某一瞬間竄出覓尋,也在同一瞬間銷聲匿跡。時時刻刻,其實是因為這樣的緣故而被創造出來的:時時刻刻都是每一個當下在推往下一個未來之際、在這中間的協議與僵持,也在這一系列的歷程中找到一條軸線。但不是所有的寂靜都是等值的,而且不等值的原因並不僅是因為寂靜的久暫、或寂靜被安置的樣式。「寂靜太容易被剽竊了。」一位樂評家這麼提示我們。13
生命自「非存有」(non-existence)中昇起,在死亡中殞息。生命在時間裡頭被支撐,以它自有的方式懸置著。關於這一段生命存續的期間,有一個古老的畫面是這樣說的:就好比一隻鳥兒從盛宴會廳的這一端飛到另一端。在入口飛進來、接著是消逝中的短暫當下、然後就到出口了。在我們生命始末兩個端點的虛無中間,是記憶串起了這憂悒而無可避免的時間,意識乃於焉誕生。在音符與音符中間,寂靜裡到底存在了什麼?一個人,在他的誕生之前、以及在他的亡滅之後,他又是一個怎樣的存有?赤裸的生物並不是一個人。一個人,他有沈重的聲名之累,有著恆常得背負的期許與責任,這些都是我們終其一生不斷向前拖行的包袱。這一個人,
頁二十
他有可能是控訴者、可能是叛徒、或者一個倔強的小孩。真實生活中的我,與外界據此指涉而形容的我,兩者中間的鴻溝,逐日形成我們肩背上隆起的那個硬塊—原來看見我的人,也是審判我的人。於是乎包袱竟也變成某種衡量不同鴻溝的知覺,這個鴻溝是存在於「這樣活著的我」、「僅只是活著的事實」、和「此時此刻言語不清而一言難盡的我」之間。14姑且稱之為自我異化效應(self-alienation effect)吧。對存在異化(existential alienation)的知覺或許即是恥辱、責任與絕望的開始。很有可能三者會同時一起發生了。
每一個人都受知覺的支配:它是自我(selfhood)的代價。我們都是表演者,永遠要拖著這個自我形象去演出下一場秀、下一個節目、日復一日。而如果一個人身為演奏家、一個鋼琴家,那麼他經歷的可不只我們這種共通的存在感受…
葛蘭‧賀伯特‧顧爾德(Glenn Herbert Gould)誕生於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他是羅素‧賀伯特(友稱「伯特」)‧顧爾德(Russell Herbert “Bert” Gould)和佛蘿倫絲‧艾瑪‧顧爾德(Florence Emma Gould)的獨子,佛蘿倫絲‧顧爾德娘家姓桂格〔Greig〕—她是挪威作曲家葛利格〔Edvard Grieg〕的遠房堂妹。葛蘭的爸媽對音樂都涉入很深,雖然不是職業級,但他們都在教會和社區團體中演奏、教唱。伯特在家族事業「正記顧德毛皮莊」(Gold Standard Furs)裡擔任銷售的工作。他們住在多倫多湖濱區的紹茲伍街(Southwood Drive)三十二號,他們住的那一帶是當時白種盎格魯新教徒移民的飛地,距離市中心有一小段距離,
頁二十一
尤其在冬天,長長的湖岸線望過去好像一片海洋,顯得特別孤立荒涼。
他們家在北多倫多閃高湖(Lake Simcoe)一帶也有別墅,這間別墅是後來顧爾德終生的安樂庇護所—這兒有他想要的寧靜與孤寂。在他壯年期間,別墅是他珍愛的天堂,尤其到了冬天,夏季觀光客已經退潮,把美景讓出來給熱愛孤寂的人,顧爾德徜徉其中,深覺愜意。在他童年期間,情況比較複雜。因為跟他爸爸不一樣,他爸爸熱愛釣魚,而葛蘭並不把垂釣當作他最喜歡的靜態活動。一九三九年夏天,那年他六歲,在一次跟鄰居和鄰居的孩子遊湖時,他抓到他生平的第一隻魚、也是唯一的一隻魚。「忽然間我完全可以從這條魚的角度看待釣魚這件事。」後來他回憶道,而他的悲惱也導致小船劇烈搖晃,終至毀了那次的遊湖行動,從此也將他其他小朋友區隔開來。「回家後我立刻開始說服我爸,請他應該放棄釣魚。這項工作花了我十年時間,但也許它是我做過最偉大的事情。」後來幾年他進而更積極護生,套上大衣外套和帽子,開著小船就到湖裡去,唱歌警示魚群們快逃,壞了夏日南安大略省釣捕鱸魚和河盧的釣客計畫。15
顧爾德在受完私人家教後,直接進入威廉森路公立學校(Williamson Road Public School)二年級就讀,學校讓他覺得無聊,而且他是校園霸凌的對象,包括肢體上與精神上的。
頁二十二
他跳過三年級沒唸。五歲的時候,他宣佈說他注定要成為一位偉大的作曲家。多倫多東區的老鄰居回憶到,五歲的他是個伶俐但已經顯得怪異的孩子,這孩子對自己遠大的未來已有熱切的企圖心。接著顧爾德唸了梅爾文學院(Malvern Collegiate Institute),在那所學校裡,他是個優異的好學生;但他沒有唸畢業,因為他拒絕去考學校指定的體育課考試。之後他去多倫多音樂學校(Toronto Conservatory of Music,現為多倫多皇家音樂學校)學音樂,包括師從艾伯托‧加雷洛(Alberto Guerrero)達九年。往後他會宣稱他是透過自學而成,而且他自己也不收學生。
他的一生都花在演奏上,一開始是舞台演出和室內錄音都有,到後來就只剩下在錄音室裡演奏了。他一生都沒有結婚,但他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間有過一段很深的戀情,對象是一個已婚女人。當年她帶著她兩個孩子搬到多倫多去,住到顧爾德附近,只是最後她還是回到她丈夫身邊。顧爾德求她嫁給他,而她拒絕了,在這段關係結束後,顧爾德仍持續每晚打電話給她長達兩年。最後她說服他別再打了,然後他們從此沒有再見過面。
顧爾德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過世,也就是他五十歲生日剛過完沒幾天。熟識他的人說,他早已預言了這個剛過半百的死亡。顯然地,就許多方面看來,他是加速了這個預言。
起始。終點。
頁二十三
第三章
虛構
個人特質(personhood)是記憶的函數,也是記憶的一部虛構小說。每一個醒來的早晨,如果我們無法將我們的過去喚起,置入我們有所知覺的心智中,我們就不是我們自己了。記憶是碎裂而朦朧的,扭曲而不可信的;但它就是我們所擁有的全部。摧毀掉記憶,我們在時間裡便是徹底地無依無靠了,我們對時間的存續感以及消逝感也將被擦拭地一乾二淨。那樣,無疑是形容了意識的非經驗狀態(non-experience)或意識的匱乏,我們稱之為死亡。
矛盾的是,我們卻在生命中尋覓類似的無時間感(timelessness):我們追尋那些自我廢逐或昇華的時刻,追逐那些自我遺失(self-loss)的片刻。既然都無時間感了,那麼那些鐵定也無法稱之為「時刻」或者「片刻」等時間量詞了。它們其實是沒有一種獲共識的時間度量衡可供敘述的。它們是時間外的時間,將我們的生命引領到像生與死那麼決然確定的狀態裡。
主題與變奏、期待與解答。音樂透過存在於時間裡來揭示自身的結構。我們感應到某個被構築而起的樂章,一個問題卻也隨之奇異地被創造了。
頁二十四
我們的心智被調頻成音樂的式樣,預期並框限某種該有的結果。在這種模式之下,在未來尚未到來以前,音樂讓我們感覺是朝著那個未來進行的。當未來真的到來時—亦即期許中的未來變成經驗中的當下時—「經過」的這個歷程變成一種具體的感受,變成一種像意義一樣的東西(雖說不全然雷同)。音樂的時間是一種換位(conversion)的時間:它將接續(succession)轉換成進度(progression)。曲終結束,那一個永遠被預料並被反覆經驗的寂靜,它的作用是像詩的結尾或書的跋一樣的留白效果。沒有寂靜或留白這個東西來指示,沒有終點的那一道破折號指出接下來已經沒有東西了,也許音樂、詩、書都無從存在。透過時間,知覺以一種因果經驗被實踐出來—彷彿一切都是有因在前、彷彿一切都是無可避免的。
我認為傳記也跟歷史一樣,都是一種序列式的因果敘事。傳統上,一本傳記通常設定了一個聽起來容易卻又高難度的目標。它希望為某人一生的偶發狀況、那個人在時間中的偶然存在安置一個說法,運用的手段正是上述的換位法,「將接續轉換成進度」—這正是敘事學派(narratology)大師呂格爾(Paul Ricoeur)所稱的,自我透過一個統合的敘事來接納自身。16一本傳記會說:這就是這個人變成這位藝術家(或者這位政治家、這位哲學家)的原因。讀來有憑有據、毫無虛假,但它依然是虛構的。仔細探討起來,進步觀所隱含的問題,表現在音樂、在歷史、在人物敘述上,都是相似的。
頁二十五
「認為事件是以一種線性且有組織地在循序流轉,這種經驗是一個幻象(儘管是個必要的幻象)」齊澤克(Slavoj Žižek)如是說。這種幻象造就一種事實,那就是所有的合理性以及意義只能從終點的立場逆流而上反推回去。是的,這正是終點真正的意思,在這一點上我可以迴身過來去反推,將所有我敘事中「極端偶然」的事件賦予一種說法,遮掩掉事件原本的偶然性、蓋掉當初那些很有可能會出現另外一組完全不同狀況的時刻。「但如果這個幻象完全就是線性敘述的結果,」齊澤克質疑說,「那麼這些被環環相扣、組合在一起的事件序列怎麼可能去呈現那極端的偶然性呢?答案或許很清楚了:沒錯,就是透過逆時間方向,從終點出發,逆向呈現事件,推回起點。」17
這些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逆向案例只能從以時間為主的媒體當中去找,因為這類媒體我們才能真正地去倒推故事:例如哈洛‧品特(Harold Pinter)的電影作品《背叛》(Betrayal,一九八二)或克里斯多福‧諾藍(Christopher Nolan)的《記憶拼圖》(Memento,二00二)。即便在這些採取倒敘法的片子裡頭,分離的敘事片段被切碎重組,但電影還是必須透過倒敘情節順勢發展下去。(當中《記憶拼圖》的開頭和結尾有一小段慢動作的倒帶除外。)開頭與結尾的交錯出現,強調出敘事的預期;它並沒有真的挑戰到故事本身。
敘事的基礎本能是因果論:因為這個發生了,所以接著就發生了那個。只有少數的敘事、例如可能是兒童或惹人厭的人講出來的,
頁二十六
那種故事才會沒有因果論,而僅僅只是言說上的接續:一開始、然後是、接下來、再過來…。後者這種故事所缺乏的元素,正是福斯特(E.M. Forster)對故事(story)與劇情(plot)的著名定義:「皇后死了,接著國王死了。」這個是故事;「皇后死了,結果國王也因悲傷過度而死。」這就是劇情了。一個生動的敘事或劇情,裡頭一定要有一個合理化的說法,證明所有事件是有前因後果關係的,事件也因此被串在同一個序列裡,這也就是因果論的創造。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有可能去經驗所有敘事裡所允諾的那股慾動宣洩(libidinal release),說這樣才符合故事的結局。
敘事一開始已經預設了一個特定的、它想尋找的東西,那個東西就是—在因果架構的徵兆下,事情的發生有何意義:因此敘事不會單只說「這件事情發生了,然後是、再來是」,而會說「這件事情發生了,因此那件事才會發生,於是乎下一件事情又發生了」或者「由於這件事情的發生,導致下一件事情的出現,然後就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我們來看看跟音樂之間的比較。人們可以透過演示樂譜來指出音樂,就如同人們可以透過演示徵兆來塑造一個敘事或一個論述。只是音樂中的因果邏輯除了透過演奏之外,是沒辦法被展示出來的。《布蘭登堡協奏曲》(Brandenburg Concertos)那麼龐雜的樂曲結構只能在曲子被演奏的那一剎那一齊迸出,而且只存在聽到音符那一刻的時間經驗(temporal experience)中,它才能被完整呈現出來,亦即樂曲式樣(pattern)及其式樣變形(meta-pattern)是在這個寂靜到下個寂靜之間那麼短暫的。上述敘事的因果推理,「這件事情發生了,因此那件事才會發生,於是乎下一件事情又發生了」或者「由於這件事情的發生,導致下一件事情的出現,然後就發生了什麼事」;如此故事得以進展。論述得以成立。
頁二十七
曲子是在聆聽瞬間被解答、被下定論(原來樂曲是這樣的啊),它演奏著,而背景聲部的張力並不消退。隱藏在曲子中的這種結構經驗、或說我們自己對曲子下一輪發展的那份渴盼、是否就如同我們對故事的預設一樣,都是為了要得到合理化的結論呢?
回到顧爾德的生命。隨著年齡增加他變得愈來愈隱遁和怪異,這個情形可不可以是一個意外?顧爾德的生命可不可以去抵制潦草的合理化論述?還是無數的顧爾德傳只映證了有「真實的虛構」(actual fiction)這回事?湯瑪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的小說作品《失敗者》(The Loser)是箇中經典,它是一部加長版的內心獨白、一長段連續的記述,關於某人跟顧爾德學琴多年,而後又因為顧爾德在音樂上的天賦光采,而自己逐漸被埋沒忘卻的故事。18小說中出現顧爾德的另一位朋友、也是主修鋼琴的研究生韋特海默(Wertheimer),他因為顧爾德這個極端案例所帶來的壓力而走上自殺一途—或者,更精確地說,是被虛構的顧爾德口中所吐出的那個字「失敗者!」所殺(德語原著為Untergeher),「以他那種加籍北美人的直接語氣脫口而出」,如同韋特海默親耳聽到顧爾德當場演奏《郭德堡變奏曲》時一樣,絕對地區分出什麼是天才、而什麼只是天賦。「曲子原本是被譜寫出來照亮人心的,如今在接近兩百五十年後,這首曲子卻殺死了一個絕望的人…韋特海默的宿命注定要在莫札特大學(Mozarteum)行經第三十三號教室時,正巧聽見葛蘭‧顧爾德在教室裡彈奏那段著名的詠歎調。」19
頁二十八
小說中的自述者(即該書第一人稱)沒有選擇自殺,而是改弦易轍念哲學—算是分期付款的自殺方式。20「當我路過我老師家的時候,我想著,從今而後,我要獻身於哲學,雖然我壓根兒不知道哲學到底在做什麼。」他指說不知所云的東西,其中一篇就是他的「葛蘭論文」(Glenn Essay)—一篇永遠處於思考中、永遠未完成、以及永遠不可能成功的論文,因為它不完美,而且論文的章節段落不斷擴張,沒完沒了,已經超出界線:「葛蘭與冷酷、葛蘭與孤寂、葛蘭與巴哈、葛蘭和《郭德堡變奏曲》…我構思著。還有,葛蘭與他的森林工作室、葛蘭與他對人們的憎恨、他對音樂的憎恨、他對音樂圈人們的憎恨,我又想到這些。另外是葛蘭與極簡、我又想出來…」21
我在寫的這本書是不是也是「葛蘭論文」的一項嘗試?不得而知。但,簡明的事實是:核心的謎依然未解。令人信服的詮釋到底是什麼?是一個精彩的故事?敘述一個人的生命、一個在音樂圈的人?那要怎麼去創造預期及解答呢?
或許就跟音樂一樣吧。
頁二十九
第四章
記憶
一個人是怎麼存在的?他存在於何處?
神經科醫師奧力佛‧薩克斯(Oliver Sacks)提到下面這個可怕的例子:一九八五年,一位四十多歲的英國音樂家、音樂學家及指揮家克萊夫‧威靈(Clive Wearing)罹患了一種毀滅性的腦部疾病—疱疹性腦炎(herpes encephalitis),摧毀了大部分掌管記憶的大腦部位。22跟電影《記憶拼圖》中的男主角(蓋依‧皮爾斯〔Guy Pearce〕飾)一樣,罹病後的威靈,他的記憶只夠維持幾秒鐘,只能記得幾秒鐘以內的事情。(其實威靈的情況應該比電影中皮爾斯所飾演那位想為妻子復仇的藍納〔Leonard〕嚴重許多,至少藍納一次想得起來的範疇是幾分鐘,然後他根據失憶前他在自己身體留下的刺青來協助拼湊記憶。)
威靈的情況接近活著的死亡狀態,真的很難想像薩克斯醫生花費龐大的時間只能修復病人的極小片記憶。音樂家在朋友探視的短短時間內,會反覆地問候朋友,每一次問候都像多年不見的那種程度。他是能夠在自己的公寓裡活動,但如果被問到什麼東西放哪裡,他卻一件都想不起來。他能夠進行對話,
頁三十
而且還保持著上流社會的禮儀,可是話題只能限於家庭方面或那種不需要涉及跟前面講過有關的內容。他唯一認得出來並可以去信賴的人是他的妻子黛博拉(Deborah)。
這麼說吧,這樣的威靈,只剩下生理機能上的威靈。從他罹病以後,好幾年的時光他都很沮喪,一個無能計畫自殺、更遑論真的去執行的人,卻遭逢自殺般的命運,只能靜靜承受自己的專業生涯一夕喪失。這段時期他寫的日記都只能以條目式型態出現,讀起來像這樣:「下午2:10:此時適時地清醒過來…下午2:14:這時真的清醒過來了…下午2:35:這時完全清醒回來了。」下面:「晚上9:40:不管我前面怎麼說的,此刻是我第一次完全清醒了。」23就連眾神在懲罰希臘暴君西西弗斯(Sisyphus)時都沒有想出這麼殘忍的刑罰。
還沒完,再來是音樂。威靈再也想不起來任何他著述探討過的作曲家,播音樂給他聽他也完全記不得任何一首曲目;但他仍然可以彈奏並甚至可以指揮。自寂靜中揚起,音樂變成他唯一的庇護所,不管這時有沒有記憶。如同作曲家荀伯格(Arnold Schoenberg)所宣稱的,音樂不代表什麼,音樂是創造預期、指望、承諾和解答。我們把音樂稱為「以時間為基礎的媒材」,但或許更準確的說,「時間是以音樂來揭示的狀態」。
克萊夫‧威靈沒有辦法記得你正剛讀完的這個句子。只有音樂,在每一個有節奏旋律的時刻,依然能夠安撫著他、纏覆著他,將他抓持在這個時空裡。
頁三十一
薩克斯引用英國文學家艾略特(T.S. Eliot)詩集《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裡的詩句:「你就是那首音樂/當樂聲揚起時。」
請思考一下記憶(memory)、心智(mind)和認同(identity)三者之間的關係。標準的情況是這樣:我必須時時刻刻、日復一日記得我自己的故事,我才有辦法是我自己。這是單一個體的敘事。拿掉這個,我就不是我了;完全不是這個我了。但記憶是個龐雜的所有物,而且並不只是因為它可以分成短程記憶、長程記憶、以及它是前後連貫的。最後發生的事情是最牢固的記憶:克萊夫‧威靈可以記得英國首相是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雖然她早就不是現任首相了—但當他罹患失憶症那時,柴契爾夫人確實是英國首相。然而,記憶並不全部存放在心智裡;或者更精確地說,心智並不全部存放在我們的頭裡面。
英嘉(Inga)和奧圖(Otto)要去一座博物館。英嘉,身心健康,她已經記得要怎麼走到博物館。奧圖,他罹患失憶症,他把去博物館的路徑抄下來,因為他知道他會忘記路怎麼走。這兩者有什麼差別?我們會說,英嘉知道怎麼去博物館而奧圖不知道,因為他已經忘記了。但難道這個被抄下來的博物館路徑圖不是奧圖心智的延伸嗎?這個延伸在功能上和英嘉的記憶一樣,可以帶來辨識的作用。畢竟英嘉參考了她的記憶,就如同奧圖參考他的小抄一樣;
頁三十二
事實上,在找路方面,許多人是憑直觀、憑圖像、或記憶中所熟悉的途徑下去找的。也就是說,英嘉在出門前,是能夠從她心智中呼叫出那幅地圖的視覺印象。而奧圖的小抄則是他心智的一部份,雖然就物理角度,這小抄是存在於他的大腦之外。他和他的小抄形成一組認知系統,共同執行它們的任務。24
顧爾德在音樂方面擁有驚人的記憶力,有可能是他那個年代裡最高度發展的記憶力。現在想要瞭解他的記憶力到底是怎麼替他工作的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有些概論化的說法就顯得太過冒險。
音樂家、就算有的話,也很少運用直觀記憶去演奏音樂:也就是說,即便他們是從樂譜、而不是從聽力去學會一首曲子,在演奏的時候,他們也不是直接從腦海裡喚起一幅琴鍵上的樂譜畫面進行彈奏。音樂的記憶是比較有機的:它是配合整體的樂曲組織,確保樂譜的進展是被流暢而正確地執行出來。而譜子只能在彈奏中去把它背下來,而不是突然間一下子就記住了。演奏者在進行視奏的時候,是以一種複雜的認知回餽模式(cognitive feedback pattern)在運作:他們的視覺心智(eye-mind)一方面不斷處理進來的資訊,同時間他們的手指心智(finger-mind)卻以另一種結構型態即時輸出這些資訊。我們在精湛演奏中所接受到的愉悅,有一部份是屬於認知的,這遠出我們對演奏者的崇拜,
頁三十三
不過說真的,光是看他們在擊鍵與鬆鍵的剎那,那種靈巧、敏捷、精準的手指運作,就值得我們驚歎不已。彈鋼琴,不管是憑記憶還是看譜彈,都是心智能力的現場展現,延伸到空間與時間的心智展現。
沒有任何心智是不進行擴張伸展的。樂譜是去呈現作曲,當樂符再也無法只是存放在心智裡頭時,樂譜就去承載這份作曲的心智。樂譜的另一個作用還包括與他者溝通。同樣的說明都可以套用到錄音。錄音帶和唱片就跟紙張一樣,都是心智的延伸—這就是為什麼到了今天,我們依然能夠進入葛蘭‧顧爾德的心智,因為它被錄進去專輯裡了。以心智的複雜度和創新能力來說,我們都算處在邊緣地帶的人,我們大概都是奧圖、而不是英嘉:我們需要一些標記工具和準備工作,來讓我們的心智運作流暢。那不然除卻書寫是所有工具當中最古老且最有效的方式之外,書寫還算什麼呢?或許還有一個意義,那就是書寫是一個利用我們跟我們利用它的程度不相上下的工具。或者更精確地說,書寫即是我們。我們以媒體載具的角度來闡述這些儲存裝置,藉此表達它們在意義傳遞上的位置,到底是屬於來源端還是目標端,以及它們將文字、音樂或影像從此處運載至彼處的運作狀態。其實嚴格說來,也不應該說「介於」此處到彼處,因為這當中沒有距離,只有心智的延伸。媒介就是心智。
而心智同時也是媒介。我們提到背誦歌詞或樂曲,總認為那是靠心把它記下來的。古代希臘人把「認知」視為是最大、最重要的內臟器官—
頁三十四
勇氣和身份認同屬於肝臟,這撐起了器官,這也就是為什麼眾神把懲罰偷火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定刑為他的肝臟每天被宙斯(Zeus)的老鷹啄食,而且每天增生、更受酷刑。之後的時代看法有了轉變,將自我(selfhood)的重心從肝臟移到最北端,也就是心臟,心臟被視為是自我的核心這樣的看法維持好幾世紀之久。我們到現在還是會講「啃噬了我們的心」形容悲鬱的情緒,也會說「聽從心底的聲音來決定」,這些俚語的源由,今天憑理性推敲是無從得知的,當然我們知道今天這些說法多半是指涉到關於愛的事情。還有我們說把什麼東西背下來,意思是把它們全部記錄(record)在心裡,而record這個字是源自拉丁文的recordari—由re和cordis這兩個字首跟字根組成—此即心(heart)的意思。在心上反芻,換句話說,就是放在心上,這是心智的甘露酒。不然還會是什麼呢?
顧爾德,跟馬歇爾‧麥克魯漢一樣,他們都懂得這個,就如同顧爾德一定也認同麥克魯漢提到的論點,當時麥克魯漢說,世界正在轉變,正在從一個以視覺空間為主的現代性觀點,包括印刷、理性和唱片為主的文化,轉變成一個以聽覺空間為主的後現代觀點,包括重視情感、強烈的電子傾向、廣泛的視覺刺激等等;而且那樣一個時代氛圍的巨變幾乎就發生在他們二十世紀中葉的生存期間內。他們兩個當然沒有親身相偕一起去見證許多事情,因為這兩個高大的自我意識恐怕也沒辦法這麼被期待,
頁三十五
但他倆都認同心智延伸的重要性,儘管他們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實踐著,一個是致力於溝通理論的建構,一個是創造聽覺的新境界。有一段期間,這兩人的共同故鄉、多倫多,正在熱烈探討科技與文化的深刻思想—也就是哈洛‧殷尼斯和諾梭‧弗萊大擅其場的時期,同一時間還有以喬治‧葛蘭特(George Grant)為首的保守派陰影、再加上顧爾德和麥克魯漢所掀起的旋風—這些人加在一起,共同深入探勘了一個時代的詭異事實,那就是關於意識與科技能夠怎樣地反映我們自身,就算他們當初的形式(例如鍵盤)稍微比較老舊一點,但他們扮演觀點先鋒的事實不受此影響。
然而不管是顧爾德還是麥克魯漢,他們都未能真正勘出這項觀點的完整力道。麥克魯漢對媒體的看法是「人的延伸」(extensions of man),這項說法非常能夠定義延伸的本質、對延伸的渴望、以及延伸所可能採納的諸多工具、甚至還包括它光明面的展望和黑暗面的真相;但麥氏理論並沒有真正深入剖析心智的神秘作用是如何造福人們。25而顧爾德這方面呢,則是沒有認真持續發展他一開始所提出的驚人見解,到了後來反而誤入惑解。就像許多天才型的音樂家一樣,有時他會談及他「自己腦海裡」所聽到的音樂,用這個來辯解他在鋼琴前惡名昭彰的哼唱習慣,說那是他內在旋律一種不受控制的迴響。於是在這裡,內在性的真正意涵被曲解了;因為他錯把他自己的記憶當作內在旋律。
頁三十六
記憶,不是某座憑空想像存在於在柏拉圖《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的巨型鳥舍、不是一個我們能偶爾成功地從中抓住飛鳥的禽類飼養場。記憶,用比較通俗的說法,其實是跟心智一樣的,是某個正在跟世界交涉的人之具體化身。事實上是創造一個世界;並且透過這麼做,找出還有誰在傾聽。
頁三十七
第五章
存在
但然後:音樂存在於哪裡呢?音樂是怎麼存在的?
當音符被安置在樂譜上時,那份實體的文件就是音樂了嗎?顯然不是。同理,當我們把文字印刷到紙張上時,我們會說一本書只是一個物理形式的存在而已。我們真的要那麼說嗎?
這就是音樂嗎?
(插入一段樂譜)
音樂是所有演奏與專輯的總和嗎?音樂是一首曲子從醞釀、作曲、到首演、被研發出不同詮釋版本、甚或到被封上冠冕的發展過程嗎?這個聽起來倒是比較有道理。
但潦草粗暴地將所有演奏加總在一起,說那就是音樂,這個作法卻不免有些孤注一擲,容易引發歧見。雖說好的演奏可以將紙張上的樂符瞬間解放、掙脫物質界的鐐銬,將音樂重新賦予在時間當中,可是也有可能出現劣質的演奏,反將音樂推入曇花一現的悲劇裡。至少就這點看來,
頁三十八
一首曲子的發展是永遠未完成的,它的精髓永遠被擱淺在未來。
那麼,音樂是否為其他某種什麼的整體?它會不會是一種先驗的實體(transcendental reality)?不是只被演奏或物質界所支撐,而是統攝了這些真實音樂的簡易載具或沈思?從這個角度去想,音樂或許是像柏拉圖的理型(Platonic Forms)、或更貼切一點,音樂是聲音在無垠天界婆娑起舞、是它們永恆、和諧、宇宙之舞的跫音。我們在這塵世間所聽到的,包括微風拂過蘆桿所引起的顫動、羊毛線製成的弓所拉過的提琴絃、或者琴槌靈巧地去拉起或敲擊繃緊的鋼弦,這些聲音,較之天籟,無非只是頹唐黯淡的影子。充其量,這些俗樂只能影射那份超越人界視聽的音樂之美。
還是說音樂是比較接近語言的呢?其語義決定自演奏裡所出現的異同?同一個音符,我們在這裡聽到的詮釋跟我們在那裡聽到的演出,它被賦予不同的性能、展現不同的意義。就如同我們在這個字跟那個字裡都看到同一個字母、我們在這個句子跟那個句子裡也都發現某個單字,但它們的脈絡意旨卻可能大異其趣。意義,不管是在音樂或在語言裡頭,絕對不是一個能從整體表達被化約成其中某個單一的局部元素。意義,它而是一個在複述與重申之後、在演出與複奏之際所意外出現的旨趣。
頁三十九
這個聽起來倒還不錯,除了有一點,那就是我們有時候會說「這首曲的音樂語言」、或在一些語言嵌入音樂的時刻—例如詩歌、聖歌、讚美詩等等—音樂本身所呈現的意義似乎不盡然等同於語言所道出的內涵。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的意義顯得各行其是,它們的旨趣也變得曲折牽強。小說家與詩人萳西‧休士頓認為:「意義如石頭般完整堅固,音樂卻像滑石一樣充滿漏洞。」26音樂似乎是無法從語法上去分析的、無法被翻譯或以其他形式被描繪或呈現。事實上,它甚至根本不太可能去指攝什麼。(也許詩作也是這樣的,詩人兼評論家麥克萊希〔Archibald Macleish〕這麼認為。)27
音樂,還有沒有可能絕然不是這些哲學假設、這些概念上的吐火獸?它有沒有可能是一種複合式腦部功能的特色?就像數學裡的關係或一種能發育的構成物概念?我們從一首曲子當中所感知到的音樂之美,可以比擬成一則邏輯運算的典雅流暢:這可以視為操作奧卡姆剃刀定律(Occam’s Razor)的實際案例,這個定律是說,以更少的步驟得出相同的運算結果,或用較少的活動零件來達到同樣的運作機能。音樂裡有結構。我們甚至可以說,音樂是聽覺可辨的結構。我們有意識的心智,它們是被結構化來要去指認出結構的,結構化的心智對音樂是有反應的,就如同飢餓的人看到食物一樣。當我們接收到音樂不斷演繹出的結構,我們領略到澎湃的歡愉—主題與變奏、
頁四十
預期和預期被落實—這是我們口中所說的「我們被音樂感動了」。
還是說音樂其實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現象,就像儀式和宗教常常被聯想到的一樣?從這個角度來看,音樂是一個精湛的符碼系統,一個人類溝通的模組格式。這樣說來,音樂是有能力去展現廣袤多元的功能,這些功能我們會將之置放在仍待議定的「人性本質」這個範疇。就像神經學家暨音樂家丹尼爾‧拉汶汀(Daniel Levitin)所列出的分類,音樂或多或少可以達成如下的功能:促進友誼、誘發喜樂、傳遞知識、提供舒暢、支撐宗教、溝通愛。28
以上說的都對。可是,對於音樂,這些概念又告訴了我們什麼?強調什麼往往意味著對它的束手無策,就像斜體字正代表死路一條一樣。我們越想界定音樂是什麼,它越加地遠離我們。我們知道音樂,當我們聽見音樂,這是無庸置疑的。尤其是現在這個時代,我們幾乎無時無刻、隨處隨地都能聽到音樂,而不像之前的年代,音樂現在變得相當普及。普及到我們可能在日常生活經驗中很難感受到它的珍貴稀罕—但在過去,音樂的演奏一度在文化風景與個人生活中展現強勢的優越地位—如今去想像沒有音樂的生活,就好比去想像沒有燃料或沒有自來水的世界。但知道這一點又怎樣?我們認為我們又明白了什麼嗎?
頁四十一
甚至連去假設「對音樂的熱愛是普世的」,這都是個謬見。例如金斯萊.艾米斯(Kingsley Amis)筆下《幸運的吉姆》(Lucky Jim Dixon)就絕對是個例外,他抱怨當他必須臣服於「下流莫札特所譜的無止盡的滑稽樂章」、以及「一些布拉姆斯的垃圾」、然後是「某個條頓討厭鬼的小提琴奏鳴曲」。他真不堪吶,我們或許會這麼覺得,至少對莫札特而言是如此。但這番話還是可以聽出一些端倪:這些話是真的詛咒,而不是只描寫那些對藝術一竅不通、排斥藝術的庸俗階級。主角吉姆‧迪克森(Dixon)舉出這些大師級的名字來宣洩他的激烈抗議,藉此怨嘆他的一生都浪費在無聊的人、特別是他的雇主們身上,其實是沒什麼效果的。
但納柏科夫的話又該作何解釋呢?在《言說、記憶》(Speak, Memory)中他寫到,音樂在他聽起來「不過是些惱人聲響的胡亂拼湊罷了…。平台鋼琴和所有的管樂器都讓我覺得無聊,簡直要剝了我的皮。」佛洛依德則公開承認自己是藝術的信徒,但至於音樂,他就沒興趣了,因為「我心智中的某一部分抗拒被某種不明就裡的東西所感化,如果不能明白為什麼我被感化以及到底被什麼東西所感化,那麼我就無法感到樂趣。」
我們大多數的人是不至於這麼被折磨或這麼抗拒音樂。對音樂的熱愛是普世、不分種族文化的—雖說還是有為數不少的例外—但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還是喜歡每天聽它,而且通常是能夠被音樂深沈地打動,對音樂是沒有疑慮的。
頁四十二
古代希臘人認為音樂是來自天國般的神聖潔淨,認為音樂是永恆的,就跟數學一樣。現代的認知科學認為音樂滿足了我們「無端莫名的找碴慾」。而時下的青少年都知道音樂是最簡易的身份認同、是個最能標榜個人品味、展現我行我素的身份區隔。
一如顧爾德當初熱切地期盼,如今音樂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容易取得、更容易隨時攜帶,而且不限於某種音樂,是所有的音樂都能夠隨時聽到,我們每日生活中的iPod音軌,就是我們在聽覺方面深沈的動物慾享所導引出來的合理發展。如果去回憶一下,當年我們如何大費周章地大老遠搭巴士跑去某個家裡有套劣質低音擴聲器和一套厲害的黑膠唱片收藏的傢伙他家,然後團團圍坐在地下室的錄音間聽「倫敦之聲」(London Calling)或「國軍廣播」(Armed Forces);以及在目前可隨時存取下載的MP3被發明以前,想想當年自錄的混曲錄音帶是如何地像秘密暗號一樣被傳遞的那番酷樣,簡直都覺得不可思議。29如果再看看湯瑪斯‧曼(Thomas Mann)的小說《魔山》(The Magic Mountain)裡頭的場景情節,一部留聲機和一堆唱片就能徹底扭轉山麓療養院病患的命運,那不是更荒誕不經?
但清教徒們還是有話要說,當年他們其中的一員、也就是顧爾德首開倡議之先,認為錄音技術是優於現場演奏時,他們憂心如此一來,音樂的普及性將降低人們對它的敬意,不過這個看法並沒有任何的證據可供證實。《魔山》主角漢斯‧卡斯托普(Hans Castorp)一再播放舒伯特的《菩提樹》(Linden-tree)唱片,每播一次,他對這首曲的喜愛便又與時俱增。
頁四十三
但我們從中體認到的訊息不止這些。幾世紀以來,音樂品味都牢牢地被牽連在技術層面可被取得的這個關卡上面。只有那些有足夠財力去創作音樂的人才有可能享受音樂,而且只有那些不太仰靠音樂維生的人才能真正自由地創作音樂。因此古典音樂在歐洲的教會及宮廷傳統才會出現品味之正統性的種種確認。音樂從起源的禮拜儀式及舞蹈,逐漸走向一種美學形式,美學才是音樂的最終形式。而且它越來越吻合康德概念下的「無利害關係」(Kantian disinterestedness)—亦即聆賞音樂應該是為了其他目的,而不該是為了它本然俱有的美感。
但這種反功利、或說純粹的審美本身,它反映的是一種階級資產觀念,而不是心智的基本特性。它為少數有財力在時尚體系中品味音樂的人(通常是有錢人)建構了一個品味的位置。而這個由少數人及稀罕資源所建構出來的品味系統又會隨著物質條件變動而變得不穩定,尤其當音樂的取得管道發生重大變化時,品味更是變動不居。「音樂會」由高尚的社交宴聚轉變到讓顧爾德這麼深惡痛絕,從這個角度來看,它不過是貴族品味系統的最後一顆病瘤罷了。品味系統有一種偽民主的現象,表面上似乎是聽憑各人喜好而論,但其實它仍深受所謂「好品味」的語彙價值所宰制。
頁四十四
尤有甚者,顧爾德對演奏會的罷黜可以視為古典音樂演奏會的一股乖戾叛逆的殭屍力量、一陣古典音樂演奏會的最後痙攣。從一個正統品味的美學形式,轉變到隨時受「真民主」大眾品味危及的情況—例如廣播電台或音樂專輯散播流行音樂的模式—音樂將越來越積極而奮力地宣示其權威性。30
頁四十五
第六章
天才
我們在找尋天才的徵兆,用此解釋無法以其他方式說明的現象。「沒有一個天才不被染上瘋狂的氣息。」亞里斯多德如是說,甚至連科學界也對天才保持某種罕見的信念,認為天才是神的禮物、被上帝授記過的印痕。接著各種靈感就好像理所當然一樣,被穿鑿附會了起來,即便是現在這個比較世俗化、沒那麼神秘兮兮的年代,我們依舊會覺得天才的周圍好像瀰漫著一層特殊的氛圍,因為他們可以做出我們無法想像怎麼去做到的事情,那些都是萬中選一、絕僅罕見的高難度任務。
天才的浪漫敘事輕輕地將神性的瘋狂、那些超塵脫俗的奧秘現象,推進到一個較為自然、不那麼勁爆的述說範疇。天才應該是要在最幼年的階段即嶄露跡象—就算不是,那些以後見之明建構出來的故事也一定會讓事情看起來像是這樣。莫札特童年時期所譜寫出來的作品便是不容置疑的,這跟畢卡索小時候的素描有異曲同工之意。在顧爾德的案例中,我們掌握到一些較為輕微、但同屬天才的徵兆:他的父親對外宣稱,幼年顧爾德小時候都不是用哭的,而是用哼的,還會伸長手臂、「張開手掌,就像在彈奏八度音一樣。」另一個更可靠的徵兆是,顧爾德三歲的時候就展現出完美的音感(pitch)、
頁四十六
可以辨別音調(tonality)、轉調(modulation),而且是信心十足地確定—這在他後來所能展現的超強音樂記憶方面是一個必備條件,憑他那麼在意自己的表現,以及他性格中的精準特質,如果沒有這個關鍵的能耐作後盾,他鐵定不可能做到那樣。
但我們必須承認,音感並不能保證作曲的能力,更別提是要作出優美的曲子。音感對音樂創作來說,也不是單一的充要條件或必備條件。雖然顧爾德五歲就開始寫曲,包括一些曲子還在他的學校或教會中被演奏過,同時他在鍵盤上也展現出優渥的精準度和正確率,他能彈到什麼就唱出什麼,但他在作曲方面的努力結果,以專業角度而論,充其量只能說是泛泛之作。他那首備受青睞、並被錄製成輯的《絃樂四重奏》,作品一(String Quartet op. 1)是一首對位法的試作,但就如同他自己所承認的一樣,他犯了所有作曲新手會犯的錯誤。該曲也是以古典形式去譜寫,照理說,這首曲完成的年份(一九五三年),是當時所有像顧爾德這樣強力擁護十二音列作曲法的前衛份子都會很不屑的作曲款式。
但他喜歡這麼解套,說他獨創的「對位式廣播」(contrapuntal radio)才是真正展現他作曲天賦的作品—例如他對位式廣播紀錄節目的極品代表作《北方印象》(The Idea of North,一九六七年),還有另外一首小巧淘氣但也能說明他作曲才華的作品,是一九六三年完成的《所以你想寫首賦格?》(So You Want to Write a Fugue)—這是一首以多層次的語音疊錄而成的賦格,語音內容是在建議一些有望成為對位法的作曲家,想當然爾,該曲有十足插科打諢的戲謔意味。
頁四十七
這首歌最早播放於加拿大廣播電視台(CBC-TV)一個叫〈賦格的藝術〉(The Art of the Fugue)這個電視節目,當作節目的壓軸,隨後則是收錄到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發行的雙CD《葛蘭‧顧爾德銀慶專輯》(Glenn Gould Silver Jubilee Album,一九八0年),部分歌詞內容是這樣的:「所以你想寫首賦格?你有迫切的需求要寫首賦格?你有寫賦格的那條神經嗎?寫賦格的唯一辦法是馬上投入、立刻就寫。但千萬別為了想出風頭而自作聰明,千萬別為了自作聰明而自作聰明!」31
而值此同時,針對自己在鍵盤前的種種音樂介入表現,顧爾德常常會認同、甚至是偏好被稱作「娛樂的藝術家」(recreative artist)(而不是「有創意的」〔creative〕這個字眼)。每一次的詮釋,都是一個合理正當的全新作品,這對巴哈的作品來說尤其正確,因為巴哈的譜沒有標明特定的速度、表情記號,他把這些相關的裁決定奪留給演奏者或指揮家的手去決定,包括速度、發音、裝飾音等等。儘管詮釋者在每一刻接著每一刻的演奏運作當中,是循著樂譜的垂直向度去發展,藉此慢慢推動出一個樂題章旨,因此,若要在詮釋上有所創新的人,他必須能對樂譜提出一個水平向度的觀照與省思,亦即樂曲的建築構造—這是詮釋上的另一個議題。如果再加上這位鋼琴家所能展現的聲勢強度、音色變化,這對當初為古鋼琴或大鍵琴譜曲的作曲者而言可能是全然意料之外的手法,或許我們就比較能明白,還真有所謂的「詮釋天才」這回事存在。
頁四十八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時代雜誌》(Time)這個主流的正統媒體宣告時年三十一歲的顧爾德「他的錄音事業少了點天才」。然而接下來他卻繼續錄製了後來佔他所有專輯完成量一半左右的作品,當中還包含許多當今最受讚揚的專輯。
以上這些情節在往後都還有下文。例如他的雙親後來強調他們並不希望看到顧爾德過著一種音樂怪胎的扭曲生活—「莫札特」、「天才」等字眼在他們家都是被禁止的—可是從一開始他的母親就深深相信自己的兒子會是一位擁有超級天份的音樂家,更確切地說,會是一位鋼琴演奏家。音樂從他還沒出生開始就已經佔據了他的生命:懷孕期間,顧爾德的母親就刻意營造音樂環境,常常彈奏或播放音樂,用以作為胎教,這個方法後來倒是成為一種風尚。
顧爾德的第一次公開演出是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那年他五歲:那是在「商團查經班」(Business Men’s Bible Class)的三十三週年慶上,他父親是這個查經班的成員,顧爾德為他雙親所組成的二重唱伴奏。同年八月,他參加了一個在加拿大國家博覽會(Canadian National Exhibition)舉辦的鋼琴大賽,但沒得獎。十二月九日,他在多倫多的艾曼紐長老教會(Emmanuel Presbyterian Church)第二次登台演出。他的彈奏震撼了在場觀眾,然後,那個小顧爾德開始宣稱他想成為一位鋼琴演奏家。
頁四十九
一九四四年起,顧爾德開始參加多倫多國際同濟會音樂節(Kiwanis Music Festival)的鋼琴比賽,後來他談到這些經驗大多語帶嘲諷。第一年參賽他贏得了兩百加幣的獎金,這個結果並為他帶來了第一篇的媒體報導。那年他十二歲。隔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他獻出他管風琴的首次登台之作,從此告別教堂演出和鄉下的鋼琴賽事,晉升到多倫多市中心的伊頓演藝廳(Eaton Auditorium)演出。他的演出曲目包括孟德爾頌(Mendelssohn)的第六號奏鳴曲、杜普意(Dupuis)的協奏曲、巴哈F大調賦格。多倫多《晚間匯報》(Evening Telegram)的一篇報導把他稱為天才—這是外界大眾第一次把這個神奇的字眼加諸到顧爾德身上。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他生平第一次跟管絃樂團一起演出,地點是在馬瑟音樂廳(Massey Hall),他跟多倫多音樂學校交響樂團(Toronto Conservatory Symphony)一起演奏貝多芬的第四號鋼琴協奏曲第一樂章。樂評們都對他的表現表示推崇。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和十五日,他跟多倫多交響樂團(Toronto Symphony Orchestra)合作,獻出他第一場的職業演出,演奏貝多芬第四號鋼琴協奏曲的完整四個樂章。樂評們注意到演奏期間他在舞台上會出現一些令觀眾分心、坐立不安的小動作,後來被解釋成是因為他西裝上沾了會讓人過敏的狗毛。
真的是這樣嗎?同年十月二十日顧爾德在伊頓演藝廳的「國際藝術家系列」(International Artists)演出他第一場的鋼琴獨奏會。他彈了五首史卡拉第(Scarlatti)的奏鳴曲、貝多芬的《暴風雨》奏鳴曲(Tempest)、庫普蘭的B小調帕薩卡里亞(Passacaille in B Minor)、
頁五十
李斯特的《泉水畔》(Au Bord d’une Source)、蕭邦的降A大調華爾滋(作品四十二)、升F大調即興曲(作品三十六)以及孟德爾頌的行板和奇想迴旋曲(Andante and Rondo Capriccioso)。評論都很正面。但樂評們也開始強調他們注意到一些不太尋常的矯飾動作越來越多:抽搐痙攣、邊彈邊唱、把頭埋到幾乎貼在鍵盤上。最慢在六歲的時候,顧爾德已經是個專注的憂鬱症患者和輕度的細菌偏執狂,他會迴避人群,把自己捆成厚厚的一團,這個穿著習慣日後也變成他的個人標記。現在,在十五歲的這個年紀,所有關於天才的外在特徵通通顯露無遺。「天才」這個字眼開始運用在他身上,未來的時光,大家會越來越常用這個字來形容這個湖濱區來的年輕人。
但,說了這麼多,究竟什麼是天才呢?像狄德羅(Diderot)、亞陶(Artaud)、龐德(Pound)這些特色各異的作家,或可符合亞里斯多德對天才的敘述:「神性的瘋狂」(divine madness)—其實有時候這種說法反而導引出一種不太切實的觀點,彷彿所有的天才都是瘋子,或者只要是瘋子他就有可能是天才。這兩種結論都沒有證據可供佐證,除非我們打算要同意說所有的優異表現,在定義上即為神性的展現。
然而因為有天才這個象徵,導致所謂「神性的瘋子」(divine madmen)這個概念一下子被擴張地太快、太遠,於是反而誘發了我們常聽到的「反神論」,而形成「尊神」與「反神」的雙重終局。天才的困擾就是,他永遠被認定在一個「過與不及」的狀態。這就如同菁英論者對民主制度的批判—
頁五十一
一塊土地上,每個人都是頭,但又沒有人真的是塊料—我們處在一個天才太多又太少的年代。這個邏輯是一樣的。所以,現在每個成功的理專就叫作「金融天才」、每個有天賦的廚師就叫作「料理天才」、每個跑得快的跑鋒(running back)就叫「速跑天才」、每個能設計商標的設計師就叫「設計天才」。
另一方面,那些一度在文壇上、哲學界叱吒風雲的天才們、那些經典名著的經典作者,現在處處都被論述化、定著化,在歷史上的地位變得牢不可破,好像不這麼賦予其地位就會有損大師威望。他們並不那麼特別。他們以為他們是誰?天才的出現變成初嚐乍紅滋味而沾沾自喜的典型,變成具有特定興趣、術業有專攻的概念,也或者是來自出身背景而佔有的優勢,這些全都被包裝成普世認定的非凡徵兆。在我們自己這個當代的社會脈絡底下,特殊個案倒是被弄得平凡無奇,所有的卓越都被拿來分析、去神秘化,好讓我們大家覺得心裡好過些。現在天才的意思,只是「某人願意每天練習十小時,好在某項事物上表現傑出」的換句話說而已。在這種套套邏輯的理解之下(譯按:即他為什麼這麼優秀呢?因為他每天苦練十小時;他為什麼要每天苦練十小時呢?因為他想變成天才),這每天苦練的十小時,其動機到底是植基於怎樣的天賦特質、怎樣的靈感啟發,都變得無關緊要而毋須探討…
對我們這些二流的平凡人來說,事情一旦被這麼解釋,我們的自我觀感就立刻舒坦多了,看嘛,事情終究沒那麼出神入化,天才也不過是普通人而已,天才還是有所不足的。我們這個時代,把天才的概念化約成非黑即白的二分法,
頁五十二
只能在「上天所賦予的奧秘天份」和「來自勤奮執著的苦練」這兩種信念之間選擇,不是「現在你明白了吧」就是「這個你永遠無法懂的」。但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對天才提出什麼觀點呢?一方面我們要怎麼規避掉神秘論?另一方面,又該如何擺脫掉如評論家哈洛‧卜倫(Harold Bloom)所言、對天才的理解「已經摻入歷史相對論和穿鑿附會的論述化」等處境?要怎麼理解天才,才能摒除「把所有作者都貶成一股社交慾望,而所有讀者都是拾人牙慧的應聲蟲」的有害思想?32
卜倫的研究興趣是鎖定在文學天才—有些人對於這個範疇是否存在會傾向質疑的立場。33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可以從對這個議題有研究的學者們那邊整理出一些關於天才的特質。首先是他們豐饒多產而充沛的天份(fecundity),當然這本來就是「天才」這個字的根本意涵:天才源源不絕地創造;他使新的技藝或境界萌芽。再來是見地(vision):那是一種去看見可能性的能力,而這個可能性對該項藝術的一般執業者來說,根本是把它否決掉的,而且此處我們指的執業者是已經涉入本行的圈內人,而不是路上隨便的粉絲或普通人。因此接著,自然是天才的原創性(originality)—哲學家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把這個稱為「幽微洞見的醺醉」。這個特質導致天才會是一項不穩定的性能,因為,做得太普通,就淪為泛泛的二流作品;做得太原創,又會蒙上不被理解、艱澀難懂的風險,天才們恆常在這兩者之間擺盪。就是因為這個因素,很多人把天才看作是處在理性(sense)與非理性(nonsense)邊緣,一個極容易揮發、消散掉的反應—這又回到「天才還是瘋子」那個版本的探討主題。
最後,在文學形式中,反諷(irony)也常常跟天才有所掛勾:反諷被泛稱為天才的蒸餾液,天才也被視為是反諷的嚴格必備條件。
頁五十三
天才欣然接受生命的有限性及終點,死亡本來就是生命在誕生時便已注定的結果,儘管如此,他們依舊奮力去提煉生命那份永恆的超越力量。這些因素全部、或部分因素集結到天才的這個人身上,就會創造出,套一句卜倫的話,「從時代脫穎而出」的作品或「把其他遜色的同業人都湮埋掉了」的景象。又或以詩人艾德蒙‧斯賓塞(Edmund Spenser)的話說:「天才者永生;而其他所有人都得死去。」
以上這些聽起來應該都沒有爭議,只要我們能夠解決一個有點煞風景並屬於套套邏輯的問題:天才者名留青史是因為天才真那麼好,還是說因為既然他已經名留青史了,所以我們說他好?再來聽聽小說家兼評論家威廉‧蓋斯(William Gass)的說法,他對有幸蒙獲「時代檢驗」的作品,態度顯得猶豫不決:「所以,通過『時代檢驗』的作品就能永免被忽略、被誤解、被漠視的情況嗎?不。沒能通過『時代檢驗』的作品才能在被遺忘中獲得永息。通過『時代檢驗』的作品將恆常地被忽略、被誤解、被剝削、被漠視。」況且所謂「時代的檢驗」只是一個歷時的(diachronic)過程,看看能不能通過跨世代的流行考驗罷了,除此之外,並沒有比這更深更多的可信度。34
天才的這個「通過時代檢驗」的解釋,也導致「到底什麼是天才」這個核心問題變得朦朧不清。更多的研究調查顯示,大部分被稱作天才的人,都如一位哲學家所形容的:是一個對比的(contrastive)狀態,亦即天才們就是在其他領域、事物中最常被否定的人,也就是典型的「他只會那樣東西」的概念。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在他的〈論天才〉(On Genius)一文中提出一個標準的對比解釋。
頁五十四
「有天賦的人就像一個射手,射中了一個其他人都無法射到的目標;而天才呢,則是射中了一個連他們自己都沒看見的目標。」換句話說,「有天賦的人能夠在某項事物上超越其他人的表現,儘管那件事情並非他們的能力所能理解;因此天賦能夠立刻吸引來讚賞的目光。」相反地,天才就不同了,天才有可能引起比較不是那麼正面的反應,甚至連擁有天才的人本身也可能覺得那是一個朦朧模糊的禮物。
這個概念槓桿一旦形成之後,事實證明它是很難抗拒的。「天賦是人的能耐,」詩人詹姆士‧羅素‧羅威爾(James Russell Lowell)寫到,「天才是決定誰是王者的權力。」王爾德(Oscar Wilde)在這個主題上也提出一番洞察,包括他經常重複提到的辯詞,說「有天賦的人用借的,是天才的話就用偷的」,還有他那句自我指涉的名言,「天才向自然學習、向他本然的天性學習;天賦則向技藝學習。」35
關於天才,王爾德還曾提出過如下一段著名的自我評價。「我的生命,我傾注我所有的天才;我的工作,我只有把我的天賦投入其中。」有些人把這段話詮釋作一位審美家的呼籲,就像尼采(Nietzsche)訓諭人們應該把自己的一生過得像一件藝術品一樣。可是王爾德是個著名的自封天才—天才的正統解釋並沒有排除掉這類的反身喝采(reflexive congratulation);有些定義甚至會主動要求這類的言詞特徵。王爾德的這個自視角度,有一部份影響導致他清楚意識到超越普通天賦時的負擔。
頁五十五
「公眾的仁慈超乎想像,」他提到,「除了天才之外,人們寬恕所有事情。」王爾德把天才定義為「製造傷痛的無限能力」,這對僅僅只是個有完美主義傾向的天賦者無疑形成一個精彩的反差,因為天賦者的奴役型定義正是「承受傷痛」,這個惡作劇般的定義,也提示了大家,天才對於天賦者根本不屑一顧,兩者是絕不等同的。或許他在說這話時,已經注意到了稍早兩個世紀前,有另一個盎格魯—愛爾蘭裔的鬼才同好也提出過雷同的公式定義。「當一個真正的天才出現在這世界上的時候,」愛爾蘭評論家強納森‧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寫道,「你或許可以透過這樣的現象知道他是誰,那個人就是所有的庸才聯合起來對付他的那個對象。」
這種庸才所結成專門對付天才的聯盟正是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核心隱憂,他本身就是一個能力優越的古怪天才,然而他強壯的精神力量依舊讓他在青春時期飽受摧殘、情緒崩潰。「準確地說,這是因為眾數意見的暴虐,意圖使怪異成為一個值得責難的對象,這是眾所渴望的,而為了破解這種眾數意見的暴虐,人們應該讓自己變得怪異。」彌爾解說道,「性格中的力量強大者,那麼他身上的怪異特質也會很多;而一個社會裡頭的怪異者,其數量大約是跟一個社會中的天才、精神領袖和道德中堅的人數成相等比例的。當一個時代裡只有極少數的人勇於怪異、勇於特異獨行,這就點出了那個時代的主要危機。」
頁五十六
但這個辯證裡頭,現在又產生一個新的困惑。首先,我們可能還沒準備好要接受天才優於天賦的對比描述。這種分類區隔在實際驗證時是很薄弱的:例如天才與天賦兩者之間的分界門檻在哪裡?以及誰有資格來審判誰是天才、而誰只是有天賦?其次,就算我們真能同意「天才與怪異特質是同時並存的」這樣的描述,甚或如同彌爾所主張的,兩者是互為關聯、呈同方向擴張的,這個見解依舊是被過度操作。更別提之後那個更具爭議性的問題,也就是怪異氣質裡頭是否絕對包括了所謂「性格的力量」、「精神領袖」或「道德勇氣」這些東西。
我們或許不必然要相信一個鼓吹平庸的人對於像顧爾德這樣的人所發出的種種質疑、想去探究顧爾德所展現的那些怪異行徑是否有價值、有意義;有時候那些怪異行徑可能是裝出來的、可能是一時風尚,甚至可能就只是一些個人的特殊怪癖而已—也許可愛、也許並不可愛。怪異或許可以是彌爾的「活著的各種實驗」這個概念底下的人權自由、各種生命樣貌之多元價值的原始呈現,其餘更進一步的推論都需要更多的佐證論述方得成立。撇開那些更次之的問題,諸如「該怎麼管束及規範怪異行為」(即「人們該如何、如何」)、以及沒有了同類多數的支持,怪異行為在社會上還會不會存在等等—首先在概念上、或者應該說最終從社會認同及財務考量上—我們一定還是會好奇天才與怪異之間的關聯性,
頁五十七
儘管當我們這麼探討時,會發現天才與天賦的區隔已從我們指縫間溜走。
比較可信的說法(至少這些觀點沒有被證明有罪),是一些把天才去神秘化而且不會任意化約成某種固執的看法。「咖啡對天賦是好的,」愛默生(Emerson)在天才與天賦的這個對照議題上說出他的看法,「但天才要的卻是祈禱。」顧爾德,如同我們都知道的,在生命晚期吞下為數不少的止痛劑與抗焦慮的混合藥物:那麼這算咖啡還是祈禱?畢卡索,這位深諳天賦豐沛為何物的大師,更絕:「天才,就是那個身上擁有只值一文錢天賦的名人。錯誤,有時就這樣從尋常情況中不期然地發生了。」而不同於一般兩極化的說法,法國詩人梵樂希(Paul Valéry)提出一個乾脆的共棲論。「有天賦沒天才不會怎麼樣,」他說道,「但有天才沒天賦就什麼都不是了。」後面這句話推敲起來,不無可能是在影射那些二十幾歲晚期唸完大學之後,一齊湧入每個歐洲和北美大城鬧區酒吧、咖啡館的年輕藝術家,他們大多是男性,身上擁有程度等級不一、未被時代發掘的藝術天份。
葛蘭‧顧爾德是天才嗎?如果我們已經準備好嚴肅精準地看待「天才」這個標籤的話,答案當然是「是的」。請注意在康德的《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中,天才並不是一個跟天賦對比的概念—畢竟這些爭論實在是徒勞無功的遊戲—相反地,天才是創造性天賦的一種特殊形式。
頁五十八
「天才是那個為藝術制訂軌則的天賦(或與生俱來的天份)。」康德指出。他意思是說,天才是在藝術領域制訂新標準的能力、亦即有能力重寫規範書的那個人。既然如此,天才一定是少見的了,因為所謂規範準則如果每五分鐘就打破一次,那就不叫規範準則了。天才的特殊能耐在於他或她有辦法制定新的軌則,並證明為什麼之前的軌則是有所不足的。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天才也算是證成了孔恩(Thomas Kuhn)所論之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即新的軌則不僅能夠解決問題或解釋先前軌則所無法解釋的特例現象,而且還能夠說明為什麼之前那個軌則是無法運作的。(問題可能就只是出在蕭規曹隨、一種制度僵化之後的無效及愚蠢;而那個特例現象很有可能就是那位天才的存在。)顧爾德那迅速竄紅的一九五五年《郭德堡變奏曲》,從輕快的省略到顯然熱愛速度甚於情感的詮釋方式,在在打破了所有演奏巴哈的規則;以及因為這麼做了,於是這個版本重新寫下這方面的規則。
不管怎麼樣,一直談論規範準則什麼的恐怕有失焦點。「天才是一種製造的天賦,在那種範疇裡頭,沒有任何明確的規則是能夠被確立下來的,」康德繼續說道;「那不是一個可以靠循規蹈矩地學習就能獲致的成就。」因此,「天才是某個領域中一種渾然天成的天賦,他是這類天賦的示範性原創力,他完全根據自己的認知官能信手拈來、揮灑自如。」換句話說,也就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做去。其中尤其這個「信手拈來」更是箇中關鍵;
頁五十九
它托顯出天才的奧秘,天才打破規則而又進入一個無規則的世界—接著在「信手拈來」的情況下兀自締造了新的規則。因為,除了以上所提之外,天才還展示了一種示範:它標指出「去路」與「前景」,天才一方面必須擁有足夠的能耐理解現存的規則,這樣才能避免掉「富原創性的廢話」。天才「無法以客觀科學的角度描述或指出他是怎麼創造出這樣的作品,但他就是有辦法如大自然一般為藝術賦予規則。」由此康德標示出奧秘的幾個特點—天才沒有辦法解釋他是怎麼辦到的、以及他到底做了什麼、或這些天賦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以現代的方式來理解,天才反而是受到人的界線所侷限的。36適切地去理解的話,「禮物」(gifts)會是一個正確的字眼:掌管天賦的神將禮物送出,禮物是只能收下不可退回的;至於凡人的我們,只能彼此交換禮物。
顧爾德的天才在於詮釋,但這項天才可沒有稍較遜色或較不具開創性,尤其以音樂美學領域而言,更是如此,因為詮釋只能存在於演奏之中。他所造成的影響已經是眾人逃避不掉的課題;在他之後的演奏家,沒有人可以避開他所設下的範例,這個範例包括他深具原創性的作風和他對自己作法的種種論點。現在,每個人都必須透過他這個標準去演奏,說明為什麼要這樣彈、為什麼不這樣彈、以及如果就他的規範脈絡下自己有沒有超越他等等,總之不管怎麼樣,反正他就是不能被忽略掉。這是真的,有時候顧爾德會像一個剛打完賽事的運動員,
頁六十
坦率但稍嫌有欠考量地急於說明他到底要幹嘛。在表達上,他比大多數人都來得清晰精準,更別提是運動員了,顧爾德的口才當然要好得多;然而,這當中始終存在著一個危機,那就是他的理論化說明會侵蝕掉他在演奏時所體驗到的美妙。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正是顧爾德生命中的一個核心面向,而這份張力也始終未獲得妥善的解決。
頁六十一
第七章
夸德力貝
在《郭德堡》序列中,第三十段變奏是一首集錦曲(quodlibet)。「夸德力貝」(Quodlibet)這個拉丁字有點等於「什麼都行」的意思,用更口語一點的說法,就是「任何東西」。在音樂作曲上,集錦曲這個標題乃指一個段落,鬆散地吸納某個主旋律的片段,而這個主旋律通常取自民間歌謠或流行樂曲,被整合吸收進來的片段,隨後被融入到一個樂曲結構較為龐大嚴謹的作品,此即集錦曲的意思。巴哈的集錦曲也是如此,他用了當時兩首著名的德國民謠作為源題材料;但這段變奏開頭的幾個小節是整首作品當中少數幾個其低音部音樂線被清楚拱出的段落。第三十段變奏,這個「雜物箱」或「任何東西」的變奏,在整首作品中以一個興高采烈、半認真半滑稽的面貌出現,在我們進入最後重複出現的詠歎調之前,幫我們把許多線頭、情緒重新整合在一起。這是一個刻意處理成不規則風貌的倒數第二段,直截了當而出人意料。
「夸德力貝」這個字也有神學論爭的內涵及意向,出現在經院哲學以列舉法提示神性昇華的特點時。
頁六十二
Quodlibet ens est unum, verum, bonum seu perfectum,中古世紀的學者們這麼說道。意思是說:凡是唯一、至真、至善、完美的主體,即為昇華。這裡的「凡是…的主體」點出了一個比表象所見更為神秘的東西。「任何東西」並非只是一個文法上的指物代名詞、裡頭填什麼都無所謂,並不是這樣的。它同時是一個本體論的(ontological)主張—有一個如是這般的存有(being)。一個什麼樣的存有呢?一個「任何東西」的存有。「夸德力貝」既是純粹的單數(那個特定的存有),也是絕對的概述(裡頭所填入的任何詞項都被認為是其可能性)。「夸德力貝」標示出樣本與階級之間、行動與潛能之間、特定和普世之間的混沌深淵。按照定義,個別存有只能算是眾生百態裡的千萬個例,在這個意義下,個別存有才會是徹底的單數。這是怎麼說的呢?亞里斯多德把所有的潛力分成兩種:一種是做什麼的能力,一種是不做什麼的能力。這兩種潛力裡頭,後者聽起來一點也不像能力,反倒像是無能。其實不然,不做什麼的能力事實上是更強大的能力,因為它把可以做什麼的能力聚積在內並統御著它,將這份能力斂藏在無限的潛能之中。於是,這個既是什麼、又可能不是什麼的狀態就是那個「夸德力貝的存有」(quodlibet being)。如同我們可以想見的,這個「任何東西的存有」裡頭已經包含了「意志的行動」(libet)—或這麼說更好,裡頭包含了「意志的潛能」、即意志的被懸置。37
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這麼敘說這個議題:「儘管每一位鋼琴家一定都有演奏與不演奏的潛能,」
頁六十三
他說道,「但葛蘭‧顧爾德是唯一一位能夠『不是』『不演奏』的鋼琴家。」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意思是說,顧爾德不但能遨遊在演奏不演奏之間(這個是大家都能辦到的),而且還能夠主動將他的「不演奏」製造成另一種形式的演奏—「這麼說吧,他是用他『不演奏』的潛能在演奏。」這個只有顧爾德可以辦到,因為只有顧爾德擅長將二流演奏變成一個可能性,儘管這麼說有點自相矛盾。「他的絕佳能力一方面直接罷黜並排遣掉他『不演奏』的潛能,」阿岡本結論道,「但另一方面他的精湛琴藝隱身並運作在他潛能不演奏的行為中…而這並不是他『不演奏』的潛能。」38
顧爾德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於美國洛杉磯給出他生平最後一場公開演出。他彈了巴哈《賦格的藝術》中四首賦格、巴哈的D大調第四號組曲、貝多芬的作品一百0九和亨德密特的第三號奏鳴曲。事前他並沒有宣布這場會是他最後一場對外演出,也不曾透露那一趟演出會是他的告別巡迴演奏。那一趟行程中其實還有其他場演奏會,但他把那些場次全部取消。
雖說打從五歲開始他就在公眾場合上演奏,但距離他在美國初次登台仍達將近十年之久。當時他才三十一歲。
初征美國的那幾場演奏會真的是傳奇,值得好好回顧當時在國際上造成的旋風與效應。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顧爾德在華府演出;九天後,他到了紐約演奏。
頁六十四
顧爾德極度清楚這幾場演奏會對他的重要性,因此在挑選曲目時可謂費盡心機,企圖尋找一套既可以完全彰顯他技巧面之高超能力,又可以凸顯他特出音樂見解的演奏內容,希望這樣一組菜色能對一個籍籍無名鋼琴家的首度登台產生好的效果。(他特殊的音樂見解即他對浪漫派曲目的反感,顧爾德不喜歡浪漫派曲目的喜怒無常及誇張曲風。)因此他下了一著險棋,選了他最喜愛的曲子之一、吉本斯的孔雀舞曲及輕快的雙人舞曲《沙利斯伯里王》(“Earl of Salisbury” Pavan and Galliard),這首曲子結構錯綜複雜,為鋼琴家的琴藝形象墊底。再來是斯威林克收錄在《費茲威廉處女樂集》的幻想曲(Fitzwilliam Fantasia)、五首三聲部創意曲(Three-Part Inventions)、巴哈的第五號組曲、魏本的《變奏曲》作品二十七(Variations op. 27)、貝多芬的第三十號奏鳴曲作品一零九、以及貝爾格的《鋼琴奏鳴曲》作品一。換句話說,這是一套聰明的曲目,幾首耳熟能詳的作品,搭配幾首罕見曲目,一齊透過他那萬中選一的精湛琴技和對音樂的敏銳理解展現出來。
華盛頓那場演出只吸引到一小搓聽眾,但樂評反應極為熱烈。樂評保羅‧休姆(Paul Hume)寫道:「要斷言整年度最好的音樂會是哪一場,一月二號這一天決定沒錯是太早了點,但看樣子一九五五這一年我們恐怕聽不到比這場更精湛的鋼琴獨奏會了,要想聽到比這位鋼琴家帶給我們更多的美與啟示的其他場演奏,我們要真的非常好運。」39 顧爾德把同樣全套曲目搬到紐約市立音樂廳演出,觀眾同樣也是不多,只是當中來了一位權力顯赫的聽眾。大衛‧歐派翰(David Oppenheim),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大師經典部門(Masterworks division)藝術家與選曲總監,
頁六十五
在一位音樂家亞歷山大‧施耐德(Alexander Schneider)的引介之下,出席了這場音樂會,並如預期般地對顧爾德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聯繫了顧爾德的經紀人華特‧洪柏格(Walter Homburger),提出一個三年的獨家合約—這是歐派翰第一次只憑一場聽審就決定簽下一位音樂家。
這紙合約導引出顧爾德往後漫長的專輯錄製生涯。而從這個時候開始,顧爾德就持續在大眾面前演出,事實上是迅速擴充他的演出行程,以應付不斷成長的需求:尤其在同年稍晚、他的第一張《郭德堡》專輯發行之後,顧爾德的聲望便牢牢釘在市場上,從此未曾下墜。那一段歲月,某種越來越固定的模式便開始浮現。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繼一九五五年美國巡迴首演獨奏會之後,顧爾德再度到美國,獻出他的美國協奏曲首演。他在底特律跟指揮家保羅‧帕瑞(Paul Paray)所領銜的底特律交響樂團(Detroit Symphony Orchestra)合奏了貝多芬的第四號鋼琴協奏曲。那場演出顧爾德總共出來謝幕謝了六次。但評論多聚焦在他古怪的舞台舉止、他的駝背、他的哼唱。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八日:顧爾德在安大略省的溫莎(Windsor)演出相同的協奏曲,但這一場他差一點取消了,因為他的神經緊繃到極點。他只彈出了一場二流水準的演奏會。三天之後他又再跟多倫多交響樂團合奏這首曲子,那次是由厄尼斯特‧麥米連爵士(Sir Ernest MacMillan)指揮。往後三週他沒有演出任何場次。他感到「極度地痛苦」,到多倫多市立醫院找一位神經科醫師求助。醫生開給他Largactil和Serpasil兩種藥,
頁六十六
這兩種藥是精神與情緒失調方面常用的處方藥,包括用在精神分裂症等等,但有時也被用來治療失眠症和焦慮症。顧爾德把這兩種藥加入他平常巡迴演出時就會使用的混合藥物;出外演奏時,在上場演出前和下了舞台之後,他都會慣性地使用多種藥物來鎮定神經。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六日:顧爾德首度跟指揮家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及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合作演出。他的貝多芬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的精彩演出造成空前的轟動與成功。伯恩斯坦說:「他是音樂界這麼多年來最精彩的一件盛事。」顧爾德在接下來那一季中演出了三十場音樂會。隔年,五十場。座位全賣光、門票大搶購、出席人數破紀錄等等變成家常便飯。
一九五七年夏天:第一趟海外巡迴展開。顧爾德首站去到前蘇聯,他是第一位在後史達林時代造訪俄國的加拿大鋼琴家及北美音樂家。顧爾德的恐懼心理更形惡化,且被媒體誇大:關於他對吃的疑慮、害怕在公眾場合嘔吐、害怕搭飛機、害怕被群眾包圍,通通被拿來大作文章。
五月七日他在莫斯科音樂學院的音樂大廳(Great Hall of the Moscow Conservatory)演出第一場音樂會,那是一場鋼琴獨奏會,他彈了巴哈《賦格的藝術》中四首賦格、E小調第六號組曲、貝多芬第三十號奏鳴曲作品一0九以及貝爾格的奏鳴曲。開場時坐不到三分之一滿的音樂廳,到了終場時已經被觀眾塞到爆滿,因為聽眾們在中場休息時間衝出去打電話通知親友趕快趕來聽下半場。曲畢,顧爾德收到長達二十分鐘的歡呼與掌聲,
頁六十七
遂得回以一段頗長的安可曲:包括一首斯威林克的幻想曲和十段郭德堡變奏。當大廳的燈全亮起時,觀眾還是繼續在鼓掌,後來走出音樂廳之後,顧爾德還被樂迷們團團圍住。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與莫斯科愛樂交響樂團(Moscow Philharmonic)在柴可夫斯基音樂廳(Tchaikovsky Hall)演出貝多芬第四號鋼琴協奏曲及巴哈的D小調鋼琴協奏曲。座位售罄。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柴可夫斯基音樂廳一千五百個座位再度銷售一空,外加九百個站位及臨時在舞台上加置的座位。曲目是完整的《郭德堡變奏曲》、布拉姆斯的兩首間奏曲、亨德密特的第三號奏鳴曲。掌聲長達三十分鐘。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二日:顧爾德在莫斯科音樂學院辦了一場當代音樂的演講獨奏會。主題是十二音列音樂,彈了貝爾格的奏鳴曲、魏本的《變奏曲》、還有克瑞納(Krenek)的第三號奏鳴曲當中的兩個樂章。有幾位音樂學院的教授臨時退席以示抗議,但觀眾們歡聲雷動。安可曲:部分的《郭德堡變奏曲》及《賦格的藝術》。掌聲歡呼震耳欲聾。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抵達列寧格勒(Leningrad)演出。瑪麗音樂廳(Maly Hall)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舞台上加座位。警察被請出來維持秩序,控制大廳外拿不到票的滋事群眾。顧爾德彈了逾三小時之久,
頁六十八
包括安可曲中的整首貝爾格奏鳴曲,最後只得不斷致謝道歉,方得離開舞台。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波修瓦音樂廳(Bolshoi Hall),一千三百個座位全數售出。另加座位一千一百席。與列寧格勒愛樂交響樂團(Leningrad Philharmonic)合奏巴哈D小調鋼琴協奏曲和貝多芬降B大調協奏曲。安可曲,以及更多的安可曲。顧爾德最後一鞠躬已經是一邊穿外套、一邊戴手套了。之後他重複講一場跟在莫斯科一樣的演講獨奏會。到場聆聽的學生對十二音列音樂的反應,他說,「製造了一種氛圍,讓人感覺好像是第一位踏上火星或金星的音樂家,也讓人感覺好像在跟一群懵懵懂懂但渴望學習的聽眾講述一片浩瀚未知的大地一樣。」40
這時的顧爾德已經被如火如荼的演奏事業牢牢箝制住,形成一個雙重的壓榨效應。他的演奏會越成功,他就有更大的壓力必須去重複、甚至擴增演出行程。而演奏會也不可能再只是維持單純的演奏會。各方的人情壓力、阿諛奉承大量湧入,對演奏家來講造成相當大的精神負擔,第一層焦慮是他對特定情境的抗拒,第二層焦慮則是來自第一層焦慮所帶來的壓力。宴會、餐聚、巡迴、應邀出席社交活動—這些都是演奏會之外看不到的額外耗損。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顧爾德去到柏林,跟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領軍指揮的柏林愛樂交響樂團(Berlin Philharmonic)合奏貝多芬C小調第三號鋼琴協奏曲。
頁六十九
預演的時候,整個樂團對他報以熱烈的掌聲和喝采。這幾場演出獲得空前的成功。歐洲的指標性樂評家史度肯施密特(H.H. Stuckenschmidt)寫道:「他技巧面的能耐好到難以置信;他兩手俱強的靈活流利、聲勢上的機動調度、和音色上的豐富變化,依我的經驗聽起來,在在顯示出繼布索尼(Busoni)之後就沒再出現過的精湛級數。」41顧爾德再怎麼飄飄然都不可能言過其實,因為樂評反應確實那麼好,他忍不住記住了評論當中的幾行字,後來常常轉述給朋友或同事聽—儘管這位樂評家史度肯施密特有點像後來顧爾德為電視節目發明的一位嘲諷的虛構角色,賀伯特‧馮‧侯赫麥思特博士(Dr. Herbert von Hochmeister)。
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顧爾德在前往此趟巡迴最後一站維也納的途上,於月台上巧遇指揮家李奧波‧史托可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史托可夫斯基是顧爾德的偶像之一。當時史托可夫斯基是世界級的音樂名流,妻子是紐約名媛葛莉亞‧范德比(Gloria Vanderbilt)、並跟好萊塢巨星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傳出緋聞,一九四0年迪士尼(Walt Disney)出產的動畫名片《幻想曲》(Fantasia),片中即找來史托可夫斯基跟米老鼠(Mickey Mouse)握手。當顧爾德得知這位偶像指揮家竟然一路對自己的迅速竄紅都瞭若指掌時,簡直激動到不可置信。兩位巨星也握了手,雖然沒有照片存證。稍後,在維也納音樂節(Vienna Festival)中,顧爾德彈了巴哈的十五首小交響曲(Sinfonia)、貝多芬的第三十號鋼琴奏鳴曲作品一0九和魏本(Webern)的《變奏曲》(Variations)。曲畢,又是全場歡聲雷動,現在顧爾德已經很習慣在最後謝幕時,一邊鞠躬致謝、一邊穿戴他的鴨舌帽、大衣、圍巾和手套。從這段期間開始,顧爾德的這套冬天穿著已經成為他的招牌形象,
頁七十
像他的制服一樣,在媒體上被大量刊載—這套穿著也變成顧爾德最喜歡自己的一套打扮。這一套形象的訊息是超乎表面上的身體意義的,諸如低的身體恆溫或害怕病毒侵染等等。真正的訊息是這樣:不管外在周遭的環境是幾度,反正葛蘭‧顧爾德站的那個地方永遠是冬天。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日,當顧爾德回到多倫多時,他的俄國之行已經被視為一項光榮勝利。他馬不停蹄地接著前往紐約錄製巴哈的《鋼琴平均律》(The Well-Tempered Clavier)專輯,而在這同時他仍繼續他那猶如懲罰般的演奏行程:秋季加冬季總共二十二場演出在等著他。當時節進入一九五八年,顧爾德即將要進行他的第二次歐洲巡迴演出時,他的身體像被榨乾似的疲憊不堪,可以聽出來他的演奏水準有明顯下降的趨勢,而且不乏有時候他在演奏會上會拿出另外幾首備胎曲目,告訴觀眾說因為原訂的演出曲目他練習地不夠充裕,這讓觀眾感到詫異。
從這段期間開始,顧爾德這塊演奏家招牌就慢慢出現頹象。他越來越常取消既定的演出行程,往往宣稱是健康因素。他抱怨的病症包括靜脈竇、呼吸道器官受損、飯店空調不當所引起的感冒、感冒所惡化成的氣管炎或甚至支氣管炎。演出旅途上,他越來越常一個人關在飯店房間裡。或許也都提出了一些好裡由。有一回在薩爾斯堡,同樣來自多倫多的鋼琴家安東‧庫爾替(Anton Kuerti)刻意找顧爾德一起外出晚餐,希望給顧爾德解解悶,
頁七十一
他點了小牛腦這道當地佳餚,當菜一端上桌,顧爾德痛苦地落荒而逃。
如今演奏變成一種嚴重的折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他跟卡拉揚及柏林愛樂合奏巴哈D小調鋼琴協奏曲,顧爾德比指揮給的提示整整提早將近一秒鐘切入,把整團的演奏者拋在腦後。同年十月,他取消了所有的演出,把自己關在漢堡(Hamburg)四季飯店(Hotel Vier Jahreszeiten)的房間裡頭,抱怨道腎臟發炎、肝臟問題。後來提到這段時間,他會用「準隔離狀態」(semiquarantined)來形容這個他認為是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個月。「在漢堡,我完全不認識任何人,這變成世界上最盛大的祝福。我猜這應該就是我的『漢斯‧卡斯托普』時光了吧;真的超棒的。」42
這真是駭人的景象。湯瑪斯‧曼的小說《魔山》是所有經典名著當中最富音樂性的一部,文中持續對時間、病痛和死亡做了沈思,這些沈思通通靈巧地安排融入到創作主題中。這部小說也是現象學(phenomenology)下一種自我剖析的練習,是對知覺事實的一種反芻。「這個書本身是對書裡所涉及的相關議題做一種具體呈現。」曼這麼說起自己的作品,「當書裡談到什麼、涉及什麼,那永遠就是書的閎旨與關懷。」那麼該書的閎旨又是什麼呢?它是以「時間性」(temporality)被經驗的知覺(consciousness)—當中既包含「時間」(time),也包含「永恆」(timelessness)。書的主題,如同莫瑞斯‧納坦森(Maurice Natanson)所寫道,既富音樂性,也有散文氣息,
頁七十二
「能夠立刻捕捉到所要呈現及所要聚焦的東西,並對於下文所要觸碰的議題帶來預示,讓人對情節與時間的進展(movements)產生一份特殊的思緒。」書中對主題及變奏往復檢視,以它特定的方式讓我們對時間升起某種知覺,「它預示,也駐留,」就如同「它在當下即時呈顯。」「駐留」(retention)、「前兆」(portent)、和「即時呈顯」(presentation):這是納坦森所稱的,被經驗的此刻、即當下之
「三重劇」(triple play)。43
卡斯托普本身是一個分裂的角色、一個多重的主題,他身上具有唐吉訶德式的狂想、還有傲慢、天真、多愁善感以及害羞等特質。他的人格形象被拆分成局部來解讀,由書中不同人物去檢視與感受他這個人,對他者而言,卡斯托普是耽溺的,永遠在他的症狀裡尋找自我。或許,就像卡斯托普一樣,顧爾德也該去一所他挑上的療養院住個七年八載,抽抽雪茄、聽聽留聲機,跟義大利自由派人文主義者薩登布里尼(Settembrini)、憤世嫉俗的反動份子猶太人那夫塔(Naphta)廝混在一起,為有著吉爾吉斯(Kirghiz)眼眸的女孩傾倒,鬆開他對時間的英明理論,讓他的計時器荒廢失修。當時間到了十一月十五日,顧爾德的冒險之旅來到佛羅倫斯,那場演奏會上,他彈的荀伯格組曲被觀眾發出噓聲,這是他進入專業生涯以來第一次在舞台上被噓。他遂考慮大量刪除接下來的演出行程,包括一趟到以色列的三週巡迴演出—十八天的行程裡頭要演出十一場的音樂會—但洪柏格說服了他別這麼做。
後來顧爾德只有再回去過歐洲一次,那是一九五九年夏天。但到了這個時候,輿論界對他都已經把焦點擺在他的舞台作風、
頁七十三
演奏會遲到請他人代打上陣、又是砍掉多少場音樂會云云爾。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他回到多倫多之後,從此他再也不離開北美。那一年稍晚、剛過完他的二十七歲生日之後,他也決定搬出他父母位於湖濱區的房子,告別這個半孤立的多倫多中產階級郊區—包括經典的安大略湖畔木板路、這裡的開放水域、以及這裡的封閉心智。一開始他是搬進溫莎徽章飯店(Windsor Arms Hotel)的套房,這是一棟在市中心的稜堡建築物,以經營風味下午茶和公寓住宅為主。這家新哥德(neo-Gothic)風格的飯店座落在聖湯瑪斯街(St. Thomas street)和蘇丹街(Sultan street)路口,就在多倫多大學的維多利亞學院(Victoria College)旁邊,設計者是柯爾克‧海斯洛普(Kirk Hyslop)這位建築師,一九二七年開幕之後,這家飯店很快成為多倫多市社交名流的最愛。(飯店裡那家雅致時髦的三屋餐廳〔Three Small Rooms〕是在一九六六年才開幕的。)
之後顧爾德曾考慮租下一幢叫「唐伽里」(Donchery)的鄉間豪宅,距離多倫多大概有十五公里之遙,豪宅內有二十四個房間、一座游泳池、一座網球場,不過他在最後一刻打消此念。沒租鄉間豪宅,他改住多倫多市內公園巷公寓大廈(Park Lane Apartments)的頂樓六房豪華公寓,於一九六0年年初搬進這棟位於聖克雷爾西大道(St. Clair Avenue West)的裝飾風(deco-style)住宅大樓。往後他終生都住在這裡,當年漢堡飯店的房內孤寂現在變成每天的生活調調。他仍持續接受演奏預約、繼續演出,只是每年彈的場次越來越少,
頁七十四
取消的越來越多。一九六一年到六二年這一季,他彈了十八場,一九六二年到六三年這一季,他才演出九場。一九六二年,他對飛行的恐懼終究制服了他:從此他不再登機。
阿岡本認為,儘管就表面上看來,顧爾德停止演出了,但他並沒有也不可能停止演奏。現在,彈奏是在他「演奏的潛能」內進行,每天在他「不演奏的行為」中反覆練習。「不演奏的行為」跟單純「失去演奏的能力」、或「剛好沒有演奏」、或僅僅只是從事演奏以外的活動,都是截然不同的。顧爾德的決定根本不算是一個真正的決定;這個動作其實是一個權力的操練,對自我、對音樂的一項權力操練,這項操練永遠都必須被重建及強化。他策動了「不演奏」來永續提示他的燦爛時光,而這乃是持續重申「任何東西的存有」的高超境界。他是一個「夸德力貝人」(quodlibet man)、一個純粹的潛能。在寂靜中演奏,使得音樂得以可能,那是一個在之前、在之後、以及在其間的無所不能。
顧爾德彈奏的,毋寧是寂靜。從這個觀點而論,他的「不演奏」、他的演奏寂靜或可被理解成他畢生所創造的最高藝術、一首生命之作。
頁七十五
第八章
競爭
所以阿岡本並不是把顧爾德的寂靜解讀成一種抵抗,而是一種聽覺之外的活動。從這個觀點來看,顧爾德或可被比喻成梅爾維爾(Melville)筆下的錄事巴多拜(Bartleby the Scrivener)和他格言式的聲明:「我寧可不要。」(”I would prefer not to.”)。小說中的巴多拜也是,一開始他的心態可能被解讀成抗拒資本主義及諸多制約下的辦公室生態,包括那些交易和運作邏輯。但後來我們會慢慢看出來,巴多拜的行為模式確實是比較偏好遲緩,將動作和言語拆解成許多步驟,而使之消弭無形。巴多拜最後死在遊民監獄。他不是卡夫卡筆下的「飢餓藝術家」(hunger artist),並不太明白他自己的抗拒和對社會的疏離,也不尋求那個已經遺棄他的社會之認同或喝采;但最後巴多拜知道他身在何處—以及他是這麼走到那一步。
有了這個終極認知,巴多拜「不動作的行為」(inaction-as-action)變成純粹性的一種成就、一個擺脫決定性因素的激烈態勢。「他用最極致的減法態勢去表達,」(用哲學家齊澤克的話說),以致於這時「身體和陳述已經合而為一」(借用評論家兼作家伊麗莎白‧哈維克〔Elizabeth Hardwick〕的說法),
頁七十六
這挑戰了理性這個字眼所代表的所有概念。44阿岡本嘉許「寧可不要」這個反覆重申的陳述其背後所斂藏的潛能。巴多拜「完美的繕寫行為」,從操作型的完美轉移成靜止不為,是一個「不繕寫」之永恆潛能的純粹舉動。阿岡本提到,在阿拉伯人的傳統中,亞理斯多德「智性代理人」(agent intellect)的這個觀念—即思考而不決策—是化作一位名叫「侉喇姆」(Qalam,意譯為「文墨人」)的天使形式存在,筆和筆所在的位置都有一股深不可測的潛能。巴多拜這個繕寫員,不僅只是停止書寫,而且是「寧可不寫」,可視為侉喇姆天使的極致形象,當中包含了沒寫東西以及不寫東西的潛能。45
跟巴多拜的「不繕寫」一樣,顧爾德的「不演奏」也有很多詮釋版本。顧爾德解釋自己開演奏會以及必須停止演出的諸多說詞提供了各種可能的敘事。從過往的媒體報導中,衍生出其他故事出現,擴充醫學方面及哲學方面的詮釋觀點。舉例來說,他在播報員約翰‧麥可路爾(John McClure)的採訪中一開始便提出兩個不同但不甚高明的理由,說明為什麼他退出演奏舞台。當被問及是否考慮重回舞台時,他公開答道「這個想法不太迷人」,接著他打斷麥可路爾的下一段話,那段話以分段語句來影射一種懸宕的質疑立場,麥可路爾原本在說:「一個富於魅力的演奏家生涯…?」
頁七十七
顧爾德迅即接話:「到底是令人厭惡的呢、還是死氣沈沈的、或者往事已成回憶?」然後顧爾德又緊接著說,「我想這一段跟當代音樂世界沒什麼關連。」46然而,「令人厭惡的」、「死氣沈沈的」、和「沒什麼關連」,三者可不盡相同。
不過,他為退出舞台所提供的第三個重要理由,乃在於綜論競爭和演奏這種場合的殘暴本質。競爭與演奏這兩種場合,都是建立在他所謂「惶惶不安的群眾」基礎上,聽眾都是為演奏失誤而來—絃樂器的絃剛好斷掉、一段搞砸的銜接樂段、一瞬間的進入失誤。「某種好奇、甚至是殘虐成性的嗜血慾征服了演奏會的聽眾,」顧爾德說道,「演奏廳內瀰漫著一種決鬥的本能渴望」。
而值此同時,在場聽眾其實是沒有資格參與這樣的專業評斷的。「大部份去聽演奏會的人又不是音樂家,對音樂也不太在行,我想。」他說道。他們為兩種理由而去,一個是返祖現象的重新確認—某種跟音樂毫無關係、自以為熱愛音樂的不正當鄉愁及迷惑假象;另一個是想親眼目睹不完美的邪惡慾望,好讓自己生活中的不完美藉機獲得消極的核可。儘管他下了這些鏗鏘有力的批判措辭,聽起來應該是很明顯了,但顧爾德卻否認他蔑視這些觀眾。
頁七十八
一般演奏會的聽眾,他說道,並不知道他要的是怎樣的一種演出,要是有人能比顧爾德知道的更多,就好像一名專業修車技工能明確指出「他開的車性能怎樣、牢不牢固等等,那麼他就有資格說話了。」47
人們本然的同理心是很有可能跟顧爾德站在一起的。所有的演出都會出現一些不太恰當的場面,觀眾表現地像個少數的專業行家般,在那裡品頭論足、昂首闊步,使人感到不勝煩擾—可是真正的行家,在所有觀眾群裡,真的只佔極少數。我們去聆賞演奏會,是為了尋求喜悅和薰陶。而演奏家出席演奏則是為了提供這兩項。在理想的情況下,這不應該變成一場零和遊戲或一場競爭;它應該比較像是一紙理想的合約,兩造都是開開心心地來,因為兩造都獲得了他們預期所得到的回饋。演奏者不僅得到酬勞,或說他所獲得的報酬不是只有金錢。他們從演出的行為當中獲致喜樂,因為他們展現了天賦與技巧。演奏家渴求掌聲與肯定,就如同毒癮者渴求藥物一樣,這個道理應該是不言自明的,這個想法也稍微緩解一下我們心中揮之不去的罪惡感,對這些容易受無情評價有時甚至是嘲弄的演奏家,我們心中難免感到不忍。
我們對於演奏家所展示出來的天賦會感覺到自卑,這個情況是演奏會這種機制所導引出來的;演出時,演奏家在觀眾面前安坐,坐在那高高隆起的舞台上。
頁七十九
但這份自卑感很快就會因為同樣一個機制而消解甚至撤回,取而代之的是第二順位的優越感:觀眾坐在底下,像評審一樣地審判著演奏家。這份優越感沿著兩個不同但互為相關的向量運作著。首先我們唾棄演奏家們的自戀,他們的自戀是我們假設已經潛藏於他們渴望在鎂光燈下演出的慾望;然後,源於這個特定的心理維度,我們感覺有資格來好好審判這場演出的優勝劣敗。於是,這就形成了所謂的競爭:儘管舞台上除了演奏家之外並沒有其他人、儘管這份競爭的概念極為抽象、看起來也只有一方存在,但演奏家確實是暴露在某種無形的競爭當中。或者,也可能更糟,有時候那位看不見的競爭者就是演奏家本身,較勁的是他之前的演奏水準—甚至也可能根本沒有之前的演奏高標,而是一種幻想中的完美標準、一個盛名聲望所化身的幽靈。
任何一個血肉之軀的演奏家都無望贏得這場比賽。若是提起任何一位演奏家在經歷一場災難性的演出後,有誰不是虛脫痛苦、奄奄一息的?這會讓人驚訝嗎?然後,污衊、憤怒代替讚美、奉承,繼之排山倒海襲來,喜劇諧星還會形容說「笑翻全場」,這難道又是新聞?當然了,在教養翩翩的古典音樂世界裡,說「笑翻全場」是比較不普及的用語!不過語下的衝動和競爭的本質是一樣的。
你來這兒付了錢看我演出,不管是表演什麼,反正這都是你不會的,因為你不會,所以你想付錢來看我表演。然後,你會針對這個你不會的東西做出審判,
頁八十
因為這是你唯一能做的,這項審判的權力已經內含在你所購買的票價裡。如此一來,在演奏會的表象下,便隱藏了這種零和遊戲的雙向契約。
顧爾德瞭解音樂世界對公開演出的競爭苛求,這方面他有更具體的例證可以抱怨,尤其是像小提琴或鋼琴這種備受矚目的獨奏樂器。他是這類競爭的痛苦受惠者,像所有天才那樣,他從茫茫競爭人海中脫穎而出、獲得輿論的關注,這份關注保障了成功階梯上的下一個梯級:先是拜於名師門下、接著是和交響樂團合開獨奏會、然後是巡迴演出、之後才會有唱片公司的專輯合約。他揭露了隱藏在這亮麗體制表象下的暗流。我們很容易接受競賽當中的這種輸贏邏輯,某人能夠得第一,是以其他全部人無法遂志為代價。我們找來日本某某十歲天才小提琴家、某某奧地利的十來歲鋼琴天才,把我們自己對音樂慾望所衍生的新興狂熱遊戲加諸到他們身上,看著他們在青春期間的生命從此邁入晦澀痛苦,而我們自己卻有辦法為這種毒害效應自圓其說。
然而如果從另外一個端點來看,我們可能會傾向於產生不同的視野。難道顧爾德內在的天才沒有比顧爾德本身還巨大重要嗎?難道他對此沒有一個正向的責任應該去分享他的天賦?
頁八十一
那如果不分享,起碼不該任意性地說退出就退出、還不給一個解釋吧?事實上,針對最後這一點,顧爾德早已準備好、甚至是十分急於提供解釋的。一九六八年這張由麥可路爾擔任採訪的對話唱片《葛蘭‧顧爾德:演奏會的退學生》,專輯封面上即列出了『部分議題』,包括下列這些標題:「演奏會已死」;「做專輯唯一的理由就是得做得跟別人不一樣」;「現場觀眾是一項嚴重的不利條件」;「電子樂是未來」。(還有「為什麼我邊彈邊唱」、「佩托拉‧克拉克(Petula Clark)的歌曲屬於後孟德爾頌傳統(Post-Mendelssohn Tradition)」。)
在這張唱片還有其他地方,顧爾德把他反對競爭、決定退出演奏舞台的理由講得一塌糊塗、一團混亂,使人更加困惑,形容得枯燥無味一點,聽起來簡直像一個情急絕望的自我辯白。現場觀眾會製造干擾,使人分心,於是恐怖的氣氛就來了。音樂會將被淘汰,因為音樂專輯廣為流佈。專輯唱片一方面雖是一場錄製的演出;但為了製造一個流暢無接痕的假象,錄製專輯時勢必動用到多重的錄音匣,在母帶上面進行瑕疵修飾、插入剪輯,並重新設定時間線(timeline)。做專輯的唯一理由就是推翻「把演奏錄下來就對了」的概念。所以未來是屬於一個完美的電子世界,在這個世界裡頭,專輯錄音會執行地毫無瑕疵或毛病。講這些話的同時,
頁八十二
顧爾德卻放縱他邊談邊唱的毛病、大聲到連錄音時也聽得見…呃,因為他可以,因為這些演奏都是掛在「顧爾德」這塊招牌底下。前述這張對話專輯,背面封套上引用了一段一九六四年《時代雜誌》的專訪,這段話道出了箇中微妙:「他所有的專輯錄音中都有一份優雅與詼諧,這讓他的音樂聽起來像是預錄的即興演出—一種個人風的、啟人冥想的、自由的感覺。這樣富於創意的興奮感是很少鋼琴家能夠達到的境界。」
原來不僅是預錄的演奏、更是預錄的即興演出!透過這段話的折射,我們可以隱約窺見顧爾德理想的大綱:一張唱片,經過完美地錄音、嚴謹地後製,可能經過幾天幾夜的演奏與混音之後,聽起來要像是音樂家隨興所做出來的音樂。不同於一些爵士樂或實驗派鋼琴家例如邁可‧史諾(Michael Snow)或凱斯‧傑瑞特(Keith Jarrett), 顧爾德從不在麥克風前即興演出,尤其凱斯‧傑瑞特也是以熱愛在鋼琴前邊彈邊唱聞名,哼唱到很大聲。48但從他的言論判斷,他確實是相信樂曲的詮釋、錄音過程中的重錄、剪輯乃屬於即興的一種形式。在一段一九七六年所拍攝的顧爾德與布魯諾‧蒙賽瓊的對話錄中(這段對話錄的文字稿後來刊於《鋼琴季刊》〔Piano Quarterly〕),蒙賽瓊譴責顧爾德常常忽略或極小化聲勢變化,也常常拒絕去留意樂譜上的速度記號,而喜歡「在所有十八世紀音樂中摻入一種即興元素。」
頁八十三
顧爾德歉歉然地為自己辯護,愉快地承認他略過所有莫札特曲子中的突強記號(sforzandos)、以及常見的琶音和弦(arpeggiated chords)。「我猜想你這麼做的原因是它們干擾了你作為一位即興演奏者的特權?」蒙賽瓊問道。「我得說我的理由不止於此,布魯諾,」顧爾德答道,「我覺得它們代表了一種我骨子裡清教徒靈魂所反感的戲劇性。」49
顧爾德老喜歡說,做專輯、錄唱片只是賦予音樂家跟其他所有藝術家一模一樣的自由而已:畫家可以任意在畫布上改變顏色、塗塗抹抹,作家可以刪刪改改、重新寫過。不過這當中的相似性並不盡然全盤一致:畢竟顧爾德是演奏者而非作曲者,就算他的詮釋被認定是藝術作品。(就像我先前所提到並判定的。)作曲家是可以把一首寫好的曲子拿來隨意改編重寫的;作曲家是唯一一位有資格說這首曲子什麼時候完成的人。而演奏者則應該是來彈這首曲子的,就某方面而言,我們保留一個美學倫理的權利,期許演奏者應當一路照本宣奏、按譜去彈。因此同樣地,灌錄專輯的音樂家至少也應該能夠並願意現場演奏或現場演唱。50觀眾把這樣的演出能力視為是一種信賴度的象徵、一個藝術上的誠信—儘管觀眾們自己也知道,信賴度和誠信有時候是很不穩定或很不可靠的指標。
頁八十四
我們在其他藝術形式中也觀察得到雷同的信賴感鬆動。例如劇場導演和他的劇組團隊不僅決定以聳動的場景重現莎士比亞戲劇—比方說以加州的黑道幫派份子來重構《羅蜜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這齣戲—甚至為了簡化劇情而把整段的原典精髓刪除掉。出於許多理由,這類的「創作自由」都被包容下來了:演出總得精簡啦、敘事必須洗鍊啦。可是如果因為這些情況本身的需要,我們接受了這樣的安排與決定,那麼換句話說,它們就變成是演出的內建規範與需求。這跟看電影的接受型態是很不一樣的,我們看完電影,是可以對電影拍攝的實際耗費時間及情節拍攝的先後次序保留質疑的。
電影是顧爾德最能拿來譬喻類比的創作題材—所以他會一再地提到電影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包括前述這張為自己退出演奏舞台而辯解的對話專輯、一九八0年跟哥倫比亞唱片合作滿二十五週年所推出的《銀慶專輯》裡頭那首多重人聲的「夢幻創作」(譯按:即《所以你想寫首賦格?》)。一個演奏者或許真的可以類比成一位導演,導演要思考劇本、跟演員們溝通、不斷要求重拍、在刻意佈置及管控的場景中要求演出必須看起來自然。以及沒有一位導演會同意應該以一種「現場精神」去導一場戲,
頁八十五
即便是那種要凸顯現實世界中的做作、不自然的劇情時也是如此。事實上,以媒體的本質來講,那樣的「現場精神」根本很難想像。
顧爾德處在世界對音樂的態度產生巨變的時刻。他的事業開展於音樂專輯首度在錄音技術與市場普及度兩方面臻於成熟的年代。他膽子夠大,敢於說出音樂專輯的最大價值不在於成為現場演出的替代品,而是音樂專輯本身就是一種媒體。如今看來完全正確。他唯一在思考上犯的失誤是錯以為這樣的交替會是二分法的排他狀況:也就是誤認為新媒體一定會取代舊媒體。就像麥克魯漢可能曾經告訴過他的—事實上這真的不無可能,因為他們倆真的偶爾會碰碰面或一起出席活動—新的媒體並不會取代舊的,而會像年輪那樣,長成新的一圈。專輯唱片並沒有抵銷掉現場演奏,就像電視也沒有消滅掉廣播、廣播同樣也沒有使報紙絕跡一樣。由於在觀點上犯了這個根本錯誤,使得顧爾德接下來反對音樂會的論調基礎出現瑕疵。
他成為「演奏會的退學生」的真正原因不是哲學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但這並不是在說他退出演奏舞台的原因是明顯或容易理解的。就他的處境而言,那時把這個論點當作一種立場來訴說,作為拒絕融入演奏會那個既定系統的理由,誠然是協調的:
頁八十六
利用當時聽起來很時髦的「演奏會的退學生」說詞,然後宣稱自己要轉向電子世界錄製專輯,由是,顧爾德被包裝成古典音樂版的提摩西‧李雷(Timothy Leary)。這套說詞對他有利,並不是因為他認定演奏會是觸怒人心、值得反對的,而是因為他自己覺得演奏是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前者的理念卻是能夠立刻合理化並包庇後者。在這樣的包藏之下,這套說詞將這位喬裝大師的心結拉抬到另外一個層次,聽起來顯得深得人心多了,他可是深深受益於這套說法。顧爾德拒絕演出的理由宛如一個高投資報酬率、可堪反覆援引的舞台出口,而當他在敘說這些理由的時候,顧爾德可就不那麼保持緘默了。
但這麼理解也還不是事情的全貌。值得留意的諷刺是,顧爾德高調轉入專輯錄製反而是所有舉動當中最強烈的競爭性發展,因為錄製專輯直接與科技未來掛勾。音樂專輯是一種經濟學家稱之為「可規模化的活動」:亦即一次的錄製工程完工以後,就不必再持續投入成本,之後可以一再地帶來收益。一張複製好、發行上市的唱片,就可以捕捉到廣大的聽眾群,而這群聽眾在演奏會的模式裡卻勢必會被切割分散的,因為聽眾不可能同時跑去聽兩場音樂會。由此推論,每一張被買下的葛蘭‧顧爾德專輯都會降低另一位音樂家被聆賞的機率。這就跟暢銷書和賣座電影一樣,熱門專輯在本質上同屬於這種「贏者全拿」的市場;唯一不同的是,音樂專輯的競爭者並非僅是另一張專輯唱片,而是其他所有型態的音樂體驗。所以說啊,什麼才叫競爭!
頁八十七
第九章
時間
所有的音樂都有拍子記號,從日常聽到的標準2/4和3/4、到巴爾托克(Bartok)一些玄秘難解的7/4和9/8、電台片頭曲的10/4、卡洛斯‧山塔那(Carlos Santana)、慈悲管弦樂團(Mahavishnu Orchestra)或法蘭克‧扎帕(Frank Zappa)的發明之母合唱團(Mothers of Invention)那種頸骨折斷似的的極快19/16。但不管這些節拍記號有多複雜,所有的音樂都是假設時間是可被使用的,或說的更確切一點,時間是可被分割的。沒有這個前提,節拍和樂譜就無從被安排起,然後,也就沒有我們所謂的音樂可以存在。然而,到底什麼是時間呢?以及它的可分割性是位於何處?
偉大的蘇格蘭哲學家休姆(David Hume)以蘇佬特有的雄赳赳氣勢談論這個問題,把它視為一個被錯置、但也是淘氣的問題。當我們試著要審視時間這個主題時,我們什麼都看不見,因為本來就沒有時間這樣東西可以去看。時間是經驗的一個抽象概念,但這個概念卻是經驗本身所無法攫取掌握的,這也就是懷疑論者會常常拿來舉例說明觀念(ideas)有一個眾所皆知的特質,即不受管束卻又四處流竄。
頁八十八
所有內含了邏輯上及數學上的必然、這類知識都是從我們感官印象中去延伸開展的,而關鍵性的檢證卻顯示我們對這個叫「時間」的東西沒有任何感官印象。更別提從這個視野下所延伸的諸多推論之一,那個我們所稱的「自我」也不過是一部記憶的虛構小說罷了,這部小說乃由我們所憶起的過往事件所構成;以及根據過往事件其已然落定的特性,幾乎是無從針對未來事件做出任何可行的預測。
乍聽之下,這些推論可能都是反直覺的(counterintuitive),但理智又很難針對這些推論去回應什麼—充其量理智所能做的,是依侍特定經驗所產生的想法去推論某個問題。休姆將意識(awareness)的延續性安置在自我(self)與時間性(temporality)的感知裡頭。但意識延續的可行性有什麼條件呢?難道不該就是對延續本身的知曉嗎?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一個連續性(continuity)和次序(order)的框架來讓經驗成立的話,一個經驗如何可能成為經驗呢?這個答案,康德認為(回應休姆的「哲學裡的不堪」〔“scandal for philosophy”〕),必然是時間與空間乃感性(sensibility)的先在形式(pre-existing forms),是這兩者使得經驗本身成立。我們不經驗這些形式;但它們是任何經驗的必要前提。我們無法從經驗主義下的知識去得知這兩個形式;
頁八十九
但我們可以、事實上是必須、去假定它們,以作為執持任何類似像經驗型知識這些事物的存在。51葛蘭‧顧爾德,跟所有音樂奇才一樣,在演奏這個特定行為中把這套整體假設做一個更外顯、明晰的揭露。事實上,正因為顧爾德演奏中很大一部份是時間的遊戲和部署—包括在節拍速度上大玩花樣、斷句上的鮮明處理(發音〔articulation〕這個字本來即含有對時間節奏之多元安排的意思)—他一再洩露出他作為一個感受力大師的特質。在先前的篇章裡,我曾說過顧爾德是演奏寂靜、而不是演奏樂譜,他的寂靜甚至包括「退出演奏舞台」這麼大的規模。或許,推到極致,形容他是在演奏時間本身,這樣的說法是不是更直截了當些?但是在一開始,讓這般的時間演繹變得可行的那個「時間之可分割性」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沒有時間上的測量與分割,音樂無從可行。從某個角度來說,時間的測量與分割正就是音樂,我們不斷從作曲及演奏中接收到聲音,而這些
聲音乃透過部署好的樂曲結構及關係中傳送過來。汽車的喇叭聽起來就是一個音符—專家說最常落在F調或G調—這等於海鷗的叫聲;但這兩者都不是音樂,儘管它們的音調是可以在音樂當中被找到的。(豪華禮車裡,那種可以奏出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頭四個音符或通俗名曲「迪克西」〔“Dixie”〕第一音節的喇叭不在此處討論範圍內。)在一個上昇的音階裡、按照某個拍子記號來進行,假以適當的安排去組織,
頁九十
這時聲音就構成了音樂(的可能性)。一份標準的音樂部署、在圖表上顯現為樂譜形式,事實上它是時間及聲音的交涉:五線譜既有水平軸,也有垂直軸。
樂譜傳統一直到十六世紀才真正確立下來,而且一旦確立之後,迅速傳遍歐洲、廣被採用,到了十七世紀中葉,這套譜記辦法已成為穩固的系統。至於音樂本身,不用說大家都知道,是遠比譜記更加古老。就這層意義而言,音樂譜記辦法及其內含的時間分割功能,恰可理解成二十世紀才發明的機械鐘。精準的計時裝置、不管多麼實用,並不含機械鐘的單位邏輯,它單獨使用時,是能夠帶來精準、均等的時間測量。時間的經驗和計時的實踐,是早於時間單位概念而存在的:所有的文明都仰望日與月過活,隨著季節更迭而生活著。
因此回顧起來,計時中的分割特性應該被理解成我們對時間的存活經驗所產生的意外特質,而不是時間經驗的必要條件。換個說法就是,某一刻我們忽然停下來,考量到時間消逝的這種感覺,於是便以某種可靠的度量衡來計算這種感覺。之後我們感覺這個辦法很有用,
頁九十一
甚至開始覺得必要了。但這個分割、就跟一般的測量一樣,仍是透過抽象過程來進行—這又是另一個後事實(post facto)的幻象,不管它多麼不可或缺。那麼自然地,一旦這個動作完成之後,這類的抽象運作便能提供強大的工具來服務我們人類的各項目的。可是它們仍舊只是工具,它們仍是倚靠這些未被言說的假設前提才得以實踐。測量和分割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所挑釁謂之的「偶然先驗」(“contingent a priori ”)—而非康德的「綜合先驗」(synthetic a priori),也就是這些先決條件是被假定存在,但並非絕對必要的。我們得以切割時間,並不是由於時間具備某種單位基礎的屬性,而是我們假定有一個結構的輪廓—這個輪廓,就跟所有框架一樣,是同時具有暴力與自由的形式—這個輪廓存在於我們對時間的揣想中。
每一個音符之間,存在著一個坑塹;每一段音程裡頭,也有真空虛無隱然逼近。音樂的時間、被測量的時間,都是在真空虛無之上的纖弱懸浮。這時再想想爵士樂團貝西伯爵(Count Basie)所唱的:「這是你聽不出所以然來的樂符。」或顧爾德所說的:「它〔偉大的音樂〕是個人特性的終極論證—在這個論證中,一個人可以創造他自己的時間叢聚而不受時間加諸到我們身上的強制性所束縛。」52
人們不得不好奇,在顧爾德表露無遺的熱情所造成的掙扎之下,他是否真的享受演奏音樂。
頁九十二
我意思是說,不在音樂會場子裡,而是純粹就彈奏音樂這件事,他到底喜不喜歡呢。這個問題並非無中生有、沒事找碴。在布魯諾‧蒙賽瓊為顧爾德於一九八一年錄製新版郭德堡專輯時所拍攝的室內影片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情景之一,是有一幕鏡頭靈巧地捕捉到這位天才迷失在音樂中、迷失在時間裡的模樣,他那柔軟的指法—當時他四十九歲!—宛若在時光中輕盈細緻地攀爬。沈醉、忘我了,是的。但快樂、昂揚嗎?還是更像某種成癮者,自願坐困在他的慾望牢籠裡?在同一個時刻裡既被囚禁、也被釋放,在同一個剎那中既施予控制也被驅動,不企圖馴服時間,而是懇求著時間…
第一章
詠歎調
那聲音:聽起來急驟、精準、自鳴得意,帶點炫耀浮誇。
皺巴巴的旁白裡,充斥了不甚高明的解說企圖,就像個太常講述內容一模一樣的學者,永遠在同一個段落強化同一個重音、插入同一個典故,由於實在講過太多回了,聽起來是這麼地迂腐油亮。那聲音也是戲謔的,帶有娛樂效果、慧黠、迴腸盪氣、兼惡作劇。它深切地投入其中,但並不閃爍其辭或自我耽溺。講述者自問自答,津津有味地咀嚼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一系列的問題當中,還會出現連講述者自己都覺得可怕或嚇人的問題。
他的語句結構俐落,段段精實,令人信服之餘,也帶有...
推薦序
不演奏的演奏.複音化的複音
龔卓軍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 副教授
一、事件:多重感覺場景
本書譯筆之活潑生動,讓我不由得回頭重新耽讀同一位譯者的另一本顧爾德傳記譯本,凱文.巴札納(Kevin Bazzana)所寫的《驚艷顧爾德:品味鋼琴巨擘的生命與藝術》(Wondrous Strange. The Life and Art of Glenn Gould)。在巴札納的這本傳記裏,我再次注意到顧爾德早期的一個演奏場景。這是一場在多倫多的演奏會,曲目是貝多芬C小調鋼琴協奏曲,一位樂友這樣回憶:
舞台上的指揮蘇斯金下了暗號,同一時間顧爾德才放開他手中的袖珍小譜、蠻不在乎地加入樂曲。幾乎沒有跟觀眾打招呼,就滑到自己的琴椅上蹺起腿來,全心全意地盯著譜看(這個譜,想也知道,他早已瞭若指掌)。他對上了蘇斯金起的第一拍,之後是這首協奏曲著名的交響樂開場白,他的手一直指揮個不停,表面上好像是對自己比的,但觀眾怎麼可能視而不見。在接近他自己的開場八度音階時,他的頭還是埋在譜本裏面、雙腿還是翹著,直到鋼琴該切入前的萬分之一秒時,他豁然合上譜子扔向空中,琴譜在鋼琴的低音狂暴聲中同時落地,跟他切入的起拍對個正著。這個時間點是完美的,他的腿還是翹著,而開場的八度音階無懈可擊。1
這裡有一場音樂會,這個是事件。聲音的振顫四處漫延,循環的樂章伴隨其泛音傳遍空間。顧爾德的演奏傳遞著多重的感覺。首先,聲音有其音高、強度、音色等等內在特質。但是,這裡除了樂器的聲源,還有顧爾德手中譜本飛起和落地撞擊地板的聲源,以及他自己後來隨之哼唱的喉音聲源。而無論是樂器、譜本、地板與喉音的聲源,都不只在傳出聲音,它們各自還感應著自己的聲音,並且在感受自己聲音振顫的同時感應著其他的聲音。這些是主動的感知,讓這些聲音在攝受自身時,也攝受著彼此:首先是協奏樂團的訴說,就像一群引吭高歌的小鳥,然後是孤獨的鋼琴傾聽著牠們的訴說,並且回應牠們,鋼琴的聲音好像來自附近的一個小島。這彷彿是暴雨來臨的前一刻。
不同的聲源即是感覺的細密微分,這些微分的感覺又以它們的感覺自我填充,形成多重感覺的共振感,相較於客觀譜本所標記的音階音符,各種聲源將本來潛藏的純粹潛能,變現為現實化的狀態,這就成為了顧爾德音樂演奏的事件性。音樂會的聲源,原本只有協奏樂團編制的各種樂器,以及鋼琴兩個部分,原本,每個聲源只能掌握它自己的感知,但它們還能與另一個聲源提供的感知產生協調,這中間依據的無非是和諧的規則,在和諧中,它們共屬於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宇宙。
但是,顧爾德的演奏帶來了許多無法協調的感知:譜本、地板與喉音。這些聲音來自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宇宙,而且是無法與樂器聲源的宇宙協調的聲源,於是,原本古典的單一世界與宇宙,在這裡產生了無法共存的宇宙之間的相互拮抗,聽眾同時聽到好幾個世界之聲源的相互拮抗與相互表出,樂器、譜本、地板與喉音,它們相互分叉,往外發散,聽眾覺得受到不同世界聲源的干擾,塑造著多重感覺無法共存的多重世界,使原本單一的宇宙因此保持開放狀態,在不和諧中保持著往多重世界過渡、伸展的發散性,保持著力量的彼此衝突、危機狀態,於是,古典理性的單一世界崩毀,和諧終結,多調性或無調性展開了複音的多重感覺世界。我們在這個四分五裂的多重世界迷宮中,聽見了顧爾德。
對馬克‧肯威爾(Mark Kingwell)這位哲學家來說,顧爾德所創造的聲音或靜默,溝通或存在感,都引領我們走入無法共存之多重聲源、多重角色、多重平行宇宙的感覺場景。如同多重異質觸覺同時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不同部位,我們為之暈眩,難以用既有的語彙溝通,而只能體會到它們的事件力量。
二、科技:過濾後的(不)演奏
從顧爾德事件化的演奏實踐,指向不和諧的多重感覺場景出發,我們才能理解,肯威爾在本書中的哲學立場,並不是在談論實在界各種聲源感知所構成的多重可能表現模式,而是在討論從力量部署的「虛擬性」如何走向前所未有的現實化過程。這種「虛擬性」,包含了顧爾德如何透過遠距科技,穿梭在虛構的角色、表象、人格、聲源科技的錄製與建築之間,達成哲學家阿岡本(Georgio Agamben)在本書第七章中所謂的「不演奏的演奏」,介於不從事音樂廳現場演奏與自我構築的錄音演奏之間。
古典音樂會對演奏的預設,就是達於和諧式的聲源共振。即使到了1958年,最早的揚聲器陣列表演,出現在布魯塞爾的世界博覽會,由柯比意設計的聲響宮置入了多重揚聲器,並由艾德加.瓦黑斯(Edgar Varése)作曲,長達八分鐘的〈電子詩歌〉(Poème Electronique)表演之後,和諧式的空間藝術仍然停留在古典或巴洛克式的設想:建築體、色彩、影像、聲音與音樂。但是,與此同時,多重感覺場景的事件性演奏,如同後來的約翰.凱吉(John Cage)所示,已經開始走向舞台,走出古典式、巴洛克式演奏的邊界。多聲部游走相互競爭的模式走向破毀,精神分裂式的發散式展演開始露出力量,這是一種後結構的賦格神遊。
這個企圖依恃結構、批判結構、並翻轉所有結構的後結構時代,顧爾德的音樂實踐遊玩其間。樂譜結構、表象結構、時間結構、樂器結構、電腦結構、音樂廳的建築空間、音樂會的運作結構、依附性的社交結構、媒體的言論結構、整個城市空間部署的結構與其聯結的官僚結構、資本流動的結構,都成為製造其異質音樂的運作要素。影響顧爾德音樂思想甚鉅,同為加拿大籍的媒體哲學思想家麥克魯漢(Mashall McLuhan)在同一個時期興起,並非偶然。而顧爾德對多重感覺場景的技術性控制論思考,亦遠非即興為之。
顧爾德可以說是二戰後成長的第一代標準宅男。一般讀者會對顧爾德愛用電話交際(而且只主動打給朋友而不主動接電話)、愛耽溺在電視前、愛研究與實驗各種嶄新的錄音設備、愛操作媒體並透過媒體表現自我,印象深刻。我們可以說,這些行徑都指向新傳播科技媒體給予藝術家的非人文主義養分。宅男所關心者,無非是原有世界結構的運作法則及其極限。然而,他們也了然於心,結構之對位關係,並非實在世界之本然。反而是古典哲學對實在世界本然狀態的預設,開始被這些後結構的音樂實踐思考者所挑戰。如同藝術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透過「布瑞洛箱」和媒體複製的邏輯所示,藝術家打破藝術世界的既有結構,已經成為藝術自我證成的重要行動指標。特別是在六○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政治反叛運動、嬉皮反文化運動影響之後,結構主義思想已顯現疲態,令各種結構源生的「虛擬性」(virtuality),開始成為眾多藝術家與哲學家探索的重要目標。
在本書作者的眼中,顧爾德儼然成為「虛擬性」哲學思考的音樂先峰代言者。第三章討論的「傳記敘事與現實虛構」、第七章討論的「夸力德貝的純粹潛能狀態」、第十一章討論的「演奏與遊戲」、第十六章討論的「表象和音樂錄音就像電影一樣」,可以說是突顯顧爾德這種「虛擬性」思考特質的幾個重要章節。或者,更進一步說,顧爾德的音樂實踐,做為當代藝術的一個思想事件,迫使我們不得不尋求以「虛擬性」思考為出路,否則,一種談論顧爾德的思考勢將落入俗套,無以為繼。
三、自我虛構:複音化的複音
「北方」可以說是顧爾德自我虛構的重要結點,是一個混沌的「夸德力貝」(Quodlibet)──它可以在任何空間生產出其分身。「北方」對他而言,不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場域,而是一個宅男藝術家的「青少年之夢」:「一個位於北極的超人總部、一個孤寂的堡壘、一個典範級的秘密俱樂部會所,裡頭有圖書館、實驗室、陪你玩西洋棋的時器人和健身設施。」我們可以說,「北方」不過是這位藝術家孤獨的創作心靈的虛構力量場所。但是,這種虛構不只是小說式的想像情節,《孤寂三部曲》的多重混音剪輯,做為其「對位式廣播」的多重聲源播放實踐,使得他得以拉出藝術創作的高度,而非停留在理論式的紙上談兵。
「北方」做為顧爾德自我虛構的結點,集結了哲學家李歐塔(François Lyotard)所謂的「後現代思想實驗」與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謂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精神分裂」,換言之,在後結構與後現代的消費社會處境中,每個人都在夢想著自己欲力極致的「北方」,只不過,顧爾德有勇氣走入這個夢境中,打造他的音樂展演基地。這是本書第十二章與十四章的要旨。
就像電影《偶然與巧合》(Chance or Coincidence)中展現的加拿大當代思想氣質,透過擷取、側錄、蒙太奇、多聲部錯落接續與打破線性敘事結構的企圖,顧爾德做為當代鋼琴演奏者的失落與創傷,得以救贖。這種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謂的「對位式意識」,不再只是某種音樂曲式上的佈署技法,而是一種企圖維持永遠新奇狀態的多層次聲源彼此對照、相互競逐,在反覆中形成差異的發散式創作風格。
顧爾德喜歡在廣播節目中同時以不同聲音,虛構出三位、甚至五位個性迥異的人物,並且以此自嘲自娛、樂此不疲。或許有人會以病理學的角度去解釋這不過是種精神分裂、亞斯柏格症或控制狂的病癥。但是,顧爾德讓這些本來可能只是病癥的行為表演模式,超越了病理的意義。我們假設,這種後結構的感覺邏輯,其思考的主要特徵就是不要停留在單一意識、單一人格的第一人稱狀態,我們假設,就像許多兒童的多重自我扮演遊戲,顧爾德的「自我虛構」是一種終極的後人類自我實驗,嘗試透過多重聲音穿透人類單一意識與聆聽經驗的極限,回返兒童對於歷史時間與單一自我建構的本能抗拒,逾越古典人文主義主體想像的界限,那麼,他對技術與機械物件的耽溺(史坦威鋼琴CD318),他對分身狀態的偏好,以及願意去承受這些角色扮演所帶來的巨大焦慮──以虛擬性解構單一自我──或許可以得較好的理解。透過這種觀點,本書第十九章詮釋了顧爾德那令人難解的自我分裂癖,它使得顧爾德這個「人」不再是個單一人格,而成為人類的一個「事件」,也成為後人類的一種「自我技術」。
哲學家德勒茲在《皺摺:萊布尼茲與巴洛克》(Le Pli)一書中,討論了巴洛克音樂到新巴洛克音樂的多調性、多重聲源佈署,其中最重要的音樂實踐思考轉折,就是法國作曲家與指揮家皮耶.布雷茲(Pierre Boulez)所說的:「複音的複音」(polyphony of polyphonies),透過事件化、科技化與自我虛構的後結構思想,肯威爾這本哲學性的音樂家傳記,引領我們為顧爾德的音樂實踐加上一個指向多元聲源世界的動詞,「複音化」的複音。經過複音化的複音,聲源的多重化、技術的多元化、自我的多樣化,顧爾德創造的極大化音場,便是萬籟俱止後的寂靜。
不演奏的演奏.複音化的複音
龔卓軍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 副教授
一、事件:多重感覺場景
本書譯筆之活潑生動,讓我不由得回頭重新耽讀同一位譯者的另一本顧爾德傳記譯本,凱文.巴札納(Kevin Bazzana)所寫的《驚艷顧爾德:品味鋼琴巨擘的生命與藝術》(Wondrous Strange. The Life and Art of Glenn Gould)。在巴札納的這本傳記裏,我再次注意到顧爾德早期的一個演奏場景。這是一場在多倫多的演奏會,曲目是貝多芬C小調鋼琴協奏曲,一位樂友這樣回憶:
舞台上的指揮蘇斯金下了暗號,同一時間顧爾德才放開他手中的袖珍小...
作者序
全球獨家中文版序
從我經驗到後來驅使我寫這本書的那一刻開始,我便一頭栽入這本書的研究裡。我一生都對音樂十足熱情,但只有小時候參加兒童唱詩班的時候曾經想過成為一位音樂家,之後便徹底放棄這個想法。我自知以一位哲學家去撰寫一位偉大的音樂家,這並不是一個尋常的選擇。
但那一個時刻卻向我顯現,為什麼這會是一個絕佳組合、以及為什麼我這麼想是好的。我依序聆聽葛蘭‧顧爾德所有的音樂專輯。它們聽起來都很出色,但當中有幾張尤其感人。當我聽到奧蘭多‧吉本斯(Orlando Gibbons)《C大調幻想曲》的開頭幾個音符,我全身因感動而起了一陣寒顫哆嗦。這位也是顧爾德最愛的作曲家。在所有美學媒材中,音樂既是最輕盈細緻、也是最強悍有力的形式。一首歌能夠將我們立刻帶回到過去時光中某個心碎的時刻、或喚起我們久遠前曾到過的地方,它可以使我們的雙眼充盈淚水、也可以教我們哽咽難語。
在這首幻想曲作品第一樂段的地方,你可以聽見顧爾德輕柔地悶哼,那是一連串從容美麗的下降顫音。他著名的琴椅在他彎腰靠近鍵盤時咯吱作響。每個音符之間都留有間隔,這使得每一個音符都是一篇神啟,富於結構與和諧的神啟。它們之間的時間、也就是這些個寂靜,跟琴響毫無二致,都是道地的音樂。
然後突然間我覺得:介於錄音彼時和聆賞此時的中間,就是那個被磨滅的當下。我聽著音樂,靜靜感受到,過去的某個東西也存在於現在。這兩個人之間的距離、兩個心智中間的距離—他的和我的、或他的和任何其他聆聽者之間的距離—瞬間灰飛湮滅。我們在這段神秘的開頭裡融為一體,這開頭就像森林裡的一片空地,於是我們把這叫作音樂經驗。
在我的生命中,曾無數次地被音樂感動過,我相信大家都是,但這卻是我第一次被一位音樂家感動了。於是對我而言,顧爾德的個人悲劇、他肩上背負的重量遂再也不是抽象的處境。我所書寫的,再也不僅只是顧爾德這個人。我而是寫著顧爾德在我身上所產生的深邃效應。
以及這也是我在理解為什麼直到今天人們依舊覺得顧爾德魅力無法抵擋時所看出來的原因:他的音樂,保存在這些錄音裡頭的音樂,一次又一次把我們每一個人帶回到他憂悒的心靈。這是他帶給這世界所有愛樂者的永恆禮物;這也是我的「顧爾德時刻」,在這種時刻裡,只要憶想著一位音樂家和他的音樂,所有一切便全然改觀。
* * *
顧爾德的對外溝通是出了名地難搞,既隱遁孤寂卻又長篇大論,他似乎永遠巧妙地避開傳記敘事的魔掌,閃躲掉傳記對一個完整人生的虛構揣測。然而他的理念卻又反向地激發出目前市面上出版的許多傳記。通常我們都把顧爾德認知成一位具有罕見天賦的演奏家,但其實他的演奏真的就是他思想的聲音紀錄。許多音樂上的艱深課題始終縈繞在他腦海裡:音樂到底是屬於物質性還是非物質性?我們所聽到的音樂是一串揭露內在結構的序列、還是一道經過協調過後的時刻之流(stream of moments)?在音樂的表象與實相之間是否存在著什麼差異?以及現場演奏是否在倫理上優於唱片專輯,或者反之為真?
顧爾德甚至提出了一些更尖銳的問題,直搗傳統的哲學領域。我們把音樂稱作一種以時間為基礎的媒材,好像我們知道音樂就是憑恃時間裡的某個東西而成立似的。可是,問題來了,到底什麼是時間呢—是一種存續期間(duration)的經驗嗎?還是經驗得以成立的前提要件?或是兩者都是?兩者都不是?還有去經驗時間、去經驗音樂的那個意識呢?更別提存在本身,是演奏著音樂、詰問著難題、或只是呆坐在那裡?又,到底誰、或者什麼是「我」,這個我們每個人都奉於中心的「我」—真的就是那個中心嗎—這個我們身處的世界的中心?
顧爾德發表過的著述揭示了他在這方面議題的深邃但未能系統化的潛思。他喜愛在文章裡鋪陳戲謔與諷喻,不只一次地自問自答,並以其他誇大性格的虛構筆名來撰稿,而且寫作時極盡挑釁之筆調,就像他在讚揚佩托拉‧克拉克(Petula Clark)和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時一樣。他的幽默感都很笨拙,有時甚至聽起來未脫稚氣,但這些事例,一如他那出了名的慮病症、反社交傾向、演奏時花樣百出的姿態等等,都是呈顯出他碎裂的存有、朦朧的人格特質中的諸多面向。即便是顧爾德擅自作主的服藥習慣—不用說,那當然是促成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因素—也是他意識重擔的一個徵兆、天才與聲望之累的邪惡代價。
只有採取一個萬花筒式的觀點,才能給予這位複雜而執拗的人一個公正的評價。 當然在這本書裡頭,我會附上所有必要的生平細節,不過在他一九六四年成為聲名狼籍的「演奏會退學生」之後,這些事蹟細節還是遠遠不足以構成或述說顧爾德,但也已經是盡力挑選出最沒有爭議的事例了。同時我也試圖去釐清及解析何以顧爾德在文章和專輯中會呈現出這麼多不同、甚至常常是矛盾對立的生命狀態,包括他後來跨足製作關於孤寂的廣播記錄節目系列。
* * *
當顧爾德在紐約錄製他第一版的巴哈《郭德堡變奏曲》專輯時—這張專輯也是為他奠立早年聲望的作品—他把開頭的詠歎調留到最後才錄。這闕詠歎調樸實而美麗,據傳是巴哈為治療薩克森的凱薩林伯爵(Count Keyserlingk of Saxony)的失眠症所作,譜寫時間早於《郭德堡變奏曲》後續的三十段變奏。也有人猜測它是巴哈寫給妻子的禮物,雖然這闕詠歎調是鑲嵌在《郭德堡》這首大型且被廣為公認是巴哈最困難的鍵盤作品之中。
當顧爾德最後終於要來錄這闕詠歎調的時候,他發現他得完整地彈完二十一遍、而且這二十一遍都有收錄下來,然後才能達到他滿意的水準。這件事對我來說,其意義似乎遠超過只是顧爾德廣為人知的完美主義之另一例證。「這個問題是這樣的,」他後來說道,「錄完前二十個版本,是為了要削減掉所有我對這首曲的多餘詮釋,而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更難做到。」
在這生滅的人間世走過一遭,顧爾德並非只在單一、固定而安穩的主題上開展生命,這個以大寫為開頭的「生命」;相反地,他一次又一次從不同的領域、不同的重心去探索生命可以到達什麼程度,尋找著那個被遮蔽、難以捕捉、到最後似乎根本不存在的正當(rightness)。那個被選取的版本,永遠都只是眾多版本當中的一個。
所以到頭來,我的書變成一本有著二十一章短篇的結集—一個內含二十一段哲學小品的系列。它們訴說了顧爾德生命的故事,值此同時又帶著一份認知,明白生命的故事絕非如此,絕非外在的生滅表象所看起來的那樣;這是一個由樸實的開端、中段與結尾所構成的故事。以及它們的內容,是關於許多大哉問的命題:諸如天才、時間、孤寂、演奏、寂靜、意識……。但這些探討都是植基於這位非凡之人他一生中所發生過眾多而感人的生平事蹟。
這本書能夠譯成中文,獻給華文讀者,真是一項光榮與喜悅。謹以此書跟世界上所有愛顧爾德的朋友分享!
M.K.,
二0一0年誌於多倫多
全球獨家中文版序
從我經驗到後來驅使我寫這本書的那一刻開始,我便一頭栽入這本書的研究裡。我一生都對音樂十足熱情,但只有小時候參加兒童唱詩班的時候曾經想過成為一位音樂家,之後便徹底放棄這個想法。我自知以一位哲學家去撰寫一位偉大的音樂家,這並不是一個尋常的選擇。
但那一個時刻卻向我顯現,為什麼這會是一個絕佳組合、以及為什麼我這麼想是好的。我依序聆聽葛蘭‧顧爾德所有的音樂專輯。它們聽起來都很出色,但當中有幾張尤其感人。當我聽到奧蘭多‧吉本斯(Orlando Gibbons)《C大調幻想曲》的開頭幾個音符,我全身因感動而...
目錄
目次
◎推薦序
<打破傳統彈奏風格的鋼琴家>顏綠芬(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
◎推薦序
<哲學家的音樂萬花筒> 焦元溥(《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談錄》作者、資深專欄作家)
◎中文版序
<我的「顧爾德時刻」> 馬克・肯威爾(Mark Kingwell)/本書作者
◎專文導讀
<不演奏的演奏與複音化的複音>龔卓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1 詠嘆調Aria 1
2 寂靜 Silence 19
3 虛構 Fiction 23
4 記憶 Memory 29
5 存在 Existence 37
6 天才 Genius 45
7 夸德力貝 Quodlibet 61
8 競爭 Competition 75
9 時間 Time 87
10 建築 Architecture 93
11 演奏 Play 99
12 疾病 Illness 105
13 清教徒 Puritan 117
14 北方 North 129
15 溝通 Communication 139
16 表象 Appearance 151
17 進步 Progress 161
18 藝術 Art 169
19 角色 Personae 175
20 驚奇 Wonder 187
21 收錄 Takes 195
致謝辭 225
附錄一 年表:顧爾德的音樂人生 附錄二 顧爾德錄音作品一覽表
目次
◎推薦序
<打破傳統彈奏風格的鋼琴家>顏綠芬(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
◎推薦序
<哲學家的音樂萬花筒> 焦元溥(《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談錄》作者、資深專欄作家)
◎中文版序
<我的「顧爾德時刻」> 馬克・肯威爾(Mark Kingwell)/本書作者
◎專文導讀
<不演奏的演奏與複音化的複音>龔卓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1 詠嘆調Aria 1
2 寂靜 Silence 19
3 虛構 Fiction 23
4 記憶 Memory 29
5 存在 Existence 37
6 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