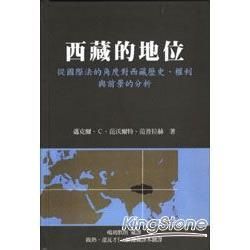第一章:古代政治史
公元821年的藏中條約與贊普時代
西藏與蒙古:宗教勢力的興起
從世俗統治到神權統治:歷輩達賴喇嘛
第二章:達賴喇嘛領導的政府以及蒙古、滿清、廓爾喀的介入
達賴喇嘛至高無上的權威
滿清對西藏的干涉
西藏與滿清關係的雛形
廓爾喀的入侵與滿清對西藏最後的干涉
滿清放棄保護的職責以及尼泊爾對此的挑戰
第三章:「大角逐」中的西藏
西藏的孤立主義與封閉的土地
與俄國的外交關係和與英國的條約關係
西藏---列強間的簽約主題
第四章:西藏堅持其主權獨立
驅逐滿清 恢復獨立
中國與英國的新政策
三方會談與1914年的《藏英協議》
第五章:謀求國家生存延續的努力
西藏對英國的信任與寄託
尋求與中國的平衡關係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
拓展國際關係
第六章:從獨立時期到遭受侵略
活躍的外交
共產中國的威脅:逼近的侵略
第七章:各種政治實體的法律地位
國家的地位
依賴關係與其他受制約的關係
中國與國際法
第八章:西藏的歷史地位:結論
從世俗國家向宗教國家的轉變
十八世紀西藏與滿清的關係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
入侵前夕西藏的地位
第九章:對西藏的「和平解放」或入侵
軍事入侵
中藏協議
中國吞併西藏的法律問題
第十章:西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盪的幾十年
合作、抵制以及反抗
拉薩、北京與達蘭薩拉三方的關係
西藏目前的地位
第十一章:超越歷史與現實,尋求公正的解決
藏人尋求自決權符合國際法
尋求解決方法
【附 錄】
1.公元821-823年《藏中條約》
2.公元1684年西藏與拉達克簽訂的條約
3-1.公元1842年拉森代表交給西藏的建議
3-2.公元1842年西藏與克什米爾簽訂的條約
4.公元1852年西藏與克什米爾簽訂的條約
5.公元1856年3月西藏與尼泊爾簽訂的條約(據尼泊爾文本)
6.公元1856年3月西藏與尼泊爾簽訂的條約(據藏文本)
7.公元1876年英中《清浦條約》
8.公元1886年7月24日英中間有關西藏與緬甸問題的條約(引自英中條約)
9-1公元1890年3月17日在加爾各答簽定的中英有關錫金的條約
9-2西藏與錫金就商業、交通、草山的章程,公元1890年英中條約附加條款
10-1.公元1904年9月7日藏英《拉薩條約》
10-2.公元1904年11月11日中英對拉薩條約的補充聲明
11-1公元1906年中英有關西藏的條約
11-2公元1906年4月27日英中就尊重在西藏不給外人提供工作機會的照會
12.公元1907年《英俄條約》
13.公元1893年為修改西藏通商章程而由中、英、藏三方簽署的協議 371
14.公元1912年8月12日藏中協議
15.公元1912年12月14日藏中協議
16.水牛年1月8日(公元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詔示
17.公元1912年12月29日藏蒙《烏蘭巴托條約》
18.公元1914年7月3日藏英聯合聲明
19.公元1914年在西姆拉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附件
20.公元1914年7月3日藏英通商章程
21.公元1914年藏英全權代表有關藏印邊界問題的照會
22.公元1918年8月19日中藏臨時停戰協定
23.公元1918年10月10日藏中為就結束戰爭自願撤軍問題的
協議
24.公元1950年11月7日在噶倫堡給聯合國的信件
25.十七條協議
26.聯合國大會決議
【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