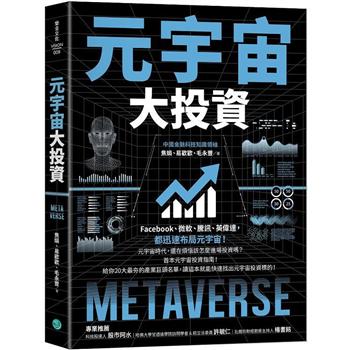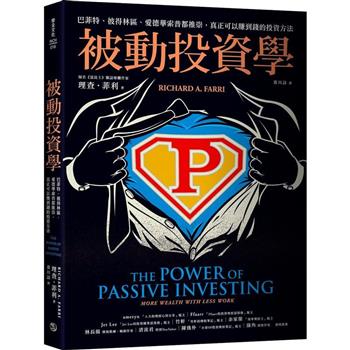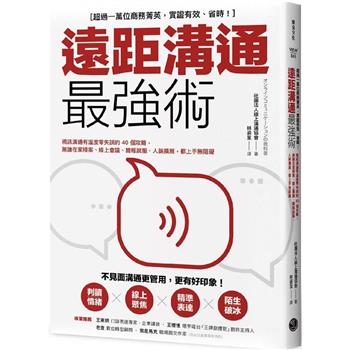日本攝影三大巨擘 森山大道最新親筆著作
收錄近年來多幅未發表的攝影作品,以及經典散文
「對我而言,所謂藝術,是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出裂縫般的瞬間,讓我透過縫隙,一窺異界樣貌。在此意義之上,與藝術的邂逅,根本就不需要博物館、美術館甚至畫冊之類的媒介。」
所以,在《邁向另一個國度》中,森山大道書寫的是日常。
他不僅用照片,也以靈光之筆寫出隱藏在表象之後的現實片段,日常生活所映照的一切。
「那一瞬間,日常生活的深邃處反轉外露,隱約可見。」
「那份可窺見的黑暗,正是核心本質所在。」
這是不僅席捲日本,也征服了全球的森山大道。
這位一代攝影大師在他「從心所欲」之年,沉殿回顧夏威夷及布宜諾艾利斯等地的攝影旅程、與生命中數位女性的曖昧情愫,以及平交道、橋樑、花器、動物園等日常風景在他心中的意象,以及隨之喚起的深處記憶……他的影像作品充滿直接原始而強烈的情緒,文字間的內心風景卻時而隱晦幽深。
書名邁向「另一個國度」,可能是和他氣味相投的魅力城市——
「唯有精明幹練才能生存」的新宿、充滿「可疑氣息」的布宜諾斯艾利斯……
也許是他內心蒼茫的風景,因為——
「路上的悲劇與喜劇多得不可勝數。攝影師唯一的應對方式是恣意拿起相機,一股腦的深入,此外別無他法……」
近距離接觸過森山大道的人,對他的描述多是「隱忍、壓抑、寡言」;
攝影評論者認為「對未來的絕望感」是森山作品的主要關注;
大師的拍照姿勢,通常是右手單手拿相機,左手……抽菸或是插口袋!
我們只能走近再走近,深入再深入,然後拼湊出一代攝影大師的「另一個國度」。
本書特色
◎獨家收錄多幅森山大道最新攝影作品
◎森山大道最新親筆著作
◎日本三大攝影巨擘系列 第一部(餘二為:荒木經惟《荒木經惟的天才寫真術》;杉本博司《直到長成青苔》)
作者簡介
森山大道
1938年出生於大阪。因喜歡船而曾夢想成為船員,卻先成為平面設計師。
決心成為攝影家的契機,是偶然看到了街拍大師威廉.克萊因的成名攝影集《紐約》。
1961年(23歲)在攝影家細江英公的工作室從助理做起,3年後以獨立攝影家身分出道。
1971年(33歲)發表了攝影代表作之一《攝影,再見》。
從此,日本人造了一組「森山專用詞彙」來形容他作品帶有的獨特印記——「□□(粗粒子)、□□(模糊)、□□(晃動)」
粗粒子的顯像、模糊的對焦、晃動的人物風景,森山大道顛覆了當時攝影強調正確寫實、相片即是紀錄工具的概念,強烈衝擊日本攝影界。
1980年代,日本歷經約10年的泡沫經濟時期。森山戲稱︰「那十年間我幾乎完全沒做事……我身上唯一泡沫化的事物,只有那累積到快腐爛的時間而已。」(摘自本書〈日日皆海參〉)
1999年,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為他舉辦個展,這是美國一級美術館首次為日本攝影家舉辦完整回顧展;2003年,巴黎卡地亞藝術基金會為他舉辦大型回顧展。近年來他的作品頻繁於日本及歐美展出,皆獲高度評價。
在日本國內,森山大道與荒木經惟並列為最具影響力的兩大攝影家。
森山大道直至今日仍維持創作質量,《邁向另一個國度》為其最新親筆著作。
譯者簡介
蘇志豪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具備日本通譯案內士國家考試資格。
熱愛日本文化與一個人的日本深度旅遊,曾擔任日本國寶級現代舞大師石井綠即席口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