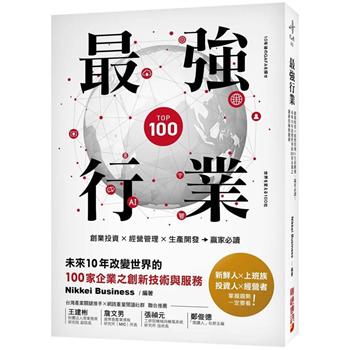畢來德分析指出的中國的沉默,就是中國人依然活在其中的,許多人熟視無睹、充耳不聞的總體社會氛圍...是在現實的重壓與誘惑之下,那樣一種彌散開來的對歷史與真相的漠然,更準確地說恐怕已是一種弄假成真的遺忘,一種系統化、有組織的失憶,其後果則是整個社會沉浸在一片渾噩的集體無意識之中,充斥著散沙般的無奈與汲汲營營的自得。
因緣際會,這本小書的中文譯本首先是要在台灣出版。畢先生信中聲明:「書中所講僅止於北京政權,而非中華民國。」那麼,在台灣看中國的沉默又意味著什麼呢?
台灣近年來不少人愛講「中國因素」。這本小書的一個啓發可能在於,今天我們在台灣談論中國因素的時候,是否也能意識到台灣身上的中國因素?包括某些台灣獨立主張者們身上的中國因素?因為這本書所揭示的一個重要的「中國」現象是,在一個壓制個性、排擠差異,推重統一、強制和諧的社會當中,衝突的協調機制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被壟斷、被潛規則化;而加之以宗法文明源遠流長的深層次社會分斷結構,一個透明開放的公共精神世界便愈發難以形成。畢來德講的是中國,但台灣又何嘗不是如此?
台灣版特別收錄:
2012年5月21日於巴黎法蘭西人文與政治科學院講座「政治哲學角度下看中國的過去」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沉默的中國的圖書 |
 |
沉默的中國 作者:畢來德 / 譯者:宋剛 出版社: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10-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213 |
科學科普 |
$ 220 |
中文書 |
$ 223 |
人文歷史 |
$ 225 |
史地 |
$ 250 |
中國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沉默的中國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畢來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1939年-)
瑞士中國思想史學者,日內瓦大學退休教授。1987年日內瓦大學成立中國研究部門,畢來德獲聘為第一位教席教授,並帶領該部門直到1999年退休,其後轉移重心於寫作上。
畢來德主張打破中國在本質上的他異性(l’altérité foncière)這個迷思, 「 ……跳脫這種迴圈思維,由反向思考,假定人類共同經驗中存有本質上的一致性,然後由此出發,試圖去理解我們研究的現實中國,並盡可能以最直接的方式來認知現實…… 」。
其《莊子四講》(Leçons sur Tchouang-tseu, Editions Allia, Paris, 2002),《莊子研究》(Études sur Tchouang-tseu, Editions Allia, Paris, 2004)正是這種學思態度的體現。2010新修訂版的《論中國書法及其深層基礎》(Essai sur l'art chinois de l'écriture et ses fondements, Editions Allia, Paris, 2010 )更是藉由探索歧異間的共同基礎以使得理解成為可能。而於2000年出版的《沉默的中國》(Chine trois fois muette, Editions Allia, 2000, 2006)及2006年出版的《駁于連》(Contre François Jullien, Editions Allia , 2006)更是從宏觀角度批判中國研究的問題,皆引起熱烈討論。
繁體中文版《莊子四講》由聯經出版。《沉默的中國》與《駁于連》則由無境文化出版。
譯者簡介
宋剛
譯有蕭沆《解體概要》、畢來德《莊子四講》等。
畢來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1939年-)
瑞士中國思想史學者,日內瓦大學退休教授。1987年日內瓦大學成立中國研究部門,畢來德獲聘為第一位教席教授,並帶領該部門直到1999年退休,其後轉移重心於寫作上。
畢來德主張打破中國在本質上的他異性(l’altérité foncière)這個迷思, 「 ……跳脫這種迴圈思維,由反向思考,假定人類共同經驗中存有本質上的一致性,然後由此出發,試圖去理解我們研究的現實中國,並盡可能以最直接的方式來認知現實…… 」。
其《莊子四講》(Leçons sur Tchouang-tseu, Editions Allia, Paris, 2002),《莊子研究》(Études sur Tchouang-tseu, Editions Allia, Paris, 2004)正是這種學思態度的體現。2010新修訂版的《論中國書法及其深層基礎》(Essai sur l'art chinois de l'écriture et ses fondements, Editions Allia, Paris, 2010 )更是藉由探索歧異間的共同基礎以使得理解成為可能。而於2000年出版的《沉默的中國》(Chine trois fois muette, Editions Allia, 2000, 2006)及2006年出版的《駁于連》(Contre François Jullien, Editions Allia , 2006)更是從宏觀角度批判中國研究的問題,皆引起熱烈討論。
繁體中文版《莊子四講》由聯經出版。《沉默的中國》與《駁于連》則由無境文化出版。
譯者簡介
宋剛
譯有蕭沆《解體概要》、畢來德《莊子四講》等。
目錄
譯者緒言
法文再版序
沉默的中國:論當代歷史與中國
引子
I. 連鎖反應
II. 中國個案
III. 三重沉默
IV. 結論
論中國歷史:以斯賓諾莎為出發點
斯賓諾莎的觀念∣中國個案∣中國的一體化是怎樣完成的∣奠基時刻∣長久特徵∣權力觀∣兩個世界∣謀略取代政治∣總體論述∣中國在當代∣當前的混亂∣第一種視角∣權力的問題∣文化的問題∣第二個視角∣結語
版本註記
台灣版特別收錄 :
政治哲學角度下看中國的過去(2012年5月21日於巴黎法蘭西人文與政治科學院講座)
法文再版序
沉默的中國:論當代歷史與中國
引子
I. 連鎖反應
II. 中國個案
III. 三重沉默
IV. 結論
論中國歷史:以斯賓諾莎為出發點
斯賓諾莎的觀念∣中國個案∣中國的一體化是怎樣完成的∣奠基時刻∣長久特徵∣權力觀∣兩個世界∣謀略取代政治∣總體論述∣中國在當代∣當前的混亂∣第一種視角∣權力的問題∣文化的問題∣第二個視角∣結語
版本註記
台灣版特別收錄 :
政治哲學角度下看中國的過去(2012年5月21日於巴黎法蘭西人文與政治科學院講座)
序
譯者緒言
這本小書譯成中文,首先是希望生活在中國的朋友能讀到。希望他們能聽到一個感覺自己「在中國是在自己家」的瑞士漢學家談論他所認知、所感受到的中國。
漢學家論述中國總是基於某種對中國的意義的理解。可能是出於對異域的好奇,旨在探索神秘中國的玄妙;也可能是應接一種知性的挑戰,所謂「以中國為方法」從事研究;還可能則是成長於具體的生命經驗,從個人際遇的切身體會走向集體命運的理性省思。畢來德先生的情況無疑是屬於最後這一種。他在這本書裏的論述,如他最近來信所言,「看似簡單明瞭,卻是自己三十多年的經歷與思考的結晶」。
畢來德先生成長的歷史大環境是戰後歐洲社會的全面重建。左翼思潮的勃興構成了當時歐洲思想語境一股重要的力量,而中國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則引起了許多知識人的關注甚至好感。主張政治中立的瑞士是西歐最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在完成大學學業,到法國學習了一年中文之後,畢來德於1963年隻身前往北京,成了中共建政以後最早正式在中國留學的西歐學生之一。那是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一個短暫的喘息時刻。他在北京三年的歲月中,結識了妻子崔文,也在北大近距離體會了文革爆發的驚悚心悸。北京家人的坎坷經歷,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數十年間他始終休戚與共。後來,他與妻子在日內瓦大學共同創辦了中文系,長期從事教學,講授中國史、中國研究(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歷史與文明、當代社會)。許多年裏,他的工作就是要讓人理解中國所發生的一切,而「首先是自己要理解。」80年代,他跟所有關心中國的知識人一道,感受過中國社會復甦生機喚起的欣喜共鳴,最後也見證了89六四的慘痛斷裂以及後來歷史的「華麗轉身」。一直以來,他努力堅持觀察中國現狀、反思中國歷史,「結合歐洲發生的討論讓歐洲人理解中國,證明中國(中國的過去)可以有多種理解的可能,而理解的方式本身也有其意義,這樣理解與那樣理解並非毫無差別。」
畢來德先生的個體際遇決定了他與中國的關係是切身的經歷。中國於他不是一種知識活動的對象,也不是一個符號化、象徵性的世界形態,而是生活過、生活著他關心的人的一個社會,也是形塑了他自己的生命與精神世界的一種文明。這本書裏提出的觀察與思考,他擔心讀者可能會覺得他太悲觀。他解釋說自己「其實並非態度悲觀,而是只想努力做到清醒。」清醒,不正是一種深切的關心必需的品質嗎?
清醒的讀者不難看出,畢來德十五年前分析指出的中國的沉默,就是中國人依然活在其中的,許多人熟視無睹、充耳不聞的總體社會氛圍。誠如他〇六年再版序中提到的,中國人現在已經越來越不沉默了。然而,我們真正能夠聽到的聲音其實依然很小很弱,淹沒在一片紙醉金迷宴舞笙歌之中,背後更時不時傳來官方中國刺耳的號令,新一代政治強人登場以後似乎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而比這強制的沉默更可怕的,是在現實的重壓與誘惑之下,那樣一種彌散開來的對歷史與真相的漠然,更準確地說恐怕已是一種弄假成真的遺忘,一種系統化、有組織的失憶,其後果則是整個社會沉浸在一片渾噩的集體無意識之中,充斥著散沙般的無奈與汲汲營營的自得。
書之所以譯成中文,就是因為這樣的中國與生活在中國的每一個人都有關。畢來德的分析表明,這不只是關係到中國而已,其實是整個世界。但是,人類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意義,因為日常世界的距離遠近,對不同人所產生的影響、意義不盡相同,所以他們各自擔當的責任也有輕重緩急。當身邊,自焚的藏人、強拆的居民、跳樓的奴工、冤獄的家屬、上訪的難民⋯⋯那麼多活在中國的人活得那樣無聲無息,他們一點點微弱的聲音也無人理會,我們就不得不問,難道不是因為太多活在中國的人太過沉默不語了嗎?這樣的沉默,恐懼衍生的絕望是原因,冷漠導致的失能也是原因。但更主要的、更核心的,是觀念的矇昧、意識的匱乏。借用畢來德的說法,就是因為「有些話沒有說出來,而之所以沒有說出來,則是因為還沒有想清楚」。要撼動一種制度,唯有觀念的力量、人心的匯流。所以這「中國的沉默」,需要說出來,需要想清楚;需要用中文說,需要用中文想。
因緣際會,這本小書的中文譯本首先是要在台灣出版。畢先生信中聲明:「書中所講僅止於北京政權,而非中華民國。」那麼,在台灣看中國的沉默又意味著什麼呢?
台灣近年來不少人愛講「中國因素」。這本小書的一個啓發可能在於,今天我們在台灣談論中國因素的時候,是否也能意識到台灣身上的中國因素?包括某些台灣獨立主張者們身上的中國因素?因為這本書所揭示的一個重要的「中國」現象是,在一個壓制個性、排擠差異,推重統一、強制和諧的社會當中,衝突的協調機制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被壟斷、被潛規則化;而加之以宗法文明源遠流長的深層次社會分斷結構,一個透明開放的公共精神世界便愈發難以形成。畢來德講的是中國,但台灣又何嘗不是如此?
反觀台灣,宗法制度(與其核心上的階序等級文化)作為高度統攝性的社會政治整合與控制機制,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當中是否就已不復存在(還是繼續在被維護,甚至已在民主機制中產生了變異而益發難以對抗)?社會肌體結構性的二分斷裂格局,在台灣是否也還在發揮作用(特別是在人心觀念上,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系列社會慣習:禮俗規制、教育實踐、資源置配)?在面對挟新自由主義金權力量的脅迫與誘惑而來的中國因素時,清理從政治慣習到心理結構當中根深柢固的中國因素──泛權謀化的關係邏輯與價值想像、社會肌體分斷體制之下被扭曲淹滅的公共性──,應該也是台灣必要而緊迫的任務。
說到中國的沉默,可能也不妨反省台灣身上是否還存在某種中國性的沉默。包括就畢來德所謂的「三重」沉默:近代歷史、現狀、長期歷史,對應於台灣這樣一個社會體,也需要想想能夠如何理解。釐清今日的台灣與自身歷史和周圍世界的關係,正視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個體的際遇與集體的命運,真正讓多元的台灣社會能夠差異共生而不再是各自為陣,就必須也只能透過共同話語的建構。公共生活內在地要求人們創造打破沉默的機制,參與交流對話的實踐。不只是對話,更是從敘述到論爭的多種話語公共化行動。假如說今天台灣的媒體,由於陷溺於金權政治文化結構之中,似乎失去了其應有的公共話語平台的功能,那麼如何建立另外的話語機制,參與到話語的生產交流之中,的確是當代台灣民主生活面臨的挑戰。而在社交網站幾乎取代傳統媒體的信息樞紐功能之時,或許對於話語品質的反思、實踐的創新,都依舊是高難度的功課。
為一個社會肌體公共意義的生成建立制度性的保障,其基本的條件自然是民主制度、司法公正,但在更深層次上有如空氣、土壤、活水一般的,而從作用上講也更具有體質指標意義的,還是公信話語。所以公共話語的多元不只應該有倫理原則的約束──如不撒謊等,更要有制度性的機制來反制各種對話語公共性的破壞行為:從所謂密室協商到不實廣告、從所謂國安機密到商業專利,都應該有嚴格的監督與制衡機制,而歸根結底就是一種獨立自主、體質健康的輿論生態。這樣大格局的話語活動,需要的是龐大的、活躍的話語生產者,以及有效的話語甄別運作機制,其基礎則在於話語實踐的日常化、普遍化。當社會成員普遍擁有發言的思考與表達習慣,掌握話語交流的生活法則之時,所謂的輿論,或是公共話語生態,就一定會得到改善,逐步形成生態系的自我調節功能。
畢來德先生近十年來發表的一系列「小」書,其「小」的用心所在正是對話語意義生成所做的一種努力。在連篇累牘、旁徵博引、術語生硬、學理艱深而乏人問津的學術巨著與輕鬆詼諧、討喜媚眾、即時即景而止於己見的博客碎文之間,小書的篇幅、文辭都力求實現敘述平實、說理清晰、觀點明朗的話語品質。這在話語形態多元的基本格局下,無疑是一種循著話語本質的交流願望為內在要求的實踐選擇。譯成中文,不只是因為它們與中國、中華文明有關,也是希望中文世界的敘述與討論形態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啓發。若從畢先生來信補充的說明來看,他對此亦是不無期待的:
「這兩篇綜合論述並非相關思考的終點,自十五年前發表至今一直持續在變化。第一篇所寫的內容不會改變,但現在寫會寫得不同。第二篇,特別是對中國的過去的分析,應該說是已經完成了。附錄文章,更像是一隻漂流瓶。提出的問題是我自己已沒有時間去處理的問題,希望有朝一日會有人來接手。」
這自然也是譯者的希望。
甲午十月廿八於新竹
這本小書譯成中文,首先是希望生活在中國的朋友能讀到。希望他們能聽到一個感覺自己「在中國是在自己家」的瑞士漢學家談論他所認知、所感受到的中國。
漢學家論述中國總是基於某種對中國的意義的理解。可能是出於對異域的好奇,旨在探索神秘中國的玄妙;也可能是應接一種知性的挑戰,所謂「以中國為方法」從事研究;還可能則是成長於具體的生命經驗,從個人際遇的切身體會走向集體命運的理性省思。畢來德先生的情況無疑是屬於最後這一種。他在這本書裏的論述,如他最近來信所言,「看似簡單明瞭,卻是自己三十多年的經歷與思考的結晶」。
畢來德先生成長的歷史大環境是戰後歐洲社會的全面重建。左翼思潮的勃興構成了當時歐洲思想語境一股重要的力量,而中國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則引起了許多知識人的關注甚至好感。主張政治中立的瑞士是西歐最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在完成大學學業,到法國學習了一年中文之後,畢來德於1963年隻身前往北京,成了中共建政以後最早正式在中國留學的西歐學生之一。那是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一個短暫的喘息時刻。他在北京三年的歲月中,結識了妻子崔文,也在北大近距離體會了文革爆發的驚悚心悸。北京家人的坎坷經歷,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數十年間他始終休戚與共。後來,他與妻子在日內瓦大學共同創辦了中文系,長期從事教學,講授中國史、中國研究(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歷史與文明、當代社會)。許多年裏,他的工作就是要讓人理解中國所發生的一切,而「首先是自己要理解。」80年代,他跟所有關心中國的知識人一道,感受過中國社會復甦生機喚起的欣喜共鳴,最後也見證了89六四的慘痛斷裂以及後來歷史的「華麗轉身」。一直以來,他努力堅持觀察中國現狀、反思中國歷史,「結合歐洲發生的討論讓歐洲人理解中國,證明中國(中國的過去)可以有多種理解的可能,而理解的方式本身也有其意義,這樣理解與那樣理解並非毫無差別。」
畢來德先生的個體際遇決定了他與中國的關係是切身的經歷。中國於他不是一種知識活動的對象,也不是一個符號化、象徵性的世界形態,而是生活過、生活著他關心的人的一個社會,也是形塑了他自己的生命與精神世界的一種文明。這本書裏提出的觀察與思考,他擔心讀者可能會覺得他太悲觀。他解釋說自己「其實並非態度悲觀,而是只想努力做到清醒。」清醒,不正是一種深切的關心必需的品質嗎?
清醒的讀者不難看出,畢來德十五年前分析指出的中國的沉默,就是中國人依然活在其中的,許多人熟視無睹、充耳不聞的總體社會氛圍。誠如他〇六年再版序中提到的,中國人現在已經越來越不沉默了。然而,我們真正能夠聽到的聲音其實依然很小很弱,淹沒在一片紙醉金迷宴舞笙歌之中,背後更時不時傳來官方中國刺耳的號令,新一代政治強人登場以後似乎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而比這強制的沉默更可怕的,是在現實的重壓與誘惑之下,那樣一種彌散開來的對歷史與真相的漠然,更準確地說恐怕已是一種弄假成真的遺忘,一種系統化、有組織的失憶,其後果則是整個社會沉浸在一片渾噩的集體無意識之中,充斥著散沙般的無奈與汲汲營營的自得。
書之所以譯成中文,就是因為這樣的中國與生活在中國的每一個人都有關。畢來德的分析表明,這不只是關係到中國而已,其實是整個世界。但是,人類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意義,因為日常世界的距離遠近,對不同人所產生的影響、意義不盡相同,所以他們各自擔當的責任也有輕重緩急。當身邊,自焚的藏人、強拆的居民、跳樓的奴工、冤獄的家屬、上訪的難民⋯⋯那麼多活在中國的人活得那樣無聲無息,他們一點點微弱的聲音也無人理會,我們就不得不問,難道不是因為太多活在中國的人太過沉默不語了嗎?這樣的沉默,恐懼衍生的絕望是原因,冷漠導致的失能也是原因。但更主要的、更核心的,是觀念的矇昧、意識的匱乏。借用畢來德的說法,就是因為「有些話沒有說出來,而之所以沒有說出來,則是因為還沒有想清楚」。要撼動一種制度,唯有觀念的力量、人心的匯流。所以這「中國的沉默」,需要說出來,需要想清楚;需要用中文說,需要用中文想。
因緣際會,這本小書的中文譯本首先是要在台灣出版。畢先生信中聲明:「書中所講僅止於北京政權,而非中華民國。」那麼,在台灣看中國的沉默又意味著什麼呢?
台灣近年來不少人愛講「中國因素」。這本小書的一個啓發可能在於,今天我們在台灣談論中國因素的時候,是否也能意識到台灣身上的中國因素?包括某些台灣獨立主張者們身上的中國因素?因為這本書所揭示的一個重要的「中國」現象是,在一個壓制個性、排擠差異,推重統一、強制和諧的社會當中,衝突的協調機制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被壟斷、被潛規則化;而加之以宗法文明源遠流長的深層次社會分斷結構,一個透明開放的公共精神世界便愈發難以形成。畢來德講的是中國,但台灣又何嘗不是如此?
反觀台灣,宗法制度(與其核心上的階序等級文化)作為高度統攝性的社會政治整合與控制機制,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當中是否就已不復存在(還是繼續在被維護,甚至已在民主機制中產生了變異而益發難以對抗)?社會肌體結構性的二分斷裂格局,在台灣是否也還在發揮作用(特別是在人心觀念上,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系列社會慣習:禮俗規制、教育實踐、資源置配)?在面對挟新自由主義金權力量的脅迫與誘惑而來的中國因素時,清理從政治慣習到心理結構當中根深柢固的中國因素──泛權謀化的關係邏輯與價值想像、社會肌體分斷體制之下被扭曲淹滅的公共性──,應該也是台灣必要而緊迫的任務。
說到中國的沉默,可能也不妨反省台灣身上是否還存在某種中國性的沉默。包括就畢來德所謂的「三重」沉默:近代歷史、現狀、長期歷史,對應於台灣這樣一個社會體,也需要想想能夠如何理解。釐清今日的台灣與自身歷史和周圍世界的關係,正視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個體的際遇與集體的命運,真正讓多元的台灣社會能夠差異共生而不再是各自為陣,就必須也只能透過共同話語的建構。公共生活內在地要求人們創造打破沉默的機制,參與交流對話的實踐。不只是對話,更是從敘述到論爭的多種話語公共化行動。假如說今天台灣的媒體,由於陷溺於金權政治文化結構之中,似乎失去了其應有的公共話語平台的功能,那麼如何建立另外的話語機制,參與到話語的生產交流之中,的確是當代台灣民主生活面臨的挑戰。而在社交網站幾乎取代傳統媒體的信息樞紐功能之時,或許對於話語品質的反思、實踐的創新,都依舊是高難度的功課。
為一個社會肌體公共意義的生成建立制度性的保障,其基本的條件自然是民主制度、司法公正,但在更深層次上有如空氣、土壤、活水一般的,而從作用上講也更具有體質指標意義的,還是公信話語。所以公共話語的多元不只應該有倫理原則的約束──如不撒謊等,更要有制度性的機制來反制各種對話語公共性的破壞行為:從所謂密室協商到不實廣告、從所謂國安機密到商業專利,都應該有嚴格的監督與制衡機制,而歸根結底就是一種獨立自主、體質健康的輿論生態。這樣大格局的話語活動,需要的是龐大的、活躍的話語生產者,以及有效的話語甄別運作機制,其基礎則在於話語實踐的日常化、普遍化。當社會成員普遍擁有發言的思考與表達習慣,掌握話語交流的生活法則之時,所謂的輿論,或是公共話語生態,就一定會得到改善,逐步形成生態系的自我調節功能。
畢來德先生近十年來發表的一系列「小」書,其「小」的用心所在正是對話語意義生成所做的一種努力。在連篇累牘、旁徵博引、術語生硬、學理艱深而乏人問津的學術巨著與輕鬆詼諧、討喜媚眾、即時即景而止於己見的博客碎文之間,小書的篇幅、文辭都力求實現敘述平實、說理清晰、觀點明朗的話語品質。這在話語形態多元的基本格局下,無疑是一種循著話語本質的交流願望為內在要求的實踐選擇。譯成中文,不只是因為它們與中國、中華文明有關,也是希望中文世界的敘述與討論形態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啓發。若從畢先生來信補充的說明來看,他對此亦是不無期待的:
「這兩篇綜合論述並非相關思考的終點,自十五年前發表至今一直持續在變化。第一篇所寫的內容不會改變,但現在寫會寫得不同。第二篇,特別是對中國的過去的分析,應該說是已經完成了。附錄文章,更像是一隻漂流瓶。提出的問題是我自己已沒有時間去處理的問題,希望有朝一日會有人來接手。」
這自然也是譯者的希望。
甲午十月廿八於新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