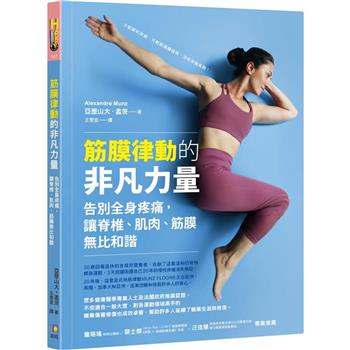明星的∕鄭聖勳
我感謝腐敗
我拒絕上帝的搜索
——<墜落>,郭品潔
我是一個不夠格的酒徒,也是一個糟透了的賭徒。
因為不敢孤注一擲的人不能當賭徒,而且我不論多麼害怕清醒,卻總試著維持清醒,酒徒不害怕酒醉與犯錯。
***
你曾經用「擦掉顏色」來畫畫嗎?
黃民安的創作方式,不是塗上顏色,不是增補顏色;黃民安幾乎要違背繪畫的邏輯,他用小刷子慢慢地在街道上「刮去某部分的牆面的灰塵」、「還原牆的顏色」。看過黃民安的作品後,我曾試著在畫滿顏料的畫紙上,用刮刀除去顏料來畫畫,但完全行不通,因為我已經預想了「要除去什麼」而「先填滿顏色」,這最多只能到達「負片的畫」,但黃民安的作品並不是,因為作畫的地點是街道的牆,在它們上面的灰塵與青苔,並不是預想要被擦拭而存在的。
而街頭塗鴉又會令你聯想到什麼呢?
狂放大膽的筆觸、用色?或是在美術館策展中,城市印象所被賦予的歡騰、疏離、批判?
用這些印象想像黃民安的作品,統統是錯的。黃民安的作品充滿童趣,而且塗鴉的語言變成了古典詩,畫面結構是山水畫。但城市裡的山水畫並不意味著恬淡、寧靜致遠;它們諧謔、不滿,但又不至於控訴地義憤填膺,它們更傾向於怪誕,因為典麗的筆觸(不,這根本就不是筆觸,而是刮去的痕跡,)與街道格格不入,畫面景象也與後現代的論述語言格格不入。
我做不到在街上畫畫。並且我太後現代了,做不到在城市裡不符合城市邏輯的喧囂與孤寂。
***
我常常因為猶豫與不安而占卜,不是用星座或紫微斗數算命占卜,而是用手機裡下載的各式各樣撲克牌遊戲。關於占卜的內容,幾乎都是「假使這局牌贏了,就買某種青菜,輸了則買另一種菜」,但牌局的輸贏還是讓我在菜市場裡非常猶豫。「假使這局牌輸了,我就繼續等待等待已久的電話」,但假使贏了,我多半還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讓你下著雨
時間未乾
唯一支援生命的
是一種強迫的重複
每一天都感受到自己
更貼近地面
——<時間未乾>,郭品潔
每天生活裡的必要儀式,用來證明自己勉強活過生活底限的儀式,噢,用潮溼來作譬喻完全超乎了我的想像,我也找不到更貼切的話來說。
詩的創作得依靠靈光,但我從不敢確定郭品潔有多少靈光。因為郭品潔是一位在創作時會反覆詠頌自己詩句的詩人,但創作時間有可能是一天,也有可能是一個月、一年。為了一首詩的完成,在無可估計的時間裡反覆念誦。這些簡潔準確的文字,這些抒情力道異常深厚的文字;我無法形容郭品潔有多少詩人的天賦,因為這些詩句是用無比的耐心交換來的。
我做不到這麼多的耐心。並且我不敢用更多的時間對自己的作品下賭注,我沒有與自己的作品拼搏到底的決心。
***
「晦澀」的意思,是只跟你說了一點點,然後說話者言盡於此,不想再說了。「硬冷」的意思,是作者節制了文字的熱度與節奏,用某一種距離感與讀者溝通。「乾燥」的意思,是說話者拒絕了更有活力的表現方式,木然地講著話。這些元素結合在一起,就是張歷君的詩∕散文詩。
他關心遠方的爆破聲他盯著屏幕死命不放
他嘴邊沒有哨子他沒有下達任何命令沒有責任可言
我們只是死命盯著屏幕上的曲線
來回踱著死亡探戈
反覆吟唱他沒有責任可言他沒有責任可言
--<談談情跳跳舞>,張歷君
這些文字該是要快快地唸,或是慢慢地唸?是要唸地專注,是要唸地悵然若失?我們仿佛可以感知到一些節奏,但是這些節奏並不順暢;或者與其說是節奏,卻又更像是有意無意的閱讀阻攔。在另外一首關於死亡面貌的詩裡,張歷君晦澀、硬冷、乾燥地描寫了對於夢魘的驚懼與喃喃自語:
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他看準我頸上的血痕正褪色
圓睜雙目念念有詞:
不能通過
不能通過
全都不能通過
——<夜與霧>,張歷君
「我」在這兩首詩裡都比較像是第三者,被死亡事件波及的他者。它們真是冷淡到了乖張的地步。
我做不到這種奇異的距離感,或者更適切地說,我做不到這麼清醒似的冷淡。
***
我在《明星》中的四篇文章,大抵描寫的是自己充滿羞恥的狀態,面對精神耗弱以及渙散的失措,以及難捱難以面對的長夢。其中有兩篇曾經在香港《字花》雜誌發表,修改後在台灣出版。
《明星》當中的詩文、圖像、插畫,深摯地表現了四種生活樣貌。好友曾問我說,《明星》一書的名字,是否來自劉吶鷗曾經參與的「明星電影公司」?還是「明星花露水」?或許兩者的意思都是有的,特別是指「明星作為形容詞」後面的兩件事;電影公司與香水,可以都因為「明星」被放在一起。
作者簡介
郭品潔
著有詩集《讓我們一起軟弱》(大田,2003),《我相信許美靜》(蜃樓,2010)。
黃民安
再現劇團好木奉的團長 全職演員月土子不會食我
女子認真的表演老師噢 要刷牆刷到疤食大壽的清潔工
張歷君
淡乎其無味。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鄭聖勳
美術編輯,動漫迷。作品散見於香港《字花》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