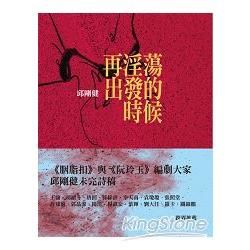邱剛健,一個曾經驚世駭俗,後來卻相對沉寂的創作者。
他在六十年代與友朋創辦《劇場》雜誌,譯介西方現當代影劇理論與作品,並衍生出另翼的實驗性創作,在台灣的文藝行動中具有開創性意義。他曾經寫下無數膾炙人口的電影劇本,邵氏時期的作品已可見其耀眼的才華,八十年代以來與多位香港新浪潮導演的合作,更步入他編劇生涯的全盛期,累次獲得香港金像獎最佳編劇與台灣金馬獎最佳原創劇本等獎項的肯定。邱剛健寫劇本極慢,講究氛圍描寫細緻,強調要用形象思考,人物對白常常充滿詩意——他認為劇本可以作為完整的獨立作品。而這些寫作劇本的特點,同樣也呈現在他的詩作裡,他的詩,往往充滿戲劇性,像他的劇本一樣講求場面調度,彷若一個個鏡頭在讀者眼前搬演。
但少有人知道邱剛健也寫詩,甚至寫詩可能是他最為重要的精神生活:現代詩是他「一生從不放棄的追求」(劉大任),也是他「最終最愛的付託」(張照堂)。晚年的邱剛健更為醉心寫詩,也一如既往的吹毛求疵:每首詩要打印四份,以便隨時修改,如改動了一字,同樣也要再打印四份,若感覺不好,還要再改回去(趙向陽)。是這樣近乎偏執的創作態度,讓《胭脂扣》與《阮玲玉》成為華語電影裡的傳奇,更讓他執導的《唐朝綺麗男》和《阿嬰》成為另類經典,也讓我們讀到《亡妻,Z,和雜念》(赤粒藝術,2011)裡「哀痛中見豔色」的抒情廢頹與奇想異念,而未完詩稿《再淫蕩出發的時候》一樣意象準確,充滿著性與死亡的隱喻,如組詩「伊人」與「祈禱室」用豔情表達傷逝悼亡與種種質疑,部分詩作中從淫蕩婦敘事位置所發出的浪聲賤語,在在都挑釁著我們所熟悉的含蓄詩學傳統:邱剛健的「淫蕩書寫」,始終駭俗,怪誕,驚世程度絲毫不減——「任何時候都是再淫蕩出發的時候」,邱剛健在創作上的堅持,從不允許自己泛舊沉寂。
劉大任在〈想到邱剛健〉一文最後,引用當年邱剛健悼念黃華成的詩句:「現在你可以盡情地嘔吐,盡情地嘔吐,/不用怕我們會再嫉妒甚至是你的穢物,追趕你,/把你打死。」(〈黃華成輓歌〉)。詩人走遠,但他留下的「滿眼新詩」,將如他總活在時代最前沿的其他創作,永遠前衛,歷久彌新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再淫蕩出發的時候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再淫蕩出發的時候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邱剛健(1940-2013)
電影編劇、導演、策劃,詩人。生於福建鼓浪嶼,1949年隨家人移居台灣。早年創辦《劇場》雜誌,聚合莊靈、黃華成等友朋,大量譯介西方現當代影劇作品與理論,並曾導演與劉大任合譯之舞台劇《等待果陀》。1966年前往香港,以戴安平、邱戴安平、秋水長安等筆名開展編劇生涯,陸續與張徹、楚原、譚家明、許鞍華、關錦鵬等導演合作,主筆與合編劇本無數,是知名的編劇大家,嘗言:「《去年在馬倫巴》是我的老師。」重要作品包括《愛奴》(1972)、《投奔怒海》(1982)、《烈火青春》(1982)、《唐朝豪放女》(1984)、《地下情》(1986)、《胭脂扣》(1988)、《人在紐約》(1990)、《阮玲玉》(1992)等。執導的《唐朝綺麗男》(1985)與《阿嬰》(1993),用風格化的影像語言為華語電影備增異色。其後移居紐約、北京,往返兩岸,在不同城市間繼續創作,晚年更加醉心於寫作現代詩,著有詩集《亡妻,Z,和雜念》(赤粒藝術,2011)。
邱剛健(1940-2013)
電影編劇、導演、策劃,詩人。生於福建鼓浪嶼,1949年隨家人移居台灣。早年創辦《劇場》雜誌,聚合莊靈、黃華成等友朋,大量譯介西方現當代影劇作品與理論,並曾導演與劉大任合譯之舞台劇《等待果陀》。1966年前往香港,以戴安平、邱戴安平、秋水長安等筆名開展編劇生涯,陸續與張徹、楚原、譚家明、許鞍華、關錦鵬等導演合作,主筆與合編劇本無數,是知名的編劇大家,嘗言:「《去年在馬倫巴》是我的老師。」重要作品包括《愛奴》(1972)、《投奔怒海》(1982)、《烈火青春》(1982)、《唐朝豪放女》(1984)、《地下情》(1986)、《胭脂扣》(1988)、《人在紐約》(1990)、《阮玲玉》(1992)等。執導的《唐朝綺麗男》(1985)與《阿嬰》(1993),用風格化的影像語言為華語電影備增異色。其後移居紐約、北京,往返兩岸,在不同城市間繼續創作,晚年更加醉心於寫作現代詩,著有詩集《亡妻,Z,和雜念》(赤粒藝術,2011)。
目錄
I
新詩滿眼 給劉大任張照堂楊識宏 10 歌的長度 11 伊人 12 詩的長度 14 伊人II 15 伊人III 16
伊人IV 18 公寓 19 伊人V 20 祈禱室 地藏王菩薩 22 祈禱室 諸佛 23 祈禱室 白瓷觀音 24
海釣 26 戲謔一首:葡萄牙的安妮 27 戲謔一首:讀高居翰「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 書
中吳偉的一幅水墨畫「春江魚釣」的照相圖版 29 以前的一位朋友現在變成植物人了 30
試想楊識宏一些畫的母題 31 伊人VI 33 試想楊識宏一些畫的母題 34 伊人VII 36
記憶的空海 37 日昃 38 伊人VIII 39 看雪 憶及曾經見過的一隻遼東白鶴 40 閃電 41
伊人IX 給老嘉華 42 啊 44 室內設計 45 祈禱室 47 空氣的形 48 祈禱室 49
賦格 聽巴哈 50 聽修曼 52 她想起三兩句 Hart Crane 的詩 53 回信I 54 回信II 56 中間 57
旁邊 58 旁邊與中間 59 記憶與忘記張照堂的兩張照片 64 旁邊 68
II
72 但是他還在沉迷看 74 前景" 75 海葬" 77 女之叫聲 78 賦格 聽巴哈 80 長城磚頭
81 女之空喊" 84 斷句殘篇 87 回顧 1962 年張照堂拍的一張照片一個人沒有頭只有立姿的黑影
89 有聊的重複・趙向陽
新詩滿眼 給劉大任張照堂楊識宏 10 歌的長度 11 伊人 12 詩的長度 14 伊人II 15 伊人III 16
伊人IV 18 公寓 19 伊人V 20 祈禱室 地藏王菩薩 22 祈禱室 諸佛 23 祈禱室 白瓷觀音 24
海釣 26 戲謔一首:葡萄牙的安妮 27 戲謔一首:讀高居翰「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 書
中吳偉的一幅水墨畫「春江魚釣」的照相圖版 29 以前的一位朋友現在變成植物人了 30
試想楊識宏一些畫的母題 31 伊人VI 33 試想楊識宏一些畫的母題 34 伊人VII 36
記憶的空海 37 日昃 38 伊人VIII 39 看雪 憶及曾經見過的一隻遼東白鶴 40 閃電 41
伊人IX 給老嘉華 42 啊 44 室內設計 45 祈禱室 47 空氣的形 48 祈禱室 49
賦格 聽巴哈 50 聽修曼 52 她想起三兩句 Hart Crane 的詩 53 回信I 54 回信II 56 中間 57
旁邊 58 旁邊與中間 59 記憶與忘記張照堂的兩張照片 64 旁邊 68
II
72 但是他還在沉迷看 74 前景" 75 海葬" 77 女之叫聲 78 賦格 聽巴哈 80 長城磚頭
81 女之空喊" 84 斷句殘篇 87 回顧 1962 年張照堂拍的一張照片一個人沒有頭只有立姿的黑影
89 有聊的重複・趙向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