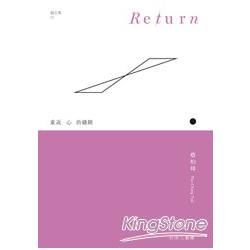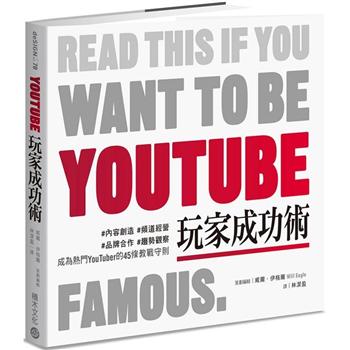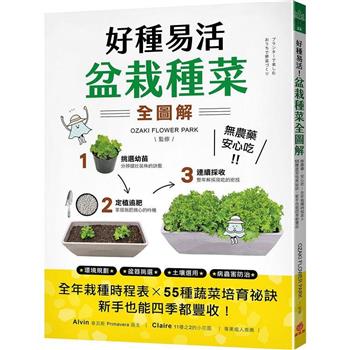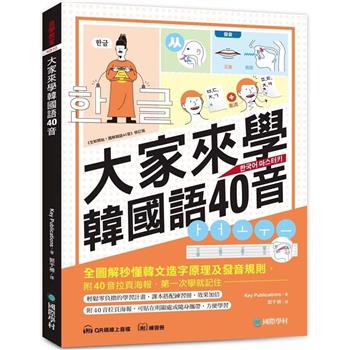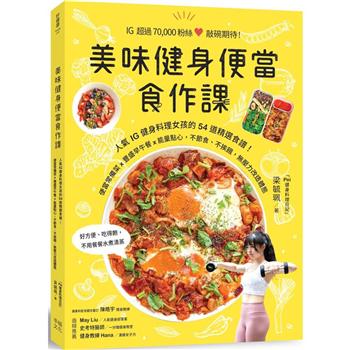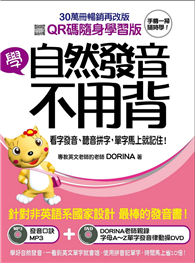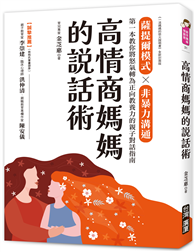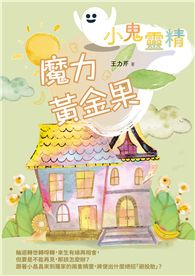◎台南人劇團「Re/turn」劇本。聞天祥秘密推薦。
◎誠品春季舞台第三號作品,2011年連演三十場;2013年壯闊重返,一票難求!
◎橫跨古今、跨越歐亞,一個可以穿越時空的奇幻門把、三段難分難解的糾葛情懷,串起一場動人的精緻好戲!
◎生命中的缺憾,會引領你到達你該去的地方。如果你心中曾經有個遺憾,Re/turn或許可以給你一個答案。
意外出現的門把,讓蒲琮文來到五年之後的未來,驚訝發現在他身邊的不是他的未婚妻簡嫚菁,而是十三年前曾與他有過一場轟轟烈烈愛情,但卻被強迫拆散,從此了無音訊的白若唯,意外之餘,琮文對嫚菁的態度也開始轉變。
白若唯的母親白襄蘭從八年前的過去來到自己已經過世的「現在」,意外阻止女兒的婚禮。為了彌補多年來對女兒的愧疚,她決定促成白若唯與蒲琮文的再次重逢,
若唯的未婚夫湯境澤,是當紅的政治明星,但他不為人知的同性戀秘密卻被自己高中的同窗好友,同時也是八卦周刊的副總編雷奕梵接獲線報而得知。奕梵知道自己要是報導這條新聞就能順利當上總編輯,但卻也將再次毀掉她和境澤兩人在高中時期那段早已生變的友情⋯⋯
如果重新開始,一切會不會更完美?
一個神秘門把的轉動,開啟了時空之門,讓六個各自懷抱遺憾的人們,再次得到一次、唯一的一次重新來過的機會。就在結局可能出現其他可能的同時,卻也再次掀起一連串親情、愛情和友情的選擇、質疑,與迷惘。
作者簡介:
⊙蔡柏璋
台灣大學戲劇系第二屆畢業,並於2008/09遠赴英國倫敦中央演說暨戲劇學院(Central School of Speech and Drama, University of London)攻讀音樂劇碩士學位,並以全班最優異的成績畢業。
部落格http://mypaper.pchome.com.tw/paochang
Twitter http://twitter.com/paochangtsai
Plurk http://www.plurk.com/Paochang
蔡柏璋是國內難得一見集編導演三項才華於一身的創作者,曾與莎士比亞的妹們的劇團、創作社、如果兒童劇團及台南人劇團皆有合作。在創作之餘,並致力於戲劇推廣和教育工作,在台南人劇團的青年劇場和各大工作坊皆可見到他的教學蹤影。
蔡柏璋雖年輕但劇場創作與實務經歷相當豐富,於臺大就讀期間便成立「戲劇主義」劇團,並發表多齣製作;他並且於2002-2003獲選臺大與美國喬 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的交換學生,至美國研讀戲劇相關課程一年。2007~08受邀擔任台南人劇團的駐團編導;2009年起,受邀與呂柏伸共同擔任台南人劇團 聯合藝術總監。由他擔綱演出的作品中多次獲得台新藝術獎的肯定,其中創作社《嬉戲: who-ga-sha-ga》榮獲第三屆表演藝術的百萬首獎、《莎士比亞不插電3:馬克白》第6屆表演藝術十大作品。此外,他的最新音樂劇創作劇本《木蘭 少女》不僅獲得府城文學獎的首獎,也被挑選作為台大戲劇系創系十週年的紀念演出,2009年6月於台北城市舞台演出。此外,他所創作的電視影集型式舞台劇 《K24》,更是開創臺灣劇場史上第一齣連演六小時喜劇的新記錄,演出成果深受兩岸學者專家與媒體觀眾的讚賞與好評
演出作品:
2007 台南人劇團《莎士比亞不插電3:馬克白》 2005 台南人劇團《莎士比亞不插電2:哈姆雷》
2005 創作社第十二號作品《嬉戲:who-ga-sha-ga》
2005 玉米雞兒童劇團《巫婆煮成一鍋湯》
2004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家庭深層鑽探手策》
2004 台大戲劇系第二屆畢業製作《第十二夜》
2004 戲劇主義第三號《RENT》
2003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30P:不好讀》
2002 如果兒童劇團《抓馬歷險記》
2002 美國喬治亞大學學期製作《Violet》
2002 台大戲劇系學期製作《高加索灰欄記》
2001 台大戲研所《櫻桃園》
導演作品:
2007 台南人劇團《K24》第一季全六集 (編導)
2005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e.Play.XD之∞》(編導)
2004 戲劇主義第三號《RENT》(原著Jonathan Larson)
2003 戲劇主義第二號《非關治療》(Beyond Therapy,原著Christopher Durang)
2002 戲劇主義第一號《性世代首部曲》(編導)
得獎經歷:
第三屆台新藝術獎年度表演藝術首獎 《嬉戲Who-Ga-Sha-Ga]》擔任主要演員
第六屆台新藝術獎年度十大表演節目《莎士比亞不插電:3馬克白》擔任馬克白一角
劇本《木蘭少女》獲得第十三屆府城文學獎劇本類正獎
「Keep Walking」第五屆圓夢學堂得主,赴英國劍橋大學Judge商學學研讀創業管理課程
榮獲97年度教育部留學獎學金(甲類)第一名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蔡柏,他是個平凡人!~ 呂柏伸 (台南人藝術總監)
許多人喜歡用天才或者是鬼才來形容蔡柏,好像認為蔡柏在劇本創作上,應該是有神助(是的,他有很虔誠的信仰)或是鬼助(沒有,他應該是沒有養小鬼?),否則他怎麼能夠天馬行空、肆無忌憚地編寫出《K24》、《Q & A》和《木蘭少女》這三齣深獲高度讚譽的驚豔之作呢?
事實上,蔡柏真的就只是個平凡人,他的創作過程都極為痛苦,特別是這次的《Re/turn》。從今年農曆過完年後,劇組夥伴第一次讀首稿,到現在蔡柏還是不斷地在修改劇本,排練場上的設計者和演員目前手上拿到的是第11稿,離首演只剩三週,但蔡柏似乎仍不願意定稿?
每次在劇本創作及執導過程中,自我質疑、自我否定、自我辯證、自我唾棄,這些症狀都會出現在蔡柏身上,然後他就會開始不斷地抱怨:「為什麼大家都覺得寫劇本很容易?有本事你去寫寫看阿?」、「我是個演員,為什麼現在大家都要找我寫劇本?」、「我不會導戲、我根本不是導演的料、我只是個演員!」、「我是小孩開大車,我根本不會導戲也不會寫劇本!誠品書店是找錯人了嗎?」
從某種層面來說,蔡柏創作會這麼痛苦或許是他所寫的每部作品其實都具有相當高度的自傳色彩,劇中角色所身處的困境、角色人物間的衝突,似乎都可以在蔡柏的現實人生當中找到原型(就像他跟我說,這次劇中角色白襄蘭就是我)。我實在無法想像蔡柏會停筆不再寫劇本,因為他對生命、對人生、對人總是有深刻的觀察、趣味的省思以及細膩的感受;更重要的是,他也樂於與人分享這些,並且勇於誠實面對並處理他個人對人生種種問題的大哉問。唯有透過劇本寫作、唯有透過舞台演出,蔡柏你所提問的這些問題也許才能夠找到些許答案,而你也得以藉此救贖自己,不是嗎?
如果真的能夠轉動時空門把,我真想跟蔡柏一起回到2005年的8月,《K24》開排兩星期之後的那天晚上。還記得那時候蔡柏問我可不可以解call演員,因為他說他的劇本寫得太糟,戲根本無法繼續再排下去了。當時身為藝術總監的我並沒有答應他的哀求,反倒非常狠毒地跟他說,請他把已經寫好的《K24》劇本全部丟掉,另起爐灶,重新寫過,沒想到隔天他居然就生出了新的劇情大綱,也就是接近大家後來看到的樣子。假如真的有機會我們可以回到2005年8月的當天晚上,看看是我改變態度,大發善心,答應蔡柏你的請求,或者是你自己做出不一樣的決定,像是甩門離開,或許過去這幾年你就可以不用經歷這些寫劇本和導戲的苦難了?
名人推薦:蔡柏,他是個平凡人!~ 呂柏伸 (台南人藝術總監)
許多人喜歡用天才或者是鬼才來形容蔡柏,好像認為蔡柏在劇本創作上,應該是有神助(是的,他有很虔誠的信仰)或是鬼助(沒有,他應該是沒有養小鬼?),否則他怎麼能夠天馬行空、肆無忌憚地編寫出《K24》、《Q & A》和《木蘭少女》這三齣深獲高度讚譽的驚豔之作呢?
事實上,蔡柏真的就只是個平凡人,他的創作過程都極為痛苦,特別是這次的《Re/turn》。從今年農曆過完年後,劇組夥伴第一次讀首稿,到現在蔡柏還是不斷地在修改劇本,排練場上的設計者和演員目前手上拿到的是第11稿...
作者序
寫在下一個旅程前…
旅行這件事情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倒不是說我是一個多麼勇敢或者是愛追夢或樂於交際的人,可能就是因為我是一個既膽小又平凡又不喜交遊的人,所以上天給我一個潛在的慾望和需求:必須出走。逼迫自己得在無助的時候向倫敦街頭的路人問路;在孤單的時候讓陌生的白俄羅斯人主動跟我問好;在不敢付出愛的時候有一群熱情的希臘、巴西、玻利維亞人湧進我的生命。
關於Re/turn中的神祕門把。
2009年的夏天,我和希臘友人到西藏旅行。在一間小學旁的理髮店裡借用他們的浴室洗澡(因為借宿的小學裡面沒有洗澡間),坐了將近四十八個小時的火車(是的,從北京到拉薩,一路上還有綿延不絕的大便味從廁所傳出,畢竟僧多粥少…),洗完澡後,神清氣爽地和那些從成都來的小夥子聊天。
他們一邊熱情地幫我吹頭髮(我發誓,我說過不用),一邊和我看著牆上那張世界地圖聊天。
「你從台灣來的啊?」他們問。
「是啊,你們有去過嗎?」一說出口,才發現好像有點蠢。
「沒去過,很想去!聽說非常美麗,有一座叫做阿里山的是吧?聽說姑娘兒們都很美?」一個平頭的小夥子興奮地說著。
某種程度上,那首關於阿里山的歌謠之威力,比我想像中的大。
「那,你們最想去哪裡哩?」很明顯我迴避了阿里山姑娘和少年的故事,直搗關於旅行夢想的核心。
「喔?」幫我吹頭髮的小夥子認真想想。「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廣東。」
「廣東?」肥胖的我心中只想到什麼都可以吃的廣東印象。「為什麼?」
「因為靠海。」他突然認真感性地說著。「這一輩子,從來沒有見過大海,只要能親眼看一次,就死而無憾囉!」
他說得一派輕鬆,繼續吹著我早就乾了的頭髮,我當時卻像被投了一顆震撼彈般,久久不能自己。
這個人這輩子最大的夢想,是看到大海。這對從小生長在一個海島上的我們,可能是一個連想都不曾想過的問題。
拉薩的陽光很烈,即便晒起來舒服,還是要注意別被晒傷。我和希臘友人常在市集的古董店閒晃,晃入一間在地人推薦加保證的店家,店長熱情地招待我們,除了送給我們一人一張西藏古錢當書籤紀念,還搬出一堆珍寶給我們欣賞。我唯獨注意到櫃子裡的一個門把。
雕工精細,雖然表面已經斑駁,但是仍顯與眾不同。
我心想,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會願意「浪費」這麼多時間,在這一個從現在角度來看,只是一個扮演功能性角色的器具上面。
只是一個簡單的念頭:如果我可以擁有它,當我把它嵌入某扇門的時候,它會不會帶領我回到那一個時空呢?我好想回去創造出這種東西和存在這種美學的年代。一定跟現在很不一樣吧?應該不會一天到晚被逼著要做二十幾件事情吧?沒有手機的日子也有可能很幸福吧?交通工具的不便其實讓人更珍惜每一次的離別吧?
這些念頭不斷延伸。
關於Re/turn中的愛情習題。
看了電影「黑暗騎士」中,小丑對人性做的挑戰後,心中浮現出一個問題:如果今天一個你深愛的人過世了,然後魔鬼出現跟你說:「我可以讓你深愛的人復活,但是同時,這個世界上就會有另外一個你不認識的人死掉,你願意嗎?」
從這一個問題衍生出另一個關於愛情的問題是:「如果今天你和A交往,你很愛A,也和A求婚了,你們打算廝守終生;但是因為因緣際會,你來到五年後的未來,你發現你身邊的那一個人竟然不是A,是B,而且你們還有了孩子。請問,你回到現在的時候,你會怎麼面對A?」
愛情究竟是什麼?我們天天都在討論愛,我們常常說愛,我們或許偶而會給承諾,我們試著相信愛是永恆,但是,信念往往是很脆弱,很容易動搖的,當某些秩序崩毀時,我們還能相信什麼?又,我們為什麼不能多相信自己一點點?
關於Re/turn中的友情價值。
高中的友情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也很有趣。
退伍之後,我和那些原本在軍中很有話聊的弟兄幾乎全部失去聯繫,我其實有點意外,因為我沒料到,除去軍營這一個生活框架之後,這一群曾經和你朝夕相處,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的弟兄,就這麼容易就散掉了。
回想高中,何嘗不是一種變相的軍隊模式?你跟這一群人,當了至少三年的同班同學,從早自習、午睡吃飯、到夜間輔導,幾乎天天十二個小時都相處在一起,比和家人相處的時間還多,能不熟嗎?能不好嗎?
然而高中又是一個人格確立的擺盪期,很多人其實到大學才真正開始有決策力以及自主能力,高中時候大部分的人的生活可能還很單純,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和高中的朋友,談論哪些事情呢?我們討論愛情嗎?我們分享嗎?我們聊過未來嗎?我們了解的,真的是那一個最真實的自己嗎?又,我們當時可能自己都還在找尋自己吧?又怎能奢望了解另一個也不見得了解自己的人呢?
所以高中的友誼算什麼?
上大學之後,就業之後,我們都變了。我們一定會變,他也會變,她也會。當我們再度重逢的時候,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或誠實,用蛻變後的自己重新認識這一群老朋友?還是我們只能啟動一個舊的機制,繼續喊著那些現在可能聽起來都過分肉麻的綽號?繼續回憶當時的瘋狂青春?然後把自己現在心中的那一塊,又不小心地藏了起來。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越來越遠了呢?
關於Re/turn中的親情認知。
友人推薦了一本書,叫做「那些我們沒有談過的事」。看完之後深受感動,我記得有很多段落是邊看邊哭的(Well,關於愛情的段落),對於那一個把自己變成機器人的父親和女兒之間的故事也印象深刻。由於自己小時候是奶奶帶大的,在創作的過程中,遇到祖孫題材的時候,反而會不知如何下手,或許是因為離自己太近了。在寫親子關係的時候,反而可以用一種比較疏離的角度來看待。在我過去的創作中,【K24】裡的Sandy,【木蘭少女】中的花家人,【Q&A】中的關英蓮和劉世仁,都是我對親子關係的一種奇幻遐想,因為沒有什麼刻板印象,反而顯得瘋狂。這一次的母女之間,多了一點自己對於親情的疑問:親情是天性嗎?親情難道不是需要努力經營的嗎?如果沒有經營,你真的覺得它會一直存在嗎?
以上對人生的許多提問,其實很多都是這些年來旅行時的感受和抒發。我認真的認為,唯有讓自己真的處在孤獨的狀態,才知道什麼是幸福;唯有體驗過背叛,才知道承諾的重要;唯有了解更多未知,才知道自己的渺小;唯有這些美麗的感受浮現,才有可能創作。
所以,怎麼可能不再度出走,尤其是在世界末日來臨前?
Re/turn,獻給我英國倫敦CSSD那一群瘋狂愛我的好友們,特別是送給我這一個門把的Aris Gerontakis。獻給我長榮中學三年二班的朋友們,高中生活是我青春記憶中最快樂的三年。獻給蔡家人,這個家族悲劇性的幽默感讓我對愛有一種強烈的渴望和害怕。獻給三媽、佛祖還有保哥,祢們無私的愛和包容,才有今天的我。
寫在下一個旅程前…
旅行這件事情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倒不是說我是一個多麼勇敢或者是愛追夢或樂於交際的人,可能就是因為我是一個既膽小又平凡又不喜交遊的人,所以上天給我一個潛在的慾望和需求:必須出走。逼迫自己得在無助的時候向倫敦街頭的路人問路;在孤單的時候讓陌生的白俄羅斯人主動跟我問好;在不敢付出愛的時候有一群熱情的希臘、巴西、玻利維亞人湧進我的生命。
關於Re/turn中的神祕門把。
2009年的夏天,我和希臘友人到西藏旅行。在一間小學旁的理髮店裡借用他們的浴室洗澡(因為借宿的小學裡面沒有洗澡間),坐了將近四...
目錄
台南人劇團簡介
推薦序 蔡柏,他只是個平凡人 呂柏伸
自序 寫在下一個旅程… 蔡柏璋
人物表
首演資訊
劇本
第一景 神祕的包裹
第二景 倒數計時
第三景 那年之後
第四景 婚禮告別式
第五景 那些我們沒有談過的事
第六景 櫻桃眼淚(ㄧ)
第七景 說謊
第八景 告白
第九景 西藏的古董店
第十景 救贖
第十一景 櫻桃眼淚(二)
第十二景 重逢
台南人劇團簡介
推薦序 蔡柏,他只是個平凡人 呂柏伸
自序 寫在下一個旅程… 蔡柏璋
人物表
首演資訊
劇本
第一景 神祕的包裹
第二景 倒數計時
第三景 那年之後
第四景 婚禮告別式
第五景 那些我們沒有談過的事
第六景 櫻桃眼淚(ㄧ)
第七景 說謊
第八景 告白
第九景 西藏的古董店
第十景 救贖
第十一景 櫻桃眼淚(二)
第十二景 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