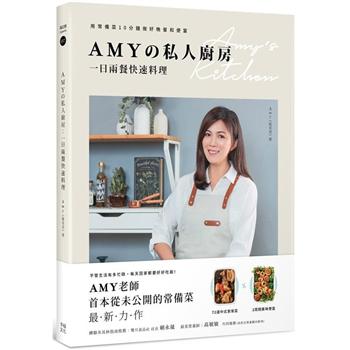那個夏夜,蘿拉被吊死,賈斯柏有了大麻煩,不知怎地我也軋上了一角。
這一切到底是誰造成的?我們能克服恐懼、找到真相嗎?
★《偷書賊》美國出版社、坎城影展金棕櫚獎製片迅速搶下版權,被譽為媲美《頑童流浪記》與《梅岡城故事》的天才之作!
★與大文豪柯慈同獲2010年西澳總理獎
★2010年澳洲書商協會年度最愛選書、澳洲圖書產業獎年度最佳書籍與最佳文學小說。
賈斯柏來到我的窗前。
我不知道為什麼,但他就是來了。
無論如何,他可真是嚇掉了我半條命。
賈斯柏是寇瑞岡鎮上惡名昭彰的壞男孩,查理則是個瘦弱膽小的書獃子,兩個屬於不同世界的孩子,卻因郡長女兒蘿拉的死,成了一場秘密戰爭中的戰友。
蘿拉死在賈斯柏的林中密居,加上他原本的壞名聲,使他成了理所當然的嫌疑犯,但是賈斯柏堅稱自己無辜,並且誓言要找到兇手,還自己清白。
為了朋友道義,查理答應保守秘密,從此查理眼中的世界變得極為不同。他發現只愛念書不擅運動的自己、有原住民血統又沒有媽媽的賈斯柏,以及身為越南裔移民的好友傑佛瑞,都必須忍受不同程度的誤解與欺凌。這個小鎮寧靜祥和的表面下,實則隱藏著許多荒謬與不公的現象。查理不禁開始思索:為何人們對不公義的事件如此冷漠與縱容,又為何對他們抱持偏見的人如此殘酷無情。
隨著故事的發展,查理從一開始的膽小怕事,到後來踏上尋找真相之路和領悟到勇氣的真諦,他終於明白,要解開賈斯柏與蘿拉之死的謎團,必須從找到自己的勇氣開始……
作者為掌握書中人物的說話方式、樣貌型態,特別到一個類似奧瑞岡的澳洲小鎮居住了一年,因此每個角色都像是真實人物一樣躍然紙上。發生在這些角色身上的誠摯友情、羞澀愛情與感人親情,也都真實動人、引人深思,使本書成為一部跨越時代與年齡的精采作品。
作者簡介
克雷格.西維 Craig Silvey
1982年出生於澳洲西部的戴林阿普,17歲時立志走寫作這條路,隻身離開家鄉,到海港城市費利曼圖闖天下,靠著當清潔工、酒保,以及替人採收水果維持生計。19歲完成第一部小說《我們都愛大黃》(Rhubarb),該小說不僅登上澳洲暢銷書榜、被選為柏斯國際藝術節的指定推薦書、澳洲政府鼓勵閱讀風氣的「書活」計畫選書,西維更獲頒「雪梨晨鋒報最佳青年小說家獎」。第二部作品《賈斯柏的夏夜謎題》更榮獲2010年澳洲書商協會年度最愛選書、澳洲圖書產業獎年度最佳書籍與最佳文學小說、西澳總理獎(與柯慈共同獲得)等多項大獎,並已售出電影版權。除了寫作,西維同時也是樂團「The Nancy Sikes!」主唱兼作詞作曲。
譯者簡介
顏湘如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法文系畢業,現為自由譯者。譯著包括《外遇不用翻譯》《事發的十九分鐘》「千禧系列」三部曲等數十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