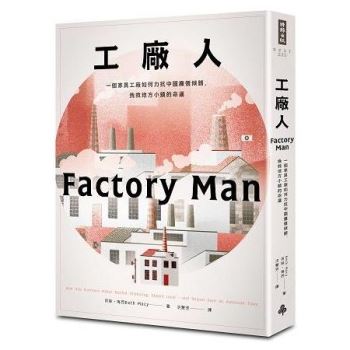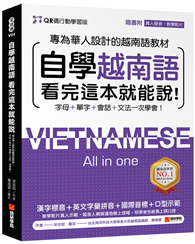後記
鬼魂不散
父親過世很久很久了。這幾年,我卻像是才逐漸反芻過來,覺得日子才過了不久。但日子的確過了好久了,我卻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過的……我記得當時在大太陽下走了幾小時,一路找到那家警察分局,我要求看他的屍體照片,照片上,剝落的皮膚是青黃顏色,皮膚邊緣是鮮艷的綠色。我不知道死人的皮膚會這樣大片剝落。死亡證明上只有四個字,那四個字,彷彿是再正常不過的死因,像普通毫髮無傷的猝死的人通常被冠上或被隨意填上的病名。我不願說它,這由不得我信或不信。我不信,但我不得不收下那張死亡證明。
都說,他死時睜大了眼,拳頭握得很緊。是誰為他拉下眼皮,掰開手指,我不知道。
那年我回鄉處理喪事,是現場唯一的直系血親,我決定了日期,選了棺材、骨灰甕和喪葬場地,但我沒能看到他完整的身體,棺材裡的他穿著□衣,棺材只開了一小道縫。準備火葬那天,他終於被抬出來放在架子上,解凍了的身體嚴重縮水,像是衣服裡已沒了東西,他的臉上冒著細水珠,張開的嘴巴裡面是黑紫色舌頭。當屍體再放入棺材,我上前看他最後一眼,不知為何,他的臉赫然是一邊白一邊黑,很突兀很分明,但棺材很快被蓋上了,抬走了,進焚化爐了。
幾天後,他來到我夢中,依舊騎著那台陳舊的富士牌腳踏車,後座載著我上學和打工時用的背包,它總是裝了太多書本,很重,壓得我駝背。腳踏車載著我的背包騎進一條隧道,洞口透出幽幽的黃色亮光,他進隧道前始終回眸望我,直到消失在看不見的隧道裡。
我心裡像是被重重的一擊,很不甘心,拿出他的死亡證明,一路找到那家警察分局,調出照片,好好看他最後一眼,完整的全身的一眼。
小時候學過一首歌,德弗扎克的念故鄉。但我忍不住說,我恨故鄉。有時候我身心俱疲,太累了,沒力氣去想著我那長期的恨意,後來,我發現我懶得恨,或者承受太多,原來的恨已排不進心裡的空間了,只剩提防和恐懼。
就像連續劇的情節,從一個不算太大的事件,滾雪球般,引發一連串的悲慘和不幸。若要說它,聽起來可能會像離奇變態的驚悚劇,不像真實的人生;但有人說人生如戲,很老掉牙的一句話,我卻不得不承認,當它發生在自己身上,確實是如戲,一場大悲劇。
從一個調查事件開始,從一個逃避般的遷移開始,一個家庭,擴及了週邊的親朋好友,就進入了長期噩夢,家破人亡。
我至今仍不說它,或者是,仍不敢說它。只把眼淚擦乾。
那麼,先說點別的吧,說我的無知和幼稚。
那是戒嚴年代的記憶了,小學三年級,蔣中正總統華誕那天,全國放假。我在家閒著沒事,把勞作課裡教的工藝溫習一遍,用一張白紙做成一個漂亮的燈籠,然後開開心心的掛到家門外。父親午睡醒時,我獻寶似的要他看看屋外我的傑作,不料他劈頭大罵,命令我取下燈籠,我不服氣,問他為什麼,他什麼也不講,衝出去扯下白燈籠,揉成一團扔進垃圾筒。成年之後,我才明白,當年若是被人看見了去告密,敢在蔣總統的生日觸霉頭,叛亂罪之類的大帽子肯定要扣下來。
小學五年級,某個星期日,老師要我們集體到學校看政治宣導影片,父親懶得載我出門,叫我別去了。第二天上學,老師當著全班學生的面叫我站起來,問我為什麼昨天沒來看電影?我畢恭畢敬,據實以答:「報告老師,我爸爸說,那只是演一些愛國的東西,不看沒有關係。」老師足足訓了我一節課,從國家的重要性和共匪的可惡性,強調沒看這個電影的罪過。
有一次下課,同學聚在一起,照著老師剛才上課的說法,同仇敵愾的批判某些人是叛亂分子,是大壞蛋。我居然引經據典的另持一見:「課本說,孫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了,才被叫做國父,如果這些叛亂分子這次成功了,是不是以後的課本也會叫他們國父或革命志士。」諸如此類的事,發生過好幾遍,我曾天真的告訴同學,家裡有叛黨寫的書哦,就像她們炫耀自己家有什麼明星畫報一樣,說得像是在獻寶,簡直不知死活。
有一天,父親忽然替我向學校請假,帶全家出遠門,平時節儉成性的他,居然大老遠帶我們去梨山旅遊,逛完了大半個梨山,一家人毫無目的的跟著父親四處亂走,父親似乎不打算回家。他低頭問我,還想去哪裡玩嗎?這是他最慷凱的一次,我記得我們又去了好幾個地方,只是爸爸捨不得買足車票,一家人擠在短少的座位上,像是電影裡那種逃命時沙丁魚般擠在一起的難民。
但是,無處可去了,終究得回家。
聽說那幾天,調查局派人來了,找不到父親,就向左鄰右舍一個個打聽,還追查到台南鄉下老家去,祖母和親戚都被盤問一番。父親一回到家,就被調查局帶走了。
有人告發了他的朋友,他是為了朋友的事被帶走。
聽說父親堅持不出賣朋友,被調查局體罰逼供……
可是父親從不對我們說。我猜想他是愛面子,他覺得讓小孩知道父親被人刑罰逼供,很丟臉。
之後我們就搬家了。換了個地方未必沒事,新的雪球開始滾動,同樣是個不算太大的起因,卻造成重大轉捩,無窮的災難開始,監聽、跟監、信件照片失竊、中毒……所有詭怪情節輪番上演,然後我天真無邪的少女時代提前結束。
父親生前希望我去投考調查局,從我讀小學起,他就這麼講,甚至要我背六法全書,及早準備。也許,這是想彌補他曾考上調查員,卻因沒有入黨而被取消資格的遺憾;或者,他覺得那個地方有令人違抗不得的特權,有命令人聽話的特權?或有胡作非為的特權?但年輕時的我,沈緬於詩書樂畫,對他口中的特權或福利完全沒有興趣。我除了聽話的隨一群黨員同學去參觀過一次調查局,聽話的加入他不想加入的政黨(但他常常很聽話的投票給那個政黨)。從大學二年級開始,每年,都是他主動替我繳了黨費,讓我維持名義上的黨員身分,以防日後失去進入公職的資格(這是他根深蒂固的想法)。每年,他寫來的信裡總不忘提起,要跟那個黨保持聯絡啊……直到他過世。他不知道,我曾有一張蔣經國總統署名的獎狀和小金色獎章(我沒有任何貢獻,忘了為何得到獎狀)。他也來不及知道,時代變了。他老是擔心我找不到可靠的工作,他總是說寫作或畫畫會餓死,他扯下我貼在牆上的水彩畫、他沒興趣看我得獎的畫作、他輕蔑地掂著我獲得的文學獎座,說這個賣給收破爛的,能換幾塊錢?我很生氣,不肯聽他的任何意見,覺得他俗氣又現實。日後有了工作,才逐漸能體會,在他卑微的心願裡,奢望的根本不是特權,只是能夠平安溫飽。這個貧農之子,自小父親就被日本人抓去當軍伕,經常挨餓,躲在甕裡逃避被送出去當養子的鄉下男孩,他不是沒志氣,只是他更清楚現實,他努力讀書、考試,為了現實,選擇婚姻,也算計現實(母親的姨父兼養父是台南市首位無黨藉市長的市府機要秘書,但也死得早),因為其他兄弟全當了童工。當年,整理父親遺物時,發現了一張來不及寄出去的「黨員聯絡單」,原來,他怕我不聽話,不跟黨聯絡,便主動替我和黨聯絡了,上面寫道:「畢業後,能否介紹工作?最好是公家機構。」好像是跟神佛祈求一樣,我啞然失笑,他那樣認真的替我繳黨費,難道是在繳香油錢嗎?日後憶起,總不免心酸,原來,他比我更天真。他不知道,時代真的會變。時代一直會變,但不見得變得更好,雖然人民總是期望它變,彷彿變了就會好。
這是難免的,人的記憶,往往停留在某個自認為重要的階段,頻頻回顧。童年時,母親常說起,二二八事件,外祖父母連夜逃亡,之後家宅被某位將軍佔住了,那座巨宅,庭院有整個學校的運動場那麼大,牆砌得很矮,附近的孩子可以翻牆進來摘水果、跳進庭園的水池裡戲魚,平日往來的都是名流士紳。我曾被帶去原地憑弔,除了剩下一棵果樹,所謂的魚池、花塢、庭園和日式屋舍,早改建成馬路、幼稚園和密密的公寓了。她說時喟嘆,而我像是站在另一個世界聆聽異國童話,現在的世界、未來的世界,彷彿不著邊際,也離我很遠。我的現在和未來,未必是當下的現在和未來。噩夢未曾離去,然而我有另行築夢的權利。
寫這個故事,不是我家的故事,虛構成份居多,但裡面的人物和命運又有些真實,場景借的是另一位朋友的家(聯同我外祖父的家),國民黨高官之子,童年就擁有貴族一樣的享受和特權,他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他家「不過是」比人早一點有這個、有那個而已。他又用高高在上的語氣提醒我,千萬不要因此產生相對剝奪感,因為沒有一個地方是你能真正擁有的,你只是過客,你住的房子以前是別人住的,你站的土地以前也屬於別人的……我靜靜地聽著,因為我從沒敢妄想什麼「相對被剝奪」,但他是這麼揣測我;幾年後,他的父親過世,至親要來分房產,他卻十分激動,他忘了他當初是怎麼提醒我的,他說什麼也要保住那個當年國民黨廉價賜給他們的大宅院。我知道,他並不貪財,他是要他的家看起來仍舊完整,他懷念曾住在這個家裡的所有靈魂,哪怕已人去樓空……我想到當年那位進駐外祖父宅子的將軍,聽說入住不久就被自己的黨槍斃了。那宅子,不曉得換了多少主人,多少鬼魂,的確,沒有人能真的擁有;即使入土了,進了墳墓,也不見得安寧,外祖母的墳墓在六十年前剛下葬不久就被夷為平地,這個名門美人、留學生、巨富之妻,活在土地上的時間短、埋在土地下的時間更短,屍骨無存。她死得慘,但她不知道後來發生的事才叫可怕。我還沒打算寫我家,也不願意寫。也許我在害怕、迴避某些恐懼,或者依舊選擇緘默,於是往更早的年代裡逃去。儘管,那個年代和我有距離,六七十年前、七八十年前,也不算太遠,生活氛圍與我的童年彷彿是接近的,至於心理氛圍,能抒解我心中鬱悶之萬一,便也勉強夠了。
小說主要情節停止於蔣公過世那年,那年,我九歲,是我僅有的兩年悠哉歲月的尾聲。哪怕過了三四十年,我忍不住,總是懷念起遙遠的那兩年。而那時的蔣公,就像神話人物,離我好遠,他所住的那個台北,對我這個台南小孩而言,就像外國。至今,我仍能熟背蔣公遺囑,文言文,那時若沒背好,老師就不准我們回家吃飯。我還能把秦孝儀寫的另一首詞意艱奧的蔣公紀念歌詞,背上大半首──翳維總統,武嶺蔣公,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巍巍蕩蕩,民無能名;革命實繼志中山,篤學則接武陽明,黃浦怒濤,奮墨絰而耀日星,重慶精誠,製白梃以撻堅甲利兵……三十年後,我能得意的向年長我五六歲的朋友們炫耀這記性。當年,全國戴孝,天天在升旗典禮全體默哀三分鐘、唱蔣公紀念歌,我乖乖的照做,可是一回家,還是在浴室裡唱著瓊瑤電影情歌。哪怕不清楚裡面唱的愛情是什麼東西,不清楚即將來臨的禍害……
三種矛盾,時代的緊繃和輪替∕悠哉的天真∕民主時代囚籠般的生活,構成我勞累和不斷構想脫逃的歲月。
一直不知道怎麼寫家,從出生開始,我大概搬了四十幾次家,多半像逃難,像換個牢,再換個牢。
這本書,十六年前寫了初稿,用二十萬字,極端念舊的記我童年某短暫時期的家。十六年後,不要它了,刪到只剩五百字,保留了一位配角的形象,其餘全部另起爐灶,換了主角、換了場景、換了另一個家、換了事件,但感覺似乎更貼近了,貼近我心裡的痛,貼近我懷念的消失的家。撤換的動機,是當我看了愈多史料,那些口述歷史、國安局檔案、那些獄中的受難者,我變得激動而非感傷,彷彿隔著幾十年時空,有人和你相濡以沫,彷彿倖存就是萬幸了。我決定把這一時代的這群人納進來,那激動,是因為群體,而非個人。縱使,故事裡仍私心地隱藏許多自我、許多秘密遊戲、許多抗鬥或逃脫的幻想。
張瀛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