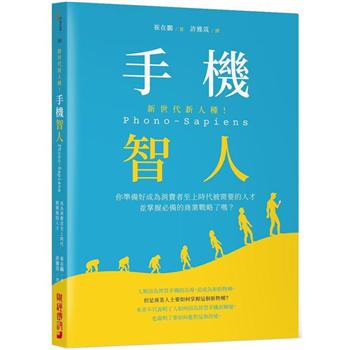旅美作家夏眉透過七則中長篇小說〈踏歌行〉、〈小夫妻〉、〈坐在窗台上的沉思〉、〈野渡無人〉、〈他的一生〉、〈懷念那已失去的〉、〈幽窗冷雨〉探討親情、愛情、婚姻、命運,種種男女之間的試探與角力、不能圓滿的戀情、無法抵抗的命運,透過作者誠摯而細膩的文筆,深刻呈現。
本書特色
1.長篇小說〈踏歌行〉曾在《聯合報.副刊》聯載,品質深受肯定。
2.內容深刻寫實,文筆成熟,描繪人生真實境遇,冷暖兼蓄。
作者簡介
夏眉
本名謝昭梅,1942年生,1964年臺大外文系畢業,美國紐澤西州立若歌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圖書館學碩士。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服務二十七年,於2010年夏天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