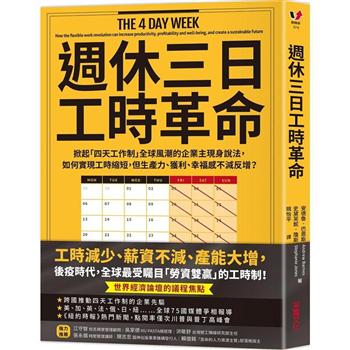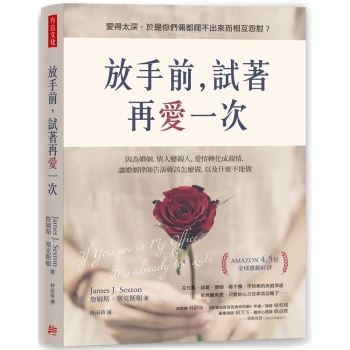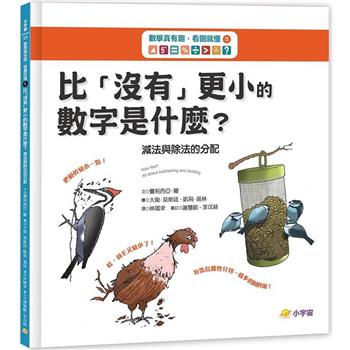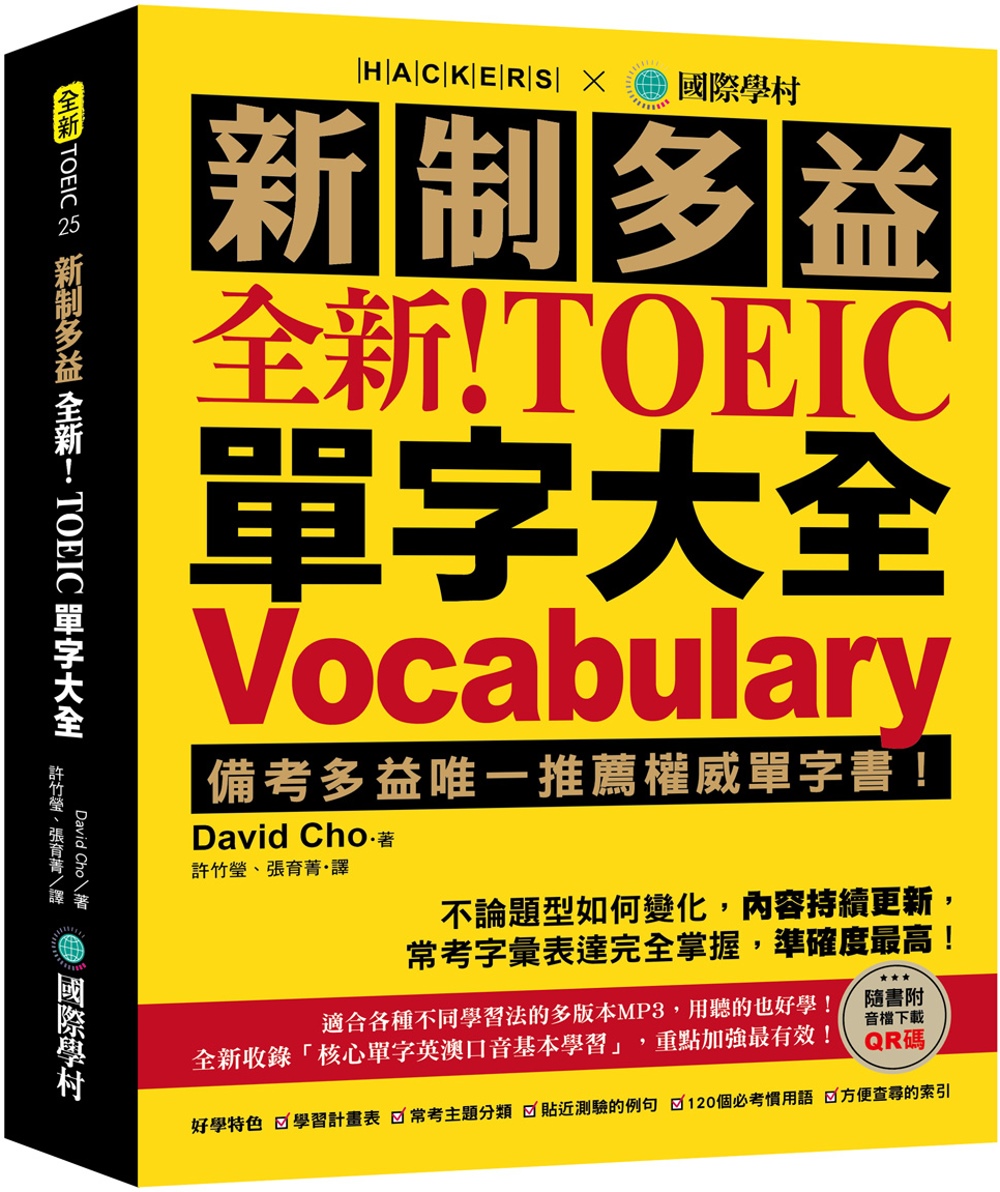我們的星斗不斷歪斜,黑洞自一旁冷眼旁觀——《輪迴手札Ⅶ》
詩人宋尚緯第一本個人詩集,細碎紀錄人世的繁瑣細語,反覆辯證生滅、真假與虛實。面對愛欲與生死,詩人用敏感脆弱的身體迎擊生存的殘酷,詩中皆是人的自我處境,以「輪迴」推敲每一個你我之間的關係。重複的夢境、賴以維生的語言、展現思想的修辭與不知生存何以為繼的隱匿與踟躕,在詩人無盡迴圈的文字圖裡,深刻的筆跡猶如一幅眾生曼陀羅,字字句句都是關於痛與愛,涉及昨日與未來,捕捉光與黑暗,漫漶著我執且剝落著我相的內心對白。
關於輪迴手札
「我試著將我的道德觀,我的價值觀都寫在詩裡面。
雖然寫得不好,雖然諸多紕漏,但我終是將他給寫出來了。
我試著將我在想些甚麼都寫在《輪迴手札》裡,生死,道德,曾經與現在。
其實一開始寫輪迴手札只是想寫一首所有人都能讀懂的詩,
不論平時有沒有讀詩、寫詩都能夠看得懂的詩,
令所有人都無法再說『詩,不管是讀或寫都難。』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卻彷彿也輪迴了一次,將我所擁有的都再次思考,
我們的思慮是有限的,輪迴也是有限的,但我們能在有限中創造無限,
我們的生命亦然,總在用有限創造無垠的未來。」
得獎紀錄~
〈駱駝〉:第四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新詩優勝
〈日夜的界線與瀕臨死亡的城〉:X19全球華文詩獎
〈找房間〉:大學校園文學詩獎作品巡迴詩展暨第二屆國民詩展
〈我們這些毫無關聯的細節〉:98年度好詩大家寫收錄
〈輪迴手札〉:2009年文創副刊年度最佳作品獎
〈日光旅行〉:2010全國巡迴文藝營創作獎新詩佳作
各方推薦~
《風球詩雜誌》發行人、詩人 崎雲:
「……在可感的疼痛之後而能有所思,有所思之後而能有所悟,有時讀尚緯的作品有如經歷一場思想的碰撞,除此之外,更多是看見詩人如何轉化其中的苦果,其中的接受與承擔。」
詩人 嚴忠政:
「這些詩篇是早熟的,像是結了痂的禱詞,傷痛之後又以傷痛回應那傷痛,但終不棄絕對於文字的信仰。如果『你』也自傷口歸來,怎麼可以不給他一點回聲。我相信,那些深淵、那些冰隙裂縫般的斷句,一定也藏著我們的賦格。」
詩人 紀少陵:
「詩人泅泳在倫理潮間帶的禁區 以寂寞的歌喉
吞吐一整個午后的牢騷」
詩人 顏艾琳:
「在反覆重沓這位年輕詩人營造的詩境,是輪迴的步伐、是離開又回來的節奏,是發現遠方就在身邊的迷悟、是好像旅行整個宇宙後卻又渴望能夠迷路的行者。或者,我讀到的是一個無法在實際生活中旅行的人/我,對夢中幻想的世界/我們,用他的文字先行伸出擁抱的手臂?」
作者簡介:
宋尚緯,1989年來到這世間,直到今日依舊在相信這世界曾被我所不信的。現於南華大學就讀。
混亂與正反之間的糾結。
生活就是不停抽絲剝繭,並且研究絲線中每一個部分所擁有的不完。
世界充斥著各種微妙的符碼,在其間穿梭的我們仰賴著其所構築出的縫隙間活著。
痛苦與快樂、真理與謊言、愛與恨、對與錯、生與死之間其實並無分別。
這世間太執著於有,但也許「無」的時候,我們反而擁有更多。
我們總在這世界來來去去,但既然來了,總會有離去的一天。
來去聚散一直都是我們人生中最大的課題,
因此我們輪迴,輪迴中自有札記留存。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風球詩雜誌》發行人、詩人 崎雲:
「……在可感的疼痛之後而能有所思,有所思之後而能有所悟,有時讀尚緯的作品有如經歷一場思想的碰撞,除此之外,更多是看見詩人如何轉化其中的苦果,其中的接受與承擔。」
詩人 嚴忠政:
「這些詩篇是早熟的,像是結了痂的禱詞,傷痛之後又以傷痛回應那傷痛,但終不棄絕對於文字的信仰。如果『你』也自傷口歸來,怎麼可以不給他一點回聲。我相信,那些深淵、那些冰隙裂縫般的斷句,一定也藏著我們的賦格。」
詩人 紀少陵:
「詩人泅泳在倫理潮間帶的禁區 以寂寞的歌喉
吞吐一整個午后的牢騷」
詩人 顏艾琳:
「在反覆重沓這位年輕詩人營造的詩境,是輪迴的步伐、是離開又回來的節奏,是發現遠方就在身邊的迷悟、是好像旅行整個宇宙後卻又渴望能夠迷路的行者。或者,我讀到的是一個無法在實際生活中旅行的人 / 我,對夢中幻想的世界 / 我們,用他的文字先行伸出擁抱的手臂?」
名人推薦:風球詩雜誌》發行人、詩人 崎雲:
「……在可感的疼痛之後而能有所思,有所思之後而能有所悟,有時讀尚緯的作品有如經歷一場思想的碰撞,除此之外,更多是看見詩人如何轉化其中的苦果,其中的接受與承擔。」
詩人 嚴忠政:
「這些詩篇是早熟的,像是結了痂的禱詞,傷痛之後又以傷痛回應那傷痛,但終不棄絕對於文字的信仰。如果『你』也自傷口歸來,怎麼可以不給他一點回聲。我相信,那些深淵、那些冰隙裂縫般的斷句,一定也藏著我們的賦格。」
詩人 紀少陵:
「詩人泅泳在倫理潮間帶的禁區 以寂寞的歌喉
...
推薦序
畢竟大樂 崎雲
有一種說法是詩人藉由文字來塑造自己的理想,然而對於一個善感的寫作者而言,所謂的理想世界其實是由眾多的不理想所構成,集合那些被世人篩檢出來的冷漠、悲傷、焦慮、憂鬱與失落等頹傾與毀壞於一處,從而顯示出不理想中的理想與有序,在文字當中體會與反省、傷痛與療癒,思索滅後如何生,破後怎麼立,於是那些在詩中被書寫出來(或者隱藏)的苦樂與悲歡,才有了其普世而又獨立的價值,一如詩人自己所說:
光是閃電,雨是露水
語言是文明,謊言是風雨
詩是過去是
未來是現在,是時間
是光,是剩餘的殘生
〈遠處蟬聲〉
詩是每一個當下,亦是殘生的依託。幾年前我曾在這樣提到尚緯的作品:「其觸及生命存在意義的作品,圓熟醇厚,可以看出詩人在面對生活困厄時的態勢與轉變。」如今再細讀尚緯的作品,使我更加肯定當時的想法,無論是
對著相同的風景:
你是誰。在之後
有個與你相同的存在
不停質問
:你又是誰
〈夢境裡的最後一只蝨子〉
的自我詰問,或者
如此偏執到令人落淚的組合
但我喜愛這些無解的偏執
像我正日漸離去的青春
〈那些我從未得見的偏執〉
這樣坦然的承擔,都或隱或顯地藏在尚緯的詩作之中,相互交涉與顯現,在可感的疼痛之後而能有所思,有所思之後而能有所悟,有時讀尚緯的作品有如經歷一場思想的碰撞,除此之外,更多是看見詩人如何轉化其中的苦果,其中的接受與承擔。
總觀其詩大致可分為三個書寫的主題,分別是:生命存在的痛苦與焦慮、情愛的掙扎與意義,以及現實(生活)的傾斜與迫害等,但歸納起來,大致不脫離愛與欲 / 生與死的這兩個大方向的探討,在詩中我們可以發現尚緯常藉詩作進行自我角色的投射與練習,尤其是在面對生命存在的焦慮時,詩人除借物象以託其志外,同時也表露了寫作當時生命過程的處境,如〈駱駝〉、〈找房間〉〈夢境裡的最後一只蝨子〉等,在這些作品當中被詩人所挑選出來「代言」的,其意象屬性大多偏向受到欺凌、壓迫與相對弱小的一方,那些生命經歷過的悲歡轉化在詩內,在此讀來顯得格外堅毅與壯烈,縱然那些自我內化與思索過程中所尋得的命題與哲思有時無法藉由詩裡種種現實投射的線索找到出路,但解脫的方法我們知道它確實存在,一如
像在尋找自己的
時候,偶爾發現自己
像尋找掛在鼻上的鏡框內
尚未穿透的光
〈日記〉
讀尚緯的詩不僅僅是對於自我的思索與追尋,同時亦是深刻的光與自我的返照。
我一直覺得尚緯是「惡世」的,尚緯的「惡」,是藉由黑暗與骯髒的所在以反身洞見自我的存在,清朝的玉琳國師曾言:「大凡修持,需量己量法,直心直行,誠能厭惡三界,堅志往生。」面對煩惱、邪見增盛,苦多樂少的五濁惡世,尚緯的「惡」其來有自,縱使:
要有愛才能造
但我們對這些反覆的世界並沒有
沒有絲毫愛意。
〈潮流集體死亡〉
我不停地患有各種憂慮
各種措辭使用的憂煩
在我將要睡時,尤其嚴重
〈如果就這麼不停地重覆〉
但我們仍然可以在詩中得知尚緯心中尚有未曾崩壞之所,仍然願意相信世界關於美、良善、勇敢、真誠與愛的存在。
我知道這個世界
所有的光源所有的夢偶爾被吞噬
到某個飄邈的角落
〈像我知道一切那般的不知道〉
那麼該不該睡,該不該醒
我知道那些是睡眠,是無妄的過程
而過程往往是醒的
一如我知道而我不知道那般
〈像我知道一切那般的不知道〉
在知道與不知道之間辨證夢與世界∕睡與醒的相關性,對於客觀物象上的觀察以及了解上的私我處境,再理想與現實的切換與互涉當中,形成了一個相互交疊而又截然不同的世界,尚緯是「瞭解」自己的,這個「瞭解」指的是生於就世的各種處境以及對於生命本身所存在的質疑,在此便有了自我與世界主客的某種悖逆,這是尚緯的「知道」,而其「不知道」的正也是因為他的「知道」未能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以面對現世中存有的苦難與疑難,「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罷,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只是一種引導、暗示或者應該說是一種自我的催眠與說服,我們不害怕受傷,我們將受傷視為解脫的一種方式,我們需要的,很多時候只是一個單純並且可供依靠的生存的理由。
尚緯對於生命的焦慮,其實亦是某種程度的肯定自己,以對抗那些「非存有」的經驗,這種「非存有」的經驗不只在於生命的無常感,同時也在於個人於現實環境當中自我消解的無意義感,著名美國神學家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認為:「人的行為,無論是創造或者是毀滅的都牽扯到某中焦慮的要素,人因為有限又自由,既受限又無限,自由與有限並存的弔詭行徑,使人生而焦慮。」對於心思細膩的詩人而言,生命的不定、感情以及生活中遭遇的一切所隱含的無常感,藉由詩作來辯證與調解,或者說是如上所述藉以肯定自己的存有:
生滅終將我們的出口
打了死結。且無法規避這些出路的行進
試著埋入一些譬喻
學著放歌,學著愉悅,學習如何種植出
一條蜿蜒的路徑
〈分解還原〉
我記得昨日我將生活流放於花園之內
而我的靈魂卻在外長遠的放逐
〈分解還原〉
看著各種題目,我不只需要答案
更需要所有的過程……
〈分解還原〉
體認到生命的有限性與無可迴避性,有生皆苦,有些時候是不得不苦,向內觀照自我的本心與來歷,除了所有一切有所限制的生命歷程與環境之外,在詩中放任自己,進入悲傷、體會痛苦,從而找到屬於自己解決生命焦慮的那個答案。
由
二十年後我回到雨中
畢生的意象滿身是傷地攀爬
複製的音節冗長且拖曳著越來越瘦越來越長的影子
為了過多的懲戒而寬恕
這個世界的病症太過沉重,我們不自覺地染病
不自覺地吐露出過多形而上的假設
〈回到光中〉
到
二十年後我回到光中
時間的雨不停下著
錯落有致的聲響節錄我傷口裡
所有不安的語氣
現實通通埋到記憶的土壤中,等待花開的季節
有什麼熱情是屬於我
諱莫如深的意象還匍伏前進著
即使帶著傷也依然相信有光
屬於自己,亦屬於世界
〈回到光中〉
正因為詩人仍然願意「相信」,便還能被招攝入光,進而成為光的本身,於是某種程度上,焦慮得到了緩解,意義也在碰撞的過程當中自然產生。佛法認為現實中的一切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構成了讓人無法安心的八風,薰習日久,則離道日遠,詩在某種程度上,亦可謂八風無法吹動的本性真如,在語言特色上,尚緯的詩中常不避諱佛教詞語的運用,將詩提高到了一種厚重與內省的高度,在生活的種種不平當中,看似妥協,實則承擔,相較於其他善於以佛典、佛語入詩的詩人,尚緯並非書寫生活體驗的禪機,而是回到自我「存在」價值的思索,向內挖掘,思辯身內與身外的諸多問題。
L,你在人海中游動的時候是否看過
他們的腳步聲響化成一串數列。密碼化的符號
從人群的中心流洩出來,他們彷彿在思量
一些變化的必要性與獨立性的存在」〈輪迴手札III〉
沿岸的浪花攀爬上岸,他們閱讀書報
埋在深海的亡靈默默浮空,看著人們的影子
這些存在竟然比他們還要稀薄」〈輪迴手札III〉
出現在〈輪迴手札〉當中的佛教詞語只是尚緯藉以表達私我價值與道德觀的一種工具,尚緯慣用語言的矛盾以及正反辯證來帶出詩中所真正要表達的意涵,在形式上亦多做嘗試,像是〈日夜的界線與瀕臨死亡的城〉、〈物化的階梯〉等,而在〈輪迴手札〉這一組詩當中,無論是形式、語言、架構、寓意以及書寫企圖上,都充分且完整地展現出他的才氣,包含長句的應用、語氣的展延以及意象的精準三者共構的敘事氛圍,藉由代名詞以形成人我對話(或者其實是「我」與「我」的對話)來探討生與死 / 情與恨 / 身與心處境等有關於「存在」本身的諸多問題與意義,縱使我們知道這些問題不一定有答案,或者應該說是不必然有固定的答案,但這一組詩的確是整本詩集完整度以及精采度最為整齊的作品了。
於是真的要我說些什麼期待尚緯的話,其實都是多餘的了,誠實一點來說,在年輕一輩(八零前後)的創作者中,林禹瑄、周禹含、宋尚緯這三位年輕詩人是我長期抱以關注的,或由文學論壇,或從文學獎,他們同時也都是X19詩獎所選出來的孩子,除了印證了詩獎的價值與影響之外,同時也讓我們驚豔於他們嶄露出來的才氣,在同輩之中的確是早慧而且頗具潛力的,禹瑄和禹含這一對學姊學妹組已於這兩年陸續出版了個人的詩(文)集,尚緯也終於在今年將作品整理出來蓄勢待發,準備在眾人的關注之下,展露他的頭角,這是詩人的第一本詩集,是起點,也代表的未來更多的可能,為呼應其書名〈輪迴手札〉,我便以佛教《八大人覺經》中的第一覺悟相贈:「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如是觀察,漸離生死。」祝福尚緯能夠在生命之流中,找到那些潛藏於困頓之中問題的答案了。
二零一一年桐月 寫於桃園 龜山微冷
※崎雲,本名吳俊霖,台南人,《風球詩雜誌》發行人、風球文化創意企業社行銷總監、五度空間表演藝術劇團演員/顧問,目前為風球詩社同仁、然詩社同仁。著有詩集《回來》(角立)。
畢竟大樂 崎雲
有一種說法是詩人藉由文字來塑造自己的理想,然而對於一個善感的寫作者而言,所謂的理想世界其實是由眾多的不理想所構成,集合那些被世人篩檢出來的冷漠、悲傷、焦慮、憂鬱與失落等頹傾與毀壞於一處,從而顯示出不理想中的理想與有序,在文字當中體會與反省、傷痛與療癒,思索滅後如何生,破後怎麼立,於是那些在詩中被書寫出來(或者隱藏)的苦樂與悲歡,才有了其普世而又獨立的價值,一如詩人自己所說:
光是閃電,雨是露水
語言是文明,謊言是風雨
詩是過去是
未來是現在,是時間
是光,...
目錄
畢竟大樂 崎雲
形而下的字跡
駱駝
找房間
日夜的界線與瀕臨死亡的城
夜間九點的餐廳
潮流集體死亡
物化的階梯
夢境裡的最後一只蝨子
日記
像我知道一切那般的不知道
遠處蟬聲
脫離可能性
如果就這麼不停反覆
聲響
不會
如果我們談論
分解還原
這些我從未得見的偏執
像我一般地留下
節制的行進
午後的語言
最後的旅程
曲解書
生活
作者已死
過往
之後
我早已訂制好的中國制大腦
離別書
一體性
一滴水與海洋能夠解釋的所有語言
現代人的床邊故事
回到光中
最後的閱讀
便條紙
四種不確定的存在
她以為自己是樹
形而上的筆記
通過最後的謊言
垂釣
之外
無雨的日子
寂寥之書
死與生各種不同的面相
趁著夜色,我寫了封信
我們僅僅是場聚會
無法結束且漸漸隱匿的夢境
為了一些巨大的什麼
那些未盡的夢
斷句練習
我的離去,便是我的歸來
而我僅僅加上一個空白的註解
然而我需要的只是一場夢境
分別
最後
聽到了聲音,自遠方……
夢境的死亡
為了一種痛楚歌唱
無聲的發音練習
最後的雨季
又看到雨聲走過
我佛
無關乎渴求的模樣
我們所豢養的自己
我終於明白
謊言
我們這些毫無關聯的細節
療傷
我們都逐漸長成陌生的人
日光旅行
假若我又遺忘了什麼
玫瑰的模樣
回來
無不奔走遠去
輪迴手札
輪迴手札Ⅰ
輪迴手札Ⅱ
輪迴手札Ⅲ
輪迴手札Ⅳ
輪迴手札Ⅴ
輪迴手札Ⅵ
輪迴手札Ⅶ
輪迴手札Ⅷ
輪迴手札Ⅸ
輪迴手札Ⅹ
死亡另有美德 嚴忠政
遊走鯨身後的地景誌 紀少陵
我寂寞地呼告著,我們即將展開的歷史 顏艾琳
畢竟大樂 崎雲
形而下的字跡
駱駝
找房間
日夜的界線與瀕臨死亡的城
夜間九點的餐廳
潮流集體死亡
物化的階梯
夢境裡的最後一只蝨子
日記
像我知道一切那般的不知道
遠處蟬聲
脫離可能性
如果就這麼不停反覆
聲響
不會
如果我們談論
分解還原
這些我從未得見的偏執
像我一般地留下
節制的行進
午後的語言
最後的旅程
曲解書
生活
作者已死
過往
之後
我早已訂制好的中國制大腦
離別書
一體性
一滴水與海洋能夠解釋的所有語言
現代人的床邊故事
回到光中
最後的閱讀
便條紙
四種不確定的存在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