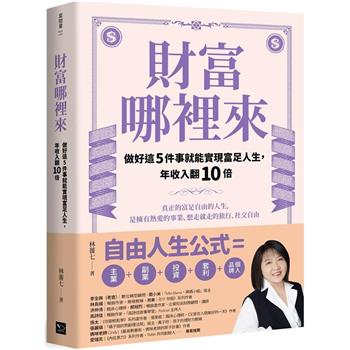神聖王國的發光二極體
黃羊川
我失去權杖
因此,我遁至另一次元
成為與你相反的王──李雲顥〈少男的復仇〉
1.
繁花盛開的森林裡垂掛黑死病般的詩句,兒童想成為詩人前須學會閃躲傳染病,並誠實地吞食自身的詩語言。
然而,在黑暗時代,仍會有人寫詩嗎?
黑暗時代,勸誘詩人離開詩的人仍在,阻撓詩人創發想像的人仍在,搖動詩旗不動干戈的人仍在,而以詩之名懷柔收編的人也仍在,更不要說結黨營詩的人了;詩世界裡不但有大人,也不乏小人。然而,在黑暗時代的黑牆上,兒童去那裡塗鴉呢?
儘管發現所有詩人的辭彙都不老實,但不爭的事實卻是:部分的人確實出於好意,另一些人的善意則鋪了無法見底的地獄。因此,兒童沿路丟下麵包屑,或是跟著黃磚走,都尋不到回家的路;只是預告了路程的艱辛。
在此表面光明內裡腐壞的小道上,仍有一個個兒童拼命地舉手發言,急欲離開中心前往邊緣,於是愈來愈多的新詩人誕生,即便大人經常在家,要求兒童閉嘴、小聲或者講一樣的話,卻仍然阻擋不了兒童成為新詩人;新詩人拆下自己的骨頭作為武器,迷途不知返地走向尚未完成的路徑。
李雲顥正是途中的一員。
剛認識李雲顥時他的周圍便已充滿「文壇」明星,而他卻仍具有幫朋友推波助瀾的熱情、替朋友搖旗吶喊的活力;這樣的熱度或許抑止了自身的光芒──身體一直都是小小,小小的,但阻擋不了其自身生命力的展現。
相對於那群明星同伴身旁已有不少讀者,李雲顥缺乏如此大量的讀者或是定量的同伴肯定下,他經常自問「我想變成你 / 你會想變成我嗎」、或自答「抱著自己;假裝有人抱著我」;鮮少人回答時,他能怎麼辦?是的,他選擇當個自嘲且自勵的「原點守詩人」,尋求作品存在的目的,為此他寫出他個人的不同,自己的逃脫,「因為老手終於牽起老手 / 一種新的詩的風格 / 就要誕生」。
後來,當他發現自我的兩面性時,他竟直視自己:「自封為妖孽 / 也是一個聖徒」,選擇「如此戀世 / 如此棄世」地存在。
因為這樣的勇氣,我如此地深信,兼具冷靜與熱情的他,是黑暗時代的鍊詩術士、神聖王國的發光二極體。
作為鍊詩術士,他書寫的最終目的直指自我,某種扭曲過的哈哈鏡,自戀映照的究竟是何種樣貌──我想明白自己;但是我沒有別人可以訴苦。
作為發光體,他私底下總是像圖一,對鍊詩術持續閃爍熱烈的光,他不斷地「提問」,經常已包含答案,但他想要的是同行者的認可與先行者的指引;矛盾地,當他身處人群中時,他變成了圖二,他的熱情照亮眾人,漸次地止滅自己。
或許有天他終將理解,他熱情擁抱的戰友並不總是同行的夥伴,他冷靜佩服的先行者多數人詩分離;作為神聖王國的鍊詩術士,具有吟遊詩人性格的他,終須再次離開,踏上旅程,面迎自身的孤獨。
我認識的鍊詩術士李雲顥對詩的熱誠與勇氣都比我還要多得多。他勸誘我發表自己的作品、阻撓我因信心不足扼殺的作品、搖動小把詩旗想一起來場干戈,並對懷柔收編的人大發豪語,最後,我們遙望結黨營詩者,並祝他們幸福快樂。他總是讓我知道,儘管又有一場暴雨惡意打下來了,但鍊詩術士仍須造詩。
每一個鍊詩術士不得不先學會造出微光,導引自己的腳步。
為此,李雲顥鍊成了《雙子星人預感》。
2.
《雙子星人預感》綜結了李雲顥的生命能量。
人群中尚未真正閃亮的他,轉向鍊詩術的王國學習,擁有發光體本質的他同時也帶有二極,因此,這樣的他無疑是辛苦的,在人人皆患有精神分裂的時代,唯有少數人承認如此矛盾的自我,他便是其中之一。
展現的矛盾不斷刺傷又同時滋養自我。
正極的所在沒有門,於是總在三重鏡射的虹之迴廊穿梭;負極則不斷講笑話,用爛廉價的隱喻,以剝奪更多感官。是的,他嚐試弄懂世界的機械內核是什麼,卻無法靠近,於是他繞行於他創建的神聖王國中,遊戲或退卻地鍊詩,探尋的世界直指內心的盡頭。
他喜愛的同行者們充斥個人風格,好行各式法術。為此,當他步上神聖王國的旅途時,他也在人生羊皮圖上,探求所謂的「自我風格」。但他不得不承認,只有演示自我時才能產生真正的自我風格,於是他拋擲自我在幾萬個分裂的樹影觀點上。
他的風格裂成兩半,不是對立而是揉和──他體內充滿了水、他用血作畫 / 鍊詩;他熱情又冷冽的內在反映了兩種或以上的書寫樣貌,如此混亂的結構多層次地形塑,投射出的正是他內心最深的焦著與對立,鍊詩時,他使用的意象從華麗展示的落地窗到艾倫坡般的闇黑可怖館都有;他投遞出水晶硬塊與亮片焦骸撒落一地。
我們瞥見他展現鍊詩術時的光影,一道道。
還得再看仔細一點。
詩集裡,他前後搖擺走過神聖王國的陰暗處與太陽下,在往世界邊陲的沿路景點上,看見的對象充滿奇異,他在神聖王國裡搜尋各種:瑪莉、雪域、飛天的嬰孩、銀河間隙、離離帽子店、幽靈船、始祖鳥、密閉的山洞、很深的房間、惡水溝、黑森林等,即便他說他的水晶球,看不見他想看見的,但神聖王國裡似乎有著看不盡的沿途風景。
旅途中,他成了異物的收穫者與發現者。如他所聲稱的:「本來這一切從來就沒有構圖線的」。
他豐沛地想像自己手持黑暗的摺扇,試圖打包世界離開,踩出流浪者的步伐,吟遊詩人般地遊走於神聖王國,沿著他自製的計畫表──對稱之旅,一方面反映了詩集編排的順序,出發與回歸,另一方面也顯現了輕快的腳步直至凝重被拖滯,再昇華至腳步重新輕快的整個過程。
然而,年輕的李雲顥即使走過一趟沙漏,仍未見其衰老,生命力反而生輝,因為那是生存矛盾的碰撞與背反,走向愛的臨界時,他尋求死之跨越,全是因為夢想和絕望恰好押著同一個韻腳,因此,即便有著悲傷與死亡氛圍的詩作占著中心,他仍然留著邊緣位置給整整四輯輕快的詩作。
無論是從「銀白色修練」脫逃至「少男復仇」而成了另一次元的王,或從「告白失敗」後的尷尬到「枕邊情詩」中以小手覆蓋你大手,他都靈巧地將沙漏顛倒,又一遍、重來。
換言之,沙漏般重置的李雲顥又從愛的露水中喚回生命的力量──讓我們互相散熱、全部的時間我都要浪費、碰撞你細膩的髮鬢、指紋是解碼機 / 揉開 / 多少寂寞──滿佈的愛情填滿青春的洋面,彼此溼熱的手心。
生命再度回覆自身──光是陰影的目的。
七個小輯中,他不斷走位與變換口音;並堅稱不要忽視許多聲音在傷心的旁邊,即使路途中險路不斷、敵人眾多,致使他有時必須戴著面具,然而即使面具龜裂再重塗,他也不停歇,雖然地圖上其它的路只剩下自己的,而他也曾懷疑「究竟我能夠走到那裡 / 成為什麼模樣」,但最終他確實明瞭所有人物都已褪成風景,於是,他正面地鼓勵自己:「前面有熱熱的苦難等我去解放」。
來到最後,身為鍊詩術士的他終於克服萬難,從陽光才剛露臉的理想下午走向內心的最深處,再從陰暗的底層一路走回那陽光普照的青春螺旋。即便很少人能回應他的呼喊──誰能來停止時間,他仍持續前行。
李雲顥的微光已經點燃,正在發亮。
起點或許就是終點。走到最後,或許跟開始一樣,無論房間多深,每個鍊詩術士都須學會在黑暗中造光。
腳步蹣跚卻智慧充滿,逐步尋得走出很深的房間的道路。
神聖王國中,類似的故事腳本將不斷重演,而我也相信全新的世界觀將產生,只因我們身在黑暗時代,只因我們必須對抗義正辭嚴的偽光明術士,只因真正的鍊詩術士終將成為神聖王國的魔法師。
神聖王國裡的你們,無論是鍊詩術士,或僅是詩字搜查員,路過李雲顥時都可以對他喊一聲嗨或是借點光,因為他是神聖王國的發光二極體,因為他會為黑暗時代的黑牆刷些白,因為在繁花盛開的森林裡,我們的影子都需要一點──光。
因為陰影,也是光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