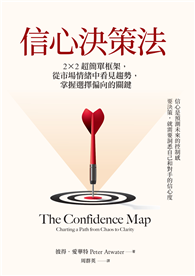序言
川田順造(Junzo Kawada)
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在妻子莫妮可(Monique Levi-Strauss)的陪伴下,曾於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八年間五度遊訪日本。在第一次啟程前夕,這位偉大的人類學家在《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日文完整版的序言中,提到了他對日本的愛戀:
「沒有什麼比日本文明對於我的智識與價值觀養成所造成的影響更早了。當然,是透過一些似乎無足輕重的途徑:我的父親,是位畫家,是印象派的忠誠支持者。在他年輕的時候,曾經擁有一個裝滿了日本版畫的大箱子。在我五歲或六歲時,他給了我其中一張畫。畫者是安藤廣重,非常老舊而且沒有邊框,描繪的是海邊松林下散步的人們。
「我被初次體驗到的美感深深撼動,將它貼覆在一個盒子底部,並請別人幫我將它掛在床的上方。這幅畫便彷若成為從露台看出去的遼闊景色。而我,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致力於將日本進口的袖珍傢俱和人物,安放在這個小房子裡。位於巴黎小田野街(rue des Petits-Champs)、名為『寶塔』(La Pagode)的商店,專門進口此類袖珍模型。自此之後,每次當我在學校有優異表現時,便有一幅版畫作為獎勵,如此持續了許多年。漸漸地,我父親的紙箱空了,畫都給了我。然而這仍無法滿足我,透過勝川春章、葛飾北齋、歌川豐國、國定忠治以及歌川國芳等畫家所發現的世界,使我深深陶醉。一直到十七、十八歲,我所有的儲蓄都花在蒐集版畫、繪本、刀劍以及刀鍔上,這些東西並不值得博物館收藏(因為我的錢只能購藏價格較低廉的作品),卻可以使我沉浸數小時——帶著一張日本字符表——只為了想瞭解它們的標題、題句以及簽名等等。因此,我可以說,就心緒和思想而言,我全部的童年以及一部分的青少年時光,在日本度過的時間若沒有比在法國的時間更多,也與在法國的時間一樣多。
「然而,我從未去過日本。並不是缺乏機會,而大概是在很大程度上,擔心對我而言仍是『童真愛情的綠色天堂』與無垠現實之間的衝突。
「然而我並非因此就不知道日本文明帶給西方的珍貴教誨,如果西方世界願意傾聽的話:那就是,活在當今並不一定就要厭恨及摧毀過去;而且,沒有任何稱為文化產物的東西,不是來自對自然的愛與尊敬。如果說日本文明能夠成功地在傳統與變遷中保持平衡,如果它能在世界與人之間維護一種均衡狀態,而且知道如何避免其中一方傷害和醜化另一方,或者總結說,根據它的哲人的教導,如果它仍然相信人類只是暫時地據有此地,而在這短暫的過程裡,並不允許它有權在一個比它更早就存在、且之後仍將繼續存在的世界造就任何無法挽救的損失,我們也許就有一點點機會,使這本書所引起的一些悲觀看法,至少對世界的某部分而言,不會是對未來世代唯有的預期。」
在本書,我們將會再度見到愛慕日本的李維—史陀。這本書首度集結他的多種書寫,有從未出版的,也有一些曾在學術刊物中發表,其中還有只曾在日本出版。這些文章寫於一九七○至二○○一年間。從這些多樣化的寫作中,可以見到他對於日本人所抱持的一種若非寬厚、至少也是慈悲的觀點——作為一位非洲人類學家的我,亦有此種感受。這種觀點正是克勞德.李維-史陀終其一生保有的目光—在《憂鬱的熱帶》日文版最後一版的序言中,特別明顯易見。
在莫妮可.李維-史陀的同意下,我建議莫里斯.歐隆岱爾(Maurice Olender)在書中放入幾張照片,都是李維-史陀的日常生活場景。部分是一九八六年在日本拍攝,一些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的社會人類學研究室。最後,有幾個特別的時刻,是在他位於林內何勒(Lignerolles)的鄉下房子所拍攝。克勞德.李維-史陀於二○○九年一月三日葬於離此不遠的村落墓地中。
不為人知的東京
這本書最初在日本出版時,我從未造訪過日本。而拜許多機構之賜,我得以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八年之間五次訪問日本。在此,我要再度對這些機構表達我的謝意: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三得利基金會、日本生產性本部、石(土反)基金會、以及國際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文研)。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希望能在六週的時間內,讓我發現這個國家各種非常不同的面貌,並且繼東京、大阪、京都、奈良與伊勢之後,在我傑出的同事,吉田禎吳教授、福井滕義教授帶領下,安排我拜訪能登半島與日本海上的隱歧諸島。此外,在三得利基金會的協助下,我得以認識瀨戶內海與四國。前述的吉田禎吳教授更在一九八三年邀我隨他前往琉球群島的伊平屋島、伊是名島、久高島,讓我盡棉薄之力參與他的民族學調查。三年之後,在另外一次居留期間,我想參訪九州。若非渡邊靖女士在我首次旅程就十分稱職地擔任嚮導和翻譯,這個超過一週的旅程將無法成行。
我對川田順造教授有無盡的感謝(就從他對這本書的翻譯開始)。他在一九八六年帶著我發現大多數外國訪問者都不認識的東京:我們搭乘傳統河船,沿著隅田川逆流而上,深入河流東、西兩邊穿越城市的迂迴運河。
在我最初幾次參訪,我在巴黎研究室的研究計畫是:研究不同社會、不同階層、在各個時期對於「工作」此一概念的想法。因此,我希望參訪行程能夠依此安排,並且能夠接觸到城市或鄉村的工匠,即使他們遠在這個國家的偏僻角落。所以,儘管我對奈良的博物館、神社,以及伊勢神宮留下了無法抹滅的記憶,但我主要的時間都用於會晤各種工匠,包括和服的紡織師傅、洗染師傅、繪師(那也是我身為染織美術專家的太太所感興趣的職業)、陶藝工匠、鍛造工匠、木工匠、金工匠、漆藝匠、漁夫、清酒師、廚師、糕餅師,以及人偶師與傳統樂師。
如此,關於日本人如何想像工作這個主題,我獲得非常珍貴的知識:在日本,「工作」並非被視為「人在不具活動力的材料上所加諸的動作」——那是西方的方式——而是被視為一種人與自然的親密關係的具體展現。就另一層面來說,某些能劇推崇日常家務,並賦予它們詩意的價值,也證實了這一點該詞的希臘字源與其藝術意涵正不謀而合)。
在造訪日本之前,想到日本人與自然的關係時,我有點理想化了,實際情況令我感到有些意外。在日本旅遊期間,我察覺到,您們在西方人眼中的那種對自然美景的崇仰,例如您們的美妙庭園、花藝、料理,以及對櫻花樹的熱愛,這些種種居然能夠和對自然環境的極度粗暴並行。對我這樣一個仍然是從北齋的精美繪本《隅田川兩岸一覽》來想像隅田川的人來說,我前述的上溯隅田川之行無疑是一場震撼。誠然,一個外國訪問者若是透過古代的版畫來認識巴黎,那麼當他面對今日的塞納河兩岸時,也會有相同的反應,即便當中的反差無疑比較小,過去和現在之間的過渡也沒那麼突兀。(然而,與人們事先所告知的相反,對我而言,現代東京並不顯得醜陋。建築物不規則地此起彼落,反而予人一種多樣化與自由的印象;不同於某些西方城市,沿著街道、馬路單調地排列房屋,而讓路人行走在兩堵高牆之間。)
此外,可能也因為在人和自然之間欠缺了清楚的區隔,使得日本人賦予自己一種權利(透過他們有時會使用的反常推論,捕獵鯨魚一事便是如此),有時讓自然置於優先的地位,有時又將人類放在優先的位置;而在必要時,也可以為了人的需要而犧牲自然。自然和他們之間難道不是一體的嗎?
由此,我見到了「雙重標準」的特殊見解,我的日本同事們告訴我,那是瞭解日本歷史的關鍵。就某種意義而言,甚至可以說,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問題——世界人口在一個世紀內從不滿二十億人變成六十億人——日本找到了自己原創的解決之道,也就是讓人口密集,以致城市綿延不斷的海岸區域和無人居住、罕有人跡的山地內陸並存在日本的土地上。這樣的對立同時也是兩種心靈世界的對立:一方是科學、工業與商業的世界,而另一方則仍舊仰賴著來自遠古的信仰。
這一「雙重標準」也有其時間向度。日本是在一種不可思議的快速演化中,以幾十年的時間就跨越了西方歷經數個世紀才達到的距離。這使得日本能夠在現代化的同時,又與其精神根源保持密切關係。
我的職業生涯中,泰半時間都奉獻在神話研究上,並致力去突顯那仍是合理的思維模式。因而我不得不深刻地感受到,神話在日本保有的生命力。沒有任何地方比在琉球群島的小樹叢、岩壁、石穴、天然水井,以及被視為是神蹟顯現的湧泉之間,更讓我感受到是如此接近遙遠的過去。在久高島上,人們指出神靈來訪時顯現的地方。祂們帶著五種不同榖類的種子,種植在最早的田地上。但對居民們來說,這些事件並非發生在某個神話時期,它們是昨日之事、今日之事,甚至是明日之事。因為踏上這塊土地的神靈們每年都會再回來,而遍及整座島嶼的儀式與神聖遺址,都見證著神靈們真實的來訪。
或許,因為日本的書寫歷史相對起步較晚,所以日本人自然將他們的歷史根植於神話當中。我在九州便確信了這一點。根據文獻,當地是日本神話中最古老的舞台。在這個階段,歷史性的問題尚不存在,有兩個遺址甚至為了何者才是迎接天神瓊瓊杵尊下凡的榮幸之地而爭執,且不覺有任何不妥。而矗立著供奉日照大神(大日□貴女神)的神社,其莊嚴感也讓人對有關祂退隱到岩穴中的古代神話深信不疑;那岩穴是如此神聖令人不敢直視,只能遠遠眺望。只要細數載運朝聖訪客的車輛,就不得不同意,那些偉大的創始神話,以及傳統上被視為神話發生地的宏偉風景,在傳說的時間與當代的感受之間,仍能夠維持一種實際的連續性。
將近半個世紀前,我在寫作《憂鬱的熱帶》時,曾對威脅人類的兩項危險表達憂慮:人類對於其根源的遺忘,以及人類因其自身數量的毀滅。在對過去的忠實和科學與技術所帶來的轉變之間,日本或許是所有國家裡,唯一到目前仍懂得找到平衡之處的國家。日本所以能夠如此,當然有賴於它以維新的方式進入現代,而不是如法國一般經由革命。這使得日本的傳統價值得以免於瓦解。但這亦有賴於長期始終保持開放的人民,他們不受批判精神與系統化精神之害。這些精神的氾濫正侵蝕著西方的文明。直到今日,外國訪客仍然讚美日本人安份守己的勤奮以及愉快的善意。相較於他們自己國家的道德表現與社會風土,那些就像是日本人民最重要的美德。期盼他們在過去的傳統和現代的創新之間能夠永遠維持平衡。這並不只是為了日本人本身的利益,也是因為全人類都可以從中找到值得深思的範例。
本文為《憂鬱的熱帶》日譯版序言(2001, p. 268——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