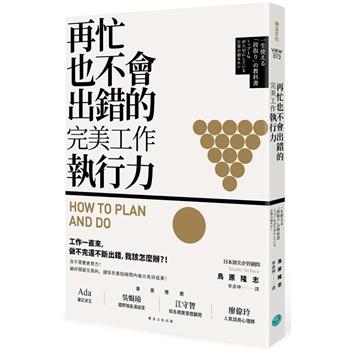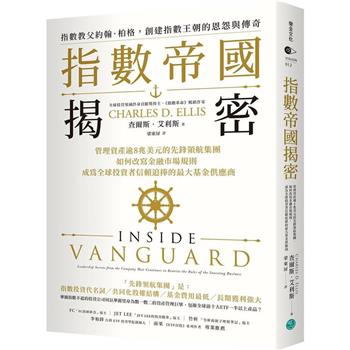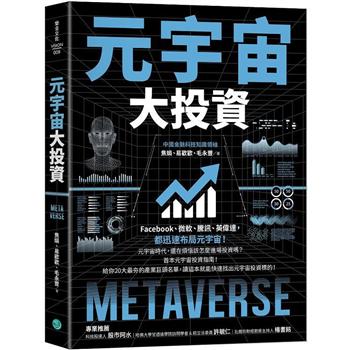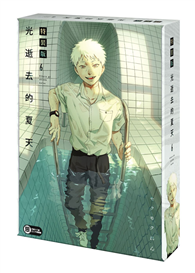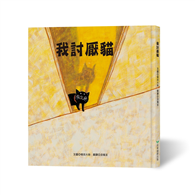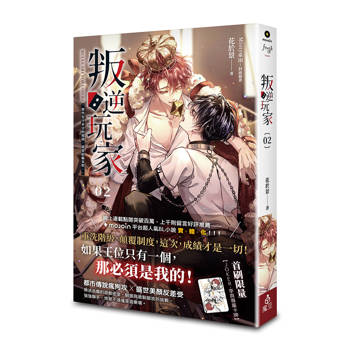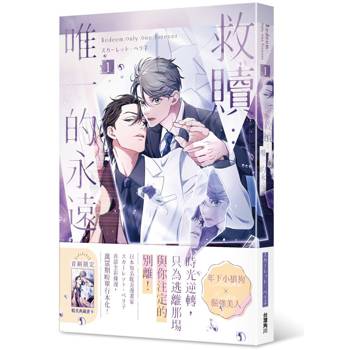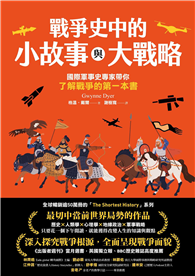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於梨華作品集01: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75 |
近代文學 |
$ 425 |
小說/文學 |
$ 440 |
中文書 |
$ 440 |
小說 |
$ 45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是「於梨華精選集」的首部作品,也是於梨華第六本單行本,第三部長篇小說,1965年動筆, 1967年由臺灣皇冠出版社上市,成為「留學生文學」經典之作,並於同年榮獲嘉新文學獎,也激發了60年代臺灣文學中流浪者認同與離散的主題,至今半世紀仍舊低迴。1999年6月被《亞洲周刊》選入「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簡稱「世紀百強」)之列,是華人世界知名小說。五十年來,《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除了作者授權繁體字版之外,有無數種未經授權的簡體字版與網路電子版流竄,句讀、分段、體例差異很大,為保存作品原貌,今經作者重新校訂後以饗廣大讀者。
六○年代臺灣的典型人物:出生於中國、因戰亂遷臺,大學畢業留美成了臺裔美國人。牟天磊就是這麼一個角色,畢業於臺大,趕著當時「出國熱」,赴美深造。遠離故鄉,一切嚮往的美好遠不如現實生活的殘酷。他在美國打工苦讀,端盤子、洗碗、跑堂、當貨櫃司機,雖然取得博士學位,生活的孤寂與失落迫使他對未來充滿困惑。去國十年為了終身大事回臺探親,牟天磊赫然發覺自己不僅僅在美國是客居;這種寂寞與苦悶並非只有牟天磊一個人有,「不管在美國的,還是在臺灣的,那個年代的人都有。美國不是故鄉,臺灣不想回,大陸又回不去……」
然而,牟天磊的失落與寂寥不為家人朋友們所理解,尤其,通信兩年的女友期盼著兩人成婚後赴美展開天堂般的人生,可是牟天磊無法說服他們,陷入留下與離去,無家可歸的兩難處境;他有滿腔熱血想追隨臺大恩師報效國家,但女友結婚的前提是去美國。故事就在牟天磊最後抉擇前打住,留給讀者無限揣想空間。
於梨華說,這本書對當時赴美留學生起了一定的作用,故事後面的事實令人思索︰到美國去讀書、進修、做研究,是艱難的、寂寞的,甚至是苦惱的,「牟天磊的經驗,也是我的,也是其他許許多多年輕人的。他的『無根』的感覺,更是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共同感受的。」
「一九六七年的牟天磊有他無家可歸的困難,但一九八○年的年輕人是不會有的,他們有家,學成了回家,他們有國,學成了歸國。如果是因為不滿現實而出國,出國後更應該有能力回去改善那個現實;如果是嚮往美國的生活,牟天磊的故事,我相信,足夠年輕人瞭解它到底是怎麼回事。現在很多留學生把『利』看得比『名』重要,畢業後留在學界的也並不多。」
本書特色
「於梨華精選集」由於梨華親自選入十八部作品,預計自2015年六月開始陸續出版,至2018年全數問世。精選集的所有作品也經於梨華親自修訂、校對,每一部作品都是絕無僅有的精彩代表作,典雅清新的圖書設計由兩屆金鼎獎圖書設計獎得主楊啟巽操刀,蒐藏價值無限。
該本精選版《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首度收錄了於梨華應文訊雜誌之邀撰寫的〈三十五年後的牟天磊〉一文,解答當時未完的結局。書中並有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推薦專文,以及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細膩的導讀。
作者簡介
於梨華
浙江省鎮海縣人。1931年生於上海。抗戰期間因父親職務關係,曾舉家四處遷徙,居住過福建、四川成都、上海等地。1947年底因父親奉派到臺灣接收糖廠,隔年於梨華也跟著遷臺並轉學到臺中女中就讀。當時,於梨華開始寫作,第一篇作品是評論沈從文《邊城》。1949年於梨華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後轉入歷史系。大學時間於梨華創作不懈,初期小說多發表於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並獲得夏志清矚目。嘗以筆名方莉夏、鴻鳴投稿,文章散見《文學雜誌》、《自由中國》、《現代文學》、《文壇》、《野風》等刊物,當時有幾篇小說,如〈鞋的憂喜〉、〈無腿的人〉、〈殞落〉、〈埋葬〉和〈追不回的幸福〉已嶄露光芒。
祖籍浙江鎮海,1931年生於上海。1947年,舉家遷往臺灣,就讀臺中女中。畢業後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隔年轉入歷史系,1953年畢業。同年9月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英文系就讀,後轉入新聞系,1956年獲新聞學碩士學位,曾以英文短篇小說《揚子江頭幾多愁》獲米高梅電影公司文藝獎首獎。1968年起,在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Albany)分校執教,教授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報刊雜誌選讀,1977年還擔任該校中文研究部主任(僅一學期),1977-1978年任該校中文研究部主任,1980年兼任交換計畫顧問。1983年夏被Yaddo Colony(耶都藝區)邀請為寫作區員。1984至1985年得富爾布萊特獎(Fulbright Fellowship)到南斯拉夫與作家交流。2006年獲佛蒙特州Middlebury College榮譽文學博士。1993年退休移居舊金山灣區,現居馬里蘭州。文體精緻,被譽為臺灣六○年代現代主義代表作家之一,也是留學生文學的鼻祖。
於梨華作品年表
1956〈揚子江頭幾多愁〉(Sorrow at the End of the Yangtze River)(又名「揚子江頭的嗚咽」)
1963《夢回青河》(長篇小說)、《歸》(短篇小說集)
1965《也是秋天》(中篇小說集)、《變》(長篇小說)
1966《雪地上的星星》(短篇小說集)
1967《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長篇小說)
1968《柳家莊上》(中短篇小說集)
1969《白駒集》(短篇小說集)、《燄》(長篇小說)
1972《會場現形記》(短篇小說集)
1974《考驗》(長篇小說)
1978《誰在西雙版納》(遊記)、《傅家的兒女們》(長篇小說)
1980 《記得當年來水城》(散文集)
1988《尋》(短篇小說集)、《美國的來信》(書信集)
1989《三人行》(長篇小說)、《相見歡》(短篇小說集)、《情盡》(短篇小說集)
1996《一個天使的沉淪》(長篇小說)
1998《屏風後的女人》(中短篇小說)
2000《別西冷莊園》(散文集)
2002《在離去與道別之間》(長篇小說)
2008《飄零何處歸》(散文集)
2009《彼岸》(長篇小說)、《秋山又幾重》(中短篇精選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