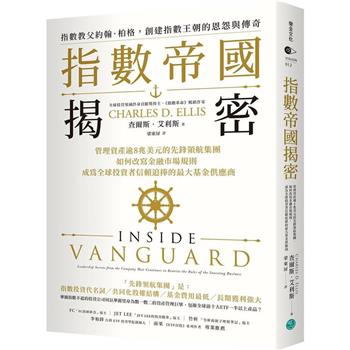第二章
法國的部落 I
有幾道平坦而迷人的山谷,從庇里牛斯山如太陽光芒般射出,其中一道山谷的南端盡頭,若碰上雲層不致太低垂的日子,可看到位在岩質平臺上的小村古斯特(Goust),平臺下方四百五十公尺處,就是冷泉度假勝地奧紹德(Eaux-Chaudes)。二十世紀初之前,這小村被視為是自治共和國。這個歐洲境內未公開宣布建國的最小國家,過去有十二間花崗岩屋和約七十名人口,統治者是由老人組成的委員會。那時境內沒有乞丐,沒有僕人,而且叫發現這一簡樸刻苦之香格里拉的旅人大為欣羨的是,不用納稅。
古斯特這個小村之國,至少自十五世紀就為外界所知,但村民始終過著自適快樂的生活,是個「完全與世隔絕的部落,保存住自己簡單、原始的習俗」。通往這小村那條陡得嚇人且布滿碎石的道路,建於距今不到四十年前。二○○五年,娜塔莉.巴魯(Nathalie Barou)帶我看了刻有她家族原始名稱巴隆(Baron)的中世紀門楣。現知十六世紀的古斯特確實有位叫巴隆的人,那人的先祖之一,因十字軍東征而貧窮潦倒,可能把地賣給他的農奴,而那些農奴從不覺得有需要加入聯盟,聯盟日後成了貝阿恩(Béarn)省,最後成為法國一部分。
古斯特村民沒有教堂,沒有墓地。人死後,就把棺材繫上繩子,垂放到下方的山谷。天氣好時,居民會爬下山去賣牛奶、蔬菜,或帶小孩受洗,或去瞧瞧前來奧紹德泡冷泉的女人。隨著一八五○年小村下方的峽谷被炸出一條路,木造小橋「地獄橋」也改建成石橋,古斯特成為某些無聊病人和遊記作家遊覽的美麗勝地。若沒有他們,它可能和曾存於法國境內的其他數百個「自治共和國」一樣,消失於世人的記憶中。
古斯特能成為特例,主要因為它較出名,且因不可抗拒的地理因素使它進入蒸汽時代時,得以保持一種元老的姿態。相較其他偏遠的小地方,它與外界的聯繫非常強。它的七十位居民(有些據說已過百歲),若完全不與外界往來,幾乎不可能活得如此好。他們的公共庫房裡,有來自巴雷日(Barèges)的羊毛和西班牙的緞帶,基因裡也必然含有到外面世界一遊帶回的紀念品。就連古斯特的死人,都要到外面走上一趟。在阿卑爾斯山同樣的高海拔村落裡,居民若在六或七個月與外隔絕期間死去,屍體就擺在自家屋頂上讓雪覆蓋著,到春天雪融,才將屍體搬到墓地,神父也才能來村裡。
古斯特之類的風景勝地,在法國民族認同的催生上扮演了關鍵角色。對於到此一遊、購買明信片、然後返回現代文明世界的民眾來說,部落屬於偏遠地方——距城市愈遠,就愈古老。庇里牛斯山上古斯特或阿爾卑斯山上聖韋朗(Saint-Véran)之類村落,危顫顫矗立在法國邊陲的岩石上,曾是受過教育人士想像中的國家公園和專門保留地。但當廉價旅行和全國性大報把全國各地拉到眼前,抹殺了古老的部落區隔時,這道理很快即遭遺忘。古斯特在許多方面是十八、十九世紀初期法國的標準社群。誠如經濟學家謝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走訪東庇里牛斯和安道爾(Andorra)之後,在一八三七年巴黎某報上所寫的:
如今每個山谷仍是個小世界,且相鄰小世界的差別,就和水星與天王星的差別一樣大。每個村落是個氏族,是擁有自成一格之愛國精神的某種國家。每走一步,都會碰到不同的種類和特色,不同的意見、偏見、習俗。
如果謝瓦利耶是從巴黎步行來,而非搭高速馬車走現代公路而來,可能會發現他的描述適用於法國大部分地區。
走訪這些氏族和迷你小國,得長途跋涉進入尚不為人知的法國,進入大到鎮、村,小到小村與不是這麼容易界定的其他聚落形式裡。你會覺得法國看起來幾乎就像是任意在西歐劃出的一塊地區。等到全國性模式出現,居民就不只是有共同的地理鄰近性,不過如果是以後代的歷史路標引導從頭到尾的旅程,那這個國家大部分的地區和其居民將和古斯特的源起一樣晦暗難明。
*
在鐵路使大地風景變模糊,將居民縮小為月臺上的臉孔和農田裡的身影之前,旅人往往為所接觸人群的突然改變而感到困惑不解。涉水過河或在十字路口轉彎之後,馬車乘客可能發現車外之人有著截然不同的外表,不僅有自成一格的衣著和建築,有自己的語言,還有獨樹一格的待客之道。眼珠、頭髮的顏色,頭與臉的形狀,乃至看著驛馬車駛過時的神態,可能比植被的改變還要劇烈。
隨著速度誇大了差異,部落的邊界往往變得驚人清楚。過去,在阿杜爾(Adour)河左岸,巴約訥東邊的夏洛茲(Chalosse)地區,據說,當地人又高又壯,吃得好,好客。右岸的居民,則骨瘦如柴、生活可憐、性情多疑。氣候、水、飲食、古代與現代的人員遷徙、氏族間的對立、習慣與傳統上所有無法解釋的改變,能使最小的地區變成未標示邊界的迷宮。就連據稱文明開化的地區,在帝國覆滅後,都給像省一樣分割。在勃艮第,據十八世紀法國小說家德.拉布列東(Restif de la Bretonne)的說法,尼特里(Nitry)、薩西(Sacy)這兩個相鄰的村子,差異非常之大(一溫文有禮,一行徑粗野),因而有位S*伯爵「特別選中它們為巡視地,以便他不必走太遠(約五公里),就可以飽覽鄉村景致,藉此對整個王國的鄉村生活提出精簡的描述」。拉布列東的生母,在尼特里村一直給當外人看待,因為她來自西邊約十五公里處,居爾(Cure)河對岸的村子。「根據習俗,親戚的小孩都不喜歡她,在村裡也不會有人替她說話,因為她是外地人。」
有錢的城市人,出發探索自己國家,卻看到一個充斥部落、氏族的瘋狂人類世界,那種困惑不解,可想而知。甚至在法國北部的一趟短程旅行,都可能使人對「法國人」的印象變得模糊。在迪耶普(Dieppe),波勒泰(Polletai)或波爾泰斯(Poltese)漁民說的方言,幾乎無法認出是法語的一種。橫渡英吉利海峽過來買象牙雕刻的觀光客,對女人穿著打褶的襯裙和及膝裙子是目瞪口呆,不解她們為何看起來與其他法國人這麼不一樣(至今仍無人知道原因何在)。沿著海岸往北到濱海布洛涅(Boulogne-sur-Mer),這勒波泰勒(Le Portel)鎮的市郊有一些特別的人口。他們總數約四千,以其身高和漂亮、強健的外表而引人注目。一八六六年,有位人類學家認為勒波泰勒人是安達盧西亞裔,但他該對族群女性(男人都出海工作了)頭、手、腳、胸的研究結果卻無法下此定論。往內陸約五十公里,有聖奧梅爾(Saint-Omer)鎮,在該鎮東邊那些「浮島」上務農為生的,乃是一個擁有自己法律、習俗、語言的社群。他們住的低矮的運河屋就在奧龐(Hautpont)、利塞爾(Lysel)的郊區,看起來就像是法國城鎮中出現了法蘭德斯人(Flemish)聚落。
過去,在許多旅人眼中,法國境內的不同族群,除了同是人,似乎幾無其他共通之處。甚至,還曾有人懷疑某些族群不是人。十九世紀末期,還有報告指出,布列塔尼與諾曼第的交界處住有自成一格的自治部落。而在蔚藍海岸(Côte d’Azur),坎城和聖特羅佩(Saint-Tropez)後面的丘陵上,據說曾有野人從山上下來到市集。他們身穿羊皮,操著沒人懂的語言。一八八○年,在維萊—科特雷(Villers-Cotterêts,大仲馬出生地,位於巴黎東北方七十二公里處)周邊森林裡,有位人類學家發現「一些偏遠村落,村民和周遭村落居民全然不同,似乎帶有某特定種族的印記,存在年代比揭開我們歷史序幕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入侵事件還要早。」
如今,過了一百多年,維萊—科特雷森林成為眾所周知的巴黎人短期旅遊景點,從巴黎北站坐車過去只要四十五分鐘,該森林的「史前」族群因此將是永遠的謎團。就法國人類學來說,史前時期到法國大革命才結束。在大革命之前,官方對廣大人民的文化、種族多元現象,不感興趣。在拿破崙掌權之前,統計資料不僅稀少,而且也不可靠。使學者得以根據身體特性、文化特性分析族群的科學,只有在他們所希望研究的部落開始轉變成現代法國公民時,才會發展出來。不過有個惱人的問題,至少是那些愛追根究底的旅人都曾疑問的:法國住民是誰?
*
在政治史領域,答案似乎很簡單。迪耶普、布洛涅、古斯特、聖韋朗的住民,都屬於同一個國家。他們不僅得向地方的最高法院(Parlement)負責,最終也得向國王負責。大部分人要繳稅——獻出錢、獻出勞役(維修道路、橋梁),在十八世紀末期開始全面徵兵時,還獻出生命。地方上有被指派來的官員——收稅的官員和維持治安的衛警。但法律,特別是與繼承有關的法律,普遍不受理會,與中央政府的直接接觸也極為有限。國家被視為危險而討厭的東西:它派來的是得供予食宿的軍人、是奪取財產的司法官、是解決財產紛爭且拿走大部分收益的律師。這時,身為法國人,並不值得引以為傲,當然更不是共通認同的基礎。十九世紀中葉之前,只有少數人見過法國地圖,聽過查理曼與聖女貞德。這時的法國,實質上是外邦人的國度。據某位來自波旁內地區(Bourbonnais)的農民小說家,不獨大革命之前如此,一八四○年代也是如此:
我們對外界一無所知。在縣界以外,在已知的地域之外,存在著據說危險、住有野蠻人的神祕國度。
法國的諸座宏偉大教堂和不計其數的堂區教堂,或許還表現出較強有力的共通聯結。當時,將近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是天主教徒。事實上,宗教行為差異極大(這差異後來會變得相當明顯)。神與拜神者同樣未能擺脫畛域之隔。同一條路上的前後兩村,都供奉了聖徒雕像或聖母雕像,但兩村的村民都認為自己的聖徒或聖母與另一村並非同一人。以史前石頭和魔法井為中心的信仰和習俗,與基督教的相似之處少之又少。地方的神父可能因識字而有益於村民,但身為宗教權威,面對信仰療法術士、算命師、驅魔者和似乎能改變天氣、使小孩死而復生者的競爭,他得證明自己的過人之處。道德與宗教情感不受羅馬教會教義的影響。對大部分人來說,羅馬教會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一直保有課稅權利一事,遠比它對控制生育下的徒勞禁令要重要得多。
王國劃分得愈小,就能使人口分布描繪出不一樣的風貌,雖然結果仍不見可靠。有很長一段時間,大革命之前的法國諸省(province)普遍被認為是瞭解民族認同的關鍵。這一主張認為,這些歷史性、政治性的行政區畫,一如顱相學家對頭顱的區畫,會對應於某些人類特性。
在馬爾蘭(François Marlin)的遊記中,可找到說明這一地理—個人(geo-personal)研究取向的有力例子。馬爾蘭是瑟堡(Cherbourg)商人,以海軍補給生意為理由,探索他的故鄉,在一七七五至一八○七年間遊歷超過三萬兩千公里。他寫道,「佩里戈爾(Périgord)地區的人活潑、機警、理智。利穆贊(Limousin)地區的人行動較遲緩、拘束。」在奧什(Auch)的客棧用晚餐的經商旅人,很容易就可認出他們來自何處,就像不同品種的狗:
里昂內人高傲而強勢,說話清楚而洪亮,風趣但也傲慢,且言語粗鄙而無禮。蘭格多克人溫文有禮,有著誠實坦率的臉。諾曼第人聽多於說,對人心存猜忌,使人對其也心存猜忌。
然而,一如馬爾蘭所發現的,即使這類認知流於溢美,大部分人仍不願把自己與這大片地區畫上等號。他們屬於某鎮、某郊區、某村或某家族,而非某國或某省。某些地區的共同文化傳統,在外人眼中,還比該地居民看來更為清楚。布列塔尼還得再分割幾次,才會成為對當地人具有特定意涵的地區。東布列塔尼人操名叫加洛語(Gallo或Gallot)的法語方言;西布列塔尼人則說幾種不同的布列塔尼語。這兩個族群幾乎未通婚。在西部,阿莫爾(Armor,「濱海之地」)人與阿爾戈(Argoat,「森林之地」)人,兩者幾無關係。而光是在阿莫爾境內,次族群彼此間的歧異之大,敵意之深,就曾讓多位作家一致認定,他們並非那花崗岩海岸的原住民,而是源自遙遠的異地——閃族部落,古希臘或古腓尼基,波斯、蒙古、中國或西藏。
*
法國乃是靠條約和武力征服拼湊成,且有三分之二地區做為法國國土還不到三百五十年,所以沒有根深蒂固的國家認同也不足為奇。在大革命之前,「法蘭西」一詞往往專指以巴黎為中心的那個蘑菇狀小省。在加斯科涅和普羅旺斯,凡是來自北部的人,都給當作「法蘭西人」(Franchiman或Franciot)。而這兩個字眼都未登錄於法蘭西學院的官訂字典上。但地區認同感同樣也非常淺淡。法國的布列塔尼人、加泰羅尼亞人、法蘭德斯人、普羅旺斯人,要在許久以後,為因應強加其上的國家認同,才發展出他們的政治認同。似乎只有巴斯克人一直是團結一致對抗外界,但在需掩飾真實想法的公開場合,他們的仇恨對象不是法蘭西人或西班牙人,而是吉普賽人、鍋匠、醫生與律師。地區間的回力球遊戲,比拿破崙的勝敗,更叫人激動。
法國的全民團結宣傳,自大革命至今,一直未停歇,要到後來人們才注意到,法國的部落區隔幾乎與行政上的邊界完全不相干。過去,沒有明顯可見的理由,表明這些族群為何該組成一個國家。誠如勒布拉(Hervé Le Bras)、塔德(Emmanuel Todd)在一九八一年提及法國家庭結構的紛然雜陳時所寫的,「從人類學觀點來看,法國不應存在。」從民族的角度來看,法國的存在,同樣不可思議。入侵古高盧的凱爾特、日耳曼部落和攻擊衰弱的羅馬帝國省分的法蘭克部落,幾乎和現代法國的族群一樣,有非常多不同的起源。唯一能讓言必稱歷史的民族陣線黨拿來代表的道地本土族群,大概就是第一批占據西歐地峽這一帶、四處遊蕩的類人猿吧。
瑟堡商人馬爾蘭最終發現,「法國住民是誰?」這個問題的最佳答案,就是沒有答案。他想用他的遊記來矯正未實際親訪的剽竊者所寫的無用旅行指南,因而只是試著觀察反映多變地理景觀的自然差異。如果將他的觀察與其他旅人的觀察合而為一,結果將是一張不能刊行的地圖,將法國劃分為醜的地方與美的地方。巴斯克婦女「全乾淨而漂亮」。「所有跛子、獨眼者、駝子似乎全給關在奧爾良。」「法國少見美女,特別是在奧佛涅;健壯的女人倒是看到一些。」「在布雷斯特,可見到最美的眼睛,但嘴巴就沒那麼迷人:該省的海風和平日疏於照護,很快就使牙齒的琺瑯質失去光澤。」
這無法令歷史人類學家滿意,對於法國的社會地理幾乎只有模糊的概念。沒有人能斷定,這些身體自然上的差異,乃是古老先祖的記號,亦或只是人所從事的貿易和飲食所致。但至少馬爾蘭親眼見到居民(或住在道路附近的那部分居民):
我很喜歡看婦女、小孩跑上前來看路過的旅人。這使好奇之人得以看到一地所有的美麗之人,而且我能精確說出庫萬(Couvin)有多少美女。
在馬爾蘭心中,這才是能經常擺在驛馬車皮口袋裡那種親眼見證的記述。其他的旅行指南,寫得頭頭是道,全是捏造之言,只該留在馬車頂上啪嗒作響的帆布底下,任雨淋,任風吹走。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非典型法國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394 |
人文歷史 |
$ 424 |
旅遊 |
$ 439 |
中文書 |
$ 439 |
文化研究 |
$ 449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非典型法國
騎在腳踏車上,欣賞到的是三百六十度的全景——葛蘭姆.羅布
對一位外國人或觀光客來說,什麼是法國人?戴高樂曾說,「怎能指望人治理有兩百四十六種起司的國家」,這樣的法國又是怎樣的法國?旅居法國十多年且從事法國文學寫作、教學的英國人葛蘭姆.羅布,藉著騎單車發現了一個非典型的法國,一個巴黎之外的法國。不同於正統的歷史寫作,羅布寫出一本介於歷史、民俗人類學與旅遊指南的奇書。
法蘭西,在大革命之前,其實只是指以巴黎為核心的磨菇狀小省,日後卻逐漸成為代表法國的象徵,當我們到巴黎參觀聖母院、羅浮宮、凡爾賽宮時,可能沒想過法國還有幾百個族群與小村落,羅布正是透過單車這樣的交通工具,造訪那些流浪民工、朝聖者走過的古老小徑,通向草根的法國。法國的歷史不再是大人物的呼風喚雨,而是重現從阿爾卑斯山到大西洋,從地中海到英吉利海峽,法國境內生活、旅行的日常經驗。
國家似乎就是有疆界、官方語言,人民理應對於國家有認同,知道自己是法國人或美國人、日本人。然而在作者筆下,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後的法國,根本不是「一個國家」,不僅各地方言彼此無法溝通,而且很多地方還叫不出名字,更遑論住民知道自己是「法國人」。也因為法國境內族群的多元與歧異,直到一九八一年,還有學者認為,從人類學觀點來看,法國不應存在。
作者認為,《非典型法國》或許才是旅人真正需要的指南書。它深入這個國家的歷史與肌理,攤開了巴黎之外繁複的法國風景,陪著每個想要冒險的旅人上路。
作者簡介:
葛蘭姆.羅布(Graham Robb)
一九五八年生於曼徹斯特,曾是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研究員。
他的傳記作品大受好評,除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巴爾札克》,一九九七年的《雨果》一舉贏得英國皇家文學會海涅曼文學獎(Heinemann Award)和惠特布瑞德傳記獎(Whitbread Biography Award),二○○○年的《韓波》也入圍撒繆爾.強森獎(Samuel Johnson Prize)決選名單。這三部傳記全名列《紐約時報》的年度好書。
羅布還寫有《陌生人:十九世紀的同性愛》(Strangers: Homosexual Lov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本書《非典型法國》更連續獲得二○○七年達夫.庫珀獎(Duff Cooper Prize)與二○○八年翁達傑獎(Ondaatje Prize)。
現居英格蘭牛津。
譯者簡介:
黃中憲
政治大學外交系畢,專職翻譯,譯有《明代宦官》、《維梅爾的帽子》、《大探險家》、《帖木兒之後》、《成吉思汗》、《劍橋伊斯蘭史》等。
章節試閱
第二章法國的部落 I有幾道平坦而迷人的山谷,從庇里牛斯山如太陽光芒般射出,其中一道山谷的南端盡頭,若碰上雲層不致太低垂的日子,可看到位在岩質平臺上的小村古斯特(Goust),平臺下方四百五十公尺處,就是冷泉度假勝地奧紹德(Eaux-Chaudes)。二十世紀初之前,這小村被視為是自治共和國。這個歐洲境內未公開宣布建國的最小國家,過去有十二間花崗岩屋和約七十名人口,統治者是由老人組成的委員會。那時境內沒有乞丐,沒有僕人,而且叫發現這一簡樸刻苦之香格里拉的旅人大為欣羨的是,不用納稅。古斯特這個小村之國,至少自十五世紀就...
»看全部
目錄
歷史人文碎片組成的法國地理萬花筒 韓良露
追尋現代法國的形塑過程 蔡倩玟
旅程
第一部
第一章 未發現的大陸
第二章 法國的部落 I
第三章 法國的部落 II
第四章 O Oc Si Bai Ya Win Oui Oyi Awe Jo Ja Oua
第五章 生活在法國 I:博物館裡的面孔
第六章 生活在法國 II:簡單的生活
第七章 仙子、聖母、神、神父
第八章 民工與通勤者
插曲:六千萬野生住民
第二部
第九章 地圖
第十章 帝國
第十一章 遊歷法國 I:巴黎的大街
第十二章 遊歷法國 II:野兔與陸龜
第十三章 開拓殖民地
第十四章 法國的奇觀
第十五章...
追尋現代法國的形塑過程 蔡倩玟
旅程
第一部
第一章 未發現的大陸
第二章 法國的部落 I
第三章 法國的部落 II
第四章 O Oc Si Bai Ya Win Oui Oyi Awe Jo Ja Oua
第五章 生活在法國 I:博物館裡的面孔
第六章 生活在法國 II:簡單的生活
第七章 仙子、聖母、神、神父
第八章 民工與通勤者
插曲:六千萬野生住民
第二部
第九章 地圖
第十章 帝國
第十一章 遊歷法國 I:巴黎的大街
第十二章 遊歷法國 II:野兔與陸龜
第十三章 開拓殖民地
第十四章 法國的奇觀
第十五章...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葛蘭姆.羅布 譯者: 黃中憲
- 出版社: 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1-12-22 ISBN/ISSN:978986872956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72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文化研究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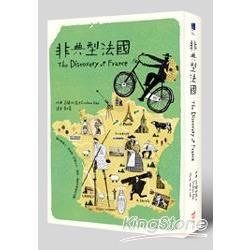
 2016/12/19
2016/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