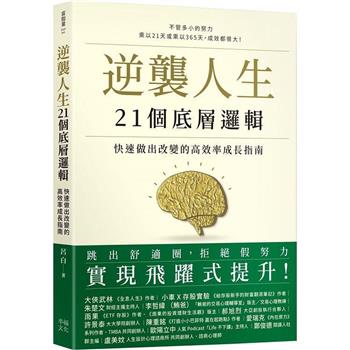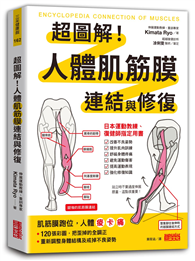我第一次拜會李維史陀是在二○○五年,地點是社會人類學實驗室(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sociale),那是一個位於巴黎第五區的研究機構,由他在一九六○年一手創立。第五區常常透著累積了幾世紀的學養氣息,除了有些街道是以笛卡兒、巴斯卡(Pascal)、居維葉(Cuvier)和蒲豐(Buffon)等名字命名以外,一些專門培養最優秀心靈的菁英機構也座落在這裡,包括了亨利四世中學、高等師範學院和法蘭西學院等。在這個「拉丁區」的東面,是那座落成於一九八○年、象徵著法國包容性的豐碑: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Institut du Monde Arabe)。它那些穿孔和帶花紋的金屬窗格讓它看起來未老先衰,就像是前朝遺物。再往前走是十七世紀的植物園(Jardin des Plantes),其幾何形狀布局裡散布一些墨西哥式溫室、裝飾藝術式(Art Deco)風格的冬季花園和一家老式動物園。
李維史陀的辦公室位於一個夾層,要爬上一道緊窄的螺旋形樓梯才到得了,屬於一家改裝過的十九世紀圓形劇場的屋頂的一部分。辦公室一邊是玻璃板,可以看到懸掛在中梁上的鐵製燈具。研究人員和圖書館理員在燈具下方忙碌著,或是敲打手提電腦的鍵盤,或是翻閱書目卡片。遠處的牆壁裝飾著花朵圖案、奇怪的盾形徽和中世紀的勃艮第盔甲。李維史陀的辦公室幾乎毫無異國風情可言(看不見面具和羽毛之類),有的只是書本和大致裝訂過的博士論文。李維史陀的樣子看起來和過去幾十年無大差別,只是皺縮了一些和衰弱了一些。他身上的粗花呢西裝現在對他變得略為大件,鬆垮垮掛在他身上。他彬彬有禮而充滿警覺性,只有他伸手從前胸口袋掏出地址本時才會洩漏出他年事已高的事實:這手會明顯顫抖。雖然已經九十好幾,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他還是會到辦公室去,只是不再寫多少東西。我們的談話以他的巴西歲月為主題,而他說的話奇怪地結合著兩種異質成分:一方面,他提到的事都是我在其他地方就讀過(幾乎和他嘴巴說出來的一字不差),另一方面,他又流露出一種我沒預期的情緒:尖刻但反諷的虛無主義。
我們從《憂鬱的熱帶》談起。那是他的巴西回憶錄,曾在一九五○年代讓他聲名大噪。它始終是他唯一一本非學術性著作,裡面的文學風格只會在他更正式的作品裡隱約出現。我問他為什麼突然會放棄這種文類,此後從未重拾?他給了我一個坦白但讓人洩氣的回答:「我簽了合約,非寫不可,而我需要那筆錢。」(這種回答在他很罕見。在別處,他都是用長篇大論而錯綜複雜的方式,說明自己寫《憂鬱的熱帶》的各種動機和文學抱負。)我們又談到了巴西原住民的現況。「他們的前景何在?」我問。「等你到了我把年紀,就不會再去想未來的問題。」他以冷面笑匠的幽默回答。但接著,他又較為詳細地指出,巴西原住民的人口雖然不斷增加,又擁有自己的保留區並獲得愈來愈大的自決權,但就文化上來說,他們的傳統業已因為西方巨輪的輾壓而衰亡。
我好奇他對巴西利亞(Brasília)會是什麼觀感(這座現代主義風格的首都在李維史陀於巴西從事田野工作之日還不存在,但他一九八○年代陪密特朗總統到巴西進行國是訪問時曾短暫一訪)。我猜想,這座城市會不會跟李維史陀的美學感性產生共鳴,因為他的結構主義研究方法富有形式主義特徵,而且又對圖案和設計深感興趣。沒想到他卻這樣回答:「我沒有足夠時間參觀,而且行程都是預先安排好的。但把我的作品和現代主義相提並論卻是大錯特錯。」他的這個回答後來反覆浮上我的心頭,因為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跟現代主義運動看似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李維史陀看來不想談他的理論。當我問他他認為自己的作品會留下什麼遺澤,問他認不認為自己的理論會存續下去時,他的回答相當坦白:「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準備離開時,他的心情變得輕鬆起來,談到了大皇宮(Grand Palais)正在舉行的「巴西印第安人文物展」,又敦促我務必要看一看。
第二個星期,我走在那些讓人目眩的羽毛頭冠陣列之間。有些頭冠是由豔麗的紅、藍兩色羽毛構成,頭冠的柳條框上裝飾著像是用混凝紙塑成的魚、鳥和美洲豹頭。展品中還包括一些在馬拉若島(Marajó,亞馬遜河出海口的一個大島)找到的四英尺高瓷製骨灰甕。李維史陀的收藏品是展覽會的壓軸。透過玻璃,我看到南比夸拉人的鼻羽、卡都衛歐人以幾何圖案裝飾的甕,還有波洛洛人用於儀式的飾物(我在《憂鬱的熱帶》讀到過這種飾物)。牆壁上懸掛著一排構圖漂亮的黑白照片,是李維史陀的萊卡相機所拍攝。投影機將他拍自田野的一些短片投射在牆上,反覆播放。影片介於早期的新聞畫面跟家庭影片,無聲、過度曝光、有點晃動,穿插著葡萄牙文的解說字幕。在令人難忘的一幕中,一個穿著襤褸花裙子的卡都衛歐老婦人把一些幾何形圖案畫在自己臉上(李維史陀終其一生都對這種圖案入迷不已)。牆上照片中那個蓄絡腮鬍的年輕人和我剛見過的那個老人幾乎毫無相似之處。時間所拉開的鴻溝看來是不可架接的,而李維史陀在這段期間所寫出的高如山積的作品只讓這鴻溝更形擴大。照片中那個幽幽人影感覺像是另一個生命,是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紀。
我們第二次的會面地點是他位於第十六區的住家,而這一次他看來放鬆許多。在兩次會面期間,我們定期通信,而李維史陀有問必答。他住的是一棟寬敞的高級布爾喬亞公寓:堅實、舒適而且極端講究品味。牆上交雜裝飾著傳統藝術品和原住民文物,包括一個來自卑詩省的木碗、一張古代的小地毯和一幅鑲金框的浪漫畫風少女像。我們在他的書房裡交談,那是一個太空艙似的房間,有著堅實的鑲木地板和隔音門。書房中的寫字檯很沉重,粗厚壯桌腳布滿精緻的雕刻,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一張黑色的模組式沙發。他接過我的外套,掛在門廳上:可以想見,一個高齡老人做這種事只能是出之以慢動作。
他以經過深思熟慮的句子憶述往事,不時會因為需要呼吸而停頓一下。我問了他在巴西的經歷,問了他是怎樣逃離被納粹占領的法國,問了他在一九四○年代流寓紐約時的生活,問了他跟布魯東(André Breton)和恩斯特(Max Ernst)等同是流亡人士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的交往情況。我進而詢問他返回巴黎之後的情形和他在一九五○年代的事業推展(當時他一度打算完全放棄人類學,改行當記者)。他起初很健談,滔滔不絕,但當我把問題轉入理論議題和結構主義的興起時,他開始出現疲態,回答內容愈來愈短。
我們最後談到的是一個當代話題:環繞布朗利碼頭博物館(Museé du Quai Branly)揭幕所引起的爭論。這座博物館體現著席哈克總統的雄心壯志,位於人類博物館(Museé de l’Homme)的正對面,外牆鋪滿植披(有人譏笑它的造型像一副巨大腸臟或是踩在高蹺上的中殿)。這個計畫引起了民族學純粹主義者對專業策展者的撻伐,引起了學院派和美學人之間的爭論。當成立博物館的計畫第一次付諸討論時,人類博物館裡響起了一片嘩然之聲。 據說,一些博物館主管把館內珍藏藏在自家起居室,不肯交給為布朗利碼頭博物館策展的美術系畢業生擺布。
這博物館的大展覽廳就像個半明半暗的巖穴,展品包括一些李維史陀從巴西蒐集回來的文物(地下室就叫「李維史陀演講廳」)。當我提到,有人批評該博物館的展出方式有讓展品異國情調化之虞時,他再次恢復生氣。「人類學是最民族自我中心的一門學科,」他說,「如果你指控布朗利碼頭博物館把展品抽離於脈絡,那羅浮宮裡那一大批宗教藝術品又要怎麼說?」所以說,我們可以用一種純美學眼光看待原住民藝術囉?「你想那樣做自然可以。」他回答說。這番思索似乎讓他筋疲力竭,訪談不得不到此為止。我幫他拍了兩張照面:他以空茫的眼神回瞪鏡頭,神情和他近期拍過的數十張照片一模一樣。
我發現李維史陀的態度坦率,甚至積極協助我填補細節,盡力為我回憶生平往事(這種事他毫無疑問已經做過無數次)。我隱約看到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看到他防衛森嚴的前沿陣地露出了一些小缺口。但他說的話仍然有點空泛,有點隱藏。他的內在沉默與他的舊大陸魅力不相伯仲。到頭來,他的面具仍然沒有挪開幾分。後來,我在信中斗膽問他一些私事(有關他第二段婚姻和他父親生病過世的情況),他禮貌而堅定地拒絕回答。
李維史陀來自一個大學受到少數菁英壟斷的時代,當時人文學的各分支還未完全建立專業性。人類學尚處於襁褓階段,只有為數幾十個學界人士在幅員仍然廣大的歐洲帝國的邊陲從事田野工作。世界地圖已經畫了出來,但就文化上來說,這地圖上的許多地區都幾乎一片空白。民族學家前往世界各地不是要尋找河流的源頭、未知的航道或峽谷,而是為了蒐羅宇宙觀、儀式與藝術。他們想要探索人類經驗的極限,想要擺脫十九世紀偏見的陰影,把人類文化的豐富多樣記錄下來。
作為一個自學的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細讀過英美和法國的人類學經典,包括泰勒(Edward Tylor)、羅維(Robert Lowie)、弗雷澤(James Frazer)、葛蘭言(Marcel Granet)和牟斯(Marcel Mauss)的作品,主要是無師自通。他是同輩人類學家中少數未上過牟斯著名田野課程的人,卻無懼於自組民族學考察隊,而且刻意挑選盡可能偏遠的地點從事研究。他的博士論文並沒有指導教授,是在流寓美國期間寫成於紐約公共圖書館(但回到巴黎後,為了進入論文審查過程,他當然得找人掛名指導教授),後於一九四九年出版,取名《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因為起初被法蘭西學院拒諸門外,李維史陀在一九五○年代常常懷疑自己是否該繼續人類學家的事業。不過,他孕育出的是一些真正具有創發性的觀念,不受當時的群體思維所囿限。
從超現實主義、語言學、美學和音樂汲取靈感,李維史陀在人文學裡闢出一條新的蹊徑。縱貫一生,他都致力於對親屬關係、原始宗教思想和神話做出推翻成說的重新詮釋。他是最寬闊意義下的人類學家,出入於最細碎的民族誌材料與文化共相(cultural universals)之間,出入於個別部落與心靈的普同法則之間。他的作品全集始於高度專技的民族學分析,卻結束於思索小說的誕生、西方音樂的演化和視覺藝術不可逆的衰亡。
由於流亡其間與俄國語言學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邂逅,李維史陀注意到二十世紀思想最根本的一個轉換:從「意義」(meaning)盪向「形式」(form),從「自我」(self)盪向「系統」(system)。他聲稱自己的使命是「瞭解存有(being)與它自身的關係,而不是瞭解存有與我們自己的關係。」——這項原則界定了結構主義方案,也在社會科學中牽引出一個姍姍來遲的現代主義轉向(modernist turn)。透過雅各布森,他發現了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重要見解,並開始把它們應用在自己的研究。自此,語言變成了文化分析的主隱喻:就像索緒爾把語言視為一個由「音素」(phonemes)構成的系統那樣,李維史陀亦把文化看成是一個由對比元素構成的系統。
因為堅定主張文化的組織原則最終是由人腦的運作方式決定,李維史陀也在社會科學裡啟動了一場認知革命。他的夢想是把一直以來不相為謀的知識領域統合在一起:讓社會科學與「硬科學」殊途同歸,讓文化與自然殊途同歸。一反當時流行的哲學氣候,他把研究焦點放在心靈而不是個人,放在抽象思維而不是主體經驗,徹底擺脫當時稱霸思想界的兩種內省哲學(存在主義與現象學)。
李維史陀是唯一譽滿全球的人類學家——美國女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雖然也是大名鼎鼎,但名氣主要侷限在英美世界內。從一九六○年代開始,他成為法國媒體的常客,常常接受《世界報》、《費加洛報》、《新觀察者》和《快報》的採訪。美國的《時尚》雜誌登過一篇介紹他的文章,攝影者和執筆人是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他上過美國的電視,也接受過《花花公子》專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週刊》和《時代》雜誌都報導過他,推許他對「野性思維」的結構分析是社會科學的一場革命,是一個哥白尼時刻,讓人類文化終於臣服科學方法的檢視。在英國,他接受過BBC的專訪,反覆出現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版面,名字也經常被一些大報提及。他在二○○九年十一月的死訊登上了全世界報紙的頭版。
雖然許多媒體寵兒都是名不符實的名人,但李維史陀的名氣卻具有堅實基礎。就像佛洛伊德曾用精神分析革命在垂死的精神病學領域弄皺一池春水,兩代之後,李維史陀也在人類學發揮了同樣的地震效果。就像佛洛伊德一樣,李維史陀的影響力波及到鄰近學科,成為了一種思考新風格的參考座標。就是透過他在《野性的思維》(La Pensée sauvage)最後一章對沙特的尖銳攻擊,傅柯、巴特和拉康才得以更快攻占戰後一直由卡繆、沙特和波娃所盤據的思想高地。哪怕下一代人不欣賞李維史陀的大理論風格,但由他發端的那些哲學爭論至今不衰。若是不理解李維史陀在二十世紀中葉造成的決定性轉向,我們亦無由瞭解當今最頂尖的一些思想家:如斯洛文尼亞的齊澤克(Slavoj Žižek)、法國的巴底烏(Alain Badiou)和義大利的阿岡本(Giorgio Agamben)。
做為二十世紀思想的樞紐角色,李維史陀的目光既前瞻又戀舊。他早期與前衛圈子過從甚密,樂於搭乘現代主義的新潮流。 二次大戰後的科技發展讓他耳目一新,從而相信這些發展說不定可以為人類學所用。早期的電腦科技、模控學(cybernetics)、原子物理學和數學看來都可以為低科技但異常複雜的原住民社會與文化提供新的觀照。儘管他一再否認,但現代主義的各種技法(跳躍、錯置和拼貼)都是他這時期作品的主要特色。
但他同樣著迷於一些更早期的意象:鏡廳(hall of mirrors)、萬花筒、紙牌遊戲、埃及象形文字、時鐘和蒸汽機等。這些意象反覆出現在他的作品裡,被用作比喻。到了中年,他又受到十九世紀文化的巨大吸引,深深愛戀華格納的音樂、維爾內(Joseph Vernet)的浪漫海港畫,以及巴爾札克和狄更斯的小說。他討厭不具象藝術(non-figurative art),又表示自己早年會對超現實主義感興趣,不是被它的怪誕和著迷於性與死的題材所吸引,而是喜歡它優雅和時髦的一面(可以回溯到象徵主義的一面)。退休之後,他宣稱自己對二十世紀的音樂泰半失去興趣,也從不看電影,只讀至少出版了五十年的小說。
本書是李維史陀漫長心靈生活的思想傳記,也是評價他的一個嘗試。它會追隨他從巴黎去到聖保羅,再進到巴西的內陸。它追蹤了他的動盪戰時歲月,敘述他如何逃離維琪政府治下的法國,流寓紐約,過程中又是如何尋覓出那團讓他的思想既趣味盎然又獨標一格的「殘渣」。本書不是李維史陀學術生涯的全紀錄,不會一一記載他在戰後發表過哪些講演、出版過哪些著作、參加過哪些會議和獲得過哪些獎項。本書也不企圖挖掘李維史陀的私生活。做為一個傳統的法國人,李維史陀對自己三段婚姻始終守口如瓶。他頭兩段婚姻相對短命,娶的分別是蒂娜.德雷福斯(Dina Dreyfus)和羅絲瑪麗.于爾莫(Rose-Marie Ullmo),最後一段婚姻則貫徹始終,娶的是莫妮克.羅曼(Monique Roman)。他有兩個兒子,洛朗(Laurent)是羅絲瑪麗所生,馬蒂厄(Matthieu)是莫妮克所生。李維史陀真正引人入勝之處不在於生平細節,而是這個苦行僧型的人物(他的個性與沙特一類魅力四射型知識分子大異其趣)是如何在二十世紀的一個特殊時刻攻占了理論與觀念的高地。雖然他的作品常常專門和艱深,但他就是有辦法同時在學院內外引起深深共鳴。
在本書的前半部分,我會較為詳細地考察李維史陀的思想形成階段,而這也是他人生較為周折多事的時期。我會從他在巴西從事田野工作的日子談到他流寓美國時期的生活,再談到《憂鬱的熱帶》的出版,以此追溯他思想的萌芽生長過程。從一九六○年代開始,他的人生開始穩定下來,而他也一頭鑽進了神話、面具和原始藝術的世界,樂此不疲。「我沒有社交生活。我沒有朋友。我的時間一半在實驗室渡過,另一半在辦公室渡過。」他在一九七○年代初期這樣告訴一個《世界報》的記者。這話固然是一種誇大修辭,卻大體道出他晚年愈來愈離群索居的傾向。
本書的後半篇幅會把生平細節丟開,集中探討李維史陀的思想觀念。透過重新評價他的主要文章與書本,我設法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之間闢出另一條路:他一方面被一些批評者說得一文不值,另一方面又在法國和(說來奇怪)巴西繼續受到普遍推崇。讚嘆一個不凡心靈的驚人生產力不代表要對他的方案照單全收——畢竟這個方案有時不太實際,而且隨著李維史陀年紀愈大而愈往一個高度個人色彩的方向漂移。他在一九六○年代取得的成功,反映出那是一個較為寬鬆(大概也是更有創發性)的時代,其時一些大膽和實驗性格的觀念可以製造風騷,而一個心靈的意識流猶能在文化裡烙下深深印記。他的極端高壽意味著他的人生可以做為我們理解二十世紀思想演變的一條重要線索。不管結構分析的未來會是如何,李維史陀的思想都是我們時代思想地貌的一個重要海岬。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2 |
二手中文書 |
$ 356 |
人文歷史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思想家 |
$ 405 |
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
二十世紀下半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引領結構主義思潮的學術大師
1938年,李維史陀最後一次深入巴西內陸進行田野考察,十七年後出版的《憂鬱的熱帶》,激起了學院內外讀者的熱情,也開啟了結構主義橫掃全球知識界的時代。
李維史陀的理論一掃先前以沙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開闢了二十世紀下半截然不同的思想氛圍。從精神分析到流行時尚,結構主義的原則被運用到各種領域。如果沒有李維史陀,傅柯、羅蘭.巴特、拉岡、阿圖塞等人的理論思想將難以想像。
李維史陀將一種藝術的感性注入學術研究,如同詩人一般運用意象與意念。他在亞馬遜流域深處進行考察的同時,一邊撰寫有關奧古斯都的悲劇;他的四卷本鉅著《神話學》,是用一連串樂章的形式所組成。
本書是李維史陀漫長心靈生活的思想傳記,也是評價他的一個嘗試。會追隨他從巴黎去到聖保羅,再深入巴西的內陸。追蹤了他的動盪戰時歲月,敘述他如何逃離維琪政府治下的法國,流寓紐約,過程中又是如何尋覓出獨樹一格的理論架構。
本書作者威肯不但具有人類學背景,同時也是研究巴西歷史的專家。除了深入研究李維史陀的著作與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檔案資料外,作者亦兩度親訪李維史陀,並規律通信,是李維史陀逝世後最新的完整傳記。
作者簡介:
派翠克.威肯(Patrick Wilcken)
成長於雪梨,就讀倫敦大學戈德斯密學院及拉丁美洲研究學院。他是國際特赦組織的巴西研究人員,經常替《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及《衛報》撰稿。著有《帝國漂移:里約熱內盧的葡萄牙宮廷1808-21》,曾在巴黎與里約熱內盧長住,目前與妻兒定居倫敦。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台灣大學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譯有《老年之書》、《毛二世》等。
章節試閱
我第一次拜會李維史陀是在二○○五年,地點是社會人類學實驗室(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sociale),那是一個位於巴黎第五區的研究機構,由他在一九六○年一手創立。第五區常常透著累積了幾世紀的學養氣息,除了有些街道是以笛卡兒、巴斯卡(Pascal)、居維葉(Cuvier)和蒲豐(Buffon)等名字命名以外,一些專門培養最優秀心靈的菁英機構也座落在這裡,包括了亨利四世中學、高等師範學院和法蘭西學院等。在這個「拉丁區」的東面,是那座落成於一九八○年、象徵著法國包容性的豐碑: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Institut du Monde Arabe)。...
»看全部
目錄
緒言
第一章 早期歲月
第二章 奇風異俗
第三章 龍東電報線
第四章 流寓
第五章 基本結構
第六章 在巫師的沙發上
第七章 回憶錄
第八章 現代主義
第九章 肆恣的心靈
第十章 神話的星雲
第十一章 輻湊
結語
注釋
第一章 早期歲月
第二章 奇風異俗
第三章 龍東電報線
第四章 流寓
第五章 基本結構
第六章 在巫師的沙發上
第七章 回憶錄
第八章 現代主義
第九章 肆恣的心靈
第十章 神話的星雲
第十一章 輻湊
結語
注釋
商品資料
- 作者: 派翠克.威肯 譯者: 梁永安
- 出版社: 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1-12-29 ISBN/ISSN:978986872957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00頁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思想家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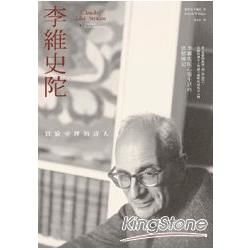
 2012/02/01
2012/02/01